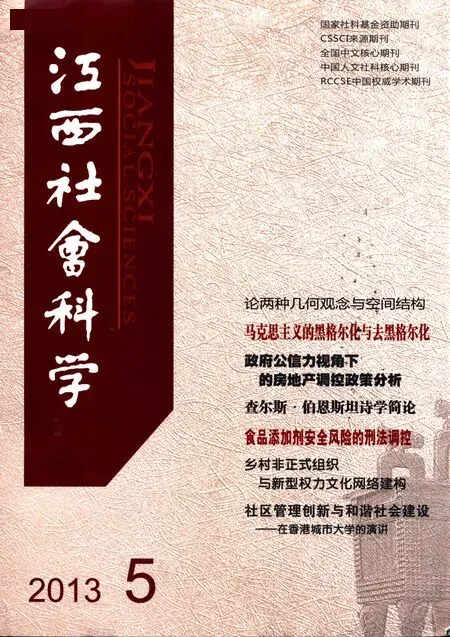从赵孟頫到董其昌:古典绘画规范的量变与质变
■曹院生
谢赫“六法”在中国美术史中的意义不只是为中国画提出了审美标准,更是确立了以形象为中心,笔墨服务于形象,意境出于形象的古典绘画规范。但是从元代到晚明,从赵孟頫到董其昌,古典绘画规范逐渐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衍变。
一
古典绘画规范的确立不仅促进了中国画的发展,也促进了许多杰出人才的涌现,赵孟頫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古典绘画规范的捍卫者又是革新者,他的三类作品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首先,在人物画、界画、青绿山水、工整花鸟中,他仍以形象为核心,笔墨服务于形象。如其《秋郊饮马图》、《红衣罗汉》、《幼舆秋壑图》卷、《浴马图》等明显取唐人之遗意,可以窥见其“作画贵古人意”的复古思想,工整而又非“用笔纤细,敷色浓艳”,都以仿晋唐人风格为主。这皆说明赵孟頫的绘画作品还遵循着古典绘画以形象为中心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在一画跋中评曹霸、韩干画马时说:“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韩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之上。”[1]曹、韩皆是以形象塑造为中心的写实画家,赵却说他们“不求形似”且“出众之上”,此为何意?为的是“使全画达到一种‘古拙’的感觉,这种特色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来的,因为即使山形、树木、茅舍、船只和人物牲畜等,虽都写得不全合乎比例,也不具那种媚人的艳丽,却有着独特与纯真的地方,使我们在一般景物的外形之外,还可以深入领略到古人的意境”[2](P122-123)。这与那些因造型能力不足而提出“不求形似”欲盖弥彰的文人迥然有别。他是想实现“师法古人”而“以己法出之”,以摆脱为古典绘画规范所束缚的宋末绘画困境而求得创新,重新激发古典绘画规范的活力。
其次,在复杂山水画中,形象与笔墨并为核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苍秀简逸,学董源而又有所创新。董其昌跋此图云:“吴兴此图,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故曰师法舍短,亦如书家,以肖似古人不能变体为书奴也。”[3]“元代画家特别指出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源自王维《辋川图》,而且可以与之媲美。”[2](P1453)可见赵氏“复古”的决心。
虽然赵孟頫在上图中运用书法笔法塑造形象,但其所绘济南郊外的华不注山和鹊山的大致轮廓、位置与今之实景还基本相符。所画风光虽距今几个世纪,人事、地理、风俗的变迁也很大,然仔细浏览两山之间的村舍、沼泽、池塘,还宛如赵画所见风味。[4](P445)显然,如果赵孟頫不能以形象为核心描画这些故事,那也无法解其好友周密思乡之情,并从中获得一种慰藉。这就是建立在认识功能基础之上的审美功能。可见赵孟頫既遵循了古典绘画规范又充分发挥了笔墨的审美趣味,使之具有独立于中国画形象之外的独立审美价值。在此幅作品中,绘画中的笔墨和透过它所表达出来的情怀也成为欣赏者玩味的对象。此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以及明代中期沈周、文征明等的绘画皆属此类。他们作品中的形象与笔墨各自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可以相提并论,都是绘画的核心。
还有一类是简率山水和枯木竹石画,在此笔墨成为绘画的中心。如果说第二类绘画中有书法的笔墨趣味,那只能说是“以书入画”的开始,而在第三类作品中却是刻意地去表现笔墨所具有的独立审美价值,完全是以书法为核心进行绘画创作,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也与赵孟頫开创了在半生熟宣纸上用淡墨干皴或飞白的笔法画山的技法有关。这种笔法疏松而秀润、潇洒而含蓄,概括力很强,非常适宜表现山野自然苍茫幽眇之境。如其《秀石疏林图》就把文人最擅长的书法艺术融入中国画的笔墨线条之中,增强了中国画的写意性,生动地演绎了赵孟頫的绘画观念:“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5]显然,赵孟頫试图建立另一个中国画造型标准,而这个造型标准就是书法。除赵孟頫以外,同时代的柯九思画墨竹也如法炮制。据载:“柯九思善画竹石,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6](P1061)
与前朝画家不同的是,赵孟頫与其同时代的柯九思、黄公望、王蒙、倪瓒等,这些人大多为书法家兼画家。他们利用书法线条便于情感抒发的优势对古典绘画规范进行改良,使其绘画自然蒙上一层主观的意味与色彩,从而达到主客观均衡状态。在他们的画中,形象与笔墨的关系虽然处理得和谐,但是还没有否定以形象为核心的古典绘画规范,只是笔墨在绘画中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地位。相对于整个中国画领域而言,第三类绘画作品还是小范围的绘画试验。他们绘画中所呈现的古典绘画的发展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量变而已,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二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本是书法与绘画在特殊题材方面的笔法相通,是特殊性中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元代画家追求“逸格”虽然较多地引进了“非画之本法”,但这种引进始终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极限,便会导致“画之本法”的破坏,创作沦于“狂肆”、“粗鄙”,自然也就失去了“逸”的真正含义;超过这个极限,抽象意味所产生的程式就会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书法最终还会破坏中国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中间实含有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要借书法以伸张绘画的意味在里面。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7](P89)
虽然如此,但是到了16、17世纪,董其昌却将书、画在特殊绘画题材上技法相通的特殊性扩展到整个中国画而成为普遍性。他强调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8](P1013)在此“屈铁”、“画沙”都是书法术语,是指书法运笔过程中笔锋所带来的线条美感。董其昌认为中国画必须用书法之法,这样就可以“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然绘画“纵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要想成为“透网鳞”就必须“超越”古典绘画规范,让书法全面地介入中国画,变绘画性绘画为书法性绘画。
又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8](P1028)意思是说,如果从形象美来说,画不如生活中的自然山水美;如果从笔墨美来说,生活中的自然山水绝不如绘画美。很明显,董其昌是在用以笔墨为核心的规范否定中国画以形象为核心的规范。于是,书法成为中国画的基础,评价一幅画,要考察中国画中的线条是否具有书法的用笔规范和审美趣味。诚如德国学者雷德侯所言:“绘画的情形尽管未必与书法完全一致,却也是非常相似。正如他们所作的书论,文人在其论画的文章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主张,而且将曾为书法而首次阐明的审美标准用之于绘画。”[9](P263-264)
本来中国画的笔墨是用来配合并服务于形象塑造的,书法的笔墨是用来配合结字章法的,而今中国画以书法性笔墨为中心,形象为了配合笔墨而变得程式化、符号化、文字化。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质变。
再看极力反传统的石涛,他和董其昌一样。虽然他口头上批评董其昌,其实他是反向继承董其昌,他在反向继承过程中正是以研究董其昌一系为起点的。
石涛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10](P583)此前,“六法”被认为是“画之本法”,然石涛却认为“六法”确立并完善的古典绘画规范束缚了绘画创作个性之发展,所以他提出“无法而法”,要颠覆古典绘画规范。相对于董其昌正统派而言,石涛代表的野逸派文人画家洋溢着反叛传统的热情,要求个性解放和心灵自由。古典绘画传统让他们感到压抑,他们重视笔墨,追求用“我”之笔墨抒发“我”之情感,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冷静的客观性。
最为赤裸裸的文人画规范宣言,莫过于石涛所谓的“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盖以运夫墨,非墨运也;操夫笔,非笔操也;脱夫胎,非胎脱也。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10](P583)。他由“笔墨”直指“精神”,强调中国画以笔墨为核心,认为中国画的存在是以笔墨的存在而体现的。
三
从元代的赵孟頫到晚明董其昌,中国绘画经历了一个质量互变的过程,更是一个绘画发展创新的过程。绘画创新的结构一般要经过常态绘画—非常态绘画—创新后复归常态三个过程。众所周知,常态绘画是一个高度累积性的事业,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在“六法”规范的引领下,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人物画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的目标在于稳定地扩张绘画知识的精度及高度,这与绘画共同体成员的工作要求也非常吻合。但是常态绘画并不试图去发现新奇的事实和发明新的理论,而且成功的常态绘画研究并不会发现新东西。即使是吴道子也只是在“六法”的摄制下进行了用笔技法的改进,使得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有表现力。山水画的发展也经过了荆关董巨、李成、范宽、郭熙、刘李马夏的努力而达到巅峰。所以,从整个绘画史来看,绘画似乎是一个绘画技术的累积过程,进而“技进乎道”,作品更加“气韵生动”而已。
然而,中国画史给我们的又是另一种印象,绘画研究经常不断地发掘出新奇的、始料未及的现象,而且画家也不停地提出各种新奇的理论。有时在常态规范指导下的绘画研究会导致一个极为有效的规范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之为非常态绘画。而且,其必然是新事实、新理论导致的结果,从而造成一个绘画规范的质变。
一般来说,在质变之前总有一个量变的过程。
画家在面对一种现象时经常是武断地认为没有规范不能解决的谜,即使是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规范,只是以为是时间和技术等问题有待解决。如赵孟頫提出了“以书入画”理论,但他并没有将南宋末宫廷画家的衰落看做是危机,而是在“六法”、“六要”的规范之内,利用“以书入画”的方法使古典绘画推陈出新。即使在规范将要变迁之时,也还是小心谨慎地只在绘画领域的小范围,简率山水画中以笔墨作为绘画的中心。
画家并不把异常现象当做规范之反例。虽然在绘画哲学的词汇中,异常现象的确是规范的反例。“一旦某一科学理论成为研究典范之后,除非另有一理论能取代它的地位,科学家决不会放弃这个理论。”[11](P144)放弃一个规范而接受另一个规范的过程并不是仅仅依靠规范与事实的吻合验证,导致这个过程转变的另一因素是规范与规范之间的比较。比较哪一个更与事实吻合,更能有效地解决更多的谜。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怀疑画家遇到异常现象及反例就会抛弃已有的规范这一论点之真实性,因为这里面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痛苦过程。所以,即使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差距达到无法解决的地步也不会引起深刻的反应,很多画家总是愿意“走着瞧”,尤其是当常态绘画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如赵孟頫面对宋末院画僵化这个难以解决且公认的异常现象时,就不以为这会导致危机。没有人会因为规范的预测与事实越来越不相符,或者说,规范无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开始怀疑古典绘画中的“六法”和“六要”的正确性,于是赵孟頫“以书入画”很意外地解决了当时绘画僵化的问题。画家们包括赵孟頫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会导致规范的危机,所以也没有感觉到惶惶不安,而是以一种“笔戏”的状态将书法规范介入到简率山水画中。也许他已察觉到这可能是个反例,而有人认为可以暂且将它们搁置一旁以待观望。
元代画家不再像晋唐宋画家那样以“注精以一之”、“神与俱成之”、“恪勤以周之”的态度去刻画物象的形似,而是以一种放松、娴雅的态度去作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中国画以形象为核心的古典绘画规范。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等以及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皆重视客观形象的塑造。即使是“逸笔草草”的倪云林,其一点一划也无不神完气足。足见,无论是赵孟頫还是黄公望、王蒙抑或倪瓒等元代画家,他们的绘画形象皆是提炼过的“真”形象。
毋庸置疑,元代绘画形象的情感抒写由于书法的介入而有所减弱,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画家们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关注线条的韵律和节奏,以至于降低甚至淡忘形象的塑造。这就是枯木竹石、简率山水等小景画成为后来画坛一个主要题材的原因,也是文人厕身于中国画的一个最佳的契机。
至明中期,中国画更多地融入了书法因子,如沈周晚期的作品和文征明的作品,在吸收书法因子之后,再现性与表现性之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其作品除了书法因素外,还保留着对自然物的写实性。
不管绘画共同体如何武断地认为规范是如何的万能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使规范与实际相吻合的解谜活动始终会遭遇到问题,虽然大部分问题可能被解决。自“六法”确立古典绘画规范以来,山水画在此规范内的解谜活动一直有效地进行,并取得了纪念碑性的成就。自元代赵孟頫以降,至明中期,古典绘画规范仍然以形象为中心,但笔墨也获得了与形象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所以,即使是反例出现,只要规范内解谜活动能够持续进行,这仍然是一个规范量变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元代绘画的高度是因为主客观达到了均衡状态,而这要归功于赵孟頫,是其“以书入画”所带来的事实。当然,也有少部分异常现象的问题难以解决,它很有可能将常态绘画引入非常态绘画之中。
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得绘画共同体觉得某一绘画异常现象值得让大家去共同研究?且看董其昌提出文人画规范的三个背景因素:一是院画的毫无生机,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早在宋画中就已解决了,而且还不如宋画解决得好,其存在价值定然会遭到质疑。二是赵孟頫“以书入画”的实践为绘画以笔墨为中心的文人画规范夯实了基础。三是禅宗与心学的兴起,为绘画理论提供了哲学指导。这三个因素合并在一起便使得晚明绘画异常现象不再只是常态绘画中的一个谜,此时常态绘画开始进入危机与异常阶段。代表主流绘画的明院画中的异常现象已广为人知,这一异常现象也被越来越多的画家所注意,除了院画家,还包括吴门画派和松江画派。这些画家皆是绘画社群中的核心人物,而且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但是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虽然他们都把化解这个问题当做绘画的要务。显然,此时绘画发展的状态已大不如前了,部分原因来之于绘画的新焦点和新视阈。
虽然大家都在研究绘画问题,都在尽力遵循原有的古典绘画规范,但是当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时,越来越多的实践活动就难免会对原有的规范做或大或小的修改,而且大家会各出新意,各擅其美,百家争鸣。于是此时的绘画规范就会越来越模糊,原有的规范也已经名存实亡,原有的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也慢慢遭到怀疑,而当有人把这种怀疑提出来时那更是让人不得不接受。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明显察觉到了古典绘画规范的大厦将倾。
危机阶段中的研究与前规范时期的研究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危机研究阶段中的画家的差异集中在界线层次较小规范内。这种发展状态下的危机有三种情形:第一,有时候危机状态仍能处理导致危机的问题;第二,有时即使使用了最新的见解还是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有人就会说“走着瞧”、“等着吧”;第三,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危机因新的候选规范出现而结束。
很明显,前两点可以概括为一个量变过程,那么我们就谈谈最后一点:危机因新的候选规范出现而结束。
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规范变迁到一个新规范(常态研究中的新传统由这个新规范产生),这项创新改变该研究中的理论通则,也改变了许多规范中的方法以及应用。虽然其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解谜方式却明显不同。当变迁完成后,绘画的视阈、方法和目标皆已改变,甚至内容反转为形式,形式反转为内容。以形象为中心的古典规范反转为以笔墨为中心的文人画规范就是一例。在这两个规范中,形象、笔墨与意境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古典规范是以形象为中心,笔墨服务于形象,意境出于形象,而今文人画规范是以笔墨为中心,形象服务于笔墨,意境出于笔墨。这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一个质变。
正如孔库恩所言:“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序幕……新理论的出现意味着要打破旧的科学研究传统,引进新的研究传统,这个规范依照一套不同的规则,在不同的思想架构中思辨。因此一定要在大家均感觉到旧传统已步入歧途、山穷水尽之后,这个过程才可能发生。”[11](P153)也许在危机阶段,要想创立新规范还得寻求哲学支持以解决目前危机。但是一般画家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规范的统摄下,画家都认为无须借助于哲学的指导,不需要明白地制定出绘画研究的规则及研究所依赖的假定。而晚明的董其昌却利用哲学在绘画研究的进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董其昌利用禅宗理论将绘画分为南北两宗,并利用文人话语权的作用,倡导文人画规范。于是,画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很小的笔墨研究领域,而且他们在绘画实验中对异常现象的发现也越来越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致危机促成了中国画的创新发展。
董其昌在其许多“仿”、“拟”之作中不断地实验,后来发现试验中作品本质的东西似乎发生了改变,所谓的“仿”、“拟”无非是借传统题材进行创作而已,而且是服务于其理论创作,对于这个异常现象其实董其昌心里有底,他也预测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更何况之前的赵孟頫早已作了笔墨实验,而且提出了“以书入画”的法则。成功的预测使得董其昌的理论假设得到认可,而成就了文人画规范。
有时候非常态绘画在处理异常现象时所思考的架构已预示了日后新规范的形式。从赵孟頫的“以书入画”到董其昌的文人画规范,不就是早已预构的一个新思路吗?从董其昌的文人画规范的确立到石涛的深化就是对传统束缚的挣脱,然后进行笔墨审美价值的大解放。从赵孟頫、“元四家”、吴门画派,再到松江派,其中彼此相关,在这若隐若现的危机现象中,没有人能事先预知文人画规范的结构。新规范或者它的雏形的出现往往是突然地出现的,就像灵感一样,来不及把握就稍纵即逝。而董其昌就是能把握住的一个人。
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中,赵孟頫作为古典绘画规范的捍卫者,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复古”作品,同时他又是一位革新者,他将书法引入绘画丰富了绘画的笔墨。他的大部分绘画作品中仍然以形象为中心,形象与笔墨达到圆融的妙境。虽然他的笔墨也逐渐成为绘画中的关注重点,但是并不像董其昌绘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笔墨,它没有取代形象的中心地位。古典绘画规范在赵孟頫时代只是发生了量变,这种量级变化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而至晚明董其昌时代则发生了颠覆性的质变,确立了以笔墨为中心的文人画规范。
[1](元)汤垕.画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李铸晋.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明)董其昌.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Z].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
[4]王伯敏.王伯敏美术文选(上册)[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
[5](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题跋诗[Z].北京:故宫博物院.
[6](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八)[A].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五)[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A].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 (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9](德)雷德侯.万物[M].张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A].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一)[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11](美)孔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王道还,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