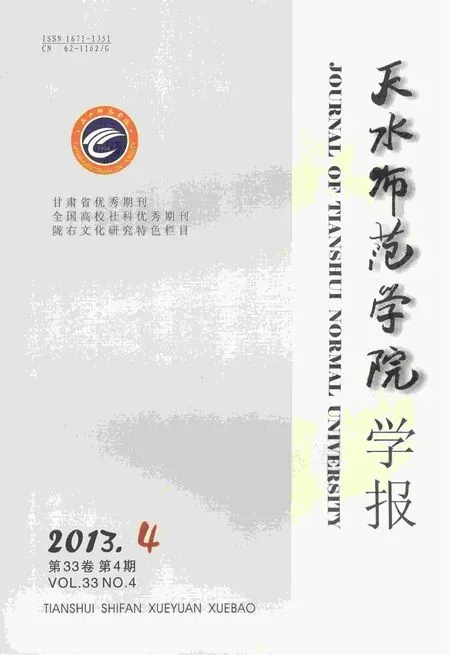爱伦·坡哥特小说新的生命体征
李天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一、爱伦·坡哥特小说在传统中的创新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小说家欧摩尔波斯的《佩特罗乌斯》、悲剧作家塞内加的一系列作品以及阿普列尤斯的小说《变形记》就已经零星出现恐怖叙事的片断,但是由于其叙事的朴素、不自觉的创作意识,并不能作为哥特小说真正的渊源所在。作为自觉的文学形式,哥特小说发端于英国18世纪中期的墓园诗歌,得益于埃德蒙·伯克(1729~1797)的“哥特式”美学标准以及当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克拉丽莎》的问世,除了由鬼魂、墓地、死亡和恐怖构成的哥特情景,还形成哥特小说“女郎——恶棍”的经典模式。但是,标志哥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真正确立当属1764年英国作家贺瑞斯·瓦尔普的小说《奥特龙多堡》的出现,从此哥特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英国逐渐定型。这部小说,在其内容主题上,具有典型性特征,如“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和一个残忍的迫害者;迫害者通常与邪恶有关并具有超强的和超自然的能力,受害者常被一种来自迫害者的无法解释的力量所蛊惑。故事背景通常设在无法穿透的高墙内(现实世界和心理世界的)以加强受害者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故事的主要意象通常是阴森的教堂或闹鬼的大宅,里面囚禁着孤独的受害者;氛围中弥漫着神秘、黑暗、压抑、恐怖和毁灭,并预示着灵魂的死亡以及人类将成为永久的受害者的厄运。”[1]10其结局也具有哥特小说的典型性特征,即正义与光明战胜了黑暗与邪恶的道德说教。因此,瓦尔普被视为哥特小说的鼻祖。
其后的作家开始了继承和突破传统的尝试。1790年,萨德将短篇小说《美德的厄运》扩展后写成小说《于丝汀或美德的不幸》,并与小说《于丽埃特》合并改写为《美德的不幸与恶行的走运》。在序言中,萨德表明他要破除人们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幻想。小说中的妹妹于丝汀身上集中了一切传统道德却沦为命运的玩偶、施暴的目标,最终沦为“美德的不幸”。当命运借助姐姐之手杀死了妹妹则凸显着恶行战胜了美德的主题。这种与传统哥特小说完全不同的倒行逆施的结尾,不但抨击了宗教的欺骗性,而且通过强奸、同性恋、乱伦、性变态、性虐待、小说初版中带有的100幅色情内容的插图和血淋淋的暴力场面确立其反道德的价值取向。
至18世纪90年代,哥特式小说在英国逐渐演化成两个分支。其一是以安·拉德克利夫(1764~1823)的《尤道弗的奥秘》为代表的感伤型哥特式小说,其特点是保留中世纪古堡场景,抛弃过分的神秘成分和极度的恐怖气氛,使故事的发展变得合乎逻辑,侧重心理恐怖的刻画。在安·拉德克利夫看来恐怖可分为“心理恐怖”和“本体恐怖”两个类型。前者以“恐惧”(terror)为目的,作品中很少或几乎不出现超现实主义的幽灵,而只是通过充满悬念的“未知物”存在,暗示可能发生的凶险,从而“扩充灵魂,使各种功能警醒到生活的高程度”;而后者以“恐怖”(horror)为目的,通过赤裸裸的超现实主义的暴力、凶杀等描述,刺激人的感官,使灵魂“凝聚、冻结,甚至湮灭”。而她的《尤道弗的奥秘》则是典型的“心理恐怖”小说。其二是恐怖型哥特式小说,特点是坚持传统的手段,并在此基础上融入病态的邪恶,以增加神秘、恐怖的效果。如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1795)就是典型的“本体恐怖”之作;沿袭着这两支血脉,美国的哥特小说创作行列中也出现了以萨莉·伍德(1759~1855)的《朱莉亚》和伊萨克·米契尔和《庇护所》闻名于世的感伤型哥特式小说,以美国小说家之父查尔斯·布朗(1771~1810)的《威兰》为代表的恐怖型哥特式小说,由于试图表达人物在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意识所造成的困惑,被称为“政治潜意识”的哥特小说,在后来的作家威廉·福克纳、霍桑马克·吐温、爱伦·坡都可见其影响。
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以逐利为目的的大量粗滥作品给哥特小说造成了很坏的声誉,随着销量减少,以至于使安·拉德克利夫封笔,甚至阅读哥特小说成为人们的笑柄。在美国学者戴维·里克特伊迪丝·伯克黑德、罗伯特·梅奥、德文德拉·瓦玛等人看来,哥特小说已经衰亡,英国学者弗朗兹·波特得出结论:1800年至1835年这段时期意味着哥特式小说的衰落。但是,爱伦·坡的《怪诞故事集》(1840)的诞生,为早已成为一滩死水的哥特小说注入一股清泉,标志着一个新的哥特小说时代的到来。爱伦·坡“容不得任何中间的、寻常的、平凡的、一般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被夸大到惊世骇俗的地步”,[2]220而且,他将这种效果渗透到小说的各个层面。比如,从阅读接受的角度,他将读者纳入到恐怖的场景中,模糊了主人公和读者的界限,让其产生身临其境、无法自拔、与主人公共时的精神焦虑,那是一种“在引领着我们见证过最为极端的恐怖场景后,坡通过迅速把一切事物回归正常颠覆了我们的反应。然而,在经历过这一幕幕后,我们对身处何方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从人物的处境来看,坡通过小说展现一种绝望之境,因为近距离的阅读让读者无处可逃,恰如18世纪美学家埃德蒙伯克所说:“当危险逼得太近时,它们带不来任何欣悦除了恐惧。”[3]221从表现方式来看,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漂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并将他引向恶的事物”,[4]188从而模糊了现实和文本的关系,所有的主体都处于梦魇的似真似幻的情境中;从写作目的来看,追求混杂和多元的效果,即遵循“把滑稽变为怪诞、把害怕变为恐惧、把奇特变为神秘的原则。”[5]7故而,封闭的房间、地窖、船只和漩涡、书房以及古宅就成了人物活动的场所,这些地方不但失去了与外界的沟通显得突兀怪诞,而且由于规定性的限制充满了神秘恐怖和横空出世的效果。没有历史、没有了现实联系,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混杂性扑面而来。总而言之,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源自爱伦·坡哥特小说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新的生命特征,其一,具有魔幻色彩的“死与美结合”的诗意追求;其二,由传统单纯的“心理恐怖”的表现转向具有本体意义的“内心恐怖”的探索,进而以预言的姿态自觉反思人类荒诞的生存处境。
二、死与美结合的诗意追求
死亡是爱伦·坡创作最常见的主题,以小说《莫雷拉》、《丽姬娅》、《贝蕾妮丝》、《长方形箱子》、《厄舍府的崩塌》、《梅岑格·施泰因》、《红死魔的面具》、《死荫——寓言一则》、《静——寓言一则》为代表。上官秋实认为:“要理解爱伦·坡在他的作品中执着地描写恐怖、怪诞的情节,表现美的幻灭,对死亡、忧郁的恐惧,就应该看到,他对表现恐惧、死亡的热爱与他的身世分不开。”[6]虽然爱伦·坡对母亲的记忆甚少,印象并不深刻,可她垂死的景象却烙在了爱伦·坡的心中,作品《丽姬娅》中的丽姬娅无不体现着其母亲的影子;同样,斯坦纳德夫人是爱伦·坡少年时期的爱慕对象(他同学的母亲),其于31岁病故,这使年少的爱伦·坡受到巨大的打击,“以致于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思念起斯坦纳德夫人都神思恍惚,并常常做恶梦,甚至在夜里到斯坦纳德夫人坟头悼亡幽魂。”这种强烈的“失美之痛”使他在15岁时写出《致海伦》一诗。而给爱伦·坡最沉痛的打击是他的妻子弗吉尼娅的早逝,这位曾给爱伦·坡带来难忘的尘世愉快生活和写作灵感的美丽柔弱的女子却于24岁英年早逝。此外,母亲和哥哥也都是24岁死去,父亲酗酒后失踪,仅存于世的妹妹罗丽莎自幼神志不清,可以说,死神的阴影从未离开过这位苦命的作家。
在作品《红死魔的面具》、《死荫——寓言一则》、《静——寓言一则》中,人无时无刻不在与死神进行面对面的对抗。在效果的制造上,爱伦·坡认为,应该预设一种情感和氛围,然后不惜一切达到预设的情感,即在死亡气息下喘息的恐惧。《死荫》则利用声色光的渲染,从“瘟疫的黑色翅膀”、“乌木圆桌”、“苍白的面容”、“令人想起鲜血的红酒”,到影子出现我“大而响亮”的声音,逐渐微弱,逐渐无迹可寻,回音遥遥飘进房间,一张一弛,一动一静的强烈效果反差,营造了恐怖神秘的氛围,而“影子的声音不是任何一个人发出来的,而是众多人的声音,说话时音节上的节奏又各不相同,它是那些成百上千个业已死去了的朋友们的口音,那么熟悉,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朦朦胧胧地落在我们的耳鼓上”,[7]674到此戛然而止,将恐怖推到极致。但是,死亡造成的“本体恐惧”不再是构成传统哥特小说的原始动力,甚至传统哥特小说中的恐惧已成为迂腐不堪、被嘲讽的证物,正如美国批评家本·因迪克所说,恐惧成为了最普通的东西,不再仅是超自然恶棍的邪恶制造;没有人可以被相信,十几岁的学生、警察、无聊的旅馆看守,甚至一个小婴儿都不可信。
然而,恐惧在爱伦·坡的作品中却变成了展现魔幻效果的有力手段,“小说场景氛围铺垫和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细节方面的生活化以及具有魔术奇幻性的叙事情节,而这其中又不失叙事的现实感,他在精细的哥特环境氛围的描摹上和对叙事情节中偶然性的把握上无不流溢出怪诞恐怖因子这一独特的哥特小说审美吸引力”。[8]26这种似真似假的描写将本质现象化,将现象本质化,体现生命多元化的体征,已然摆脱了大多数哥特小说的套路,“活死人”的意象就是利用魔幻的手法超越死亡的不可逆转性,并死而复生的想象,让读者在恐惧中有所期待。
比如《莫雷拉》、《丽姬娅》、《贝蕾妮丝》、《厄舍府的崩塌》就是一系列死而复生模式的作品。女主人公智慧而美丽,她们无一不在践行着“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这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因上帝不过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及万物。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7]307的信念,所以,死去的女主人公都凭靠惊人的意志力复活。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魔幻世界中散发出一种倒行逆施的癫狂与悲剧之美。“悲剧是一种强壮剂”[9]382不仅对于坡,这些故事是他在世间踽踽独行的拐杖,对于读者,也在这种悲剧中“被迫正视个体生存的恐怖……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正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9]71从美学角度讲,“任何可以使人感觉痛苦和危险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可以使人感觉可怕,或与可怕产生联想,或以近似可怕形式出现的东西,都可为崇高美之源;换言之,任何可以产生人们所能感受的最强烈感情的东西都是崇高美之源。”而这一切在爱伦·坡看来,却是诗意追求的曲折诉求:“我问自己——依照人类的共识,在所有悲郁的主题中,什么最为悲郁?答案显而易见——死亡。于是我又问:‘那么这个悲郁的主题在什么时候才最富有诗意?’当死亡与美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10]166所以,死亡在爱伦·坡的创作中获得了美学形而上的意义,对于人物而言死亡不再是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无限循环的生命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既是结尾又是开始,既是毁灭又是重生,在《催眠的启示》中,他把想象的催眠实验看作是一种设想的根据,认为死仅仅是一种形态变化,而包括内心恐惧的这一切都是为过渡到“美好、无限、不朽的”的未来做准备。
三、以本体的“内心恐惧”反思人荒诞的生存处境
爱伦·坡认为自己更善于表达人“内心的恐惧”,和安·拉德克利夫以及查尔斯·布朗表达的“心理恐怖”不一样,后者心理的恐怖是有明确的对象和行为,即与主观的心理对应着一个客观的世界。但是,爱伦·坡内心的恐惧是找不到现实理由的主客体交融的产物,“他越过了美学的最险峻的高峰,投入了人类智力最少探索的深渊;为了使想象力吃惊,为了吸引渴望着美的精神,他通过仿佛一阵没有间歇的风暴一样的一生,发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前所未有的手法。”[10]170其目的在于,用看似正常却又失去生存理由的人置换了在神秘环境中神出鬼没可以引发好奇心的主人公,用渴望投入与渴望远离的状态彻底将读者推向荒诞的深渊,去体会人类生存之荒诞,预言下个世纪生存的荒诞之境,为此,爱伦·坡甚至愿意“花一个世纪等待读者”。
《被用光的人》讲述了一名久经沙场的退伍老兵史密斯,一个拥有完美身体和优雅风度的人,竟然是与机械人无异的拼装人,终于“我”明白为什么人们说“这是一个发明的时代”,并由此惊呼:他是一个被用光的人。他内心的恐惧就来自于对自己“既是人又不是人”的境遇的自明。《椭圆形画像》是一个奇特的美之死的故事,画家将美妻作为模特摹下她的绝色,却发现画像完成之日,正是美人死去之时,因为画画所用的颜料竟取自活生生的生命。画家内心的恐惧不是来自妻子肉体的死亡,而是文明带来了高尚的艺术,文明也带来死亡的荒诞境遇让他无所适从;《泄密的心》中的主人公为了把自己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采用了极端的方式,结果却陷入“做是错的,不做也可能是错的”荒诞之境。
在这类创作中作者已然摆脱了传统哥特小说的原始元素诸如城堡、神秘压抑的氛围、神经质的苍白主人公,也放弃了能引起感官刺激和阅读欲望的低俗表现,而是用形而上的方式将“内心恐惧”的存在变成了生存处境的本体。即活着就是恐惧。人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无法走出的荒诞迷宫,既安于现状又无法自拔。当不幸发生时,他们痛苦不堪;当不幸不发生时,他们更加痛苦,人既要受到理性意识的折磨,又要遭受非理性潜意识的折磨,因为“任何潜入无意识的人都进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的窒息空气之中,在这死胡同里,精神的地下世界会放出他那黑暗洞穴中的一切熊禽猛兽,他将在这条死胡同里遭受所有凶兽的袭击”。[11]238精神的困境成为心理恐惧的根源。比如《人群中的人》从传统的哥特城堡中走出来,回到热气腾腾的人间,但面对人群,却倍感焦虑孤独,也就是说只要人存在,城堡就是人无法选择和逃避的荒诞处境。作品《过早埋葬》中最大的敌人不是鬼怪而是自己:最终过早埋葬自己的,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或者焦虑,这种内心的惶然,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威胁,但又不可或缺。同样,《乖戾之魔》中的“我”受到乖戾的心魔的控制犯下罪行,终无法忍受内心折磨而发疯;《威廉·威尔逊》描写两位同名同姓同年出生外貌十分相似的威廉·威尔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后堕落的威廉·威尔逊杀死了道德的威廉·威尔逊,但是随着一个威廉·威尔逊的死亡,另一个威廉·威尔逊也随之死去,人就这样恐惧地活着,恐惧地死去。
人生存总是向往着美好的事物,又因为担忧未知的不幸所以产生恐惧。但是,对于爱伦·坡而言,生存的美与恐惧是并存的,因为单纯的愉快是美的最庸俗的饰物,而忧郁才可以说是他的最光辉的伴侣,爱伦·坡内心恐怖的诉诸并不代表、试图摧毁一切厌世悲观的倾向,恰恰相反,通过内心恐怖的本体取向才能引发人心灵重创,然后在绝望中反思、在死亡中的复活、充满生活的冲动:“他的作品尽管在数量上充斥着绝望、失落、冷漠、痛苦、悲凉和恐怖,但是,这恰恰暗示了他内心深处饱含着超越人生的渴望与追求,对甜美、温暖和爱情的向往”[12],这似乎构成了爱伦·坡探索人与世界的独特途径,即不论是“死与美”的结合诗意追求还是通过内心的恐惧探索人的生存处境都体现坡在悖论的张力中认知的倾向,看似一切都不符合逻辑推理,但是却又真实撼人,因为生存并不总是按照逻辑推理进行的,所以真实必然是不符合逻辑,这样往往在惊奇之中让本来平淡的美突然之间变得不平淡,正如波德莱尔所言:“爱伦·坡赢得有思想的人的欣赏并不是那些使他有名的表面的奇迹,而是他对美的爱,对美的和谐条件的认识。”[13]166爱伦·坡在《诗歌原理》也认为:“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诗来再现他和世人一样感知到的那些景象、声音、气味、色彩和情趣,不管他的感情有多么炽热,不管他的描写有多生动,我都得说他还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远方还有一种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尚未解除的焦渴,而他却没能为我们指出解渴的那泓清泉。那种焦渴属于人类的不朽。它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结果和标志。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14]683不论怎样,爱伦·坡一边用文学隐喻着信仰衰微之际的现实,另一方面又用最绝望的方式表达着希望即将来临的颤栗,通过赋予哥特小说新的生命体征,否定了传统哥特小说道德规劝的教条,将道德消泯在不能确定的真假摇摆之中,甚至通过“反道德”的行为表达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精神危机,从而也赋予鬼魂、恶棍和吸血鬼多样性的性格特征,使之更具有文学审美的吸引力;其次,颠覆了传统哥特小说宗教的权威,爱伦·坡通过主人公无法用原则判定的行为解构了善恶、魔鬼与上帝对立的深度模式,展现一个漠视上帝、善恶错位的世界,让终极意义在此失去了价值;此外,爱伦·坡以更高的姿态和立场上让人变得“不是”人,大胆表达人性恶的一面,用此来反思人类的理性灾难,反思人类优越心理带来的隐患,以及科技和文明带来的异化问题。显然,爱伦·坡的这类小说属于哥特小说之列却已经完全挣脱了“哥特小说”这一形式的局限,将文学的触角伸进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文学领域,无不体现着一位作家对文学犀利的预见性。
[1]王晓珠.哥特之魂——哥特传统在美国小说中的嬗变[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EDMUND ABAURK.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in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Western Critical Theory[M].Beijing:Foreing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1999.
[4]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朱利安.西蒙斯.文坛怪杰——爱伦坡[M].文刚,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6]上官秋实.人类心灵隐秘的探究者[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2).
[7]奎恩.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下[M].曹明伦,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
[8]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9]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
[10]EEGAR ALLAN POE.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J].Graham’s Magazine,1984.
[11]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文集: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12]曹曼.爱伦·坡死亡主题的内涵解读[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13]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4]爱伦·坡.爱伦·坡精品集[M].曹明伦,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