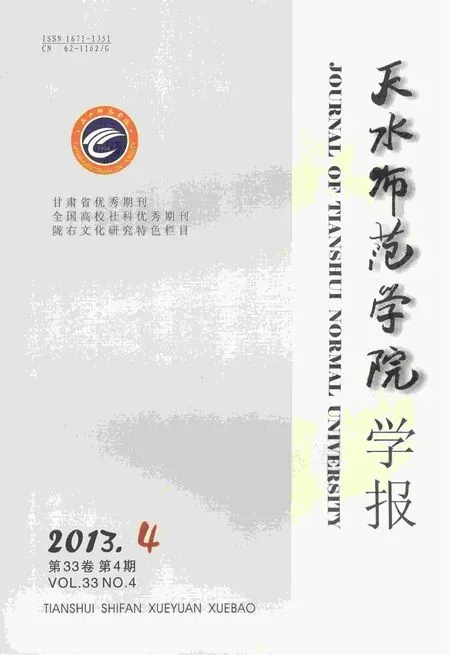论谭嗣同的文学主张
马争朝,曾贤兆
(1.兰州文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谭嗣同尽管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但是他的思想和观念已经开始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且认识到文学创作除了直抒胸臆、抒发怀抱之外,应该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责任。面对日益加剧的列强侵略和日渐加深的民族苦难,他开始将自己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视为“旧学”加以摒弃,也开始在他卓越的社会活动之余创作有益于民族国家的“新学”,探索新的形式,并提出了新的主张。
一、骈散结合的散文理论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
谭嗣同早年学习桐城古文,之后转向先秦汉魏六朝之文,对于当时桐城派古文束缚甚多而且唯我独尊的文坛形势,他主张骈散结合:
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下此若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至于汪容甫,世所称骈文家,然高者直逼魏晋,又乌得仅目曰骈文哉?自欧、曾、归、方以来,凡为八家者,始得谓之古文,虽汉、魏亦鄙为骈俪,狭为范以束迫天下之人才,千夫秉笔,若出一手,使无方者有方,而无体者有体,其归卒与时文律赋之雕镌声律,墨守章句,局促辕下而不敢放辔驰骋者无异。于是鸿文硕学,耻其所为,而不欲受其束、迫,遂甘自绝于古文。而总括三代两汉,咸被以骈文之目,以摈八家之古文于不足道。为八家者,不深观其所以,而徒幸其不与争古文之名,遂亦曰此骈文云尔。呜呼!骈散分途,而文乃益衰,则虽骏发若恽子居,尚未能一处蠲除习气,其它又何道哉![1]
谭嗣同针对时流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和桐城文的一统天下,提出秦汉魏晋文章具有很高的价值,而相比之下,“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他认为欧阳修、曾巩、归有光、方苞以来对骈俪的摒弃,最终使古文走向了衰落。同时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古文尤其是桐城文囿于固定的章法,了无生气,而清初王夫之之文,“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的文章都具有反对陈腐的传统观念和迫切要求革新的愿望,都提出过匡济时艰的主张,除语言和风格的具有独创性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所包蕴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主张的作品,在当时阴霾满布、万马齐喑的社会里,对于每个不满现状的迫切希望变革的人来说,必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正是从这一角度推重他们的作品的。谭嗣同还认为汪中骈文的风格和精神逼近魏晋,不可与世俗的骈文相提并论。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也提出了对骈文的新观点:“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2]他提出了要吸取骈文词藻华美、音调谐和、富于气势、适于表现的特点,而摒弃四六排偶的形式。基于这一主张,他也创作了一些骈散不拘、独具特色的文章。
关于散文的社会功能,谭嗣同认为,桐城古文“义法”、“雅洁”以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诸多约束与清朝建国以后国家逐渐安定出现的承平景象相适应,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与科举取士紧密相连。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民族危机的加深,桐城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举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形势的急剧变化。他对桐城文的批判也与对科举制的批判相联系。在《报贝元征》中指出:“岂惟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1]这实际上表现出的是谭嗣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他站在文学为社会改良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角度,提出“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也就是对文学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三十自纪》中感慨:“子云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谭嗣同强调经世致用,与清初思想家提出的“文须有益于天下”[3]的主张一脉相承,认为在国家民族危难当头之日,应该放弃不切实际、无补于社会大局的文字游戏,进行有益于民族国家的思考。
二、语言革新与言文合一的主张
谭嗣同站在维新派的立场上,要求诗文创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服务,因而推崇新学,将西籍名词入诸诗文创作,从而为中国古典诗文衍生出新的形式,即新学诗和报章体散文。这种西籍名词的输入,冲击了原来的诗体、文体,动摇了中国古典诗歌严整的格律和桐城“义法”以及八股文僵死的格局,对传统诗文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并从而影响了东南数省的文风。这种新的文风,恰恰也是新名词入诗文的结果,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首先把新名词引入中国文学的,在近代是王韬、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4]他们都写过一些融入新名词的诗文。特别是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四首》,里面充满新名词。这都难免给人一种生吞活剥、艰涩费解之感,但确实也令广大读者感到耳目一新。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新名词的运用愈趋于自然,像黄遵宪的《今别离》,蒋智由的《卢骚》,柳亚子的《放歌》、《空言》等,这些诗中虽也杂有新名词,但并无生硬别扭之感,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新气息和时代感。新名词的输入,不仅给近代文学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而且也促使文学形式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散文为例,新名词的入文,对当时笼罩文坛的桐城派散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而促进了文体的革新。[4]
除了在诗文创作上大量引用新名词之外,谭嗣同还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即要求书面语与口语相协调,从而为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创造条件,最终为政治改良运动服务。他在《管音表自序》中提出:
然而语言、声音,无能久存,其流播赓衍,亦不能无讹舛。古今之积变,何殊中外之顿隔?于是乎乃贵有文字,是文字即语言、声音,非有二物矣。
今中国语言、声音,变既数千年,而犹诵写二千年以上之文字,合者由是离,易者由是难,显者由是晦,浅者由是深,不啻生三岁学语言、声音,十岁大备,备而又须学二千年以上之语言、声音,如三岁时一人而两经,孩提一口而自相鞮寄,繁苦疲顿,百为所以不振而易隳,而读书识字者所以戛戛而落落焉。求文字还合乎语言、声音,必改象形字体为谐声,易高文典册为通俗。[5]
谭嗣同希望通过文字改革来开发民智,普及文化,进而改革文体,宣传维新思想。他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希望建立一种表音文字拉近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从而普及经典,传播文化。不仅与龚自珍、魏源以来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华传教士傅兰雅等的影响。傅氏要求文学语言在于“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6]谭嗣同之后,裘廷梁更坚决地打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7]的旗号,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纵观从黄遵宪开始,经过宋恕等人的努力,再到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最终到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系统的言文合一主张,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也没有完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任务,但它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维新运动如报刊发行、书籍出版、学校教育、拼音文字等有着多方面的推动,成为近代文学革命的先声,也为以后“五四”白话文运动扫清了道路,积累了经验。[8]
三、报章文体说
晚清报纸的出现是近代散文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散文写作的方式和传播方式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报纸数量的增多,以及王韬等报人的大量创作,散文的社会功能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看好。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提到报纸的社会作用:“至于新闻报纸,最足增人见识,而籍知外事。林文忠督粤时,广翻西国新闻纸,故能洞悉其情而应其变。今日切要之图无过此者。况乡间无所闻见,尤须籍此为耳目。中国之大病,莫过于不好游历,有并此无之,终身聋盲矣。”[1]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致汪康年》中说:“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能过撰文登报之善矣。而过乡党拘墟之士,辄谓报章体裁,古所无有,时时以文例绳之。嗣同辨不胜辨,因为一《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示人,在湘中诸捷给口辨之士,而竟无以难也。”[9]谭嗣同站在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服务的角度,提倡报章文体,认为可以自由的不受“文例”拘束的表达思想,是维新党人能够采用的有效的斗争武器。于是作《报章总宇宙之文说》,[1]站在天下之文为维新变法运动服务的角度,为“报章体”文章的推行呐喊呼号。他将天下文章分为三类十体,不仅包括了传统的文章体裁,也涵盖了图、表、谱、章程等形式。显而易见,这些都不是文章体裁,充其量只是用文字或部分用文字表现的形式。而谭嗣同充满热情地鼓吹这些,用意在于利用报纸这种新的传媒形式,扩大传统的文章创作的范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报章体”这一新的文章形式的发展,并回应传统守旧文人对报章文体的攻击:
若夫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宏史官之益而昭其义法,都选家之长而匡其阙漏,求之斯今,其惟报章乎?咫见肤受,罔识体要,以谓报章繁芜闒葺,见乖往例,此何异下里之唱,闻鼖镛而惶惑,眢井之蛙,语溟瀚而却走者矣。[1]
他也确信报章文体功能巨大,“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园囿,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图”。[1]这就把报章文体与传统文体、传统文学观念结合起来了。[10]另外,《报章总宇宙之文说》在文体分类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报纸上刊载的文章,已开始挣脱旧文体的羁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具有独创性的风貌,即报章体或称新文体。[11]这种文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近代散文变革中的一种创造,是适应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符合近代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代表作家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他们共同为这种文体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而谭嗣同则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这种文体的发展,也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政论散文《仁学》便是典型的“报章文体”,汪洋恣肆、长于雄辩,行文则时骈时散,纵横古今,力求文意表达通畅,以感情之笔说理,情因理发,理因情显,情理相得益彰,被称为骇俗之文。
谭嗣同的《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及他创作的以《仁学》为代表的报章文字,从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加快了散文社会化的步伐,呈现出为救国救民和维新变法服务的鲜明的特征。
四、余 论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改革者,他的文学主张,与他冲决罗网的主体精神有关,也是激烈变革的时代的反映。他对文学的主张是配合他改造社会、适应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对新学诗的创作和提倡尽管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但在文学史上的探索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对报章文体的提倡,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为中国散文古今演变和现代报章政论散文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言文合一的主张最终在很多人的努力下为白话文运动铺平了道路。[12]他对于文学的很多见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改良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创作实践,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对其文学作品的在接受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使得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文作品广泛传播,为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1]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77,210,221,376,375,377.
[2]谭嗣同.三十自记[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55.
[3]顾炎武.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释: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79.
[4]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02,35.
[5]谭嗣同.《管音表》自叙[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
[6]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晚清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57.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8.
[8]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17.
[9]谭嗣同.致汪康年:三[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493-494.
[10]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
[1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34.
[12]曾贤兆.谭嗣同散文论略[J].船山学刊,201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