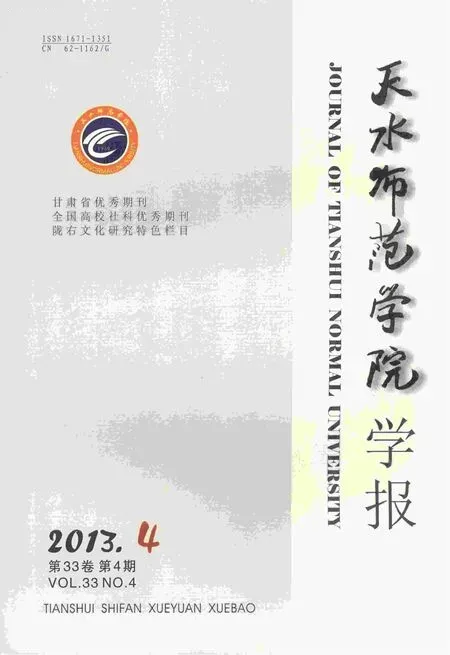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数理知识和数字崇拜解读
张倩红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周易·系辞下》有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结绳以记事。结绳记事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结绳实物,但不可否认的是,结绳记事所包含的数字信息折射出蕴含于先民思维中的数理知识和数字崇拜。这种数理知识和数字崇拜,一直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本文通过研究河姆渡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遗物、遗迹的鲜明特征,分别对两种文化数理知识的认知程度加以分析与探讨,并且试图解释相关的数字崇拜。
一、河姆渡先民对数理知识的认知程度
河姆渡文化大约距今6000到7000年,是分布于浙江杭州湾南岸平原至舟山群岛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镇而得名。
河姆渡人在长期的实践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他们在制作生活用器时,出于美观和实用的考虑,使用了一些数字概念和数理知识。研究者能轻易地从河姆渡人使用的器具中找到“二十”以内的数字的影子:石璜或玦两端各有一个系绳的穿孔,说明“一”、“二”这两个数字概念的存在。数字“三”的发现来自于第三文化层出土的支丁,三支粗大的支脚成品字形排列,便于置放炊器。古井的口部是用四根木条形成框架,以防井口的塌方,说明“四”这个数字概念的存在。数字“五”蕴含于五叶纹植物的陶块。口沿外侧呈六角形的陶釜反映出数字“六”的概念。“十”的数字概念表现在出土的一件陶豆盘向外突出的十个角形上。此外,一件陶釜的口沿外侧成十八个折角表示了数字“十八”。然而,数字概念的出现和存在只是数理运用的基础和前提,河姆渡人对数理知识的认知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河姆渡文化中最重要的遗存系大量的木构建筑遗迹。在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尤以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木建筑遗迹最为密集和壮观,其总数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构件有长圆木、木桩、长方形木板、带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一种以木桩为支架,在支架上方架设大小梁来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它们是河姆渡人为适应自然环境和改善居住条件的一大发明创造。河姆渡遗址第一、二两期的发掘,发现干栏式房屋建筑有三栋以上,其中一栋房屋面宽达百米,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3米的前廊长屋,若以2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1]干栏式房屋被分隔成若干小间,计算间数需用加法;间隔的墙被砌成相互平行,说明河姆渡人已经熟知直线与平行线的概念。面对河姆渡人智慧的结晶,考古学家很难想象建设者不经过精密测量和计算就能建造出如此规模和实用的房屋。河姆渡先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完成了从基础结构式到梁柱结构式建筑形式的转变。[2]
遗址中出土的木构件柱头榫、柱脚榫、转角榫、梁头榫、燕尾榫、企口板的制作难度都很大,没有各种角度的几何概念是难以制作出来的。以梁头榫为例,相配套的长方形卯孔深度只有与榫的长度相一致,才能彼此制约。[3]转角榫卯的出现表明河姆渡人对垂直和直角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由于气候温度的变化对木构件榫卯产生了忽缩忽胀的微变形的影响,面对松动的分力,采取了插入销钉的办法,把分力降到最低点。这是一个将数理知识运用到建筑生活中的典型例子。
水井的考古发现再一次表现了河姆渡先民的聪明才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四角转角处的木桩较粗,这是为了增强四角的抗压力。人站在井边打水,使井壁压力增大,为保护井壁以防止坍塌,就在壁边打木桩,增加壁面的抗压力。为了更好地抵消压力,增加抗压强度,就在每排木桩的内侧各横贴一根圆木或半圆木,其中横木两端制作成榫卯结构,加强牢固性。在水井的保护中运用了分力与合力的关系,反映出河姆渡先民对数理知识的精通程度。
这些文化遗存都充分说明了河姆渡人不仅有数字的概念,而且还熟悉几何概念,掌握了测量技术和计算能力,通晓一定的数理知识。
二、三星堆文化展现的数字崇拜与数理知识
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第一至第四期文化通称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是古蜀人创造的,具有自身独特文化特征的青铜文化,距今约3000多年。
(一)古蜀人的“五”文化
细读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考古材料和古文献资料,不难发现“五”这个数字在古蜀人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它像是一把魔杖,用神秘的宗教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古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面之广、渗透力之深都是惊人的。
1998年,郫县古城遗址的腹心地带发现一所距今约4000年的“大房子”,房屋残留的基址内依次排列着五个由卵石砌成的台;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一组图案,人头上戴着五齿高冠;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也是头戴五齿高冠;同时出土的还有类似车轮的青铜太阳轮形器,它的辐条均为五条;二号坑出土的石牙璋,射部和柄部双面都阴刻两组图纹,每一组都由五幅图案构成,而且各组图案均出现了五个人物形象;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窑藏青铜器和抗日期间川西地区发现的青铜罍,都是以五件为一组,还呈一大四小的形状相互叠压;[4]237此外,文献中有关“五”的记载甚多,比如五丁力士,蜀王妃有五妇女,石有五块石,地有五丁担,墓有五丁冢。[4]238这么多的“五”在考古和文献资料中频繁出现,绝非偶然,当与蜀人“尚五”的观念有关。
蜀人“尚五”,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作为依据,但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记载与出土材料做出合理的推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4]227开明九世为已逝的先祖立庙,在明明已有八代先祖死去的情况下,却只将前五世列入庙中,称“五色帝”。个中理由只能是,剩下的三个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只有当第二个“五”筹齐时,才能将剩下的去世蜀王都列入庙内,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由此体现了“五”在蜀人心中是个吉利的数字,代表了一个周期,一个轮回,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生命轮转。
古蜀人“尚五”的传统,亦可从当时周边国家和后世统治者的一些行为中得以反窥。例如,秦惠王知蜀人“尚五”,便答应把秦国的五个美女嫁给蜀王,给蜀王一种错觉,令其以为秦国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沦为蜀国的从属国,从而成功地蒙蔽了蜀王,为秦国的修养生息及后来的统一赢得了时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将数字“以六为纪”,将全国各地修建的道路宽度统一为六尺,但他深知蜀人对“五”较为敏感,为蜀人开了特例,允许他们可以将道路宽度修建为五尺,蜀人知道后很高兴,把成都平原和周边地区的道路修建得又快又好。后来李冰到四川当蜀守,新官上任必然要先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结果他也发现了蜀人“尚五”的秘密,因此在修建都江堰时,他便“以五石牛以压水精”。
(二)三星堆文化中的数字“七”
三星堆青铜器造型奇特,自成一体,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透过古蜀青铜文化,笔者推测蜀人除了“尚五”以外,对“七”也有独特的爱好。笔者认为有六点理由:
其一,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金杖,全长142厘米,几乎是数字“七”的20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金杖内的木质材料已经腐朽,金杖才比原先略微压长了一点,即金杖原长可能为140厘米。引人注意的是,金杖一端有浮雕图案,从纵向来看,该图案分为上下完全相同的两组,内容依次是:头戴高冠的人头像、令羽、鸟、鱼、令羽、鸟、鱼,共计七个图像单元,[5]彰显的文化内涵是部落首领或帝王有权发布捕猎的命令。这个代表权力的金杖,显然具有对数字“七”崇拜的文化因素。
其二,属于三星堆“六大国宝”之一的凸目青铜大面具,宽138厘米,高64.5厘米,眼睛呈柱状外凸,极具地域特色,双耳雕有纹饰,夸张地向两侧充分展开。宽度为138厘米,约为数字“七”的20倍。
其三,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太阳轮,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象征五大行星的青铜轮形器直径70厘米,是数字“七”的10倍。
其四,在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的大石璧,直径为70.5厘米,也是数字“七”的10倍。
其五,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青铜大立人像连同底座的高度为262厘米,推测其头部原来或许还有某种约20厘米高的装饰物,如羽冠等突显地位的装饰品,因此它的总高原为280厘米,为数字“七”的40倍。
其六,出土于二号器物坑的青铜神树,残高396厘米,有学者估计原高约399厘米,即数字“七”的57倍。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这说明度量衡的出现与人体有关,人类身体某些部分如手、足等可作为测量单位的标准,“分手知尺”就是这个缘故。不难看出,在三星堆文化里,长度基本单位为一拳,即10厘米;一臂的长度为七拳,即70厘米。有鉴于此,笔者推测生活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人们普遍使用着七进制。
(三)从建筑遗迹来看三星堆文化的数理知识水平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城墙及各类建筑遗迹,显示出古蜀人在城市和民居建筑前经历过详细的规划和测量。蜀地的民居建筑,以木构建筑最为常见,它有长方形、方形、圆形三种形式,房顶为榫卯结构,分为穿斗式和抬梁式,体现出灵活而高超的建筑技术。建筑学是对数理认知程度要求较高的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平行、垂直、测量、方向、计算、统计等数学知识,那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就不会上演一段建筑学的传奇了。
月亮湾台地东侧发现有深达4米的夯土堆积。从夯土堆积周边的一条水沟边铲出的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的夯土夯层水平,夯面清晰,每层厚约15厘米,整齐规范,夯筑方法已很成熟。[6]古蜀人建造的大面积的古代城址在商代前期实属罕见,准确无误的测量反映了娴熟的建筑水平,充分展示了蜀人在数理知识上的认知程度。
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考古工作者在十二桥地区发掘出了商代晚期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7]其中包括宫殿庑廊的遗迹,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和小型附属建筑,它们相互连接,形成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体。古蜀人继承、创新前人的数理知识,通过建筑形式演绎了超凡的技艺。
三、结 语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没有像三星堆遗址的器物群那样表现出对某个数字的不断重复,而是单纯地出现了数字概念和相应的数理知识,若想在该文化中找到数字崇拜的文化特征,从目前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水平来看,难度较大。而三星堆文明在新的高度上继续发展,出现了对某个数字的大量重复,因此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数字崇拜的探索与考证,还是值得期待的。三星堆文明传达出某个数字在古蜀文化中居重要地位这一深意,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古蜀人的数字崇拜是“七”。试分析如下。
战国时,蜀王杜宇上任后重视农业,结束了古巴蜀多年来弥漫民间的巫术气氛。大禹治水推动农业的发展,刚进入夏代的中原普遍重农的思想也强化了古蜀“以农为本,教民耕作”的观念。到了商代,古蜀中心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
农业文明的发展与天象的观测密不可分。根据天文学知识,星空中的北斗七星是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星座,它本身拥有着神秘的数字“七”文化。如北方地区:黄帝族以“帝车”称北斗,而其他部落联盟的重要成员有熊氏、轩辕氏,他们的名称均与北斗七星有关,足以说明其地位特殊。《尚书·舜典》有言:“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笔者认为三星堆轮形器宛如五大行星,可称其为璇玑,而在月亮湾出土的大石璧代表月亮,称之为玉衡。先人崇拜数字“七”,可能源于月亮月初、上弦月、满月、下弦月的七日周期,而人的生理周期也与此相关。
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给考古工作者做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带来障碍。又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和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正因为如此,三星堆文化一直是考古学界研究的热点,从这些出土器物中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尚待深入发掘。河姆渡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是惊人的,在考古学界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不仅因为它是任何一个稻作文化聚落遗存所不及的,更主要的是它的文化面貌特征鲜明,带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在至少拥有十项内容堪称“世界之最”的河姆渡文化中,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的耜耕农业、卓越的干栏式房屋建筑成就、发明的漆器、开凿的水井等文化遗存。笔者认为只有用严谨的治学姿态去对待这些来自遥远文明的文化遗存,才能使千年璀璨文明薪火相传。
伴随着考古发掘研究的日益深入,河姆渡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数理知识和数字崇拜现象会被更好地认识和解读,从而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注入新的思考视角。
[1]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5.
[2]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65.
[3]吴汝祚.初探河姆渡文化人们的数理知识[C]∥王慕民.河姆渡文化新论——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164.
[4]肖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5]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27.
[6]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14.
[7]段渝,邹一清.日出三星堆[M].成都:巴蜀书社,200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