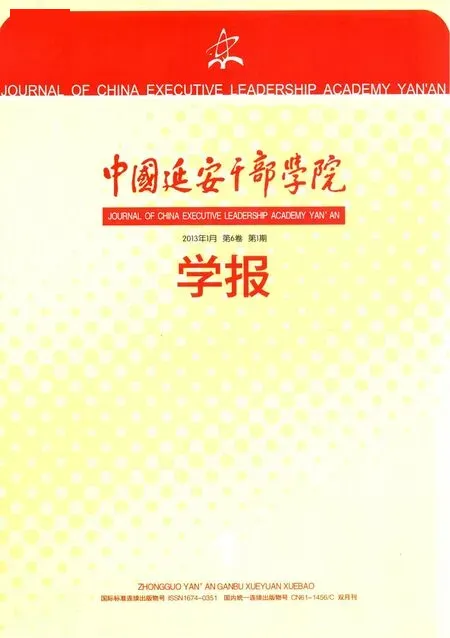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张 戈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延安时期,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新文艺运动,对诸如秧歌、民歌、说书、道情等陕北民间文艺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研究和改造,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动了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其中,“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它既是陕北说书史上的重大变革,又是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成功范例。本文重点考察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对“新书词”内容的分析,深入总结“新说书”所产生的宣传与社会功效以及历史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关注。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35年至1949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延安为中心,在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历程,是为延安文艺运动。边区“改造说书”运动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和发展的。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是极富陕北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传统的陕北说书由盲艺人手执三弦或琵琶,左膝系檀板按节拍,独自坐场说唱,其历史悠久,现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康熙十二年重修的《延绥镇志》卷六《艺文志》:“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1]563据此可知,陕北说书在清初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陕北说书流传久远且独具特色,可以说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誉为“陕北农村的民间叙事诗”[2]。就其书词内容而言,表现主题大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开朗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在近代陕北农民与恶劣自然环境和兵祸灾荒的斗争中形成的;就其表演形式而言,盲书匠“一人管三事”,自弹自唱,多采用方言俚语,形式灵活,语言风趣。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陕北说书虽然秉持了通俗活泼的文化形式,但其自身又“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3]203。首先,与封建迷信的结合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说书艺人一般都身兼算命先生的双重身份,“过去的陕北说书,多以单人串乡说书为主,他们除过说平安书、口愿书外,为了糊口,还要进行一些其他附带的活动。如保锁娃娃、扣娃娃、算卦、揣骨等。”[4]140其次,传统说书的题材内容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传统的陕北说书“绝大多数还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那一套,有意无意地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的思想,或多或少总是含着对群众有害的毒素。”[2]这与延安时期提倡的社会新风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说书具有必然性、急迫性。
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就已认识到改造旧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进而指出:“利用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利用一切新的旧的形式,使一切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我们今天的一部分血和肉”。[5]1940年1月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达成了“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6]815的共识。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普及化、大众化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积累素材。在党的民族化、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掀起了向陕北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并对传统文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创新。改造说书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展开的。
1945年4月,边区文协正式成立了说书组,负责人为林山,安波、陈明、高敏夫、王宗元、程士荣等也先后参加了这一工作。说书组的任务不仅是发展民间曲艺,更重要的是联系、团结、教育和改造说书艺人。这些旧艺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7]115由于乡村说书艺人的分散性,对说书艺人改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具体帮扶,个别改造。其中,韩起祥的转变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改造民间艺人的典范。说书组对韩起祥的改造是分了三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记录旧书目,了解说书人,同时对其进行教育,启发他在原有书目的基础上,去掉糟粕,并添加有关边区生活的新内容。第二步,向说书艺人灌输新思想,提高其思想境界,并由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共同创作新的说书作品。正是在林山等人的引导下,韩起祥明确了自己“文化娱乐我承当”[8]11、“一段一段宣传人”[2]的社会责任感。第三步,在说书组的安排下,由“进步了”的韩起祥现身说教,以期改造更多的说书艺人。在韩起祥的影响下,一些边区艺人开始了“新说书”创作:杨生福、高永章、冯明山等先后创作或改编了《狼牙山上五神兵》、《劳动英雄李兰英》、《血泪仇》等新曲目。
改造说书人的运动无疑是成功的,韩起祥被誉为“多产作家”、中国“荷马”、“红色宣传员”,他一个人的表演“俨然是一小队乐手的合奏”[9]。韩起祥由“过去的穷瞎汉成了先生”[10]118,昭示着陕北说书从旧民间艺术到新文艺的转变。
(二)“改造说书”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林山等知识分子与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努力创作与配合下,“改造说书”运动在边区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
改造说书,编写新书词是重点。为了能使说书为政治宣传、工农兵群众服务,在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的共同努力下,众多优秀的“新说书”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如:韩起祥和说书组的同志们共同创作的《刘巧团圆》、《张家庄祈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宜川大胜利》、《时事传》、《血泪仇》、《红鞋女妖精》、《四岔捎书》、《阎锡山要款》、《王丕勤走南路》等二十余部作品,杨生福、高永章的《狼牙山上五神兵》、《红军打清涧的故事》、《劳动英雄李兰英》,常栓、刘子有和石雄俊等人创作的《捉活鬼》、《刘志丹打延长》、《赶走何绍南》、《打日本》、《自由结婚》、《皖南事变》等作品,冯明山改编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反内战》。这一时期优秀作品涌现,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对说书的改造并没有停留在书词内容的改革上,也创新了书词的形式和曲调。首先,新书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七字或十字的字数,而是采取更加自由的、只是略带韵律的三四字至十字组成的诗歌,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认为这“发展了久具雏形的中国诗歌传统”[11]。其次,韩起祥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甩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生动。
报刊杂志的频频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5年8月5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林山的《改造说书》一文,介绍了解放区改造说书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指出了改造说书的重要性。该报同时刊登了傅克撰写的《记说书人韩起祥》,高度评价了韩起祥改造旧书说新书的事迹。这也是《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第一次用全版的篇幅来介绍陕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两天之后,《张家庄祈雨》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林山在《附记》中写道:“他(韩起祥)有很强的创造力,自己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在农村演唱很受欢迎。”[12]为了彰显韩起祥编说新书的事迹,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的短短一年之内,《解放日报》17次刊登了韩起祥的作品和从艺活动。[13]195这一系列拔高韩起祥的宣传攻势,提高了说书在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1947年8月中旬,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给毛泽东说新书。毛泽东夸奖他新书说得好,群众语言很丰富,将来要推广到全国去。8月25日、26日,朱德在枣园连听了两天韩起祥的说书,鼓励他多编新书,学讲普通国语,将来去更多的地方说书。韩起祥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巩固了陕北说书在新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说书组举办了“说书训练班”,在成功改造韩起祥的经验基础上,更多的旧艺人接受了改造。据统计,“全陕北有盲艺人483人,参加训练班改为说新书的有273 人。”[14]4边区新说书从此蔚然成风,“至1946年,到处都有新说书,陕北说书已成为新文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4]143“改造说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典范。
二、“新说书”的社会功效
说书的主要艺术手段是“说”和“唱”,它运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的生动形象的、说唱化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状物写景、描绘人物、抒发感情,合乎大众的欣赏习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作为有效的宣传手段,说书历来为政治家、教育家所重视。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很重视利用说书来教化民众、讲经劝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开展平民识字运动的时候,也曾组织了五十多位说书艺人向民众宣传识字的重要性。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在不同时期陕北说书所宣扬的内容是不同的,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功效。延安时期的“新说书”是解放区新气象的反映,其宣传功效是积极的、强大的。
(一)开启民智,教化民众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甚至几乎不需要文字的社会。这一特点在落后、闭塞的陕北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的陕北社会,真正对农民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并不是学校教育,而是诸如说书、道情以及民歌等民间口头叙事。可以说,陕北说书于开启民智、教化民众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新说书”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更是居功至伟。
首先,较之传统说书,“新说书”更加贴近时事、通俗易懂。旧书词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历史演义类、公案传奇类以及爱情故事类,如:《杨家将》、《清官断》、《玉簪记》等。听旧书,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加之众多说书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历史人名、地名被混淆、讲错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听者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其所言。而“新说书”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和革命战争,广大群众耳熟能详,更加通俗易懂,更易被接受。
其次,“新说书”中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启蒙了落后、愚昧的陕北民众。(1)“新说书”宣传了自由、民主思想。在新书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民主”、“婚姻自由”、“思想”、“为人民”、“选举”等等。新说书作品《黑白分明》介绍了乡村选举会上的风波,宣传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边区新气象。结尾所讲的“边区事事讲民主,检查政府能批评”[15],反映了这一时期乡村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巨大成绩。(2)“新说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与封建迷信思想的结合是传统陕北说书的主要特点之一。经过改造,说书成了反对迷信的重要工具。李寄的《卜掌村演义》分六回:“骗百姓编造神鬼”、“揭鬼计英雄学医”、“露马脚神官丢脸”、“讲真情阴阳求救”、“破迷信斗争十年”、“讲卫生人财两旺”,[16]254-273批判了“不会治病,就会骗钱”的阴阳巫神,提倡讲科学,讲卫生。(3)“新说书”提倡教育,反对愚昧。近代的陕北一直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是文盲[17]1。《四岔捎书》讲述了在外经商的文盲王氏父子找人代写家信,结果错把“忙”写成了“亡”、把“雇”写成了“故”,令人啼笑皆非。该书的结尾讲道:“没有文化的苦处说不完,新社会的年轻人……学好文化为人民。”[18]95说书对学习文化知识重要性的生动宣传,使扫盲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正是“学习文化脑袋新,不信鬼来不信神”。(4)“新说书”提倡新生活,主张革除陋习。近代陕北,鸦片盛行,土匪、娼妓、巫神等二流子众多。针对这一现象,边区政府发起了“禁烟”、“改造二流子”、“讲卫生”等运动。“新说书”极大地宣传、推进了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吃洋烟二流子转变》、《卜掌村演义》、《老蔓菁偷麦》等新说书作品对吸食鸦片、游手好闲、偏信巫医、不讲卫生等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5)“新说书”促进了女性的解放。旧的传统的陕北婚姻习俗为包办、买卖婚姻,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新说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鞭挞。《刘巧团圆》热情地颂扬了勇于抗争买卖婚姻的刘巧、赵柱等形象,嘲讽、批判了热衷于婚姻买卖的二流子刘彦贵、刘媒婆、王寿昌。《刘巧团圆》以其生动的表现主题和丰富的地方色彩风靡解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民众转变思想观念。新说书作品《大翻身记》中所描写的妇女生活“我母亲苦撑苦熬往前过,每日里眼泪洗脸过光阴”[19]3,也唤起了民众对妇女的同情。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更是直接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们送来了民主的光辉。
(二)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
说书是延安时期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1946年9月7日、8日、9日,《解放日报》全文连载了王宗元、韩起祥合编的《时事传》。随即,林山发表了评论:《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读〈时事传〉后几点意见》,认为只要把宣传时事的新说书作品,如《时事传》、《刘善本飞延安》、《李敷仁走延安》等,教给各地的说书人,就能达到很好的时事宣传效果。另外,他针对如何通过说书人宣传时事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首先,发动文艺界和民间艺人经常地编写所谓的《时事说书》;其次,出版机关迅速编印,并下发各地;最后由各县宣传机关负责把收到的《时事新书》传教给当地说书人。这个宣传时事的新办法颇有成效。据孙犁回忆,当时“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不外:报纸、黑板报、讲报、广播。但想起来,哪一种方式也没有说书这种方式好,因为说书人的创作,和他的技艺,这是活的时事教育。”[20]255
通过说书表演宣传时事,虽难免有主观色彩,但在当时新闻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亦属不错的选择。也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主观色彩,赋予了说书评议新闻事件的功能。说书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一是体现在书词,一是体现在艺人。在书词方面,写到毛泽东时为“一轮红日照乾坤”、“是人民大救星”,而蒋介石“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善恶是非,一语道明。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评判,也体现在艺人的表演中。艺人韩起祥说唱《时事传》时,唱到民主运动胜利,时局好转之时脸上的阴云消逝了,喜上眉梢;当唱到蒋介石破坏和平的时候,他的脸上又乌云密布。民间艺人正是用这种舞台表演的情感流露,使时事宣传更加深入民心。
(三)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
战争年代,人民大众急于了解当下的战争信息,对新闻媒介的依赖更加强烈。为了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需求,在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努力创作下,“新说书”在战争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媒介作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地区,各党政机关、团体被迫迁移。许多群众不明真相,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韩起祥毅然留在延安,并坚持在农村搞宣传工作,到情况紧急之时,甚至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去村子里说书。这一时期,艺人们经常表演的新说书作品有:《三大胜利》,反映的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时事传》,写国民党在三次谈判中的丑态;《西北时事传》反映了解放军在沙家店等战役中的胜利。1948年春,在解放宜川战役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4个整编旅,正所谓“胡匪军,没路逃,个个举手把枪缴。”[22]128韩起祥根据这一事迹,编成《宜川大胜利》。“延安光复后,韩起祥率先第一批进入延安,当天下午就在新市场沟口说《宜川大胜利》……深受群众欢迎。”[4]143-144这个时期坚持在延安农村的“新说书”活动,作为唯一的宣传工具,及时地告知了群众有关新闻和战争信息,起到了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影响下,对旧的说唱艺术的改造在各解放区兴起。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说唱艺人李国春致力于编写新鼓词,为宣传服务。他所在的文工团跟随主力部队,四处编演新鼓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勇气。据《冀中导报》1946年10月26日报道:在扫除新城外围据点的战役行动中,文工团的“李国春同志在拿岗楼的时候说大鼓,一个小段未完,前方又传来胜利消息,于是又赶到前面去说。”[23]1947年 6月 12日,我军在攻打永清城的战斗中歼灭了国军第三保安纵队。李国春根据这一讯息,立即编成《鏖战永清城》的鼓词,在军民中广泛演唱,起到了很好的战争动员作用。
(四)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4]36“改造说书”运动兴起于1945年,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内战阴云密布。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难免人心不稳,各种舆论四起。“新说书”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和传播媒介,发挥了较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首先,新书词体现了民众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控诉,歌颂了边区新气象,引发大众对新生活的向往。正如韩起祥在《翻身记》里所唱的:“我说书把舌头磨成锤尖尖,指头磨成了光片片,每天累的喉咙疼,还是半饥半饱度营生。风天跑,雪地奔,赚的钱都被官府勒索清。每月捐税三元整,欠了捐税了不成……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上三弦唱红军。横山县无法无天难存身,四〇年,我夜走延安找红军。延安、横山隔架山,两下里天地不一般。解放区人民生活好,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不愁吃来不愁穿,学习生产都起劲。”[19]12-13其中对国统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述,唤起了大众的同情,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号召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翻身做主人。
其次,新书词凸显了我军战士的英勇,鼓舞了士气,宣传了军民团结。1948年春,艺人韩起祥赴前线慰军,受到战士和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其说书次数高达19次,听众约八千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期间所说的多为描写战争时事的《宜川大胜利》、《慰问词》等新说书作品。其中多有对战士们的不吝赞誉:“解放军,是英雄,勇敢作战保人民,二月打仗到十月,仗仗得胜仗仗赢。”[22]118也有对良好军民关系的描述:“水担满,院扫净”、“又规矩,又亲近”、“一路走,一路行,到处的百姓都欢迎。”[25]121勾勒出了一幅军民和谐的新画卷,与国统区军队欺压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书词讽刺了敌人的丑态,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心。与对我军战士的赞扬相对,新书词中充斥着对敌军丑态的嘲讽。“延安的敌人着了个慌,一个驴滚倒缩跑出了延安”[26]275,——艺人用诙谐、通俗的语言描绘了国军逃离延安的狼狈情形,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念。又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传》中说蒋介石,“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一个妖魔化的形象跃然纸上,唤起了民众对反动统治的憎恶,增强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新说书”对社会、战争的描述和评价,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这些有利于战争进程的舆论,配合了军事威力,鼓舞了军心民心,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
三、“改造说书”运动的启示
“新说书”从兴起到完成历史使命,经历了一个从旧说书到新文艺的发展历程,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也极大地促进了说书艺术自身的发展。这些都对当前说书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说书艺人的培养
说书艺人的培养和自身艺术创作对于艺术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改造说书”运动中,对艺人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首先,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如韩起祥被誉为“红色宣传员”、“三弦战士”。其次,物质方面的奖励也很可观,如编写新书词所获稿费八成都由说书艺人获得,参与编书的知识分子仅获两成。[25]160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韩起祥曾用稿费购买 316个芝麻饼劳军。[10]146再次,加强对艺人创作的鼓励和引导。“改造说书”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即知识水平、文艺素养较高的专家和民间艺人亲密合作。
(二)关注社会题材,重视大众需要
说书作为一门群众艺术,必须大众化。要做到这一点,说书艺人必须深入群众,感悟生活。在“改造说书”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深入体验群众生活,积极向民间艺人学习。在作品的选材上,通常针对陕北农村特殊的环境和需求,将一些现实和容易理解的事件展现给群众。比如在宣传改造生活陋习时,他们选择的大多是关于破除迷信、讲卫生、禁烟等题材;在宣传战争事件时,则更侧重于解放区武装斗争方面的题材。
(三)发挥说书的批判功能
“改造说书”运动中,艺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说书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批判性功能,赋予新说书作品以强烈的斗争性,对“二流子”、封建迷信、国民党军队的反动统治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达到了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的目的。这也是增强说书艺术自身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1]谭吉璁撰,刘汉腾,纪玉莲,校注.延绥镇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林山.改造说书[N].解放日报,1945-08-05.
[3]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曹柏植.陕北说书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5]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N].新中报,1938-05-25.
[6]徐辶西翔.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理论史料集[G].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7]张炯.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韩起祥,高敏夫.刘巧团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9]付克.记说书人韩起祥[N].解放日报,1945-08-05.
[10]胡孟祥.韩起祥评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11]李福清.中国民间说书与韩起祥的创新[J].国外社会科学,2008(5).
[12]林山.张家庄祈雨附记[N].解放日报,1945-08-07.
[13]裴文学.中外残疾名人传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
[14]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5]戈西.黑白分明[N].边区群众日报,1945-10-07.
[16]李寄.卜掌村演义[G]∥延安文艺丛书·舞蹈曲艺杂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18]韩起祥.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上)[Z].延安:延安市政协文史和学习文员会出版,2008.
[19]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翻身记·唱词集[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63.
[20]孙犁.介绍时事传[M]∥孙犁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1]韩起祥,王宗元.时事传[N].解放日报,1946-09-07.
[22]韩起祥.宜川大胜利[G]∥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说唱文学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3]钟惦棐.重视文艺为兵服务的诱导过程[N].冀中导报,1946-10-26.
[24]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25]迪之.延安文艺丛书·舞蹈曲艺杂技卷[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26]韩起祥,林山.慰问词[G]∥延安文艺丛书·舞蹈曲艺杂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