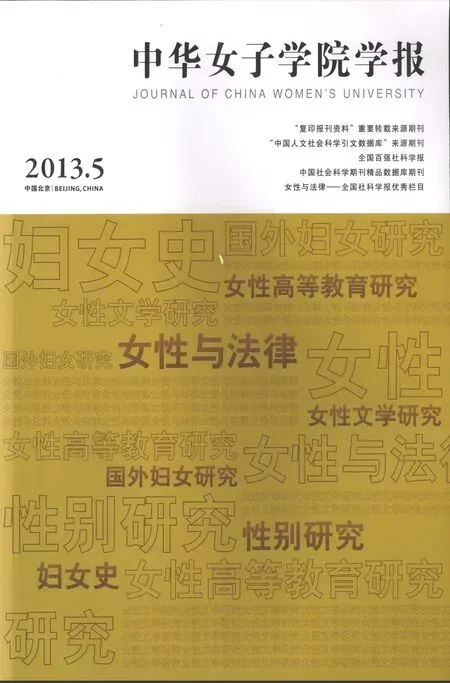对有关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之批判性反思
周小李
对有关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之批判性反思
周小李
有关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种观念:大脑存在性别差异,只有抽象思维(男性思维)适合科学学习,以及母性非智性。这些智力迷思与事实真相并不一致,但由于社会性或历史性力量的作用,其影响至今依旧普遍而深刻。批判性地反思有关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有助于为女性的科学弱势提供客观而公正的归因。
性别差异;科学;智力迷思
美国当代学者查尔斯·默里使用历史计量研究法,界定与测量了公元前800年至1950年人类所取得的科学与艺术成就。根据成就的卓越程度,默里编制了全世界科学与艺术领域的4002位重大人物名单。在这些重大人物中,妇女只有88位,占总数的2.2%;而且这些女性绝大部分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域,仅24位属于科学领域。[1]235自公元前800年至18世纪上半叶,只有一位女性入选科学领域重大人物;不过,自1800年至1950年的150年间,科学一览表里的重大女性人物从1个增加到了19个,这可能是由于20世纪前半叶教育与就业领域对女性的开放,帮助女性增加了投身科学的机会。[1]236那么,随着20世纪中期之后全球范围内妇女地位发生的重大变化,科学领域杰出女性所占比例是否会有更显著的变化呢?默里的统计发现,“根据诺贝尔奖这一卓越成就的最显著标志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在1950年至2000年间,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女性仅占2%,化学、医学及物理学中则分别只占1%、4%及1%;较之1900年至1950年间同类奖项获得者中的女性比例,仅医学由2%上升到4%,科学类保持着2%,而化学由4%下降到1%,物理学由2%下降到1%。[1]240
在卓越科学成就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小这一现象,自其引起人们注意之时,关于其何以形成的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各种观点中,一种历史悠久的声音是“生理决定论”,另一种声音是“社会决定论”。然而,正如默里的统计所揭示的,最近半个世纪女性在科学领域的状况较之以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观,这种态势愈发令人们趋于相信,男女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主要是智力的差别,很有可能是导致女性科学劣势的根本性原因。“人们倾向于相信来自‘硬’科学的证据,如生理学和生物学,而不是‘软’科学,如心理学或社会学”,“生物性的效应被相信比社会性的效应更加不可逆转”。[2]268
这种关于智力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其实质是对男性智力优越性的肯定以及对女性智力的贬损,其意图则旨在为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弱势提供貌似确凿的“理论依据”。
然而,这样的“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关于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什么是迷思(Mythos)?迷思是人们面对无法解决的冲突而编造出来的理由或者故事。我们可以将迷思操作性地理解为与客观事物或事件真相不符合、不一致的观念。迷思具有一种力量,能让人们在某些问题上不再产生认知冲突,并让其相信某些观念或形象(譬如神)是客观的、真实的,或者认为诸如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等不公平现象是正当的。[2]187但迷思即便拥有一定数量的受众,也不能因此而被视为真理。
笔者基于对女性与科学关系史的把握,认为有关性别与科学的智力迷思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观念:大脑存在性别差异,只有抽象思维(男性思维)适合科学学习,以及母性非智性。对这三个命题的批判性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为女性科学弱势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归因。
一、大脑存在性别差异?
“在一般大众——包括许多心理学家——的心目中,智力实际上就是‘脑力’的同义词。于是取得高成就者的大脑被翻来覆去地研究,研究者企图从中发现一点线索,找出这种奇妙成分究竟是什么。”[3]13历史上科学成就为男性所垄断这一现象,同样吸引着人们翻来覆去地研究男女大脑的差异。
关于女性大脑较早的科学研究隐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这就是女性在心智上的劣势是固定的、难以改变的。基于这一前提,研究者努力寻找有关的生物性依据。研究者首先断言,女性的智力劣势源于她们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小的大脑体积,一些科学家认定许多女性的大脑在大小上接近于大猩猩而不是男性。[2]221但是这一“发现”在以下事实面前被轻易颠覆了:根据这个标准,大象和河马的大脑体积比人类的大,因而应当比人类更聪明。不得已,科学家转而考察男女大脑体积与其身体重量的比值,并将这一比值作为测量男女心智的标准,比值越大则心智越发达。研究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占优势,于是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再有什么进展。
科学家接着考察了男女大脑特定区域的差异,指出大脑中的一个区域——额叶,是存放最高心智的场所,并相信男性的额叶更大和更发达。但是,这样的断言不仅起初很难得到证实,而且后来又有研究证实男女大脑的额叶是类似的。[2]222相关研究又转移到了男女变异性问题上。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假设,即男性作为一个群体更具有变异性,更多男性处于人类行为的两极;也就是说,在最傻和最聪明的人中男性要比女性多。这一观点为更多男性能够企及天才般高度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虽然这一发现同时也预言,拥有弱智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男性比女性更多,但在更多关注甚至崇尚精英的文化里,这种估计几乎被忽略不计。
继而男女大脑的偏侧性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偏侧性(Lateralization)指的是人类左右半球大脑运作专门性的程度。[2]266这方面的研究者声称,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运用左脑和右脑,但却各自擅长于其中之一。通常,男性的左脑更发达,而左脑控制线性思维、抽象思维及逻辑推理等;女性的右脑更发达,因此女性的想象力更丰富,更擅长直觉思维。[4]23这样的观点虽不乏对女性大脑机能的肯定,但主要还是突出男性的理性智力优势。不过,批判性的观点也随之而来,这些观点认为,较之不同个体大脑偏侧性的差异,男女大脑偏侧性差异并不会显得更明显。
最后,则是凭借智力测量证明男性空间视觉、逻辑推理等能力比女性优秀。不少智力测验宣称,男性智商要高于女性,尤其在空间知觉与想象、数学及逻辑推理能力等方面占优势。[5]223-225不过,另有研究者认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男性比女性智商更高。在这类研究中,较早的是苏格兰教育研究委员会公布的一次智力测验结果。[5]222-223这一测验的实施者发现,由于生物的和文化的因素,男孩会长于做某类测验,而女孩则做另一些测验成绩比较好;如果这种差异在测验中得不到平衡,那么,测验结果就会显示出男孩的智力优势。苏格兰的这次测验关注到性别平衡问题,最终使得智力测量中未出现性别差异。看来,貌似客观的智力测验,其实回避不了社会性因素的干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关于男女智力的测验变得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
有关男女智力差异原因的观点也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男女智力差异的根源在于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如当今美国学者古里安就认为,男女两性的大脑不是以相同的方式被构造而成的,它们天生就是有性别差异的,而且这些差异还是后天力量无法改造的。[6]49除了以某些脑科学研究结论为依据,古里安还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论证其观点:“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能发现男孩和男人通过狩猎等空间——机械运动原理、经济和贸易上的数字往来、发明创造中涉及的科学原理——进行有机的自我发展。男性大脑是一个美丽的连接迷宫,正等待连接数字、距离、大小、方位和方向。”[6]131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文化才是导致男女智力差异的根本原因。“男女两性的先天性智力是差不多的,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社会压力和性别歧视阻碍女性追求科学与数学成就。”[7]“生物性的影响如遗传现象或荷尔蒙,和智力表现之间的可能联系仍然在探索之中。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的影响。”[2]214-215
尽管对此莫衷一是,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关于男女大脑差异的观点所隐含的规律,这就是:当社会需要或者重视男女两性智力差异时,发现或论证智力差异的科学活动就会活跃,生物决定论亦会得到传播;反之,当社会需要男女之间不存在智力差异,且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男女两性时,就会有不少人士去发现或论证男女大脑的相似性,并以社会环境决定论去论证某些性别差异的根源。
在当今社会,大多数的国家、政党以及群体,都需要女人像男人一样有能力从事社会生产,成为社会的“人力资源”,由此强调男女大脑无先天性显著差别的观点以及认同社会环境是影响男女智力差异的观点已越来越普遍。但是,要求女性像男人一样付出并不意味着赋予女性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待遇,男性在社会公领域的强势地位依旧是许多团体或个体不希望、不愿意改变的现实,同时,期待女性为社会、家庭及男性作出更多奉献的意识依旧相当流行。在这样的情形下,证明女性逻辑理性、抽象思维不如男性的研究就仍具有存在的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群体间表面上存在的(智力)差异已经为了政治上可以的目的而被开发。”[8]137关于性别差异的辩论各有论据,“它们都以科学的语言表达,用人体作为证据。虽然许多时代都利用科学使其对男女本质的讨论显得客观而不可辩驳,但显而易见,关于性别的基本思想受政治因素的影响”。[9]116
二、只有抽象思维(男性思维)适合科学学习?
与智力这一概念紧密关联的另一范畴是抽象思维。“自(智力)测验运动兴起以来,抽象思维能力就一直被当做是智力的标志之一”;“抽象推理总是被认为是智力发展的最高阶段”。[10]160一般而言,抽象思维就是透过表面的知觉现象推断出内在的规则。与抽象思维对应的是具体思维或形象思维,其特点一般被理解为容易受到经验和直觉的制约。长期以来被视为抽象思维的典型就是逻辑推理,此外,对数理逻辑的理解与把握也一直被视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抽象思维。善于使用数学的人常常被认为是聪明的、高智商的人,使用数学语言进行逻辑思考也被认为是具有创造力的智力活动。
若将思维、科学学习和性别相关联,我们会发现这一流行观念:男性擅长抽象的逻辑思维,女性擅长形象思维,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学好科学。从人类思维方式的生成及演变历程来看,抽象思维的确与男性的关系更为紧密。抽象思维之所以得以存在,源于劳动阶级与闲暇阶级的划分。闲暇阶级拥有过纯粹理性的生活的基本条件——适当的智力以及自由,但这些条件的创造者却是劳动阶级——妇女、奴隶和工人。“奴隶、工人和妇女被用来提供生活的手段,使具有适当的智力的人可以过闲暇的生活,从事有内在价值的事情。”[11]271这种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情,就是纯粹的脑力劳动。闲暇阶级中的少数精英男性发展起了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方式。
抽象思维是以男性为隶属者的思维,科学需要的是抽象思维,因此科学领域理所应当以男性为主体——这种流行观念为科学排斥女性或者女性疏离科学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起着符号暴力的作用。为了减小甚至消解这样的符号暴力,有必要对这样的观念予以审视。
首先,透视一下所谓的抽象。
抽象一直被视为脱离真实情境与个体经验,但是这样的界定只不过是以精英男性为主体的闲暇阶级生活方式在思维活动中的体现。因此,这样的界定是人为的。那么,是不是联系生活情境与个体经验的思考就不包含着逻辑呢?一位西方学者以如下三段论考察过非洲尼日利亚农民:[3]160-161
例一:所有的派勒人都种稻谷,史密斯先生不种稻谷,他是派勒人吗?
例二:所有的房产主都付房产税,博玛不付房产税,博玛拥有房产吗?
对于例一,第一个被访谈的人坚持说他不认识史密斯先生,所以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对于例二,被访谈的人的回答是:“博玛没有钱来付房产税。”这样的回答在受过基本学校教育的人看来,似乎都是缺乏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表现。但是研究者指出,这样的判断是武断的,因为被访谈的农民实际上作出了完美的逻辑演绎。例如对于例一,被访谈者的逻辑思维是这样的:我所能作的所有推论都是关于我认识的人的,我不认识史密斯先生,所以我不能对史密斯先生作出推论。
接下来,看一看是否数学语言最具抽象性。
以数学语言为工具进行的思维,其抽象性一直被视为要强于以其他语言进行的思维,最高级别的抽象思维也曾被视为是数字性的或几何形式的。一项关于抽象性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反思这一迷思。
研究智力的美国学者塞西等人邀请一群专家对“抽象”进行评定。[10]165-166参与评定的专家在各自领域从事着具有高度抽象水平的工作。研究者分派给这些专家32个问题,要求他们根据解决过程的抽象程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等级评定。调查结果表明,不仅某个领域的学者同其他领域的学者在32个问题的抽象性评定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同一研究领域内,学者们也常常无法达成共识。例如,某些学者认为,较之某些数学问题,诸如“何为勇敢”这样的问题更加抽象,需要更高级水平的抽象思维。这些数学问题如:“一件夹克平常卖32美元,减价时打7.5折。如果无人购买,商家在此价格的基础上再打对折。试问在第二次减价后夹克的价格是多少?”他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属于计算题,并不需要更深入的抽象思维,而关于“勇敢”内涵的理解却需要抽象思维。不过,也有学者在评定这两个问题的抽象水平时得出相反的结果。
显然,关于“抽象”的理解并不存在单一性或一致性,抽象思维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数学或几何领域。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领域表现出的高水平复杂性思维,都可以称之为抽象。
最后,谈一谈女性擅长的思维是否真的不适合科学学习。
就科学而言,抽象思维一直被视为是最适合的,且为男性所拥有。很长时间内只有少数人对这一迷思予以质疑,当代科学史研究专家伊夫琳·福克斯·凯勒即为代表之一。伊夫琳通过研究细胞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女士的科研经历,发现了这位女性科学家独特的思维方式。
一是对认知对象投入感情。麦克林托克对认知对象所投入的感情,不完全是那种寻找物质世界内在规律的执著——在许多时候,这种执著更像男性气质中的征服品质,而是将认知对象看做与自己一样的生命。带着情感接近研究对象,显然有别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抽象理性。
二是看、听及观察。麦克林托克一再告诫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心去“听材料对你说话”、去观察。[12]201她也正是以这些方式走进生物世界并取得成功的。这一告诫明显背离了科学探究的最流行姿态——不停地做实验,进行逻辑理性推理。
三是相信直觉。麦克林托克认为阐明自然规律的主要方法不仅仅是推理和实验,还有直觉。[12]203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女士,同样非常强调直觉对于其科研的意义,她坦言“只是跟着自己的鼻子走”。[13]看来,女性的直觉同样有助于科学发现。
事实上,统领科学领域的纯粹抽象理性并非只在当代遭遇质疑与批判。洛克说在感性里没有的东西在理性里也绝不会有。当达尔文失去了音乐、诗歌等情趣爱好之后,他哀叹:“我的心灵好像变成了一架机器,它从大量的事实中抽取一般的规律。”[14]136弗洛姆则指出,被纯理性、纯策略思考统治的人们将会发生情感退化、人格异化甚至人的本质的萎缩。[14]138如此看来,女性思维方式有可能改善传统科技理性存在的缺陷,其不仅是适合科学的,而且还能促进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
三、母性非智性?
长久以来,社会赋予女性的期望几乎一直包含着这一稳定内涵——母性。人们要么希望女性成长为合格的母亲,为国家民族培育强健的后代;要么期望女性能成为全社会的母亲,为所有人提供母性的照顾与滋养。但是,女性在教育、医护等“女性”领域同样难以获得卓越成就,究其根源,在于这样一种智力迷思,此即母性非智性。
母性非智性的含义是这样的:母性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德性,这一德性包括关怀、利他、慈悲、隐忍、奉献、牺牲等美德,这些美德的培养需要的是榜样、灌输、陶冶等手段或方式,而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或逻辑理性;即便需要自然科学之类的知识,那也是浅显的、基础的。总之,母性并非人类智慧或理性的体现,母性的养成与实践也不需要多少科学知识与理智训练。
正是基于对母性的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教育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向女性或母性关上大门,女性才得以被彻底地排除于科学问询活动之外。有史以来社会培养母亲或母性的教育,充斥其中的几乎全是道德楷模、教条、训诫、机械操练以及习俗,尤其是舆论的引导与评判,教育活动史上几乎从未存在过以培养母性或母亲为目的的严格的、系统的理智训练体系。
母性非智性是否真的符合客观事实呢?显然不是,母性与智性或理性之间存在着必然关联。斯宾塞早就指出,抚养和教育子女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人类活动之一,这一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需要科学知识,譬如生理学原理和心理学知识。[15]2918世纪女权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斯特则进一步阐明,“理性乃是妇女正确地完成任何责任所不可或缺的”[16]57,“一个妇女要想成为一个好母亲,必须要有理智以及独立的思想”。[16]157她认为,妇女越有理智,就越能理解和履行她们的责任,因此,女性必须与男性一样学习自然科学、钻研医术;只有接受这种旨在培养理性与理智而非盲从他人品质的教育,女性才能拥有理性,继而才有能力担当起她们的重要职责——母亲。
培养合格母亲的教育,其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知识类型之一就是科学知识,但是这一观点即便在当代也尚未得到实践。究其根源,在于科学教育一直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男人们习惯性地将科学教育的目标对准他们活跃其中的社会公共领域,同时将科学教育的价值定位于有助于男性的事业成功。科学教育中的男性特权导致了家庭私人领域被排斥其外,相应地,家庭私领域的母性培育及其实践也就难以得到科学教育的引导。所以,理性、理智、独立思考和判断与养育和关怀一样,理应成为公私两大领域以及男女两性共同需要的能力与品质。
[1]查尔斯·默里.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M].胡利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上册)[M].许敏敏,宋婧,李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3]肯·理查森.智力的形成[M].赵菊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人生[M].徐俊,尚文鹏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5]珍妮特·希伯莱·海德.妇女心理学[M].陈主珍,等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6]迈克尔·古里安,凯西·史蒂文斯.男孩的脑子想什么[M].田文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
[7]Lewis Asimeng-Boahene.Gender Inequity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Africa:the Causes,Consequences,and Solutions[J].Education,Vol.126,No.4.
[8]Howard Gardner.智力的重构——21世纪的多元智力[M].霍力岩,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9]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M].何开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0]S·J·塞西.论智力——智力发展的生物生态学理论[M].王晓辰,李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2]伊夫琳·福克斯·凯勒.情有独钟[A].章梅芳,刘兵.性别与科学读本[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13]看看,诺奖科学家也是平常人[EB/OL].http://csxb.bandao.cn/data./20091007/html/23/content-1:html.
[14]埃·弗罗姆.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M].杨慧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15]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6]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斯特.女权辩[M].谭洁,黄晓红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董力婕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 Mythos about Gender and Science
ZHOU Xiaoli
The intellectual mythos about gender and science are following: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brain;only abstract thinking(patriarchal thought)is suitable for scientific study;motherhood is non-intellectually.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or historical power,although such mythos i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truth,they still influence us widespreadly and profoundly.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 intellectual mythos about gender and science will help provide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 attribution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vulnerable of female.
gender;science;intellectual mythos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5.006
:2013-08-25
C913.68
:A
:1007-3698(2013)05-0035-05
周小李,女,武汉工程大学高教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教育及女性学。43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