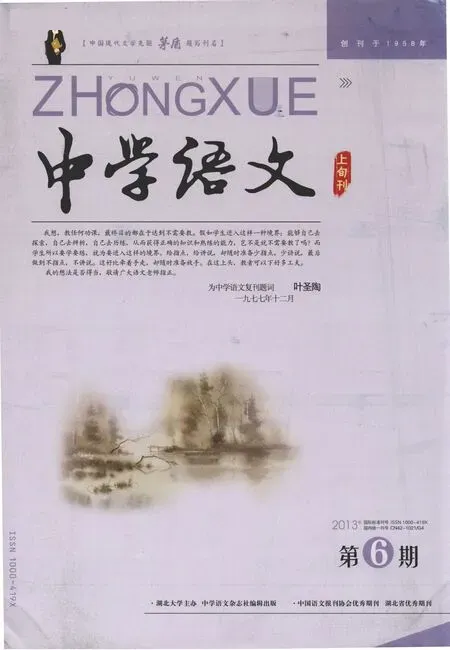浅析鲁迅为何钟情“小人物”
关业锋
纵观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些下层社会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或农民、或小市民、或小知识分子、妇女、孩子。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阿Q列传》中的阿Q,《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件小事》中的车夫,《祝福》中的祥林嫂……鲁迅先生以锐利、深邃的眼光,以小见大,借助这些“小人物”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来寓示更大的社会思想内涵,使“小人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作家笔下的一些“小人物”如狂人、阿Q等已成了世界文学长廊上典型人物,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种通过写小人物来寓示更大主题的创作方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文学创作的天地对于作家来说是那么广阔,古今中外总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鲁迅先生为什么总选取“小人物”来写呢?譬如写张勋复辟这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写张勋而写赵庄的六斤一家?反映辛亥革命的教训为何不直面历史而写“华”“夏”两家。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这虽然同作者的创作方式有一定关联,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鲁迅先生之所以刻画一系列“小人物”,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与鲁迅先生成长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可以说,这些“小人物”是他自身生活经历及所见所闻的折射。鲁迅先生小时候家庭由小康渐入困顿,在动荡年月下乡避难和为父治病进出当铺、药店的过程中,饱受世人的歧视,深深体会到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从而憎恨自己出身阶级,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农村外婆家,后来仍和农民保持着联系,因而熟悉农村社会,既同情农民的苦难和不幸,又为农民愚昧落后而忧虑,这在《故乡》中闰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促使他后来长期关注农民,思考农民的解放问题。鲁迅先生曾说:“我生活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到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身受压迫,有很多痛苦和花岛并不一样了。”
1904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一次课间放映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在看到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杀头时,不少中国人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热闹,神情麻木,无动于衷。这使鲁迅异常痛苦,认识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愚昧,精神颓废,是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根源。
另外,鲁迅年轻时也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过多地看到人民群众身上麻木落后的一面。他感兴趣于“什么是理想的人性”,注重于“立人”。他认为“生存空间角逐到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后凡事举。”究竟什么是“理想的人性”,立何种“人”。在鲁迅当时看来,尼采的哲学就是提供了一个与自己思想立向相投和使自己内心的朦胧要求清晰起来的答案。这就是那种“意力轶众”的人格理想。据许寿裳回忆,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鲁迅最关心的是下面三个相关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十分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国家的富强‘根柢在人’,因此校园之道也是‘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凡事举。”他认为只有立“人”,国家才可以救可以兴文明才可以进步。而立人,在鲁迅看来只有立下层广大劳动人民,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被愚弄的对象,是历史前进的巨大推动力量。
其二,与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关 关于国民性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是由他“我以为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他想通过唤醒人民的觉悟,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来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莎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是同中国当时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相适应的。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有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不难看出,鲁迅把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作为“第一要著”,他写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
鲁迅分析中国的国魂有三种,官魂,匪魂,民魂,他积极主张发扬民魂,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其进步。”无论国民性的积极面或消极方面,鲁迅所注视的对象都是劳动人民。积极面固然不必说,他明白地说:“民魂”是“老百姓”,当然是劳动人民。鲁迅承认国民性中也有值得肯定和发扬内容的,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尖锐地批判阿Q精神,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加以批评。但也在《一件小事》中赞扬了人力车夫关心别人的高尚品德。又如闰土的勤劳,爱姑的反抗都不能说是值得发扬民魂的内容。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民魂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
鲁迅也曾明白地说这“国民”是与“圣人之徒”相区别的,象压在石底下的草一样的百姓。可见他要改造和批判的是劳动人民身上落后和消极的东西,所以他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写到“小人物”。这并不是说统治者身上就没有落后和消极的东西,他们甚至更为严重,但鲁迅的思想上对于“圣人之德”和老百姓还是区别得很清楚的,他从现实出发,已经分明地看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看到阔人和“窄人”,“圣人之德”与百姓的对立。而且自己是怎样鲜明地站在被压迫下层社会一边的。他说:“古人说,不读书便是愚人,那自然也是错的,然而世界却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因此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也不能笼统地认为是阶级的。他所着重的当然是劳动人民身上的弱点,因为这是妨碍他们觉悟起来的精神桎梏,如同阿Q精神之于阿Q那样,是必须严加批判的。通过鲁迅小说中劳动人民身上具体表现出的国民性弱点,以及鲁迅对其中人物“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叹,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期待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从而结束自己奴隶地位和命运的。只有使那些充当“小人物”的劳动人民觉醒起来,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使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民族魂才可发扬光大。
其三,这与鲁迅创作的大众化思想也有一定联系 鲁迅从他一开始文艺运动就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他一方面反对那种“立宪共和”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他认为这种社会理想不过是干白的无赖和市侩来代替独夫的专政罢了,而老百姓还是不堪其苦的。另一方面,又坚决地反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他要摧促那些被围在“古训”——即是统治阶级的教义——的“高墙”里的人民觉醒过来,把这世界改造成“其的人”的世界。鲁迅从这个立场出发,给予自己的写作任务:就是揭露出“上层社会”人们的堕落和丑恶,通常是侧面烘托,描写出“下层社会”的人们的不幸与苦难,这就必须涉及到下层社会的一系列“小人物”。鲁迅的这一创作“纲领”,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可得到证实。
鲁迅在一篇题为《革命文学》的文章中就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可见鲁迅很注重革命性问题。这样就必须使写作的范围限定于下层人民的生活,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文艺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的土壤,他很重视创作的大众化问题,把国民的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他说:“据我的意见,即使是从前的人完全埋于政治的土壤,确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联系中国的实际,大众化问题在鲁迅的文艺思想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使文学冲破士大夫阶级的掌握,努力与人民群众接近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作了很大的贡献。当文艺大众化问题开始讨论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文艺本应该为大多数人所能鉴赏的东西“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因此,既要使大众作品流传,又要为大众而作。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写大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