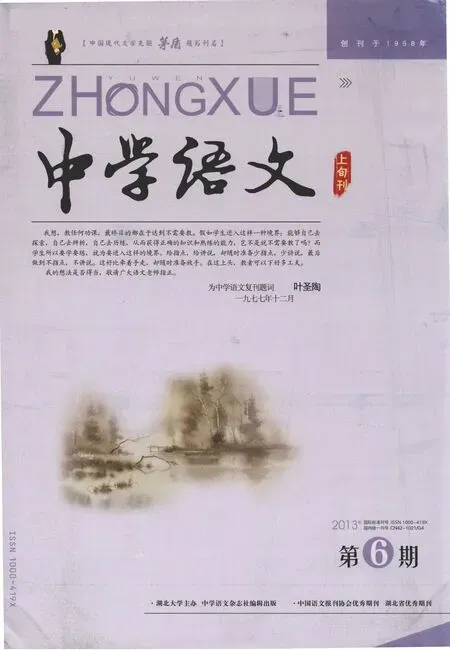从理性到诗性:语文教学中意义世界的嬗变
张金辉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对理性精神的执著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不可否认,科学理性主义的兴起,很好地推动了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认知世界的能力,但“因视科学为唯一的途径,我们却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失去了或至少忽视了故事(我们的文化)与精神(我们作为人的意识)”这也是当前语文教学中的弊端所在。
一、理性观:诗意与惊异的遗忘
(一)以理性主义为指导的语文教学通常只关注语言作品在场的意义
“在场”和“不在场”是近代哲学的一对概念。所谓“在场”是指当前呈现之意,也就是平常说的出席的东西,所谓“不在场”,就是指未呈现在当前或缺席之意。正如我们欣赏画家梵高的一幅名画,透过他所画的一双沾满泥土的再普通不过的农鞋,我们却仿佛亲见了农夫在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场景,甚至体验到了穷苦农人对死亡的恐慌,对面包的渴望……在这里,农鞋的画面是在场的,而由农鞋所传达的其他意味却是隐蔽的、不在场的。其实,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隐”与“显”的统一,这在由艺术符号所构筑的语言作品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品中在场的是表层语言文字所描述的“白发三千”,而透过它我们却能捕捉到诗人心中无限绵延的一腔愁绪,这便是诗歌作品中“不在场”的意义。语文教学中“在场”的意义表现为经语文教材或参考书的直接陈述,师生通过简单认知性学习便可获得的意义。而“不在场”的意义则是作品语言中没有直接呈现,而需要师生共同潜心思虑、调动灵思妙悟才能挖掘出的“象外之象”“蕴外之味”,这是需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获得的。语文教学中,师生对语言作品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是由“文表”到“文心”的“横向超越”,是要达成语言作品中“在场”与“不在场”意义的内在统一。
(二)以理性主义指导的语文教学遗忘了学生的惊异与创造
惊异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最原初方式,表达了人类由“无知”走向“有知”的渴望。因此,惊异是智慧的开端,人类最早的哲学便是在惊异中诞生的。同时,惊异也是人类的一种诗性存在方式,怀抱惊异之人善用“散文化的眼光”来瞭望世界,因此,即使再过平常的事物,也总会以非同寻常的姿态撞入惊异者的眼帘。叶燮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这种“神明才慧”就是人类面世的惊异感,也就像老子说的超欲望、超知识的高一级的愚人状态,或“复归婴儿”的状态。“惊异感”本是内在于人的生命的。然而,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语文教学,常常抹平他们对世界天真浪漫的奇思妙想,阻断了他们用语言去构建自我意义的坦途。科勒律治曾经说:“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我们的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因为“太熟悉”和“太自私”的缘故,遗忘了学生对语言意义世界的惊异和想象呢?语言知识的强行灌输,标准化的统一答案,语文教学的诗性本质被遮蔽,分段、人物分析、概括中心思想等程序化的授课方式,学生灵动的生命在遭受放逐。
二、诗性观:意义世界的多元生成
“语言常常被看成是等同于理性的,甚至就等于理性的源泉,但很容易看出,这个定义并没有包括全部领域,它乃是以偏概全,是以一个部分代替了全体,因为与概念语言并列的还有情感语言,与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并列的还有诗意想象的语言。语言最初并不是表达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和爱慕的”。卡西尔这番话在道出语言诗性特征的同时,也道出了语文教学的诗性本质。而这一本质正是由其构成本体——汉语言符号的诗性存在方式决定的。
汉语言符号诗性隐喻的存在方式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想象和创造来促发意义生成的张力空间。我们说,任何一种语言符号在整体上都是一种隐喻性的符号系统,它们是图式,是密码,字字都是“无底的深渊”,句句都充盈着“诗性智慧”。正如诗人哥特弗里德·伯恩在《一个词语》中的描述: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留驻,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哥特弗里德·伯恩《一个词语》
可见,象征、隐喻特点使语言符号内蕴着一种神秘的、能够召唤万物的力量。海德格尔将语言的这种诗性召唤称为“天、地、人、神四方体的聚拢”,加达默尔将其称为“语言的思辨性”。因此,他们认为语言不是简单的命名,语言是一种召唤,这种命名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之中,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在语文教学中,它们在召唤着学生主体的感悟和体验,召唤着他们对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能动的想象与创造,从而迈向一个丰富多彩的意义无限生成的空间。譬如,一个“涉”字,学习它时我们不仅认识了它的构成形态和基本含义,更重要的是那崎岖弯转的会意形体更容易让我们想象到一部汉民族栉风沐雨、艰难跋涉的宏大民族史诗。同样,在舒展着生命姿态的语言作品世界里,我们可以想象诗经时代动人心弦的爱情吟唱,想象楚辞世界神秘莫测的巫风神话,想象魏晋世子洒脱不羁的生命意识;想象盛唐时期金碧辉煌的恢宏气度,想象宋元田园山水的显隐之境;想象明清末世清静淡雅的世俗图景……
除了诗性隐喻的特点之外,汉语言符号也是颇具审美性的符号系统,审美精神执着于汉字洒脱不羁的飘逸形体,渗透于汉语金声玉振的天籁细语,镌刻于语言作品中浪漫唯美的诗意铺陈。它使汉语言符号的意义世界展现为一个多层审美的天地,从而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诗质的审美空间。
汉语言符号的诗意审美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汉语言符号的音乐美 中国古代汉语是以汉字为本位的,一字一音,一字一词,四声相谐,平仄相生,这很容易在音调自由的组合中搭配出抑扬顿挫、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汉语是适合歌咏的,其中表现出的“神气”便是一种美的韵味,美的气质。如徐志摩的小诗《再别康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首小诗中,汉语十三辙中的“言前”“江阳”等洪韵响亮悦耳,表达了欢快愉悦的情感意义,“遥条”“怀来”等柔韵缠绵悱恻,表达了忧愁失落的情感意义。就是在这抑扬顿挫得如珠落玉盘的乐律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欢悦与哀愁纵横交织的复杂心绪,从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符号世界里真正感悟到了语言的多重意趣。
二是表现在汉语言符号的绘画美 汉语具有整体性、具象性、形象性等特质,这样的语言具有触发人的想象和联想的特点,闻一多先生曾这样说:“唯有象形的中国文字可以直接表现绘画的美,西方的文学变成声音,透过想象才能感到绘画的美。可中国的文学,你不必念出来,只需一看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诗,立刻就可以饱览绘画的美。”可见汉语言符号的绘画美不只是表现在描摹物象,更重要的是借助语言符号来 “画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 “大写意”,从而传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更深层的意蕴与更宏阔的气象。作为民族母语教育的语文教育,在其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汉语言符号这种独特的诗性审美特质。因此,一定要引导学生立足于本民族语言符号的诗性审美特质来学习语文,让学生在诗一样的语言中去解读语文、欣赏语文,用诗人一样的智慧去开启语文的奥蕴之门,用诗一样美好的思想来陶冶学生的性情,塑造学生的灵魂,澡雪学生的精神,让学生在诗一样美丽的语文世界探寻意义的多向度生成,在语文意义世界里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