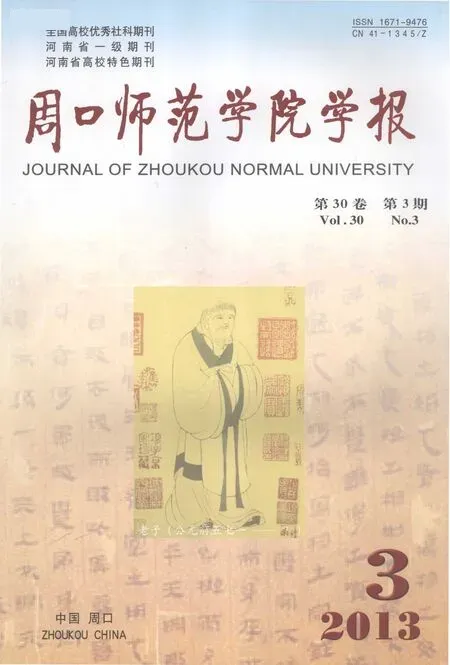雨夜独徘徊:与时代和理想的多重对话:浅析朱英诞的诗歌《苦雨》
刘 畅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于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为中国新诗带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黄金时代。现代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果断摒弃了象征派的怪诞和格律诗的严苛规范,自觉探索着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融合的路径。然而抗战的到来和时局的动荡,让这个自古就缺乏象征主义哲学基础的国度重新举起了“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现实主义大旗,人们不再去关注纯诗、抒情、意象和个人情绪,而是将那些狂热的、为民族奔走呼号从而发挥战斗作用的诗歌奉为圭臬。
在中国北方沦陷区,对于诗歌本身的探寻和坚持面临着更加严酷的考验。但尽管如此,仍有一批年轻的诗人活跃在诗歌创作的前沿,在时代氛围的重压下,默默固守自己的理想、倾诉内心的声音、寻求生命的意义,勇敢地进行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尝试和深化。朱英诞就是这批诗人当中的代表。当然,他的“另类”很难见容于社会。在历史和文化夹缝中艰难前行的他,将诗歌当做漫长道路上执著追求的信念,用尽一生心血去建构一座诗歌的城堡,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安放于此。在这座城堡中,不仅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多重元素,还蕴藏着诗人在时代边缘的自省、挣扎与坚持。据统计,朱英诞创作新诗近3000首,这在整个新诗史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苦雨》是他的一首代表作,这首诗歌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出诗人在时代漩涡中的迷茫与困惑,凸显其个人理想无法实现的落寞和精神的宣泄。诗人用独特的体式完成了与自我、音乐、古典和当下的多重对话,其交错的诗行、齐整的韵律和丰富的意象都极富研究价值。
一、与自我对话:逆境中挣扎的独语
诗歌的题目“苦雨”是诗人所建构的一个整体意象,它包含着双重意蕴:一方面,凄冷的雨夜成为诗人情绪表达和诗歌内容生发的背景和环境,渲染着诗歌的艺术氛围;另一方面,“苦”作为整首诗的关键,在字里行间游离,奠定了诗歌压抑、孤独的基调。在这样阴霾的天气和氛围之下,诗人开始了与自我的对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一个典型的变革便是对“自我”的关注,并通过向内心的开掘,传达主体的苦闷与渺小。“‘自我’在人与社会关系中,成了遭致社会压迫的软弱无能的自我;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一个孤独冷漠的‘自我’,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是灵肉分裂的痛苦的‘自我’。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以‘自’为中心,将外部世界的种种感受内化为心灵的苦闷、孤独、悲伤。”[1]
诗歌以“无怪人们说”这样口语化的表达开端,运用不同的句式和频繁的人称转换完成与自我的对话,整首诗可以看做是诗人的喃喃自语。诗歌第二小节写道:“叫你还访友,出城!”出城访友本是好事,在这里却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的苛责,从这里可以推断诗人访友的过程不甚如意;而下一句“我也送?送”则用了一个设问句,把作者内心的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对自我的反省和质问,实际上是在诉说身不由己的困境和际遇。第四小节“将就点吧,放下‘诗’,好”是整首诗的关键句。诗人让自己不要再固守诗歌理想,并回答以“好”,其实是对自己进行假意的劝说,回答得越肯定,越能显示出作者满心的无奈与悲凉,显示出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遭遇的种种不顺遂。朱英诞曾说:“我只是‘诗人’。逃人如逃寇。一向只是为自己写诗,然而我对于诗却永远是虔诚的……诗是精神生活,把真实生活变化为更真实的生活。”[2]在《诗论四篇》中,他更是提到“当写着诗的时间,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些时间并未消逝而是融化在诗里,这时间似乎就成为最美丽的实物了”。写诗的时候忘记自我,时间都因诗歌而变得美丽,足可见诗人的爱之切。这就再一次证明诗人与自我的对话,只是他在重压之下于精神层面为自己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而这些宣泄,更是对整个时代的一个深沉的叩问:难道这个社会已容不下一个诗人,容不下一颗爱诗的心?难道只有“放下诗”才能明哲保身,才能求得解脱?
诗歌所表现出的对话体式,实际上是诗人运用反讽来表达个人理想与内心压抑的工具;与自我对话,既完善了自由诗参差不齐的句式,也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其内心感受。
二、与音乐对话:齐整的韵律与抑扬的节奏
诗歌的音乐性是西方象征主义诗派创作的重要原则,主要表现为语词选择和诗句组合遵循一定的音韵和格律形式。20世纪30年代音乐性逐步被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所吸纳,从而内化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大特征。《苦雨》的音乐性,既和法国象征派的追求一脉相通,同时也出自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在双方面的影响之下,《苦雨》在诗歌韵律和节奏上都显示出了极强的音乐感,齐整的韵律与抑扬的节奏与自由诗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
《苦雨》共有5个小节,第1节和第3节都用“无怪人们说”作为开端,运用叠句形成了语言和结构的回环;除此之外,这两小节在用韵上也完全相同,第1节当中的“树”与“步”、“扎”与“家”,第3小节的“你”与“里”、“动”与“梦”,全部采用第一行与第四行押韵、第二行与第三行押韵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也被称为抱韵。而第2节与第4节也采取了同样的用韵,第2节中的“返”与“安”,第4小节的“剖”与“走”,都是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全诗的最后一节转变了押韵方式,将第一句与第三句、第二句与第四句进行押韵,韵脚分别是“寐”与“味”、“海”与“买”,这种方式也被称为交韵。诗歌在表面看来是典型的自由诗格式,灵活使用各类参差的句式,但其内在用韵却十分严格,5个小节的韵律呈现出ABABC的整体形态,前四小节构成回环,最后一节进行总结。
朱英诞无疑是自由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整首诗歌对话的形态,参差相交的句式,便是现代新诗自由化和散文化的范例。然而他对于新诗的观念具有客观性和包容性,他曾在《谈格律诗》中提到“自由诗写熟了,韵律便会降临”[3]。他强调新诗的创作要自由采用各种句法,但也注重诗歌的音韵和美感;他不反对纯诗化理论,但更提倡多元化的诗学观,从而将西方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融合到新诗创作中来。
谈及诗歌的音乐性,除了韵律之外,当属节奏了。“节奏是传达情绪的最直接而且最有力的媒介,因为它本身就是情绪的一个重要部分。”[4]布洛克在《美学新解》中说:“诗歌最难传达的意义往往是通过整首诗的音乐和音调揭示出来。诗人心里明白,要想传达出某种意义,必须使用什么样的音调和什么样的节奏。”诗歌的节奏既包括诗行内部的节奏,也包括诗人在诗句中构筑的情绪起伏,《苦雨》的对话体式不仅浓缩了诗人的困顿、寂寞和忧郁,其独特的句式组合更是与诗人的情绪相互照应,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轮廓清晰的疲倦归途者的形象。如果将这首诗看成是一首哀伤低沉的歌曲,那么诗歌中作者的自语可以说是节奏鲜明的鼓点,在诗歌阴郁的整体氛围中凸显诗人对诗歌理想和生存方式的坚定固守。
诗歌第1节先描写归家路上看到的景物,平铺直叙又充满哲思,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静默的思索。第2小节则转入诗人内心的挣扎,用“叫你还访友,出城!”“归鸦,晚安!”两个感叹句和“我也送?送”一个设问句展现内心的波澜。跟第1小节相比,语句缩短,间隔增加,节奏加快。第3节重点描述整个时代的大环境,诗歌随即转入一种客观陈述的语气,取消诗行中的间隔,语句变长,并在第三行“像我们在做梦……”中运用省略号放慢节奏,将舒缓的语气与自己的犹疑迷茫融合在一起,构成情绪上节奏由快至慢的变化。而在第4小节,诗人先用几个逗号将第一句话分割成短促的小段,“五年,十年,廿十年了”,使诗歌陡然转入急促,“将就点吧,放下诗,好”不仅进一步加快了诗歌节奏,同时也将全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高潮,原来诗人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在是否要“放下诗”这个问题上,而最后一个“好”字,集中反映出诗人的无奈、愤怒和绝望,将所有的矛盾冲突推至顶点。难道只有放下诗才能生存,才能保住身上这件“蓝布大褂”?诗人在疑问在反思在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其实是一种否定。到了诗歌的最后一节,诗歌从情绪的巅峰慢慢步入平静,仿佛是长舒了一口气,“把一下午的寂寞当一个假寐”,不如把这一切当做是场梦,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将现实当做虚幻,将虚幻变成现实,看似自我安慰,却隐藏着诗人更深沉的落寞。这样的情绪在无形中回归到诗歌题目所建构的凄苦、悲凉的氛围之中,在首尾呼应的同时,也完成了诗人情绪的挣扎起伏与平静。正如戴望舒所述:“诗的韵律不应只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个层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安排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5]。
三、与中西对话:多元化意象体系与现代审美意识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术语,最早见于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的意象指作者在构思过程中脑海中浮现的艺术想象。意象是诗歌的重要元素,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和审美形态特征,诗人多将生命体验和灵性之光凝聚在意象中。中国现代意象论在承袭了传统诗学的同时,更多地汲取了西方的相关理论。朱英诞受到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派的双重影响,在意象的选取和使用上体现出了与古典对话、中西交融的艺术特色。
诗歌第1小节就引入“树”的意象,并极富哲理和思辨地将树和人进行对比:“无怪人们说人像一棵树/树也有人形的挣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强调比喻是“由心及物”,即作者先有内心感受,再用一个外物的形象来表现,在这首诗中亦如此。诗人先有内心的挣扎,看到路边的树,也觉得那枝桠生发像极了人的挣扎之状,因而这里的比喻实则是作者情绪表达和形象意蕴的再创造。除了“树”之外,诗人在第2小节引入了“归鸦”的意象,这二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都是十分常见的。例如黄升《卖花声》中的“数尽归鸦人不见”,纳兰性德《山花子》中的“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等,都是用以渲染衰败孤寂的氛围。诗人将“枯树”、“归鸦”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元代散曲作家马致远著名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同样是萧瑟的日暮,同样的凄凉的景致,刚刚送别友人而又偶遇“苦雨”的诗人,大约与马致远一样,同为断肠之人吧。历史与当下在这里重叠,不同时代的诗人们在这一刻心灵相通。除了古典化的意象之外,诗歌还在第2节化用了《庄子·山木》中“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的典故,不着痕迹地将古句改写,意在表达送别友人过后的凄清和感伤,从而完成了诗歌的再创造。诗歌结尾“金色的贝,没有人卖,也没有人买”,则是化用了戴望舒《寻梦者》“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中“金色贝”的意象,用以比喻他的诗歌理想。而在这个时代,犹如珍宝的真正的诗歌却鲜有人顾及,所有人都在战争的喧嚣中奔走呼号,诗人本身是不容于这个社会的,这也是整首诗歌之所以会散发出浓郁孤独感的原因。
郭绍虞曾在相关论述中写道:“新诗中原不妨容纳旧的,但必须使人不觉……容纳旧的以后依旧不妨碍新诗的风格和体制,那才是成功。”[6]朱英诞便是在吸收古典文化精粹的基础上自觉进行新诗的实验和创造,诗歌中大量运用了跳跃的意象和现代派的技巧,从而建构了他极具个人风格的穿梭于古典与现代的诗歌美学。从整首诗来看,诗歌前半部分枯树、归鸦的意象具有与古典的关联,后半部“假寐”、“夜”、“水手”、“落叶”的意象则呈现出了如“梦”一般的不连贯性和陌生感,同时,诗歌小节之间相对独立,客观上削弱了语段间意义的连缀。这样的建构方式使诗歌较为晦涩,但也扩大了诗行跌宕的空间,可以说是现代派诗歌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陌生化”一词最初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它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提出了诸如“好的诗歌永远是充满陌生化”之类的观点。因而,朱英诞诗歌语言的陌生化与形式的疏离感是对西方理论的吸纳和实践。除了对意象进行陌生化的组合之外,诗人还用反逻辑的方式将诗歌进行陌生化处理,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醒。第一节中的“可是走吧,走吧,回到家/无数的路,却没有走一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句诗运用视角转换,突破了以人为主体的惯性思维,将路作为主体进行审视,反观诗人无论走了多少路,路永远以“冷眼旁观”,不会因为谁的行走发生改变,用路的静止和人的匆忙进行对比,进而流露出一种徒劳和消极的心境。朱英诞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主义诗潮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朱英诞在此潮流之中,在融合了古典诗歌特质的同时,在创作中加入了现代派的诸多技巧与方法,形成了与中西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多元的现代审美意识。
四、结语
朱英诞是孤独的,与时代的不相容让他只能将自己圈禁在自我的世界,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份孤独,才导致了落雨的苦涩之味和树木的挣扎之状,才使得他在对话中寻求解脱和救赎,才成就了这一首极富张力的诗歌。
美国作家、批评家威尔逊认为,“孤独的挣扎,真诚的内省,才是文学的力量之源”[7]。这首《苦雨》,正是诗人挣扎和内省的集中表现,他在与自我和时代的对话中完成了一种全新体式的创造,一方面用沉重的独语展示出在特殊年代的迷惑与孤苦,另一方面将古典的意象与韵律和现代自由诗现代派的技法相融合,从而成就了诗歌的独特品格。时代淹没了朱英诞,却也赋予他诗歌创作的灵感与情绪积淀,这位勤恳又极具才气的诗人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和感动。这样一位在重重困境中执著于自己诗歌信念的诗人,相信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文学史价值。
[1]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
[2]朱英诞.一场小喜剧[J].中国文艺,1942,5(5).
[3]朱英诞.谈韵律诗[J].星火,1936(4).
[4]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117.
[5]戴望舒.诗论零札[N].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02-06.
[6]郭绍虞.新诗的前途[J].燕园集,1940.
[7]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M].黄念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8.
[8]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吕周聚,胡峰,褚洪敏,等.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多维透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