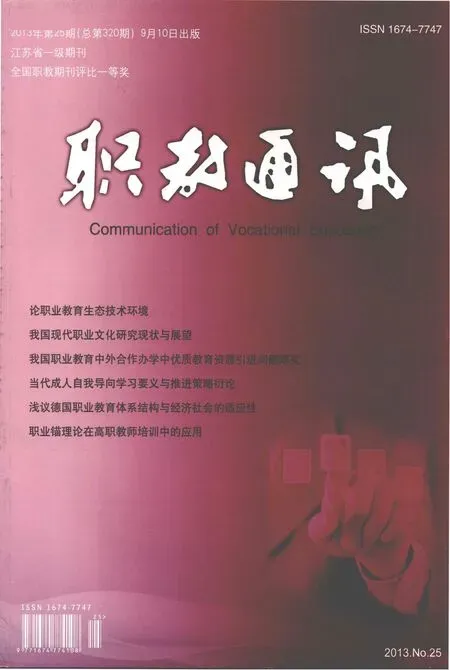试析中国学徒制中师徒关系的变化
施刚钢,柳靖
学徒制是指在职业活动中,学徒在师傅的引导下习得知识和技能的形式。有学者认为,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最早形态,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1]外国学徒制的相关研究和应用成果都较为丰富,而中国则相对较弱,只在介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有所提及。介于学徒制对某些专业工作人员培训的特殊优势,引起了很多学者对其的深入思考。近年来,也开始有研究重视对中国学徒制发展的探索总结。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形成之初就有了学徒制的身影,历史的演变也记述了学徒制的产生、变革和发展。通过历史的视角,来探寻“师徒制”这种技术训练形式中师徒之间关系的变化。
一、“前学徒制”下单纯亲密的“父子”形式
(一)原始社会学徒制雏形时期的父子形式
教育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说,自有人类社会之时就存在教育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教育活动首先是职业性的教育活动。[2]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古籍记载了伏羲氏教人渔猎畜牧的传说。以从事耕种为主的劳动重心的转变,扩大和加深了这一分工。《易·系辞下》中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撕木为耜,揉木为耒,来褥之利,以教天下。”《孟子·滕文公上》里记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此外《通鉴外纪》中也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出现了育蚕制丝、石器、制陶等原始手工艺。据学者考究,此等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需要对制作者进行严格训练,这无不体现着师徒传授的雏形。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此时师徒关系只反映在单一地传授狩猎、采集、耕种或者制作过程中的某些直接经验之中,首先是在社会范围内推广技术,运用动作示范和口头传授,在实际操作中或在一些氏族公共活动场所进行传授指导,以长者、智者、能者教之。由于生产运作流程较短,技术较为简单,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在人们获得经验之后都发展为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拥有劳动组织和生产经验的家中长者,在养育、教导子女的同时,传授职业经验,逐渐形成父子身份、职业世代传习的传统。此时,在这学徒制雏形中,师徒关系主要体现在家族父子之间,父母教自己孩子模仿学习基本生活技能。[3]
(二)奴隶社会及转型期的“养父子”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的积累,阶级分化日渐凸显,历史进入大约1 300 年的奴隶制社会。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展、繁荣。为获取大量劳动力,奴隶主四处捕获奴隶,如羌人擅长田猎牧放,商人捕其为之。另有大批奴隶从事体力劳动,如冶炼技术,仅“司母戊大方鼎”的冶炼工序就需几百人,这都强烈要求对奴隶进行技术训练。另有设官使部分人成为掌管某行业的官吏。这其中不论是奴隶还是官吏,都各守其业。在官吏中实行子习父学的职官教育。在奴隶中实行强制性职业训练,于是,在生产劳动中涌现出大量能工巧匠,他们作为师傅传授技艺,出现了早期的艺徒训练活动。在官工业之中大批能工巧匠被聚集相互切磋、观摩、传授技艺,使技术在交流中得到了发展。[4]
“自东周以来,天子失宫,诸侯自政”,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奴隶获得了自由,“井田制”的废除,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克绍箕裘的学徒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齐桓公就倡导“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子就父学、弟就兄学”。如此,士、农、工、商的个体家庭就成为当时教育文化知识以及相应专业知识的基本单位。
传授某种专业知识技能的私学也在此时显浮于世,招收学徒,徒弟随行于师傅,在实际环境中传授知识技能。墨子以传授力学、几何学、光学和机械制造创办私学;鲁班成名后,也将其一身本领传授给徒弟。也有原来的职官流于民间著书立说,设学收徒,《汉书·艺文志》中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此外,还有个别授徒的事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医术高明的长桑君经十余年指导、观察,并以“勿泄禁方”为条件才收扁鹊为徒。[5]
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采取学徒制的形式,以现场教学为主,重言传身教,师徒关系在家庭父子外有所扩展,培养养子,但仍强调师徒的亲密关系,师徒朝夕相伴,亲密无间,内容从单一的生活技艺扩大到学识、道德等多方面。技艺传授可概括为家业世传、世袭职官、设学收徒以及以师带徒,可称之为养父子关系的“前学徒制”。[1]此外,以“畴人之学”的职官教育形式也衍生出了一丝阶级的色彩。
二、封建社会各种“关系”影响下的师徒关系
(一)秦汉至隋唐时期社会关系影响下的师徒关系
秦汉继承发展了前朝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家业父传、以师带徒等传承技术的历史经验,通过设官教民等形式加以集中推广,使各业的科技水平、经济效益均有了显著提高。秦朝就有“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职官教育形式。汉武帝曾下诏命全国各郡守遣人到京学习新耕作法,学成后再负责传授给广大农民。这是我国汉代采取设官教民,普及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的一个范例。
在私学的基础上诞生了专门学校,汉灵帝末年建立的鸿都门学是一所专习尺牍字画的艺术专科学校,培养拥护宦官派的知识分子与士族势力所占据的太学相抗衡。学生在有技艺并得到推荐下,经考试合格入学。南朝宋文帝又在京师设立四学: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
唐代学徒制的主要形式为官营手工业的艺徒制教育,设立“掌百工技艺之政”的少府监和“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从全国各地挑选高技艺的传技师傅、优秀工匠,艺徒从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加以培养和训练。在皇权严令和丰厚奖励下,师傅们拿出祖传绝技,名师加上较为严格的培训计划,培训出了大批优秀的工匠。
专门学校在唐代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以医学为例,分设中央和地方两级,学完基础课后再分科学习专业课,有修业年限和考试的规定。
职业教育形式主要有设官教民、专门学校和艺徒制,多样的教育形式体现出不同阶级对兴办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学徒制由于受此时儒学的推崇和权力因素的影响,要求尊师重道,师徒之间注重师道尊严,使师徒关系在亲密的私人关系之外,又具有了社会关系的性质。这些“培训机构”都隶属于政府部门,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可见一斑。
(二)宋元明清时期宗法性的师徒关系
学徒制在宋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手工作坊规模扩大,为提升学徒训练效率,徒工在实践中随师学艺,“因其能而分其任”,推行“法式”学徒培训法,以《营造法式》、《弓式》和《熙宁法式》等为标准传授并进行考核。此时,已出现类似于欧洲的行会组织,据《梦华录》记载,宋代手工业都设置了“团行”,其中有“行老”。行会学徒制要求凡是作坊雇佣工匠和学徒都要经“行老”首肯,没有学徒经历的人无法在该行业立足。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催生出行会组织的萌芽,《论语》中有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就是最早的行会组织。汉代史籍中谓之“行列”、“市列”,而明确记载“行”之称呼始于隋朝,在明清时行会制度达到了巅峰。
元朝专门设置了掌管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并任命劝农官,劝助农耕、发展农业生产,编印一些总结农业科学技术的书籍以教民,推动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滋长,各行业的知识技能在民间广泛普及,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出现总结工艺技术的趋向,《算盘珠法》、《园治》等著作也相继问世。同时,行会制度的兴盛也揭开了学徒制新的一页,因为,“学徒制职业教育的产生需要城市的兴起、手工业的发达和手工业行会的出现”。[6]
行会以收徒训练培养可用之人,其系统体系一般分为录用、培养、出徒以及学徒录用禁忌四部分。行会一般以保举制度严格限制招收学徒的条件和数量,全面考量,对招收的学徒知根知底。一经录用,就对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进行教导、培训。一般以三年为学习期,期满合格后出徒,方可独立执掌业务,但工作自由仍在东家和掌柜的掌控之下。而能否出徒,主要取决于学徒在学徒期限内的表现。学徒第一年是考察其忠诚和耐心,主要是伺候师傅(掌柜);第二年,开始接受一些本行业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导,并且,允许做一些简单的日常事务诸如打听行情,抄写文书以及帮帐等;第三年,前半段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学做正经事物,之后经人推荐,可以被派往各分号经受业务锻炼。考察合格后,学徒要行磕头礼拜谢恩师,从此结束学徒生涯。此外,行会一般还有自身独特的学徒录用禁忌制度,如招聘员工需知根知底以同乡为先;跳槽者和被其他商号开除的人不用等。[7]
因注重招收的学徒的生活背景,这种学徒制的师徒关系主要表现为宗法性。学徒投入师门之后,生活在师傅的家族之内,吃、穿、住、行皆由师傅安排,同时,学习职业技巧,可以说师傅代替了父亲的角色。因此,学徒在师傅家里必须绝对服从师傅的管教,完全寄人篱下,无法支配人身的自由,如同师傅或业主的家奴。而且,学徒在学习期间,没有工资收入,但在每月或年终时能得到一些“月规”或“压岁钱”。在票号、典当业,以师傅的意志决定在学徒期限内给予一定量的红利。“月规”、红利的存在,反映了师徒之间不是一种劳资雇佣关系,而是显示了师傅待学徒如亲子般的恩宠,而学徒为报答这种“恩赐”,应毫无“怨”言地服从师傅的驱使。[8]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说,学徒以及由学徒转化而来的帮工,“绝对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处的”。其间的师徒关系产生契约化,带有雇佣劳动的色彩,徒弟在出师之前,绝对屈从于师傅的声威之下,形于父子,严于君臣,苛于主雇,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
三、近代学徒制契约与劳工制度影响下的师徒关系
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使自然经济结构和传统工商业部门逐步解体,新兴工商行业逐步形成。清朝末年,地方政府中出现了设局收徒的官局学徒制。洋务企业聘请洋师傅或将学徒送往国外学习。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迫于内外压力,统治者提出“振兴实业”。
1902 年,清政府在各地创办了大批工艺局,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培训学徒的场所,秉承“传习工艺,振兴实业”的培训宗旨。工艺局扩大了师源和生源,学制灵活化,综合化设置工种,教学内容在坚持技能为主的前提下,授以普通教育。此外,确立激励机制,以技术和学徒成绩奖励工师,提高了师徒待遇,也采取了纪律、考核措施规范师傅和徒弟,并对公费学徒予以分配。[9]设局收徒在民国成立后依然受到高度重视,开办模范工厂,“聘请中外高明艺师,就本省所产之材料,编成讲习”,在各县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入厂学习,毕业后可自行设厂或由政府派回本县充当艺师,将各县原有的劝工局或习艺所改为贫民工厂,招收艺徒。[8]北京政府时期,倡导推行在普通学校推广习艺教育。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公办培训使得师徒间关系表现出一般化的特性,师傅只停留于单纯意义上的教。
在民族工商业中行会内部破坏和维护行会制度的激烈斗争,促成了晚清学徒制的重建。重建的学徒制规定:限定学徒年龄,非本地本帮弟子不收。确认师徒授受关系需签署投师字据,严格限制学徒人身自由,并规定师徒人身依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学徒年限、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师俸,等等。学徒的学费包括押柜钱和出入师门钱。但学徒培养开始注重因材施教,学习技艺循序渐进,学习之初还是逃脱不了奴役的命运,随时听候老板、师傅调遣。[8]另外,还制定了师徒处罚条例,以契约的形式进一步了明确师徒间的义务关系,雇佣色彩更为鲜明。
旧式手工业学徒制依然故我,而传统行会则向同业公会和工会方向发展,开始具备资产阶级法人团体的特征。在民国成立后,继续加强工商业组织的法规建设,使学徒制更加符合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获得大量任意驱使的劳动力,不再严格限制学徒数量;工场手工业的成型,使原先复杂的工艺被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工序,学徒的训练机制日渐淡化不需再熟悉每个环节;经理和监督的角色取代了业主兼师傅的地位,师徒间不再朝夕相处,亲密指导;依然留有宗法特色,学徒仍需拜老板为师(这在工厂学徒制中表现弱化),然后与技艺精湛者学技,称之为“带师”,资本家以师之名榨取学徒劳力。不同的是入门礼节简单化,学徒在学期间亦可获得一定收入。商业在招收学徒方面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封建性:进门依旧要行拜师礼,出入师门要缴费“谢师”,否则终身为学徒。学徒所执投师贴是学徒单方面向师傅做出保证,习业期间人生权利被剥夺。[10]各行业的学徒基本仍处于最低等的奴仆地位,不平等契约化雇佣特色突出。
南京政府在1929 年通过了《工厂法》,其中,第十一章以11 条的内容专门对学徒契约、工作、待遇等内容做出规定。1936 年8 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核定通过的《上海市工人待遇通则》中规定,雇主招收学徒,“不得雇佣未满14 岁之男女儿童”(第11 条);“未满16 岁之童工与学徒,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在午后八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不准工作”(第12 条);对于学徒,“每日应于工作时间外酌予受教育之机会”(第13 条);雇主收用学徒,必须与其监护人订立契约,其内容除基本规定如学徒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种类、缔结日期及存续时间外,还必须载明“相互之义务,如约定学徒应受报酬时,其报酬及其给付期”,并“不得有限制学徒于学习期满后营业自由之规定”(第26条);当“雇主所招学徒人数过多,对于学徒之传授无充分之机会时,社会局得令其减少学徒之一部”(第27 条);学徒习艺期限以所习技艺之难易为原则,“但最长期限不得过三年”,等等。[8]
近代学徒有商、工业之分,工业中有手工业与工厂、官局与私营作坊之别,略微的不同,只存在于资格、年限、待遇等细微之处,但却仍旧避免不了被压榨、剥削。因为进场劳动,被称为工徒的学徒,处在被雇主剥削、压迫的地位。而他们的“学生”身份又表明他们与业主的关系不是雇佣与被雇佣,而是一种师徒契约关系,其劳动力的价值不是体现为工资,而是生产技能。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学徒是行业中的弱者。由于学徒部分还是由业主的亲戚、同乡等介绍而来的,业主与学徒之间依然带有宗法性的师徒关系。相对而言,在官局学徒制中,师徒关系比较大众化。同时,在近代手工业中,学徒制也已不仅仅是职业技术传授制度,更是一种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学徒习艺的重要性下降了(除一些传统手工业外),技艺传授主要依靠旧学徒、技术工人和匠师等,业主徒占师名夺取学徒劳动价值,学徒由学习者变成了重要的劳动力,尽管业主与学徒之间形式上体现为师徒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尖锐对立的劳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劳工制度的颁布,对学徒技艺的要求和劳动力价值的一定认可,为削弱师徒间固有的宗法关系和不平等契约关系提供了可能,为学徒与业主间建立现代经济契约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徒也在学习中斗争,以进步的思想努力冲破这样的关系枷锁和恶劣环境。
四、现代社会迈向理想化学徒制下的师徒关系
(一)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教学制度化下的师徒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有大批的失业人员,国民经济的建设也对技术工人提出了迫切需求。此时,学徒制依然被作为培养熟练工人的重要方式而得以保留并完善,取缔了其中的各种陈规陋习,制定新办法对学徒权利进行维护。师徒关系体现平等性,以教学契约为纽带,均享有生活费、工伤医疗等方面的合法权益。1950 年6 月1 日,国家颁布《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其中第4 条规定对工厂进行技术教育,建立学徒制,签订师徒培训合同;建立激励机制,给师傅一定的奖金报酬;加强技术考核,调动学徒学习培训的积极性等。[11]
三大改造的完成更是加速了对学徒的培养,学徒学习期限缩短,出师后待遇提升较快。仅对南京公私合营机械厂1956 年学徒考核情况进行分析,就可发现一些问题:此时,主要表现为学徒学习期限太短,期间生活待遇过高,转正后技术水平较低,经验缺乏,却又飞速升级,严重影响了新老工人的团结和师徒间的合作。学徒的培养成本较高,易与师傅及其他工人形成竞争,也导致师傅不愿招收徒弟。[12]1958 年2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学徒期限一般为三年,技术较简单的工种也不得少于两年;在此期间,学徒按月领取生活补贴;并明确了出徒考核转正的办法以及工资待遇问题。在同一时期,国家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学校与工厂一体化,既培养学生,也生产产品,学生既学习理论,也参加劳动,实现了工学一体。
《规定》的出台,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学徒制度,师徒间签订师徒合同,以教学契约为纽带,形成了新型的师徒关系,即学徒以学为主,不再是旧社会师徒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平等的,是教学关系,但师傅仍可分配学徒担负一部分技术、业务以外的杂务工作或者其他体力劳动,学徒不得拒绝。师徒享有同样的政治和劳动权利,同时,积极提倡尊师爱徒。[13]没有了依附的限制,服务于教学制度,师徒间的责权利更加明确,但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约束,使得师徒之间出现了利益相争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对“技术挂帅”的批判,技术领域的教育被迫停顿,师徒合同自行解除,是我国学徒培训和职业教育的灰暗时期。
(二)改革开放以后趋向合理化的师徒关系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受到影响,在后期逐渐得到正确认识而逐步恢复。1979 年9 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搞好技工培训工作的通知》。为使学徒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1981 年5 月,劳动局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学徒培训工作的意见》,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学徒培训仍是培训技术工人的一种重要方式,招收学徒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企、事业单位要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1987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正式提出学徒培训要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加以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技术教育的决定>通知》中指出:“对传统和少数特殊工种应按有关规定继续实行学徒培训,其他工种应将招学徒工逐步改为招定向培训生,做到在企业进行操作训练,在职业技术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等培训机构进行专业技术理论学习和基本功训练,以提高培训能力和培训效益”。[13]同时,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引进,也促进了我国学徒制的发展。此时的学徒制,更确切地说是学徒培训,引入了资格认证制度,拥有了一套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系,注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学习在学校和企业间不断转换,实行工学交替,企业与学徒培训生签订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培训生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后,由企业正式录用,不合格的不予录用。[11]在众多企业中学徒制的实践实行规范化,对师傅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标准,一般要求要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有责任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师徒关系一旦确立,权责明确,师傅以身作则对徒弟进行安全操作和实践操作培养,辅之其他教育影响;徒弟虚心学习,尽快掌握所教知识、技能、态度。同时,又辅之以评价激励政策,督促师傅好好地教、徒弟认真地学。现代学徒制双向选择、导师制、名师带徒等制度的出现,帮助师生以及师徒之间可以充分相互了解。[14]教师及师傅犹如引导者、长辈、领导、朋友般对学生的能力、倾向、素质等各方面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培养。师生和师徒处在同一教学情境下,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启发,达到教学相长,消除了传统学徒制度的一些弊端,师徒关系更加融洽,趋于自然。“师徒制的优越性,是感性与实践性的结合,是德性与人性的相加。它源于人与企业的需求,反映了部分人心中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教育形式,或者说,是职业准备、就业过渡或者谋生准备的一种较佳的选择。”[15]徒弟在学到技术的同时,也学会了做人,德技双馨。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学徒制就一直处于一种自发、渐进的调整与反馈的状态,以内在制度的运行方式对人们与社会产生影响。“显然,学徒制是由禁令引导的、受规则约束的一种典型的自发性秩序。”[16]从外部条件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学徒制中师徒关系的演变。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大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子承父学,父母将用以养生之道和基本品行教育下一代。在财产私有化的影响下,阶级概念引入学徒制,统治阶级借此笼络人才,培养势力。行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促使宗法性日渐突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师傅剥削徒弟的劳动力,师徒间雇佣色彩凸显。计划经济调控下,师徒间虽权责利明确,却也存在利益相争。市场经济调节下,学徒制逐步向合理化推进。
师徒间关系的确立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交际范畴除正常的职业教导外,常表现有经常性的私人交往关系。中国学徒制发展至今,其组织制度由简单的私人习惯发展到受相关职业领域约束的社会劳动和培训制度,再发展到由国家法律和专门机构管理。其组织形式也由单一的世袭家传发展为设学收徒、设官教民、艺徒制再到了行会工会和职业培训机构。但在教学方式上,“做中学”仍是学徒制的主导核心。师徒间的关系从单纯的家族父子之间,到亲密的“养父子”关系,在统治阶级办学影响下亲密的私人关系与社会关系兼而有之的性质,到行会制度下具有较强的宗法性的依附关系,带有雇佣色彩的契约化形式与近代劳动用工与管理制度下的进步式师徒关系,责权利更加明确的学徒制下的理性化师徒关系,促使师徒关系更加归于自然,迈向理想化,使师徒制成为职业准备、就业过渡或者谋生准备的一种较佳的选择。
[1]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81-89.
[2]李守福.职业技术教育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3]刘晓.我国学徒制发展的历史考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1(9):72-75.
[4]谢广山,宋五好.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之法[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6(31):74-77.
[5]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4,5-7.
[6]王川.论学徒制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J].职教论坛,2008(5):60-64.
[7]单文杰.明清时期晋商行会制度研究——以习惯法为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
[8]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9-200,305-326,231,223-304.
[9]栾炳文.清末工艺局对学徒制的改革[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4):91-93.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绍兴文史资料选辑(9)·工商史料专辑[M].绍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l99O:106-108.
[11]崔铁钢.新中国学徒制演变的制度分析[J].职教论坛,2012(10):77-82.
[12]陈俊兰.1949 年至1965 年中国学徒制政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8):22-24.
[13]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现代企业学徒制度建设课题组.我国学徒制的历史沿革与创新[J].中国培训,2012(4):8-11.
[14]胡锦秀.“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97-103.
[15]陈俊兰.中国学徒制的现实与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33):19-21.
[16]陈俊兰.中国学徒制研究——需求与原因分析[J].职教论坛,2011(31):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