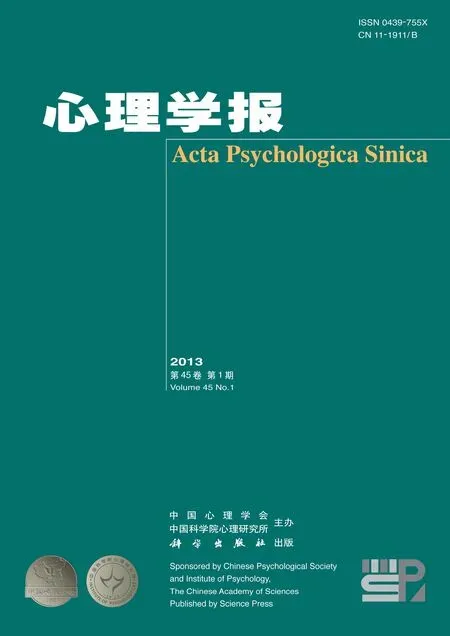不同加工深度非符号数量信息的SNARC效应:眼动证据*
司继伟 周 超 张传花 仲蕾蕾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
1 引言
数字的出现是基于人类对计算物体数目的需要,自从产生以来,数字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直觉上看来,人们所进行的数字加工是一种脱离物体的纯数字符号加工,与数字数量的空间信息无关,但许多研究发现数字与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Dehaene等人(Dehaene,Bossini,& Giraux,1993)首先采用数字奇偶判断任务揭示了数字大小与两侧手反应速度的关系,并把这种数字和空间方位间的关联命名为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简称SNARC效应)。SNARC效应是指对于较小的数字,左侧的反应(比如左手按键,向左眼动等)比右侧的反应(比如右手按键,向右眼动等)更快; 而对于较大的数字,右侧的反应比左侧的反应更快。即在心理数字线上的数字表征位置和反应手位置一致的条件下,反应速度较之于不一致条件下更快。
Dehaene等人对SNARC效应的理论解释为:心理数字线是从左至右走向的,零在数轴的最左端,越大的数字越往右,因此当小数在左端时反应会快一些,大数在右端时反应会快一些(Dehaene et al.,1993; Gevers,Reynvoet,& Fias,2003)。心理数字线的空间走向反映了空间信息对数字编码的影响,它的发现在心理表征层次上支持了数字的空间分布特征。另外,有证据表明数字加工和空间加工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的脑机制,主要在右侧下顶叶皮层部分(Dehaene,2003; Feigenson,Dehaene,& Spelke,2004)。来自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顶叶皮质的活性受所比较的数字之间距离调节,而与数字的呈现方式无关(Dehaene et al.,1996)。Zorzi等人对右顶叶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病人的表现受比较数字之间距离的影响(Zorzi,Pritfis,& Umiltà,2002)。上述研究都说明心理数字线和物理线段具有相似的空间特性,空间注意的方向和心理数字线的走向是一致的,Rusconi 等人的研究(Rusconi,Bueti,Walsh,& Butterworth,2011)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关于水平方向SNARC效应的研究(Schwarz,& Keus,2004;Fischer,Castel,Dodd,& Pratt,2003; Fischer,2001;Calabria & Rossetti,2005)一致表明,小数字与左侧空间相联系,大数字与右侧相联系,这与心理数字线上数字从小到大由左至右的分布是吻合的。
SNARC效应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心理数字线的观点提供支持证据,更重要的是对 SNARC效应的深入探讨使研究者对数字的空间表征有了全新的认识。Dehaene (1997)提出数字的空间表征应该是一种数字地图,在垂直方向,小数被表征在下方大数被表征在上方。当小数字出现时向下的反应要比向上的反应快,当大数出现时向上的反应要比向下的反应快。Schwarz和Keus (2004)的研究证实了垂直方向上存在SNARC效应,而Jarick等人(Jarick,Dixon,Maxwell,Nicholls,& Smilek,2009)以及 Bae等人(Bae,Choi,Cho,& Proctor,2009)的研究则表明数字的空间表征要比数字线复杂。关于垂直方向的SNARC效应的方向问题,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被试身上得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大部分研究得到的是小数字与下方反应相联结,大数字与上方反应相联结(Pecher,Boot,& van Dantzig,2011; Ito,& Hatta,2004; Jarick,Dixon,Maxwell,Nicholls,& Smilek,2009),但是Hung等人在以中国人为被试的研究中得到了垂直方向上逆转的SNARC效应,并认为这与中国被试自上而下的阅读习惯有关(Hung,Hung,Tzeng,& Wu,2008),Fischer等人的近期研究(Fischer,Mills,& Shaki,2010)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也有少数研究联合考察了水平和纵向维度的 SNARC效应的关系,Cappelletti,Freeman和Chipolotti (2007)对5名左侧忽视症患者的心理数字线和物理线的加工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数量表征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是否存在联系因人而异,水平和垂直方向数字线的加工过程中存在部分独立机制。Holmes和 Lourenco(2011)最近开展的三个实验表明,数字在水平方向的表征要强于垂直方向,因此他们认为数量的空间组织中,水平方向胜过垂直方向。Jarick等人(2009)通过对两名犹太被试的研究则发现了纵横交替的复杂空间表征,1~10数字是在垂直方向上表征的,10~20则是在水平方向表征,21~40也是水平方向上表征,依此类推。因此他们认为数字的空间表征远比数字线要复杂。
“心理地图”的提出为数字空间表征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目前对水平和垂直维度上SNARC效应的方向、强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达成共识,这使得“心理地图”的观点不能得到充分证实。主要问题是相较于较为稳定的水平 SNARC效应,并不是在所有加工任务中都能发现垂直方向的SNARC效应。目前用于考察SNARC效应的实验任务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需要加工数字信息的任务(如奇偶判断、数字大小判断),另一类是无需加工数字信息的任务(浏览、自由观测)。有研究者认为,只要任务中存在和数字大小有关的信息,无论是需要较深加工的数字任务(Schwarz & Keus,2004)还是需要较浅加工的非数字任务(Fischer,2001; Calabria & Rossetti,2005; Fischer et al.,2003),都存在SNARC效应,这些数字的空间表征会被自动激活,数字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自动灵活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水平方向 SNARC效应研究的支持,以往研究已经多次在奇偶判断(Dehaene et al.,1993; Bae et al.,2009)、数字大小(Brysbaert,1995)等数字加工任务中发现了水平方向上的SNARC效应。Fischer等人(2003)的研究在屏幕中央呈现数字,随后会有一个探测刺激随机出现在左侧或右侧方盒中,被试根据探测做出相应反应,结果发现,仅仅让被试注视数字就能在水平方向上引起基于数字数量的向左或向右的注意转换。沈模卫等人(沈模卫,田瑛,丁海杰,2006)使用相同的浅加工任务在水平方向上得到了一样的结果,但垂直方向上却没有发现SNARC效应。目前仅在需要数字加工的任务中发现了SNARC效应,例如,Müller和Schwarz (2007)在研究中使用奇偶判断任务发现了垂直SNARC效应。因此,本研究拟考察加工程度对水平和垂直方向上SNARC效应可能存在的影响。
另外,SNARC效应的数字形式不仅仅局限在阿拉伯数字范围,研究者发现其它的数字形式如言语数字、听觉数字、点阵、字母和月份等也存在此种效应(Nuerk,Wood,& Willmes,2005; Gevers et al.,2003)。Nuerk等人(2005)对阿拉伯数字、言语数字、听觉数字和筛子点数等形式的SNARC效应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四种形式的数字均存在显著的SNARC效应。Eagleman (2009)对月份的空间表征方式也进行了研究,他们在电脑上用 3D形式呈现月份,结果发现只有少部分被试的报告表明月份是按椭圆形进行空间表征的,大多数被试的对月份的表征是直线形式的。Fischer和 Rottmann (2005)考察了负数的SNARC效应,研究显示绝对值大的负数,右手反应快; 绝对值小的负数,左手反应快,即负数的SNARC效应在方向上与正数正好相反。Wood (2005)的研究表明,个体可以使用视觉-空间编码来表征语义数字加工,他将此解释为视觉-空间信息和语义信息共享认知资源并与其它空间表征相互作用。一些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符号的SNARC效应的强度。刘超等人对不同注意条件下的SNARC效应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中文数字所受的影响比阿拉伯数字更大,他们认为中文数字作为词本身的 SNARC效应更弱,更具有不稳定性,更易受到影响(刘超,买晓琴,傅小兰,2004)。杨金桥(2009)的研究表明:在奇偶判断任务下,激活中文数字的言语信息,不会引起被试对中文数字进行空间表征; 而在大小判断任务下被试则会对中文数字进行空间表征。Fias (2001)也发现阿拉伯数字上的SNARC效应比英文数字的SNARC效应要强。
从以往对不同符号的SNARC效应的研究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数量既可以用符号数字来表示(阿拉伯数字等),也可以用非符号数字来表示(点阵等)。而已有的SNARC效应的研究大多考察的是符号数值,仅在一项以非符号数字(筛子)作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发现了 SNARC效应(Nuerk et al.,2005)。由于非符号数字本身具有不同于符号数字的特性,因此符号数字 SNARC效应的研究结论未必完全适合非符号数字,仅通过符号数字的SNARC效应的研究来考察数量的空间表征似乎并不全面。因此,本研究拟以在数字认知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的非符号数字—— 点阵为实验材料,考察其SNARC效应,以期对数量表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二是,其它数字符号(包括中文数字、英文数字)的 SNARC效应强度比阿拉伯数字的SNARC效应弱。本研究采用点阵这种非符号数字形式,本身具有一些不同于阿拉伯数字的客体特征,比如面积、密度、形状等,被试在对点阵进行加工时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表征转化过程。因此,我们推测点阵数量的SNARC效应的稳定性相对于阿拉伯数字来说较弱。
最后,在对 SNARC效应进行研究时,为了控制反应中可能由手动引入的与运动相关的无关变量,有研究者(Schwarz,& Keus,2004; Fischer,Warlop,Hill,& Fias,2004; Fernández,Rahona,Hervás,Vázquez,& Ulrich,2011)已经尝试使用眼动的方式获得无干扰的 SNARC效应。Fischer等人(2004)首次使用的眼动方法发现了数字和空间相关联的证据,通过分析被试对数字0~9进行奇偶判断时的注视过程,研究发现,对于小数字向左反应更快,对于大数字向右反应更快,并且眼跳幅度不受数量或奇偶性的系统影响。随后,Schwarz等人(2004)在采用奇偶判断任务的研究中先对水平方向上手动和眼动反应下 SNARC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眼动和手动条件下获得了方向一致、大小无差异的 SNARC效应,证实 SNARC效应反映的是从左到右数量的空间表征; 然后又考察了眼动条件下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SNARC效应,结果在垂直方向上发现了与水平方向大小相等、特性相似的SNARC效应,证明数量表征类似于数字地图而不是数字线。最近,Fernández等人(2011)使用眼动技术考察了对数字进行较浅程度加工时的SNARC效应,他们在实验中采用了自由选择任务,在屏幕中央呈现数字之后,同时在屏幕两边各呈现一张面孔图片,让被试在数字消失之后浏览屏幕。对第一次注视的分析证实数字数量影响自由选择任务的注视方向。由于采用眼动技术能够精确地观察到被试的眼动轨迹,准确计算出被试的注视时间和眼跳幅度,因此既便于准确观察,又提高了研究的精度,使我们对SNARC效应有更全面详细的了解。
由于以往SNARC效应的研究中,深加工和浅加工的实验任务有所不同,深加工任务要求被试对数字的某一特性(奇偶性、数量大小)进行反应,而浅加工任务中要求被试对探测刺激做出反应而不是根据数字刺激做出反应,本研究需要控制不同反应要求这一无关因素。参照Fischer等人(2003)和沈模卫等人(2006)考察 SNARC效应时采用的探测任务,结合研究目的及眼动技术,对范式进行了改进。考虑到被试在反应前目光不能离开中央注视点,而出现在中央兴趣区外的探测刺激可能会引起眼动反应从而干扰数据,因此本研究中无论是深加工任务还是浅加工任务都要求被试根据出现在中央注视点附近的提示线索对目标区域进行眼动反应。浅加工要求被试对点阵进行浏览,深加工时我们采用的是相较于奇偶判断能够更加直接地加工数量信息的大小判断任务,点阵呈现时,让被试口头报告点阵数量与5进行大小比较的结果,主试记录。
因此,本研究采用点阵这种非符号数字形式,对点阵进行较浅和较深程度的加工,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根据提示线索对目标做出眼动反应,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考察不同加工程度下的点阵数字是否出现 SNARC效应,如果出现,那么其方向是怎样的、大小是否相同?SNARC效应是否受加工程度的影响,点阵数量本身特性是否引起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结果。
2 实验一:水平方向上点阵数量加工的SNARC效应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选取某高校32名大学生,男生12人,女生20人,年龄为18~23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眼动实验经验。2.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分为浅加工任务和深加工任务两部分,均采用 2×2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数量大小(小数量1、2,大数量8、9)和眼动方向(左、右),因变量为眼跳反应时,是指从“+”出现到被试做出眼动反应(眼动至相应正方形)为止。2.1.3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材料如图1所示,点阵图片为 25个小方格(每个方格的长和宽均为10mm),方格中分别含有1,2,8,9个点。提示线索为靠近中央注视点左侧或右侧的黑色十字(0.4°×0.4°),反应区域为偏离中央注视点 5°的左右两侧的正方形(1°×1°)。实验仪器使用 Eyelike型眼动仪一台,头部旋转校正范围为-15°~+15°,校准模式是 Hv9,即 9个栅格点校准。实验由一台 P4兼容计算机控制,刺激呈现在 19英寸彩色显示器中央,分辨率为 800×600。实验时,被试眼睛与显示器中心齐平,距离为60 cm。
图1 四个点阵数量
2.1.4 实验程序
(1) 呈现指导语,被试理解之后按Enter键消失; (2)进行眼睛的9点校正,根据主试的要求完成; (3)呈现带中央黑点的空屏,时间为300 ms; (4)黑点消失后出现点阵的图片,时间为600 ms,被试按要求对点阵数量进行加工; (5)点阵消失后,呈现反应区域500 ms; (6)随后在靠近中央注视点的左侧或右侧出现提示线索(十字)2 s,要求被试当十字出现在左侧时向左侧的正方形眼动,出现在右侧时向右侧的正方形眼动,完成后按 Enter键进入下一个试次。浅加工组和深加工组各包括 12个练习试次和40个实验试次。当点阵为小数量时,提示线索出现在屏幕左右两侧各为 10次; 同样当点阵为大数时,提示线索出现在屏幕左右两侧的次数也各为10次。练习和正式实验过程中每个题目的出现顺序采用完全随机化设计。具体的实验流程如图2所示。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尽量保持头部不动,在提示线索出现后进行左右眼跳反应时记录,记录下被试的眼动反应时。

图2 水平方向上点阵数量加工的实验流程
2.1.5 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 12.0对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本实验的数据分析包括:(1)计算每个被试在所有实验条件下的平均眼跳反应时。(2)检验SNARC效应。SNARC效应的考察采用 Dehaene等人(1993)的方法,对不同方向上的不同加工程度的点阵数量的反应数据进行 2(眼动方向:左、右) × 4 (数量大小:1、2、8、9)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初步检验是否存在 SNARC效应。若交互作用显著,说明大数和小数在左右眼动反应时上有差异。然后基于前人研究(Dehaene et al.,1993; Nuerk et al.,2005; Fischer,2003; Lorch &Myers,1990),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先计算各个被试在每个数字上向右眼动平均反应时与向左眼动平均反应时之差(向右眼跳反应时减去向左眼跳反应时),然后建立平均左右眼跳反应时之差对数量大小的回归方程,若回归系数显著则说明出现了SNARC效应,根据回归系数的正负确定SNARC效应的方向。如果出现SNARC效应,即对于小数来说向左眼跳的反应更快,反应时小,向右眼跳的反应时大,那么向右眼跳减去向左眼跳的反应时之差接近零或为较大的正数; 而对于大数来说,向右眼跳的反应更快,反应时较小,向左眼跳反应时大,那么向右眼跳减去向左眼跳的反应时之差为较大的负数。(3)比较SNARC效应的大小。如果两种加工条件下都出现了SNARC效应,则对其回归系数进行t
检验,以考察 SNARC效应的大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2 结果分析
浅加工条件剔除1名注视点大都落在兴趣区外的女生,有效被试为31人,深加工条件剔除2名数据大都落在兴趣区外的女生,有效被试为30人。剔除注视点在兴趣区以外的数据后,被试两种加工条件下的反应正确率是 100%,可能由于大小点数的数量区别较大,任务较简单,不存在速度和正确率的相互作用。剔除反应时在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最终浅加工条件和深加工条件剔除的数据分别占总数据的12.1%和17.1%。
2.2.1 在水平方向上对点阵进行浅加工时的SNARC效应
当点阵为1和2时,向左眼动反应时分别为(260.82±68.40) ms 和(256.33±61.50) ms,快于向右眼动(298.52±96.97) ms和(292.86±92.74)ms; 点阵为大数量 8和 9时,向右眼动反应时为(270.30±69.78) ms和(275.19±73.15) ms,快于向左眼动(277.05±76.49) ms和(292.52±96.27) ms。初步判断点阵数量的大小导致了SNARC效应。为进一步证实在水平方向上对点阵进行浅加工出现了SNARC效应。我们对眼跳反应时进行2 (眼动方向:左、右) × 4 (数量大小:1、2、8、9)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眼动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
(1,30)= 3.03,p
>0.05; 数量大小的主效应不显著,F
(3,30)= 0.90,p
>0.05; 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
(3,30)=5.00,p
<0.01,说明在水平方向对点阵进行较浅程度的加工时,出现了明显的 SNARC效应。浅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左右方向上眼动反应的SNARC效应出现情况见图3。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回归方程显著,F
(1,30)=209.12,p
<0.01,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较好。回归方程为:dRT =47.53-7.00×点阵数目。对平均回归系数-7.00与0进行t
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与 0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t
(30)=-14.46,p
<0.01,说明出现了 SNARC效应。由于平均回归系数小于0,所以对小数量点阵(1、2),向右眼跳与向左眼跳反应时之差为正数,即小数量点阵,向左眼动快; 而对大数量点阵(8、9),向右眼跳与向左眼跳的反应时之差为负,即大数量点阵,向右眼动更快,出现了明显的SNARC效应(见图4)。
图3 浅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水平方向上的SNARC效应

图4 浅加工时数字水平方向上的回归分析图
2.2.2 水平方向上对点阵进行深加工时的SNARC效应
当点阵为1和2时,向左眼动(275.63± 68.60)ms 和(269.29±58.34) ms,快于向右眼动(303.11±96.53) ms和(315.59±98.11) ms; 点阵 8和 9时,向右眼动(281.30±77.07) ms和(271.48±71.53) ms,快于向左动眼(309.29±92.75) ms 和(307.80± 76.37)ms。对眼跳反应时进行 2 (眼动方向:左、右) × 4 (数量大小:1、2、8、9)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眼动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
(1,29)= 0.07,p
>0.05; 数量大小的主效应不显著,F
(3,29)= 0.20,p
>0.05; 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
(3,29)=10.06,p
<0.01,说明在水平方向对点阵进行较深程度的加工时,出现了明显的 SNARC效应。深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左右方向上的SNARC效应,如图5。
图5 深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水平方向上的SNARC效应
回归方程为:dRT =50.17-9.56×数字。t
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与 0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t
(29)=−4.73,p
<0.05,说明出现了SNARC效应。由于平均回归系数小于 0,所以对小数量点阵(1、2),向左眼跳快; 而对大数量点阵(8、9),向右眼跳更快,出现了明显的SNARC效应(见图6)。
图6 深加工时数字水平方向上的回归分析图
我们检验了两个方程回归系数差异,结果不显著,t
(4)=0.2965,p
>0.05,即水平方向上浅加工和深加工条件下两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没有差异,两种加工条件下SNARC效应的大小没有差异。2.3 分析与讨论
在实验一中,无论是对点阵数量进行较浅还是较深程度的加工,被试对水平方向上呈现的提示线索进行左、右方向的眼跳反应后,两种情况下均出现了SNARC效应,SNARC效应的方向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如Dehaene et al.,1993; Bull,Marschark,& Blatto-Valleeg,2005; Fischer,2001; Fischer et al.,2003; 沈模卫等人,2006),说明对点阵进行加工时激活了数字的空间表征,点阵的数量特性与其空间表征发生了自动联合。浅加工条件要求被试仅对点阵进行浏览,由于我们设置的点阵任务较简单,而且本实验所设置的小数量和大数量差别较大(1、2与 8、9),因此被试分辨起来较为容易。在心理数字线上,小数量(1、2)位于大数量(8、9)的左侧,因此本实验中,对于小数量(1、2),当提示线索出现在左侧时,与其在心理数字线上的表征方向一致,向左眼跳会快一些; 当提示线索出现在右侧时,与其在心理数字线上的表征方向相反,向右眼跳会慢一些。对于大数字(8、9),当提示线索出现在右侧时向右眼跳会快一些,而当提示线索出现在左侧时,向左眼跳会慢一些。另外,我们发现浅加工和深加工时所出现的SNARC效应的大小没有差异。因此,实验1证实点阵数量在水平方向上进行空间表征时的SNARC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采用手动方式(Dehaene & Cohen,1997)和眼跳方式(Schwarz et al.,2004)的研究都表明数字的空间表征可能不只存在于水平方向,而且还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在垂直方向也存在着线性表征。数字的空间表征应该是一种数字地图(number map)。在垂直方向上,现有发现认为小数被表征在下方而大数被表征在上方(Schwarz & Keus,2004;Pecher et al.,2011),当小数字出现时向下的反应要比向上的反应快,当大数出现时向上的反应要比向下的反应快。但对于在垂直维度上SNARC效应的方向目前仍存在争论。有研究表明认为垂直方向的表征方向与此相反(Hung et al.,2008; Bae et al.,2009; Fischer et al.,2010),还有研究者得到了水平垂直交替的复杂空间表征(Jarick et al.,2009)。因此,仅仅考察点阵数量水平方向上的SNARC效应是不够的,那么点阵数量这种非符号数字在垂直方向上的表征模式究竟会怎样呢?是否会出现SNARC效应,如果出现,方向会是如何?加工程度对其是否有影响?以及会有怎样的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第二个实验,对垂直方向非符号数字信息的SNARC效应进行探讨,以期对数量的空间表征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3 实验二:垂直方向上点阵数量加工的SNARC效应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被试选取与研究一相同。
3.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分为浅加工任务和深加工任务两部分,均采用 2×2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数量多少(小数量 1、2,大数量 8、9)和提示线索(上方、下方),因变量为眼跳反应时,是指从十字出现到被试做出眼动反应(眼动至相应正方形)为止。3.2.3 实验材料和仪器
实验材料 点阵图片与实验一相同,提示线索为屏幕中间靠近中央点的上方或下方的黑色十字,反应区域为上、下两个小正方形。实验仪器 同实验一。
3.1.4 实验程序
呈现待反应区域为上下方向的小正方形,要求被试当十字出现在上方时向上边的小正方形眼跳,出现在下方时向下方的小正方形眼跳,其它与实验1一样。每个实验共包括12个练习试次和40个正式实验试次。当点阵为小数时,提示线索出现在屏幕上下两侧各为 10次; 同样当点阵为大数时,提示线索出现在屏幕上下两侧的次数也各为 10次。练习和正式实验过程中每个题目的出现顺序采用完全随机化设计,具体的实验流程如图7所示。在提示线索出现后进行上下眼跳反应时记录,记录被试的眼动反应时。
图7 垂直方向点阵数量加工的实验程序
3.1.5 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 12.0对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本实验的数据分析思路与实验1相同。
3.2 结果分析
在浅加工条件下剔除1名注视点大都落在兴趣区外的男生,有效被试为31人。在深加工条件下有2名被试没有理解实验要求,对点阵没有进行反应,还有1名被试的注视点大都落在兴趣区外,我们将其剔除,因此有效被试为29名。将注视点在兴趣区以外的数据剔除后,被试在两种加工条件下的反应正确率为 100%,因此不存在速度和正确率的相互作用。剔除3个标准差以外的反应时数据,最终浅加工条件和深加工条件剔除的数据分别占总数据的10.8%和5.5%。
3.2.1 垂直方向上对点阵进行浅加工时的SNARC效应
当点阵数量为小数(1、2)时,向下眼跳平均反应时,分别为(305.95±71.39) ms 和(318.62±79.92)ms,比向上眼跳平均反应时(292.14±78.89) ms和(288.02±89.70) ms长。当点阵数量为大数(8、9)时,向上眼跳平均反应时分别为(308.31±117.16) ms和(300.06±108.22) ms,向下眼跳平均反应时为(300.39±89.61) ms和(302.30±79.15) ms。对数据进行2 (眼跳方向:上、下) × 4 (数量大小:1、2、8、9)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眼跳方向主效应不显著,F
(1,30)=0.86,p
>0.05; 数量大小主效应不显著,F
(3,30)=0.15,p
>0.05; 两者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F
(3,30)=1.58,p
>0.05,说明在垂直方向对点阵进行较浅程度的加工时,不存在SNARC效应(见图 8)。
图8 浅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垂直方向上的眼跳反应时
回归方程为:dRT=-25.87+3.24×数字。将平均回归系数3.24与0做t
检验,结果发现t
(30)=1.88,p
>0.05,回归系数与 0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即回归分析也显示没有出现SNARC效应(图9)。
图9 浅加工时数字垂直方向上的回归分析图
3.2.2 垂直方向上对点阵进行深加工时的SNARC效应
当点阵数量为小数(1、2)时,向下眼跳平均反应时分别为(306.17±90.27) ms、(314.39±106.21)ms,比向上眼跳平均反应时(273.38±94.71) ms和(289.84±88.89) ms要长。这与SNARC效应现象相反。当点阵数量为大数(8、9)时,向上眼跳平均反应时分别为(268.39±62.87) ms和(278.63±97.22) ms,小于向下眼跳平均反应时(304.20±97.41) ms和(311.65±89.22) ms。总体看来,垂直方向上对点阵数量进行较深程度的加工时,点阵数量的多少没有导致明显的SNARC效应。同样对数据进行2 (眼跳方向:上、下) × 4 (数量大小:1、2、8、9)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眼跳方向的主效应显著,F
(1,30)=9.59,p
<0.01; 数量大小的主效应不显著,F
(3,30)=1.07,p
>0.05; 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
(3,30)=0.11,p
>0.05,说明在垂直方向对点阵进行较深程度的加工时,也没有发现SNARC效应,这一点与我们假设的不一致。深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上下方向上的眼跳反应时如图10。
图10 深加工时不同大小的点阵数量在垂直方向上的眼跳反应时
回归分析的方程为:dRT=−28.07-6.94×数字。将平均回归系数−6.94与 0做t
检验,结果t
(28)=−1.01,p
>0.05,回归系数与0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即没有出现SNARC效应(图11)。
图11 深加工时点阵数量垂直方向上的回归分析图
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差异不显著,t
(4)=1.6525,p
>0.05,说明垂直方向上浅加工和深加工条件下两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没有差异。3.3 分析与讨论
实验二中,在垂直方向上无论是对点阵进行浅加工还是深加工都未出现明显的SNARC效应。浅加工条件下没有出现 SNARC效应,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Fischer et al.,2003; 沈模卫等,2006)。浅加工条件下仅仅要求被试浏览点阵,不需要对点阵数值做直接反应,对数量的加工程度较浅,没有激活数字在垂直方向上的空间表征,可能是因为与水平方向相比,垂直方向的空间表征阈限更高(沈模卫等,2006)。值得注意的是,被试对点阵数量进行深加工时仍没有出现 SNARC效应,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则不一致(Schwarz & Keus,2004; Müller &Schwarz,2007)。我们对部分被试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他们在垂直方向上对数字进行加工时,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将小数字放在垂直方向的最上端,而将大数字放在垂直方向的下端,所以深加工的结果表现为对所有数字来说都是向上眼跳快于向下眼跳,但是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没有出现SNARC效应。我们认为,虽然垂直方向上空间表征的阈限较高,但是对阿拉伯数字进行深加工时,其数量信息与空间表征之间的联结较强,因此会出现垂直方向的SNARC效应。点阵的数量信息与空间表征之间的联结较阿拉伯数字更弱,且在垂直方向上的空间表征激活阈限比水平方向上高,因此当让被试进行深加工时,足够引起阿拉伯数字空间表征的加工却未达到点阵数量空间表征的阈限水平,以致垂直方向对点阵数量信息进行较深加工并没有发现SNARC效应。
4 总讨论
以上两个实验表明,点阵数量在水平方向上出现了 SNARC效应,而在垂直方向上没有出现,且点阵数量的SNARC效应不受加工程度的影响。在实验一中,无论是对点阵数量进行较浅还是较深程度的加工,根据水平方向上呈现的提示线索进行左右方向的眼跳反应,左右方向的眼跳反应时均差异显著,均出现了 SNARC效应。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如Dehaene et al.,1993; Bull et al.,2005;Fischer,2001; Fischer et al.,2003; 沈模卫等,2006),也与心理数字线相吻合。另外,两个 SNARC效应的大小没有差异说明加工程度对水平方向上点阵数量的SNARC效应影响不大。在实验二中,无论是对点阵数量进行较浅还是较深程度的加工,根据垂直方向上呈现的提示线索进行上、下方向的眼跳反应,发现上、下方向的眼跳反应时均差异不显著,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出现SNARC效应。
近年来的行为研究表明SNARC效应出现在反应相关的晚期阶段,随后的电生理研究结果又进一步把数字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定位在晚期的反应选择阶段。Fischer等(2003)发现数字空间表征的自动激活会影响空间注意的转移,但这必须是在刺激呈现后的400~750ms,当延迟期短于400ms或者超过1000ms时,注意转移效果消失。在本研究的两个实验中提示线索均是在点阵出现后600ms呈现的,符合注意转移的时间范围,因此实验一的两种加工程度条下中都出现了SNARC效应,这进一步证实数字对空间信息发生作用的时间是处在中间的反应选择阶段。由于数字的这种空间特性是独立于刺激的呈现形式和反应器的类型,所以在采用眼动进行反应的实验中仍然发现了SNARC效应,但是这与杨金桥等人(杨金桥,仝宇光,李今朝,2010)的发现并不一致,杨金桥等人(2010)在实验中让被试对点阵的大小进行手动反应,结果没有发现SNARC效应。我们认为与手动反应相比,眼动反应作为SNARC效应的行为指标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本研究再次证实了使用眼动技术考察SNARC效应的可行性。
4.1 水平方向的SNARC效应是否受加工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被试对点阵数量进行不同深度加工时的SNARC效应。结果仅在水平方向上发现了SNARC效应,且深加工和浅加工条件下的SNARC效应大小没有差异,这可能与点阵数量本身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加工程度的影响。原因可能是,点阵数量本身具有不同于阿拉伯数字的一些特征。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符号数字,被试无论对阿拉伯数字进行深加工还是浅加工时,主要对其数值数量信息进行编码,只是编码的程度不同。点阵除了具有数值数量(点的个数)这一特征外,还具有非数值数量特征(总面积、密度等)以及非数量特征(颜色、形状),当被试对点阵数量进行加工时,被试除了关注点阵的数值数量,还可能会对点阵的客体特征(颜色、大小、形状、面积、密度等)进行编码(丁锦红,张钦,郭春彦,2010)。阿拉伯数字符号只需一个符号就可以表示一定的数量,而点阵的点数是随着数量的增大而增加的。例如,同样都是“9”这个数量,阿拉伯数字只需要一个符号“9”,而点阵数量则需要空间中分布 9个圆点,点的分布、形状、大小、密度、总面积等视觉客体特征信息是阿拉伯数字所不具备的。结合实验的任务要求,对点阵数量进行浅加工时,要求被试只对点阵进行浏览,此时点阵更可能被知觉为一个整体,除了点阵的数量信息,被试也可能对点阵整体的总面积大小和/或密度进行编码。而已有研究已经表明,除了数值数量(阿拉伯数字、点阵中点的个数),连续或离散的非数值数量(亮度、面积、时间)也存在类似-SNARC效应(胡成林,熊哲宏,2011;Ren,Nicholls,Ma,& Chen,2011; Kiesel & Vierck,2009),其方向与SNARC效应一致。因此,我们推测,被试对点阵进行浅加工时可能同时激活了对点阵的总面积和/或密度等非数值数量的空间表征,从而引起了类似-SNARC效应,由于类似-SNARC效应与 SNARC效应方向一致,因此,浅加工时点阵的SNARC效应的削弱并不明显。而深加工条件下,被试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被试除了关注点阵所表征的数量,一些与数量信息无关的视空间客体特征信息也得到了自动加工(颜色、形状等)。而已有研究证明,在对数字进行视空间表征的加工时,工作记忆的视空间成分起到了重要作用,视空间信息的保持需求导致 SNARC效应的消失(Herrera,Macizo,& Semenza,2008)。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深加工条件下由于被试对点阵的客体特征进行编码,占据了原本用于数量加工的有限的认知资源,也就是说被试虽然可能比浅加工条件下投入了更多注意资源,但是这些注意资源并没有全部用于数量表征,反而被客体特征信息所占用,并且这些无关信息的表征会对数字-空间联结的激活具有一定干扰作用。因此,进行深加工时,被试对与数量信息无关的点阵其它特征的注意削弱了对点阵数量的表征强度,从而削弱了 SNARC效应。总之,加工程度和点阵数量两者共同导致了实验一水平方向上两个SNARC效应的大小不存在差异。
4.2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SNARC效应的比较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的点阵 SNARC效应,结果水平方向出现了 SNARC效应,而垂直方向上没有出现,SNARC效应在水平方向上具有优势。这符合Holmes和Lourenco (2011)最近提出的观点,即数字在水平方向的表征强于垂直方向。在水平方向对点阵进行浅加工和深加工时,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点阵数量都在 10以内,而且都是规则排列,因此很容易激活点阵在心理数字线上的空间表征,出现了显著的SNARC效应。可以认为,在垂直方向上之所以没有出现SNARC效应,可能与该方向上数字信息的空间联结较弱有关。受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人们获得了更多在水平方向上对数量进行表征的机会,因此数字数量在水平方向上的空间表征激活阈限较低,而垂直方向上的阈限相对较高。当对点阵数量进行加工时,仅能激活数量在水平方向的空间表征,而无法激活其在垂直方向上的表征,因此在垂直方向对点阵进行加工时没有出现SNARC效应。
数字的空间表征是否还与点阵有关呢?已有证据表明阿拉伯数字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存在SNARC效应(Dehaene,1993; Müller & Schwarz,2007; Holmes & Lourenco,2011)。而对于其它数字符号,更多的是对其水平方向SNARC效应的进行考察(Nuerk et al.,2005; Dodd,Van der Stigchel,Leghari,Fung,& Kingstone,2008),尚未见到关于垂直方向SNARC效应的证据。而本研究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对点阵数量的SNARC效应进行了考察,发现与对阿拉伯数字进行加工所得的结果不同,即使是在深加工条件下,垂直方向上也没有出现点阵数量的SNARC效应,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垂直方向上数量-空间表征的阈限高于水平方向,二是由于点阵数量本身的数字-空间联结强度比阿拉伯数字弱,因此垂直方向上没有出现SNARC效应。正如我们上面讨论中所提到的,深加工时点阵数量本身的客体特征会干扰其数量表征,使得其SNARC效应相较于阿拉伯数字更弱。而水平方向上,点阵数量虽然对其具有一定削弱作用,但是由于数量在该方向上的空间联结强度较强(Holmes &Lourenco,2011),因此对点阵进行较深程度的数量加工时激活了空间表征,在水平方向上出现了SNARC效应。
水平方向的SNARC效应证实了心理数字线的存在,但是“垂直方向没有发现 SNARC效应”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否定心理地图。仅凭点阵数量垂直方向上的SNARC效应研究结果来否定心理地图是不合理的,毕竟已有的阿拉伯数字的研究支持了心理地图的观点。我们推测,数量的空间表征可能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性。总之,是否出现SNARC效应以及 SNARC效应的大小及方向与符号有密切关系。对于点阵数量,方向维度在其SNARC效应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深加工还是浅加工,水平方向都出现了 SNARC效应,且效应的大小没有差异,而在垂直方向上都没有出现SNARC效应。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加工程度影响其它形式数字的 SNARC效应,因此本研究观测到的是数量形式、方向维度和加工程度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因此,(1)点阵数量本身的特性使得其SNARC效应的稳定性不如阿拉伯数字; (2)二维方向影响点阵数量的 SNARC效应,加工程度对SNARC效应的影响受到了点阵符号本身特征的影响。这些发现为从不同数字符号形式和空间维度角度理解SNARC效应乃至数字的空间表征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 SNARC效应的其它特性提供了可能。在今后研究中,应进一步对不同数字形式在不同方向的 SNARC效应进行联合探讨,以便更加直观地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另外,今后的研究还需注意到:(1)相比于要求被试直接根据数量信息进行反应,本研究无论是对点阵数量进行深加工还是浅加工,被试的反应方向都是由“+”所在的位置而不是由数量信息决定的,即数量加工和眼动反应任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的反应方式可能导致得到的 SNARC效应会弱一些。因此,本研究对垂直方向点阵数量空间表征的讨论是在特定任务前提下展开的。而对于直接对点阵数量信息进行反应时是否能出现垂直方向SNARC效应及是否受加工程度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2)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除了水平方向和垂直于水平面的垂直方向,还有一个同时垂直于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维度,即远近维度,已有研究发现了远/近维度的SNARC效应(Santens & Gevers,2008),小数字与靠近身体的一侧相联系,大数字与远离身体的一侧相联系,今后的研究可以结合这三个空间维度,考察更复杂的三维的数字-空间表征联结。(3)本研究采用点阵这种非符号数字形式来研究SNARC效应,由于关于点阵数量的已有研究较少,在点阵的形式上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中采用了较为规范的点阵形式,如果采用不规则的点阵,SNARC效应会不会有所不同。另外,如果要进一步明确点阵符号本身特征对 SNARC效应的影响,仅仅单独对点阵数量进行考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研究中直接将点阵与其它符号数字进行对比,这些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进行进一步探讨。
Bae,G.Y.,Choi,J.M.,Cho,Y.S.,& Proctor,R.W.(2009).Transfer of magnitude and spatial mappings to the SNARC effect for parity judgmen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35
(6),1506–1521.Brysbaert,M.(1995).Arabic number reading:On the nature of the numerical scale and the origin of phonological recod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24(4),434–452.Bull,R.,Marschark,M.,& Blatto-Valleeg,G.(2005).SNARC hunting:Examining number representation in deaf students.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
(3),223–236.Calabria,M.,& Rossetti,Y.(2005).Interference between number processing and line bisection a methodology.Neuropsychologia, 43
(5),779–783.Cappelletti,M.,Freeman,E.D.,& Cipolotti,L.(2007).The middle house or the middle floor:Bisect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ental number lines in neglect.Neuropsychologia,45
(13),2989–3000.Dehaene,S.(2003).The neural basis of the Weber-Fechner law:A logarithmic mental number line.Trends in Congitive Sciences,7
(4),145–147.Dehaene,S.,Bossini,S.,& Giraux,P.(1993).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parity and number magnitud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22
(3),371–396.Dehaene,S.,& Cohen,L.(1997).Cerebral pathways for calculation:Double dissociation between rote verbal and quantitative knowledge of arithmetic.Cortex,33
(2),219–250.Dehaene,S.,Tzourio,N.,Frak,V.,Raynaud,L.,Cohen,L.,Mehler,J.,& Mazoyer,B.(1996).Cerebral activations during number multiplication and comparison:A PET study.Neuropsychologia,34
(11),1097–1106.Ding,J.H.,Zhang,Q.,& Guo,C.Y.(2010).Cognitive psychology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丁锦红,张钦,郭春彦.(2010).认知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odd,M.D.,Van der Stigchel,S.,Leghari,M.A.,Fung,G.,& Kingstone,A.(2008).Attentional SNARC:There’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numbers (let us count the ways).Cognition,108
(3),810–818.Eagleman,D.M.(2009).The objectification of overlearned sequences:A new view of spatial sequence synesthesia.Cortex
,45
(10),1266–1277.Feigenson,L.,Dehaene,S.,& Spelke,E.(2004).Core systems of number.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7),307–314.Fernández,S.R.,Rahona,J.J.,Hervás,G.,Vázquez,G.,&Ulrich,R.(2011).Number magnitude determines gaze direction: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in a free-choice task.Cortex,47
(5),617–620.Fias,W.(2001).Two routes for the processing of verbal numbers:Evidence from the SNARC effect.Psychological Research,65
(4),250–259.Fischer,M.H.(2001).Number processing induces spatial performance biases.Neurology,57
(5),822–826.Fischer,M.H.(2003).Spatial representations in number processing-evidence from a pointing task.Visual Cognition,10
(4),493–508.Fischer,M.H.,Castel,A.D.,Dodd,M.D.,& Pratt,J.(2003).Perceiving numbers causes spatial shifts of attention.Nature Neuroscience,6
(6),555–556.Fischer,M.H.,Mills,R.A.,& Shaki,S.(2010).How to cook a SNARC:Number placement in text rapidly changes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s.Brain and Cognition,72
(3),333–336.Fischer,M.H.,& Rottmann,J.(2005).Do negative numbers have a place on the mental number line?Psychological Science,47
(1),22–32.Fischer,M.H.,Warlop,N.,Hill,R.L.,& Fias,W.(2004).Oculomotor bias induced by number perception.Experimental Psychology,51
(2),91–97.Gevers,W.,Reynvoet,B.,& Fias,W.(2003).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ordinal sequences is spatially organized.Cognition,87
(3),B87–B95.Herrera,A.,Macizo,P.,& Semenza,C.(2008).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 magnitude and space.Acta Psychologica,128
(2),225–237.Holmes,K.J.,& Lourenco,S.F.(2011).Horizontal trumps vertical i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numerical magnitude.In L.Carlson,C.Hölscher,& T.Shipley (Eds.),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pp.2276–2281).Austin,TX: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Hu,C.L.,& Xiong,Z.H.(2011).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continuous properties of stimuli:Evidences from the SNARC-like effect of area and luminance.Psychological Science,34
(1),58–62.[胡成林,熊哲宏.(2011).刺激模拟量的空间表征:面积和亮度的类SNARC效应.心理科学,34(1),58–62.]
Hung,Y.H.,Hung,D.L.,Tzeng,O.J.L.,& Wu,D.H.(2008).Flexible spatial mapping of different notations of numbers in Chinese readers.Cognition, 106
(3),1441–1450.Ito,Y.,& Hatta,T.(2004).Spatial structure of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s:Evidence from the SNARC effect.Memory and Cognition,32
(4),662–673.Jarick,M.,Dixon,M.J.,Maxwell,E.C.,Nicholls,M.E.R.,&Smilek,D.(2009).The ups and downs (and lefts and rights)of synaesthetic number forms:Validation from spatial cueing and SNARC-type tasks.Cortex,45
(10),1190–1199.Kiesel,A.,& Vierck,E.(2009).SNARC-like congruency based on number magnitude and response dur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 35
(1),275–279.Liu,C.,Mai,X.Q.,& Fu,X.L.(2004).The 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 effect of number processing in different attention conditions.Acta Psychologica Sinica,36
(6),671–680.[刘超,买晓琴,傅小兰.(2004).不同注意条件下的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心理学报,36(6),671–680.]
Lorch,R.F.,& Myers,J.L.(1990).Regression analyses of repeated measures data in cognitive research.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16
(1),149–157.Müller,D.,& Schwarz,W.(2007).Is there an internal association of numbers to hands? The task set influences the nature of the SNARC effect.Memory and Cognition,35
(5),1151–1161.Nuerk,H.C.,Wood,G.,& Willmes,K.(2005).The universal SNARC effect: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 magnitude and space is amodal.Experimental Psychology,52
(3),187–194.Pecher,D.,Boot,I.,& van Dantzig,S.(2011).Abstract concepts:Sensory-motor grounding,metaphors,and beyond.In B.Ross (Ed.),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pp.217–248).Burlington:Academic Press.Ren,P.,Nicholls,M.E.R.,Ma Y.Y.,& Chen,L.(2011).Size matters:Non-numerical magnitude affects the spatial coding of response.PLoS ONE,8
(6),e23553.Rusconi,E.,Bueti,D.,Walsh,V.,& Butterworth,B.(2011).Contribution of frontal cortex to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Cortex,47
(1),2–13.Santens,S.,& Gevers,W.(2008).The SNARC effect does not imply a mental number line.Cognition,108
(1),263–270.Schwarz,W.,& Keus,I.M.(2004).Moving the eyes along the mental number line comparing SNARC effects with saccadic and manual responses.Perception &Psychophysics,66
(4),651–664.Shen,M.W.,Tian,Y.,& Ding,H.J.(2006).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one-digit Arabic numbers.Psychological Science, 29
(2),258–262.[沈模卫,田瑛,丁海杰.(2006).一位阿拉伯数字的空间表征.心理科学,29(2),258–262.]
Wood,G.M.O.(2005).Neuronal and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attentional and automatic semantic number process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RWTH Aachen University.Yang,J.Q.(2009).The impact of verbal information on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verbal numbers.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Education Edition)
,32
(2),52–56.[杨金桥.(2009).言语信息激活对中文数字空间表征的影响.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32(2),52–56.)]
Yang,J.Q.,Tong,Y.G.,& Li,J.Z.(2010).Symbol satial representation can not be activated by magnitude 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30
(10),45–49.[杨金桥,仝宇光,李今朝.(2010).数量信息不能引发符号的空间表征.心理学探新,30(10),45–49.]
Zorzi,M.,Pritfis,K.,& Umiltà,C.(2002).Brain damage:Neglect disrupts the mental number line.Nature,417
(6885),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