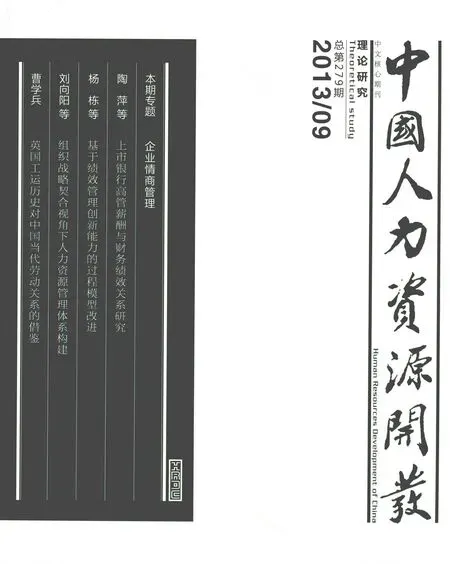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 程永宏 张翼
■责编/韩树杰 Tel: 010-68345891 E-mail: hrdhsj@126.com
据报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直到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发出了《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酝酿了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才终于出台。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经历这么长时间才最终出台,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究其原因,除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之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影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也将影响已经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
一、收入分配制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根据顾自安(2010)的观点,从制度指向的客体来看,制度可以划分为六个不同层次:针对最基本的个人行动者的制度;针对更为抽象和更“社会化”的社会角色的制度;针对社会群体(利益集团)的制度;针对机构和组织的制度;针对各类职业技术行为和技术系统的制度;针对最抽象的、最复杂的客体——社会系统、社会秩序或广义社会行为的制度。
根据上述的制度分类方法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制度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有些制度通过若干法律条文即可确立,如针对个体行为的婚姻法、公司法等。有些制度则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不是体现在几部具体的法律或政策条文当中,如针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秩序的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显然就属于后者,它规定了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规则,但却无法完全体现在任何一部具体的法律文件当中。实际上,收入分配制度是由一系列更低层次的具体制度构成的综合性制度。一切影响到个人收入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项具体制度都构成收入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是收入分配制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与要素市场有关的一切制度都会对初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都构成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就业相关法律决定了各类劳动力所有者获得收入的机会,其中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制度决定了中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最低工资制度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经理人市场的相关制度则决定了高收入阶层的职业经理人收入水平。又比如,资本市场的相关制度决定了资本所有者获得收入的机会,其中某些金融市场制度决定了市场利率,这对资本借贷双方的成本、利润和收益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同样地,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与再分配有关的一切制度都会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欧洲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社会保障税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的北欧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都较低,相反,社会保障税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的其他欧洲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都较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个人所得税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市场初次分配的结果,它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决定了一国政府可以用于转移支付的财政收入水平。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除了上述的就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制度对收入分配状况存在重要影响,还有其他各种复杂因素参与塑造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
首先,各种形式的腐败本质上都会表现为权力寻租,腐败官员在牺牲国家利益的同时,自身获得了巨额的腐败收入,也让从事贿赂以获取政府权力资源的企业和个人获得了巨额的非法收入,从而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最近几年,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中,腐败官员的腐败收入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亿元、几十亿元。这些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巨额收入对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各种不平等指数的共同特征,因为各种不平等指数本质上度量的恰恰是极少数人占有巨额财富的程度,是非法收入造成巨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形式之一。
其次是各种灰色收入。例如个体私营经济利用收入监控和收入申报制度方面的漏洞,采取各种隐瞒收入、逃避纳税的手段,导致初次分配形成的巨大差距不能在再分配制度下得到应有的改善。还有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等行为,也都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
第三,中国市场化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擅自越权出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导致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私人资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无需任何成本和贡献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摇身一变成为合法资产的所有者。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中揭露的侵吞国有资产现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国人的收入差距。
第四,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由于市场竞争、机会、个人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个人在市场竞争制度下获得的合法收入的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发达国家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活力的同时,都有完善的再分配手段缩小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但中国这方面的制度相当不完善。
第五,其他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也会造成明显的收入差距。例如,沿海开放地区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中东部地区收入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些现象都是国家特殊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导致的收入差距。此外,特殊的产业政策、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等,也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差距。
综上所述,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相应地,影响收入分配状况的制度可以归结为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由此可见,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制度因素非常复杂,几乎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都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状况,都是收入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复合性的制度,它可以分解为多种更为具体的制度。因此,相应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就不可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这种形势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实质性地降低收入差距,可能是难以如愿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历经八年,几易其稿才能够勉强出台。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更多更具体的配套方案,发改委的这一改革方案很难实质性地改变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
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和目标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
既然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抽象性,那么要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首先明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收入分配制度的综合性和抽象性,决定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不是一两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而是所有与收入分配状况有关的具体制度的集合。
这里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概念加以澄清。实际上,“收入分配”对应的英文是income distribution,它可以被译为“收入分配”,也可以被译为“收入分布”,意指收入在一定人口中的分布状况。把income distribution译为“收入分配”显然是受了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存在一个权威当局,它可以把国民收入在全体国民之间进行某种指令性的“分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权威当局,有权利、有能力对国民收入进行这种指令性分配;相反,市场机制取代权威当局,将国民收入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自发地进行初次“分配”,政府至多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手段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进行调节,但不可能进行指令性的“分配”。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不可能由政府进行“分配”的。
既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不可能由政府进行“分配”,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显然就不是某个独立存在的、可以由政府随时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而是一系列与收入分配状况有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集合。这显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方案所能涵盖的,而必须对所有与收入分配状况有关的具体制度进行改革。
具体地说,当前需要特别关注的改革对象包括就业制度、工资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司制度等等。其中,就业和工资制度改革应该确保所有人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就业者获得合理的、合乎公平原则的报酬,这对于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有效率至关重要。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确保中国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显著的再分配功能,特别要确保这两个重要的再分配手段不出现逆向再分配效应,这对于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严重不平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司制度的改革应该立足于防止国有企业高管借年薪制等理由,无节制地提高自身报酬、将个人收入转嫁到企业成本,也应该防止非公有制企业隐藏实际收入、逃避纳税和社会保险缴费等行为。
2.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
刚刚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这些目标有些是高度抽象的原则性要求,有些是政府早已提出的努力目标,有些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制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不能进一步量化,则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很可能流于形式或半途而废。
所幸的是,收入差距是一个可以严格测量的变量,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指标可以测量它,最常见的就是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必须设定在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的某个水平上,即给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不能笼统地以“明显改善”、“趋于合理”、“逐步缩小”这类模糊不清的描述作为目标。
那么,多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没有严格的标准。但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同意0.4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徐宽,2003)。胡祖光(2004)则根据消费梯度理论给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最优不平等水平的标准是:基尼系数等于0.3333。纵观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可以发现大多数低于0.4,唯一超过0.4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美国。因此,中国把基尼系数低于0.4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以“公平分配”作为初次分配的基本原则,以“平等与效率达到最佳组合”作为再分配的基本原则。国内理论界对“公平”与“平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或相互颠倒(刘晓靖,2009)。国外学术界在50年代以前也存在这种概念上的混乱(Raphael,1946),但50年代以后的英文文献中基本上纠正了这个倾向。所谓“公平分配”,按照Varian(1974)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指没有嫉妒的收入分布状态,即所有人的收入与其贡献成比例。所谓“平等分配”,是指所有人的收入都相同,无论其贡献和努力程度如何。可见,公平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例如当个人的才能、禀赋条件差别特别大时,公平的分配必然是高度不平等的;同样地,平等的分配可能是不公平的,例如当个人的努力程度差别特别大时,平等的分配必然是高度不公平的,这就是所谓的“平均主义”分配。
初次分配以公平为基本原则,这是与维护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相一致的:只有按贡献分配,即公平的分配,才可能有效率;在一定的条件下,公平分配就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分配。既然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的,那么政府的政策保持公平的初次分配显然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公平分配的定义意味着与个人贡献无关的因素都不应该对个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例如垄断、权力、区域、城乡属性、性别属性等等。保持初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就要求消除垄断、权力、城乡属性、性别属性等等与贡献和努力程度无关的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
再分配要以“平等与效率达到最佳组合”为基本原则,是因为追求最终收入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可能对效率产生影响,即平等与效率往往是互相冲突的目标:过高过低地追求平等会降低效率,过高地追求效率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抉择。(阿瑟·奥肯,1987)。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也列举了23条具体的改善收入差距状况的措施,分别作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这些措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枚举的方式显然不能穷尽所有与收入分配制度相关的具体制度。因此,还需要设计覆盖所有相关具体制度的可操作性措施,才能实质性地降低中国收入差距。
总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本身,而是对整个经济体制和制度进行全面调整的改革。
1.Raphael, D. Daiches, 1946, Equality and Equity, Philosophy. Vol. 21, No. 79. (Jul.,1946), pp. 118-132.
2.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个重大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4.徐宽:《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在过去八十年是如何拓展的》,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5.郎咸平:《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 http://finance.sina.com.cn/t/20040816/12029515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