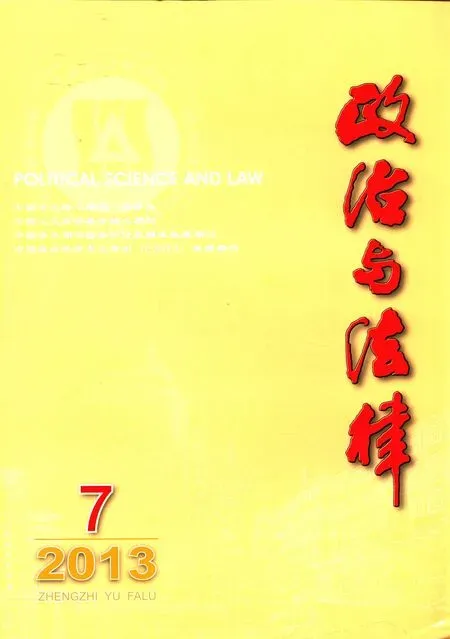论合规药品致害之国家责任*——基于合规药品致害的民事和行政救济的局限之展开
杜仪方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23)
2013年新年伊始,新华每日电讯以《找病的马兜铃科草药》为题刊发方舟子博文《一大类可怕的草药》,直揭以马兜铃科草药为原料所制药品的严重危害,将本已沉寂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再次推入公众视野。1龙胆泻肝丸事件源于2003年2月新华社记者朱玉的报道《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该报道证实,传统中药龙胆泻肝丸即使正常服用也会造成肾损害。后经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记载的龙胆泻肝丸配料中的“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而马兜铃酸可导致肾病。2003年4月4日,国家药品监管局正式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2003年3月起,有超过170多名受害患者将作为龙胆泻肝丸生产商之一的同仁堂告上法庭,要求给予损害赔偿。而同仁堂认为,药厂是按照药典合理合法生产的,其已对消费者尽到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药典委员会应该承担责任。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相关诉讼最终都败诉、被法院驳回或不予受理。2
透过龙胆泻肝丸事件不难发现,上述药害的产生并非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合格药物的副作用所导致。一方面,药品完全符合药品标准的相关规定,但另一方面,药品本身的缺陷却又确实存在。该情形明显有别于药品因未被发现的内在缺陷或者因患者的特异体质而产生的药品副作用,因此无法适用一般情形下药品不良反应的损害赔偿模式。3为表述方便,本文暂且用“合规药害”指代这一类药品损害。值得重视的是,龙胆泻肝丸事件也并非是极小概率事件。在《药典》的修订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药品标准得到了修改。若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新标准的制定至少可以说明原药典中所记载的标准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改良空间。从这一层面而言,龙胆泻肝丸的悲剧绝不会成为偶然事件。从公共政策或社会正义的角度观之,受损害者获得补偿,应是社会追求的正面价值。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能兼顾损害填补与经济效率的需求,一直是整个损害赔偿法制所追求的机能。那么,问题就转换为,对于上述合规药害的损害应如何弥补,谁又能为此负责?
一、合规药害民事救济之可能性
当出现药物损害后,寻求药物制造者的责任无疑是相对最为便利的救济途径。药物制造者是药物产销流程之源头,从理论上而言其与药害的法律关系最为密切;同时,药品制造者往往财力相对雄厚,从保障相对人的角度出发也应将其作为求偿对象。4因此,民事侵权责任似乎就成为最为直接和便利的救济方式。但是,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一)规范法学的进路
首先需要寻求民事救济在规范层面的依据。《药品管理法》第93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药品致害赔偿责任必须以违反规定为条件。而就药品质量本身而言,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第59条,即如果药品由于存在缺陷而致害,那么药品生产者将责无旁贷。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药品存在缺陷,换言之,究竟何为药品缺陷呢?《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而在药品领域,《药品管理法》第32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该法第48条规定:“当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为假药。”地方立法层面,以《药品管理法》及该法的实施条例为基础,各省、市都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但是基本没有对药品缺陷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由此,从立法角度而言,所谓缺陷,就是违反各级药品监督部门所制定的药品标准,而合规药害显然不在此列。
通过上述法规梳理,我们只能够得出以下阶段性结论:当药品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时,可以被认定为缺陷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侵权责任成立。但当药品生产者遵守药品标准时,是否可以以不存在缺陷作为抗辩事由从而不承担侵权责任,现行法律却没有给出答案。当立法失语,留给学界的任务就是理论先行。此时的研究话题可被界定为:对于合规药品造成的损害,是否应追究民事侵权责任?
(二)合规侵权致害的理论维度
1.概述
对于合规侵权致害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相对成熟的研究。5为寻求理论与实践的最佳契合点,现有对于合规致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侵权领域,将研究重点置于获取排污许可或者符合污染排放标准的行为而导致的污染损害。在以环境领域为例证的合规侵权研究中,相关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合规即可以免除民事侵权责任,这一观点的依据是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该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如果对上述条文进行文义解释,则意味着环境噪声如果符合法定的噪声排放限度,就不构成立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即使造成损失也无法寻求该法所规定的赔偿责任。
第二类观点是完全不考虑是否存在合规情节,认为行为人只要给他人带来损害并由此获得了利益,就应对该不利结果负责。其基于传统侵权归责原则中的“结果归责”,出于填补损失的需要而不问原因对加害者课以责任。“事故是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获得利润就应对由此而形成的风险负责……事故的责任应当加到从事这种危险活动的人的身上”。6《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印证了这一观点。
第三类观点认为当行为遵守行政机关所确立的基准,其所造成的损害虽不能免除行为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将合规情节作为是否能够免除责任或者影响责任承担的因素之一。此类观点将关注重心落于规则本身,规则本身的性质将影响到责任的存否和程度。合规行为仍需承担责任的原因主要有:规范本身不具有妥当性;规范所设定的义务不是以保护人为目的的义务;侵权行为违法性中的违法并不限于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包括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的违反等。当然,也有学者从公法私法分立的角度论述合规不免责的法理基础:立法者在制定公法规范或者标准时只是从公法的角度衡量,既无暇也无力仔细考量其民事效果,对于公法规定在私法领域的具体适用,如何与私法自治的价值适度调和等问题都还未作决定。7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比较,笔者认为,相较于前两类观点而言,第三类观点显然更为合理。将合规情节作为免除责任的必然藉口显得过于绝对,这不仅与公法私法二元体系相矛盾,也不利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与之相对,如果不考虑合规情节而单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结果责任原则更能使其所受损失得到救济,但是毕竟纯粹基于受害者立场有失公允。在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合理分担损失已成为当今侵权赔偿制度的主流,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某些个体的受损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可能是一种必需。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很多公共风险,无论他们有多么危险,事实上比所要消除这种风险更为安全或者有益,那么就要竭力对其成本最小化”。8这一观点在环境污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环境污染如同影子一般常伴工业文明左右时,合规排污正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因此,此时如一味追究合规企业的侵权责任就显得过于苛刻。“试图让合规行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显然是混淆了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的界限,这样做并不会减少风险,相反,却可能会增加事故,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9但是即便如此,在出现合规侵权时也无法完全免除侵权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合规只能作为抗辩的情节之一。按照通说,侵权行为主要构成要件为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违法性和过错,而合规情节正是当事人过错程度的其中一种体现。
上文以环境领域为例对合规致害的论述可以概括为:抛弃完全不考虑违法与过错要件的“结果责任”,肯定“合规”情节与侵权责任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合规并非意味着免责,合规可以作为考量注意义务的因素之一对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
2.药品领域中的合规致害
在药品侵权领域,基于与环境领域侵权类似的推演,有学者认为,制药方无法因合规而免于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因为遵守药品标准只是产品符合行政规范的根据,并不是说产品就不构成“缺陷”,因此这不能构成免除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具体原因在于,药品标准的选取有诸多考量因素,其不能包含一切安全性能指标,并且标准往往只是给予一般性的制约,其也无法去把握和斟酌每个侵权个案所涉及的个别因素,与此同时,药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初衷并非着眼于侵权案件的解决。对于符合标准的行为是否会引发侵权责任,需要对相关的诸多因素和利益进行综合的衡量。10该推演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却忽视了基本前提,即参照领域的同一或相似性。事实上,合规行为在侵权法上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效力,而是随着领域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效力,甚至在相同的领域中也有不同的效力。虽同属合规致害,但与环境合规污染相比,合规药物致害却存在自身特性。
首先,环境领域与药品领域的规范本身性质不同,即“规”不同。在环境领域,污染一旦被排放势必会引发损害,而这种损害的发生却又是工业化进程所不可避免的产物。尽管确立排污标准是试图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点,但是符合排污标准只是在侵权的前提下降低损害。换言之,环境领域的排污虽以经济发展这一公共利益为目的,但污染排放为个体带来的损害毕竟是负面效应,而且这种损害是排污行为人可预见甚至可期待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污染排放的“规定”只是对于负面效应的一定程度的减轻,合规并不能改变“规”本身的负面效应。而在药品领域,虽然时有副作用的发生,但无论是对于公众还是个体而言,药品的整体存在和个体适用都只是为了能够治病救人这一正面目的,损害的发生并非药品本身所希望达成的效果。而药品标准更是基于规范药品质量而产生,是对药品正面目的的进一步加强,“规”本身当然是正面的。
其次,环境领域与药品领域合规的方式不同,即“合”亦不同。在环境侵权领域,行政规则所制定的标准往往只是行政机关基于整体控制而确定的最低标准,违反标准将可能招致行政处罚,遵守标准则只是履行了底线的注意义务。对于排污者而言,合规排污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依然要设法减少污染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就是说,此类技术标准规定的只是一个具有“可接受性”的而非“安全”的阈值,它所给予的是一个一般性的控制,它不可能也无法去把握和斟酌每个侵权个案所涉及的个别因素,因此它对于个案正义是无能为力的。11对于个案中加害行为的责任判断不仅要考虑到合规情节,更要综合考虑其他影响到过错程度的注意义务。与之相对,药品标准彰显的则是另外一种价值。药典所规定的药品标准对药品制造商而言必须遵循且不具有任何判断余地。为确保标准的实效性,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施以行政处罚、拒绝许可方式对制药企业予以控制。例如《产品质量法》第7条对于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规定了行政处罚;在药品领域,对于生产经营不符合药品标准的企业,可以根据《药品管理法》吊销其许可证。更为严厉的是,我国《刑法》第141条、第142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而其中“假药”、“劣药”的概念就是指《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1款规定的成份、含量或者其他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因此,对于药品制造商而言,在药品管理行政机关所确定的标准之下不存在任何判断余地,对标准的遵守就可以认为尽到了注意义务。
基于规范法学进路,规范即技术标准分类所遵循的依据是《标准化法》第7条,根据是否需要强制执行可将技术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只是鼓励企业自愿采用。《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18条将药品标准、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等明确作为强制性标准,对于标准规定的内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或者“禁止”违反,而对于违反标准的行为可被施以处罚。尽管同属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标准,但不同的强制性标准的强制程度有所不同。对于以药品标准为代表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标准的规定,没有选择余地,即在一个加害行为中,加害者即使存在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三项要件,但可基于遵守精确性强行标准而排除其过错,从而允许加害人作遵守标准的抗辩;而对于以排污标准为代表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遵守限制性强行标准只是遵循了必要的底线条件,因标准本身具有开放性,要实现免责还需要在合规前提下,实现最佳合规,即尽到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符合标准仍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的,“合规”就不能作为排除侵权责任的正当理由,最多只构成从轻或者减轻责任的酌情考虑因素。更进一步说,前一种强制性标准规定的是精确适用标准,后一种则仅给出了标准的强制适用范围。正基于此,将合规药品致害与环境污染致害置于同一合规致害的逻辑维度中就会存在局限性。在合规药物致害中,符合规定而制造药物致害应有别于获得一般药物许可而导致的药品不良反应致害,后者可以认为行政法规规定的仅是最低标准,制药商不可以以获得政府许可而为抗辩。12
(三)小结
再回到龙胆泻肝丸事件。当《药典》或者药品标准在成分的记载上出现了差错时,即使制药商已经发现木通类中药材在其他国家早已因其对肾脏的危害而被禁止进口,或者也意识到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患尿毒症的病例已经存在,但是基于对生产“假药”的恐惧,制药商也不可能违反相关药品规定而擅自更改配方以实现其“注意义务”。13对药品标准这一精确性的强制性标准而言,合规而生产药品的制药企业只有完全符合规定才可以免除行政甚至刑事责任,而完全符合规定也可被认为已经尽到了完全注意义务。由于在一个侵权过程中缺乏违法性要件,制药企业的民事赔偿责任无从履行。
有损害必有救济这句古老的法谚至今流传。然而,在合规药品致害领域,民事赔偿对损害的救济显然已无能为力。此时,就要将视角转向行政救济。既然制药企业基于符合药典的规定而被免除民事侵权责任,那接下来的追问就是:制定药品标准的行政机关是否存有过错?或者说,是否存在寻求行政赔偿或补偿之可能性?
二、合规药害行政救济之可能性
(一)行政法视野中的药品标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颁布和执行〈中国药典〉2005年版有关事宜的通知》指出:“《中国药典》是执行《药品管理法》、监督检验药品质量的技术法规;是我国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所必须遵循的法定依据”,是“国家为保证药品质量、保护人民用药安全有效而制定的法典”。显然,将《药典》称为“法典”是言之过甚。与其他领域的标准一样,《药典》是由行政机关即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药典委员会制定和修订,并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标准化法》所规定的强制性技术标准。我国行政法学界习惯将制定行政规范的行政活动(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大类: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14而从药品标准文本公布、刊登和编纂形式等来看,其确实都与《立法法》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尽相同,从而可将其排除于法律规范之外。15因此,药品标准应属于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或借鉴大陆法系的一般概念而称之为行政规则。16
虽然其不具备法律规范的外形,但是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却往往将药品标准作为事实认定构成要件判断的根据,并根据事实认定的结果作出是否给予许可甚至处罚的决定。换言之,尽管药品标准从形式上不属于法律规范,也不是通过法律条文来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但是它通过设定量化的数值、指标等直接药品配方和工艺流程,通过行政机关对技术标准的反复适用,对法律概念作出了解释,对行政裁量权运作形成了自我拘束;同时,通过行政机关采取的一系列后续确保标准实效性的手段,从而间接地为私人规定了权利义务,对私人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17因此,可以认为以药典为代表的技术标准是一种具备了外部效力的行政规则,并更接近于解释性行政规则。18
(二)合规致害的行政赔偿责任
1.规范法学的进路
如上所述,可以认为药品标准属于行政规则。《国家赔偿法》虽然并未将行政规则列为排除范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该规定以法院不受理的方式事实上将公民对于行政规则赔偿诉讼请求排除在外。法院对于针对行政规则的行政赔偿案件是慎之又慎,实践中也尚无一例判决。19
2.理论层面的梳理
在学理上,行政规则本身一直不被认为是行政赔偿的免责事项。20因此,只要能够证明规则存在错误或者不当,并且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确有因果关系,那么基于行政责任基础理论,具备了外部性的行政规则就难逃赔偿责任。但是,药典存在错误或不当是否就必然等同于行政机关存有违法或者过错呢?
不可否认,药品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产品,为求药物使用之效益,常须容忍相当之危险存在。因此寄希望于国家严格管理以完全防止事故发生实属不能,而国家药物标准也只是在药品有害性和有用性之间所寻求的一种平衡,以实现药品整体的可控性。同时,即使已经进行了充分试验,药物的有害性仍可能在长期潜伏后才发作。因此,如果确实是鉴于科技水平滞后或者市场资讯不灵而产生错误标准,且行政机关已经就药物有效性、安全性及公益性作了全面判断,此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内可适用行政裁量,从而无法认定其行为存在违法或者过错。《药典》五年一次的修正,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因应五年里美国药典(USP)、英国药典(BP)以及日本药局方(JP)等国外先进药品标准的进展,以及我国药品分析和检验技术的发展。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一定时间段中即使药典出现问题,也应由于缺乏违法要件而排除行政赔偿。21
当然,裁量权的存在并不当然意味着行政绝对免责。基于宪法上国家对于公民的安全保障义务,当有证据表明行政机关制定标准的当时或在标准制定后已发现药品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就可基于行政机关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认定其行为违法,并由此要求其承担行政责任。从日本轰动一时的一系列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案中,可以探寻行政机关在药品行政中所应担当的角色。法官在京都的有关判决中认为,当药品安全性可能影响到国民的生命、健康,并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后果时,如果在当时最高的学问水准和知识水平下,经过慎重缜密的审查仍然对该药品的安全性存在疑惑时,那么该药品的价值就存在质疑,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就应限缩。22法官在东京的有关判决中也认为,当对于国民生命、身体、健康有损害发生的危险可能时,如果行政机关在权限内的行为可能使损害容易防止时,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裁量权就应缩减,必须行使权力防止损害行为。23也就是说,只要药品安全性存疑,即使还未出现具体的损害事例或者有确实证据证明会发生损害,也应当认定行政机关具有对该医药品可能产生的损害的预见能力,从而判定行政行为违法,并可依照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要求其赔偿。
3.小结
在龙胆泻肝丸事件中,药害事件曝光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国家药监局即正式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并要求相关生产企业修改成药标准。应该说,在事件爆发后国家药监局的反应相当迅速且符合程序,不存在任何层面的拖延履行或者不履行,对此难以认定其行政不作为。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在龙胆泻肝丸事件发生之前国家药监局及相关行政机关能够知晓该药品可能产生损害或者不安全,因此缺乏行政裁量缩减中的预见可能性要件。24故在此事件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依然无从谈起。
(三)行政补偿
1.规范法学的进路
我国目前的行政补偿是以行政征收征用补偿为基础,以因合法行政行为而导致特别牺牲的财产或其他权利遭受损害而给予的补偿制度。25我国现存法律体系中与药品相关的行政补偿制度仅存在于预防接种领域。《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对于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其中第一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也就是说,即使行政机关在疫苗接种的各个环节中都完全尽到了注意义务,而接种疫苗仍然造成公民生命或者健康受损时,就应当给予公民一定额度的行政补偿。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其他药品领域的行政补偿制度尚未确立。
2.理论层面的梳理
大陆法系的补偿概念是源于征收,即指对个人被迫于公益而超过可忍受的牺牲利益的填补。然而,药害损害与一般意义上的征收损害有所不同。在通常意义下的征收补偿中,法律赋予侵权行为以合法性(例如征收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必然是法律所承认的(例如土地和房屋被征收),此情形下的补偿是对该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填补。但是在药害中,药物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副作用或其他损害后果——并非法律所预设的效果,因此对药物致害而作出的补偿也并不等于从正面承认了国家对于生命的剥夺以及身体的侵害的合法性。26故传统意义上的征收补偿制度在涉及人身损害时不可适用。
在征收补偿的基础之上,大陆法系又发展了征收性质侵害补偿,其是指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虽然不是公用征收,但其结果造成民众“不正常的、非本意且非可预见的附带效果”的特别牺牲,对此给予的补偿。27例如市政府依据法定程序挖掘马路导致沿路民房龟裂受损;合法建造与管理的市立垃圾场吸引乌鸦觅食,使得临近稻田果园果实被啄食;合法建设并依规定管理的市立污水处理厂发出恶臭,影响临近房屋价格等。28这类损害并非该合法行为所意欲和预见,而是附随产生造成公民之特别牺牲,从这一角度出发,征收性质侵害补偿制度确实弥补了征收补偿所形成的理论漏洞。29基于上述理念,我国对强制接种疫苗致害的补偿也可被归于这一体系。
3.小结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征收补偿还是征收性质补偿,行政补偿的产生前提无疑都是公民由于行政行为所导致的特别牺牲。也就是说,在现有行政补偿的概念体系下,无论是公权力刻意为之的征收损害抑或是附随造成的征收性质损害,至少一方面损害和公权力的行使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该损害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特别牺牲,给予行政补偿属应有之义。然而,在合规药害中,药品损害毕竟是由服用药品这一非强制性行为所导致,公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果关系很难证成;退一步而言,即使可以证明公权力与致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合规药害也难以解释为是个人为公益而作出的“牺牲”。因此,以征收为基础的行政补偿制度在此领域又难以适用。
三、救济体系之新发展:国家衡平补偿责任
通过前述分析,似乎可以看到,现有体制对合规药害的救济问题已然集体失语。合规药害之所以会在规范和理论层面均救济无门,虽是由于规则制定者对药品的阶段性认知水平不足,但主要还是因为既有责任理论对药害领域的回应性不强。
现有责任体系产生于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以前,社会生活中主要的损害来自自然灾害,由于它来自于人类社会以外的力量,人们往往视之为命中注定,将其归结为神明的力量或者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世界,责任追究也就无从谈起。30进入工业社会后,个人命运论的责任观遭到淘汰,考虑到民众所遭遇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私人主体之间的侵权,建立在个人自治的基础之上的私法责任体系得以确立,强调侵权行为的过错以及它和救济之间的因果联系,而这也奠定了民事侵权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社会风险的多样化日渐扩散,传统侵权责任中过错和因果关系等元素在现代社会的损害中或者难以证成或者干脆泯灭不见,无法通过民事赔偿获得填补损害的情况日渐增多。合规药品致害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在现代社会中,民众常常会深陷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核辐射、生态灾难等既具有不确定性又有高度危害的致害之中,却无法在传统私法责任体系中获得救济。现实与既有理论的不适应就形成了一项制度上的困境:由人为风险造成的显性与潜在的破坏日趋严重,却没有人或组织需要对此负责,即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1现代社会中风险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态已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中人们对于损害的想象力,其不可避免地对已有救济体制产生冲击。
针对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种种现象,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理念: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四伏的社会,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各种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知识是有限的,不仅难以保证认知所有风险,且会掩盖风险,甚至会缔造风险。32由于风险的整体必然性和其产生的蝴蝶效应,传统侵权行为法和国家责任法完全基于个人自治原理所作的设计在风险救济中已经不能再适用。例如在药品合规致害等一系列风险事件中,仅通过个体干预企图符合正义通常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民事侵权责任在风险领域往往无法适用。而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却开始要求国家扩大干预的范围,将国家的安全保障职责从关心现状、保护或重建一个不受干扰的状态为己任,发展到以未来为目标全面型塑社会。33在此背景下,宪法上的社会国概念开始在风险社会中延伸。基于社会国原则,国家对于人民所受若干损失,得主动给予一定之补偿,藉以实现社会正义。34“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保持或者促进经济结构的繁荣,国家还必须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面的干预……‘排除危险’是国家的法定的和不可变更的任务,该任务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供应、给付和补贴等任务得到补充。”35因此,以干预行政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行政法之前一直是国家干预社会和个人活动的重要工具。然而,以保障和提供个人福利为中心,确保个人体面地生活的给付行政应是现代行政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正是给付行政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福利保证系统,从而可以消解个人在当今社会遇到的各种风险。36
现代意义上的衡平补偿责任正是以上述社会国概念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在传统意义上,衡平补偿多适用于犯罪被害人之补偿、政治受难者之补偿等,其所弥补的损失或和损害与国家机关或公务员之作为或不作为之间欠缺直接关联性,所以一度未被列入行政补偿的范畴。37然而,如果从更广义社会连带学说出发,事实上国家中每个人彼此之间均有一定程度的连带关系,此连带关系透过国家制度予以“链结”。在此“链结关系”下,偶有遭到无可避免的损害,由于关系错综盘结,难以追究损害之肇事责任,亦难以用“特别牺牲”予以涵摄,故应透过损失补偿制度弥补这一类型损失。38因此,衡平补偿的概念在风险社会逐渐扩张,具体是指因特殊事故或特别状态,某些特定人无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国家基于社会正义的理性,对遭受到特别人为或制度性灾难的人,予以补偿。39与征收征用补偿、征收性质补偿相比,衡平补偿针对的是人民所受的损失并未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往往是受损失的人数众多,不属于个别情况),或者与公权力之间欠缺直接而紧密的关联,毋宁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累积或较为间接的关联而形成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有行政补偿的内涵,其不仅不再注目于个别公权力的行使,更以广义的危险状态为基础,因此同时具备了行政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40但是无论如何,衡平补偿作为国家责任的重要补充形式已经毋容置疑。
在此制度体系下,不存在行政违法或者过错的合规药害救济就可被纳入到衡平补偿体系之中。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颁布的“药害救济法”第4条规定:“因正当使用合法药物所生药害,得依本法规定请求救济。”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明确将药害补偿列为战争补偿和刑事被害人补偿以外的第三种衡平补偿的类型。41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中不存在衡平补偿概念,也并未建立起刑事被害人补偿体制,但是在具体领域,衡平补偿的规定也不乏实例,其集中体现在生态资源等领域的补偿。42在未来立法上建立药害尤其是合规药害之行政补偿制度也可期待。
四、结语:寻找风险社会下的救济法理
为实现合规药品致害的损害救济,应在立法体系的建构方面完善对私法和公法相关规定的协调,并与此同时推动药品损害救济理论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效仿我国台湾地区“药害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参照我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立法模式,在《药品管理法》中增加由药典制定机关承担责任的规定,即“对药品由于药典规定标准存在缺陷而造成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由药典制定机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予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纳入财政预算”,从而推动我国药品损害救济综合体制的发展。第二,在《药典》中增加责任条款,明确当药品标准存在缺陷时应由制定者承担相应责任,并就缺陷认定程序、补偿方式、范围和计算标准进行说明。由于我国尚未有统一的国家补偿法可作借鉴,模糊的规定可能会使补偿最终难以落到实处。第三,以合规药品致害事件为契机,参照《侵权责任法》第37条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方式,在《侵权责任法》中增加引致条款,规定:“因行政机关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在确定具体数额时,应当考虑该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第四,在理论研究上逐步推动药害行政补偿制度的体系发展,为药害受害者提供应有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国家责任尤其是衡平责任理论研究,构建以特别牺牲的征收补偿为基础、福利行政的衡平补偿为补充的完整国家责任体系。
由合规药品致害所可能引发的思考其实不限于药品领域。毋容置疑,在已经到来的风险社会大潮中,合规药品致害只是其中泛起的一叶微澜。相较于人类有限的认知而言,风险是不可预测的,人类有限的防范能力在万千变幻的风险面前显得捉襟见肘。43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社会下与救济相关的法学理论新发展就更能凸显其意义所在。传统法律救济制度根基于法律责任的概念,法律责任又与违法行为或先行行为密切相关,是基于违反了第一性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在风险社会下,国家所承担的救济责任已远非如此。例如2003年“SARS事件”后给予死者的丧葬费、尘肺等职业病患者的免费医疗、“7·21北京特大暴雨”受害者的补助等,在上述与国家并无明显关联的事件中,国家均发挥了救济损害的功能。显然,此时国家对于公民所担负的责任已经脱离了“先行行为”、“特别牺牲”等条件,更超出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等法律责任,而具备了国家救助和社会保险的内涵。当然,在传统概念谱系下,国家所担负的上述责任并不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而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责任。44然而,在上述事件中,承担了巨大损害并获得一定救济的民众却开始要求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是赔偿或补偿等法律责任)。45与之相应,近年来法学界也出现了相对激进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临近,在现代国家理念框架下,国家应负有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义务,与之对应,公民也应具有法律上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事先的预防请求权,使公民超越法律的层次,直接运用宪法上的基本人权来攻击某些行为,法院也可以不必以法律存在为前提直接裁决;46其也可以表现为一种事后的救济请求权,运用宪法上的人权保障条款而请求法院判决政府承担赔偿或补偿的法律责任。52如照此思路推演,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将与行为渐行渐远而只关注损害结果本身,换言之,法律上和政治上国家责任的分界将由此变得模糊,而这无疑会导致法律责任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变革。为此,在损害频发的风险社会,如何重构国家责任以及救济制度的法理,将会是今后亟需回答的问题。
注:
1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1/04/c_132078381.htm,2013年1月5日访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e4i4.html,2013年1月5日访问。
2相关报道可参见《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ht 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2/23/content_740961.htm,2012年1月5日访问。
3在药品不良反应致害的问题上,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风格各异的救济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德国、瑞典为代表的保险模式以及以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基金模式等。上述救济方式已经脱离了传统法律责任的范畴,本文不作探讨。参见宋瑞霖:《完善中国药品不良事件救济机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2011年版,第150页。
4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转引自朱怀祖:《药物责任与消费者保护》,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09页。
5相关研究可参见金自宁:《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例切入》,载《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3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政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6学者约瑟朗德提出形成风险说,参见H.&L.Mayeaud/Tunc,Traitéde la responsabil ité civile,I,1965,N.336-361。转引自朱岩:《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7苏永钦:《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载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8参见Clayton P.Gil let te& James E.Krier,Risk,Cour ts,andA gencies,138 U.Pen.L.Rev.1O27,1028(1990).转引自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9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10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2期。
11参见Teresa Moran Schwartz,The Role of Federal Safety Regulations in Products Liabi lity Action,41 Vand.L.Rev.1131(1988);许宗力:《行政法对民、刑法的规范效应》,载葛克昌、林明锵主编:《行政法实务与理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转引自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12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转引自朱怀祖:《药物责任与消费者保护》,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7页。
13当然,药品制造商也可以在可能出现的两难境地中选择停产停业从而尽到“注意义务”,但是这对于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显然承担的义务过重。
14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页、第142-169页。
15宋华琳:《行政法视野中的技术标准》,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16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根据行政所制定的抽象规范有无形式上的法律规范性将这类规范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3页。
17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转引自宋华琳:《行政法视野中的技术标准》,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页。
18参见[美]理查德·皮尔斯:《立法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的区别》,宋华琳译,《公法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30页。
19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20通说认为,对于抽象规范的性质,虽然其与法律或者规章相当,但是从其产生之机关及过程而言,则与法律或规章不同,并非由有免责权的民意代表集体制定,如其符合国家赔偿的其他要件则尚无予以排除之理。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周友军、马锦亮:《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91页。
21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转引自朱怀祖:《药物责任与消费者保护》,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49页。
22日本京都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判决书:京都地判1979.7.2,判例时报950号。
23日本东京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判决书:东京地判1978.8.3,判例时报899号。
24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可以依照是否具备预见可能性、回避可能性、期待可能性以及受损法益的重要性等要件进行判断。参见胡建淼、杜仪方:《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赔偿的违法判断标准——基于日本判决的钩沉》,《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5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
26杜仪方:《恶魔抽签的赔偿与补偿——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中的国家责任》,《法学家》2011年第1期。
27李震山:《行政法导论》,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640页。
28董保城、湛中乐:《国家责任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0页。
29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征收性质侵害仅指对财产造成的损害,而如对非财产法益造成侵害则应构成“公益牺牲补偿”,后者特指对个人因政府公法上的行为直接造成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人格等法益之损害进行补偿。参见廖义男:《国家赔偿法》,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30[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31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3[德]埃贝哈特·施密特-阿斯曼,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转引自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载季卫东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4李建良:《损失补偿》,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450页。
35[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6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7[日]宇賀克也:《国家補償法》,有斐閣1997年版,第512页。
38、39、41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51页,第627页,第629页。
40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42参见《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水土保持法》第3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7条。
43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
44政治学中的国家责任是指一个国家不仅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参见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45参见《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调查》,http://heal th.sohu.com/20100225/n270418683.shtml,2013年1月5日访问;《5公民要求监察部等追究北京721暴雨渎职公务员责任》,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id=03e1dcfb-aa50-418a-bd79-a0b101181304&user=186561,2013年1月5日访问。
43例如,德国学者Rossnagel在关于核能利用的讨论中,提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该自由和其他个人自由一样是对抗国家的给付请求权。他认为,人类在面对未知或未经实验的科技时,经常是极为无助的,人性尊严受到威胁的可能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对于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风险,若已达到社会国家原则下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人民具有主观的请求权。参见郭淑珍:《科技领域的风险决策之研究——以德国法为中心》,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8-69页。转引自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载季卫东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7例如,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指出,在现代民主福利国家背景下,国家行政机能日益扩大且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日益加深,应将反射利益“公权化”,将行政活动所产生之利益推定为国民应享之权利,只要公众的利益被行政机关侵害,就应当允许公众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参见[日]原田尚彦:《薬害と国の責任—可部判決の理論をめぐって》,《判例時報》8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