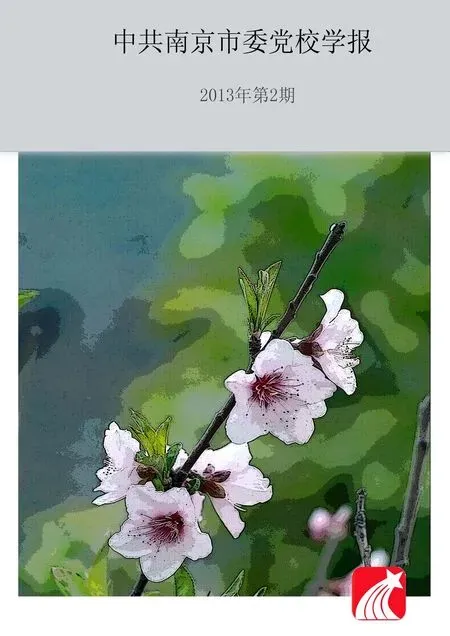儒学与儒教分离论*
孙景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东汉佛教传入后,儒文化就有儒学与儒教两说。二者是同一范畴,还是不同范畴,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而是长期混用,或叫“混合儒家”、“泛儒家”。[1]其实,“混合儒家”或“泛儒家”就是将二者当作了同一范畴。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二者是两个范畴,应当分离。本文就想对此谈点新看法,抛砖引玉,以求教于高明,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儒学与儒教应为两个范畴的历史和理论根据
把儒学与儒教分离为两个范畴,无论从历史还是理论上,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第一,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就是两个范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百家争鸣的各主要学派,都是“学”,不是“教”。就是说,不否认百家争鸣中有“教”的存在,但“教”在百家争鸣中不是思想主流,也未被学术界重视。“教”真正被重视,或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在秦、汉以后,“儒教”一词就是在东汉后期产生的。如,“百度百科”的“儒教”条载:蔡邕说:“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儒教”说,后逐渐流行,进而出现“三教并举”,“三教合一”说。不过,现在一些学者都认为,《史记·游侠列传》的“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3]中的“儒教”二字,是最早“儒教”说,笔者认为不妥。应当说,这里的“教”是动词,为教育之“教”,不是名词儒教之“教”。虽然不能否认鲁人在进行儒文化教育中,确实教过“儒教”内容,但这里的“儒教”内容,是包含在名词“儒”中而不是在动词“教”中的。因为古人儒学与儒教不分,所以,“鲁人皆以儒教”的释义应为:鲁人以儒文化教育人。“三教并举”,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如《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陈寅恪也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4]唐代“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达24次。[5]“三教合一”最早提出者为隋代的王通,他说:“三教可一”。[6]然而,“三教合一”主要在宋、明时期。如,明代陆陇其说:“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一教”,宣称“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并“立庙塑三教之像……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7]可见,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可置疑的。
第二,三次大的“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讨论的结果也说明二者是两个范畴。“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第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利玛窦来华,当时经中外学者、神学家包括罗马教皇、乃至满清皇帝多方讨论,主流观点认为“儒学(儒教)不是宗教”。到了民国初期,康有为等认为“儒学(儒教)是宗教”,建议立为国教,并成立了“孔教会”。但启蒙学者和民国文化机关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如陈独秀认为,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长期遵循儒学(儒教)是“学”的轨迹,对其糟粕进行过批判。1978年,任继愈又提出,“儒学(儒教)是宗教。”结果,中外学术界对此又讨论了三十多年,绝大多数学者对此仍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几乎每次都回到了原点,已陷入思想怪圈。[8]然而,这种讨论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儒文化中肯定既包含了儒学,同时又包含了儒教,所以当人们每次从儒学的角度来探讨儒文化时,都会产生“宗教”(儒教)说;可当人们每次从“宗教”(儒教)的角度来探讨儒文化时,结局又都回到了儒学上。最后,正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所说:“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9]既然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那么,二者无疑就是两个思想范畴。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儒学与儒教?应当说,正确理解儒学不难,因为儒学的“学”指的是“人文学说”;而正确理解儒教,则需要认真讨论,因为目前学术界对此的争论十分激烈。如前所述,三次大的“儒教(儒学)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把儒教之“教”当成了宗教之“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发现,儒教不是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如果硬要把儒教说成宗教,不是要改变宗教的内涵,就是得给这个宗教加限定词。如,张岱年认为,“根据对于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也是宗教”,这种理解就是“以人为终极关怀”;[10]唐君毅认为,儒教“可以称为道德的宗教或人文教”等。[11]那么,儒教之“教”到底该怎么解释?任文利将传统文化中的“教”,归纳为三种含义,一是教育,二是教化,三是宗教,并作了详细说明。[12]不过,李申认为:“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儒教是教化之教,这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13]而郭齐勇认为,儒教之“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14]等。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均不全面。在传统文化中,“教”至少有四个含义:教育、宗教、信仰、教化。其中,教育之“教”是人文教育;宗教之“教”是宗教信仰;信仰之“教”是一般信仰学意义上的广义信仰,既包含了宗教信仰,也包含了非宗教信仰;教化之“教”的内涵最广,既包含了教育之“教”,也包含了信仰(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之“教”。由此,儒教之“教”,既不能解释为“教化”之教,也不能解释为“宗教”之教,而应解释为信仰学意义的“信仰”。就是说,儒教不是人文学说,而是与儒学(人文学说)相对应的一种信仰学说。
二、儒学与儒教如何科学分离之我见
既然儒学与儒教是两个范畴,那么,应怎样对二者进行科学分离呢?
笔者认为,应将百家争鸣的儒家,如孔子、孟子、曾子学派、孙卿子等的学术性质定为儒学,对应的经典为《论语》、《孟子》、《孝经》和《孙卿子》,核心思想是:孔子改造过的“礼治”、孔子和孟子的“仁政”、“孝治”、“义政”。[15]其中,“礼治”是孔子前期思想核心,他晚年才提出“仁政”思想萌芽。后世凡与这些学说有内在联系、并对这些学说主要进行“我注六经”式的阐释的流派,如“汉唐经学”(除董仲舒;包括叔孙通的“制礼”,汉武帝的“以孝治天下”;唐代的《五经正义》等)、[16]宋代王安石新学、明代启蒙思想、清代考据学、民国的“古史辨”等有关儒文化,均为儒学;而将以百家争鸣儒家的任何一派的核心思想为信仰对象,并对其主要进行“六经注我”式的阐释,同时把该阐释理想和教条化的派别,其学术性质均定为儒教。如先秦的“礼教”和“义教”,对应的原始经典为:《礼运》、《郭店楚简》。后世凡与这两个学派有内在联系的流派,如秦代的《谷梁传》、《公羊传》、《大学》、《中庸》均属儒教。其中《谷梁传》属礼教,即以“礼”为核心思想的儒教;《公羊传》、《大学》、《中庸》属义教,即以“义”为核心思想的儒教。义教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教,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二程和朱熹,代表作是《董仲舒集》和《四书集注》等。[17]任继愈提出的“儒教(儒家)是宗教”问题,主要指的就是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不过,在汉代之后,儒教又产生了两种新思想,一是元代的“孝教”,经典是郭居敬的《二十四孝》;二是明代王阳明的“良知”教,即心学,心学是从哲学上来定义该儒教的,主要经典是《传习录》。后来,民国的康有为,又以“义教”为核心,整合了所有其他儒教思想,创立了孔教(新儒教),主要经典是《大同书》等。
而儒文化的《六经》,也应做大致相对的划分:《六经》的“经”,都是儒学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传”则是儒文化学者对儒学或儒教的发挥。其中,《诗经》和《易经》没有太大争议,《易传》是孔子之后的儒文化学者对《易经》思想的发挥;《尚书》的争议先在古文和今文上,后来《古文尚书》失传,今存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后发现的《周书》(包括《佚周书》)等一直未被列为“经”;《乐经》在汉初即失传,现存于《礼记》中的《乐记》,或是《乐经》残本,或是后人的发挥,所以汉人多提《五经》,除《乐经》;最混乱的是《礼》,最复杂的是《春秋》。《礼》:汉初最早发现和恢复的是《士礼》,后被增为《仪礼》;再后来是戴德编辑了《大戴礼》、戴圣编辑了《小戴礼》,二书不尽相同,内容庞杂,所记不全是“礼治”思想,还包括了其他儒学及儒教思想,但《大戴礼》始终未被列为“经”;另,古文经的《周官》,被刘歆更名为《周礼》(今本《周礼》的《冬官》是用春秋时期齐国《考工记》增补的),所以《礼》有《三礼》说。不过,《三礼》中的“礼”,纯就“礼”而言,既有孔子之前的礼,也有经孔子及弟子改造过的礼,还有后世儒文化学者发挥的“礼学”与“礼教”。《春秋》:分为“经”和“传”,多数学者都认为《春秋经》是孔子所作,但此说与《论语》不合,依照《论语》的“孔子‘述而不作’”说,《春秋经》应为《鲁春秋》(鲁国的国史);“传”有多家,后来被列为“经”的有三家,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前两传主要发挥的是儒教思想,《左传》主要发挥的是儒学思想,即以记述历史事实为主的史学著作。
应当说,把孔子等百家争鸣儒家各主要派别的学术性质确定为儒学,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同意的看法。如,陈咏明就曾批评李申,把“儒学是教”说强加到“诸子百家”,他就认为诸子百家学说不属“教”范畴。[18]不过,对儒学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儒学最根本的核心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孟子完善的“仁政”。第二,“礼治”虽不是儒学最根本的核心思想,但孔子对“礼”的改造不可忽视,“礼”仍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后世“以礼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大有人在。如,汉文帝时期的博士卢植作的《王制》,核心思想就是“礼”。[19]第三,《孝经》和“孝治”是儒家的一个流派,《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其学术和历史地位应当被肯定。[20]第四,《孙卿子》(《荀子》)一直未被列为“经”,儒文化《十三经》中没有《孙卿子》(《荀子》),《孙卿子》(《荀子》)长期以“子”学形式存在,极为不妥,现在应当予以纠正。[21]
对儒教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把《礼运》、《二十四孝》、宋明理学(除王安石等)等确定为儒教,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同意。因为《礼运》提出了“大同”、“小康”等思想,明显是一种信仰;《二十四孝》提出了对“孝”的崇拜也是信仰无疑;而宋明理学是“三教合一”的一“教”,是儒教亦无问题。
第二,为什么要否定董仲舒的儒家性质,将其定为儒教?这里:1.儒教一词实际上即与董仲舒思想有内在联系。上引蔡邕说,“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这里的《尚书》、《易》虽不是“儒教”经典,但《欧阳尚书》、《京氏易》对《尚书》和《易》的解释,已“公羊”和“董学(董仲舒)”化了。[22]2.名教就是早期的儒教。名教是儒教,这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23]但名教也与董仲舒相连。如“百度百科”的“名教”条说:“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24]3.董仲舒为儒教,根本之点,在于他对《公羊传》即《公羊春秋》“春秋大义”的发挥。董仲舒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公羊(春秋)治狱”、“公羊(春秋)史观”,并把这些观点教条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子要绝对服从于父、妻要绝对服从于夫”,这是后世义教之儒教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25]从名教到儒教,再到程朱理学,直至康有为和现代新儒家(新儒教),“三纲”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教条(信条)。4.为什么《公羊传》是儒教而非儒学?《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是“公羊(春秋)大义”,而且,这个“义”是严格贯彻该书的始终,已成为不可雷池的信条(教条)。[26]5.为什么《郭店楚简》是义教发源地?《郭店楚简》是先秦明确提出“性命”(信仰)思想的著作,该书“性命”信仰的核心思想为义,还明确把义的内涵界定为“宜”,“宜”是“义教”对“义”的根本阐释。[27]6.义教的儒学基础是什么?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义教”即董仲舒和程朱理想的儒学基础说成孟子或思、孟学派,不妥。其实,义教的真正儒学基础是《孙卿子》,孙卿子与荀子过去被当作一个人,不确。这里,孙卿子应当是老师,荀子应当是弟子;《孙卿子》的核心思想过去被当作“礼法”,也不确,应当是“义”,但他把“义”解释为“节”。所以,义教的儒学基础是孙卿子(传统说的荀子)。[28]7.《郭店楚简》、《公羊传》、《大学》、《中庸》在义教中的历史地位各是什么?《郭店楚简》提出了信仰的核心范畴“义”为“宜”,《公羊传》将“义”发展为“春秋大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大学》为“义”的政治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础,《中庸》为“义”提供了哲学论证。由于《郭店楚简》失传,董仲舒主要发挥的是《公羊传》的思想;朱熹除了继承了董仲舒的儒教思想,主要发挥的是《大学》、《中庸》的思想,《四书集注》中的《论语》和《孟子》已被“义化”。
第三,王阳明儒教的儒学基础及意义。王阳明儒教的核心思想是“良知”,“良知”思想直接发源于孟子,如《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但是,“良知”不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不过,王阳明用“良知”思想来阐释《大学》,并批评朱熹,具有一定的信仰启蒙或改革性质。
第四,儒教不是宗教学意义的宗教。“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时断时续讨论了三百多年,已被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神学家所否定,如罗马教皇就“敕谕”说:中国儒教不是宗教。[29]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儒教中有宗教思想,但宗教思想在儒教中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任继愈、李申等认为“传统儒教为宗教”说难于成立(笔者不否定现行有些儒教为宗教,如印度尼西亚的儒教等;也不排除有些国人将来把某一儒教重建为宗教信仰)。
第五,儒教的准确信仰定性。现在,学术界凡否定“儒学为宗教学意义的宗教”的学者都认为,儒教是“人文教”,或人文宗教,或道德宗教,或政治宗教,或智慧宗教等。[30]笔者认为,这是对信仰学缺乏研究的表现。根据信仰学原理,人文信仰是独立于宗教信仰的另一重要信仰。[31]如前所述,信仰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既有宗教信仰,也有人文信仰。所以,人文信仰是非宗教信仰的一种信仰,不能叫人文宗教,因为人文宗教本质还是宗教。这里,一定要理清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天生是信仰,信仰天生非宗教;只能用信仰涵盖宗教,不能用宗教涵盖信仰。用宗教涵盖信仰,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因为西方人的信仰主要是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一谈到信仰就用宗教来说明,不妥。现在,有人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在信仰上又坚持用“宗教去涵盖所有信仰”说,如“人文宗教”等说法,实际是陷入“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的表现。只有承认人文信仰是独立于宗教信仰之外的信仰,才有利打破“西方中心论”,对完善信仰学原理也是一个巨大贡献。如果把“儒教”确定为人文信仰,那么,这种人文信仰,到底属人文信仰中的什么信仰呢?现在有人认为是“道德信仰”,或“智慧信仰”等,其实不妥,应为“以伦理道德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信仰”。因为儒教信仰起始点虽然是“正心、修身、齐家”(道德信仰),但是最终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或“内圣外王”(政治信仰)。
三、儒学与儒教关系之一瞥
将儒学与儒教分离后,二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二者的渊源关系。过去,认为“儒教是宗教”的学者,如何光沪曾认为,“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的根”是“儒教”,“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是“儒学”,即“儒教是源,儒学是流;儒教是根,儒学是花”。[32]笔者认为不妥:如前所述,儒学之名,是自孔子始;儒教之名,远远迟于孔子,从二者产生的时间看,孰先孰后,应该一目了然。所以,儒学是儒教产生的思想基础,即必须先有儒学,后有儒教,儒教是对儒学某一思想的发挥和教条化。而且,儒学与儒教的历次重建,基本都是儒学在前,儒教在后。如,西汉就是先有叔孙通“制礼”、王臧“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后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33]
第二,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儒学是儒教产生的基础,但儒教一经产生,又对儒学有反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如,本来孔子已放弃了对“礼治”思想的坚持,并提出了“仁政”思想,但由于《礼运》将“礼”改造成了“大同”和“小康”的信仰,所以后世儒家又重拾对“礼治”的信心,出现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先秦的《曲礼》、西汉初期卢植的《王制》等。尤其是,叔孙通“制礼”后,对整个儒文化(儒学与儒教)在西汉的复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司马迁称为“儒者宗”。[34]
第三,二者的相互斗争。儒学与儒教虽同属儒文化,但是二者的矛盾和斗争也不可忽视,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如,西汉后期,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主体的今文经学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刘歆建议立《左传》博士,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被迫离开朝廷,左迁为一地方太守。而当董仲舒发挥的儒教思想广泛传播之际,一些儒家也不赞同,有人就伪托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35]尤其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将儒家的《诗》、《尚书》和《周官》(《周礼》)等三经立为“新学”,遭到了司马光等儒教人士的坚决抵制,最后王安石被罢相,变法也宣告失败,等。
第四,二者的主要和根本分歧。二者的主要分歧至少有几点:一是对《春秋传》的态度:儒教主要坚持的是《公羊传》或《谷梁传》,儒学是《左传》。二是对解释或注经的方法:儒教主要是“六经注我”,儒学是“我注六经”。三是对“三纲”的态度:儒教强调的是“臣、子、妇对君、父、夫的绝对服从”;儒学是“君、父、夫要对臣、子、妻起积极的主导作用,臣、子、妻也要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36]过去,学术界包括笔者都将二者当作了一个“三纲”,不妥。四是对汉武帝“尊儒”这一历史事件的认定:儒教认为,汉武帝“尊儒”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认为,是采纳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37]其中,最后一点是儒学与儒教的根本分歧。
第五,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儒学与儒教在历史各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历史上各尊儒的封建王朝及帝王,对儒学与儒教的态度不同。如,秦始皇打击儒家,崇尚儒教(这个问题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汉武帝崇尚儒学,冷落儒教;唐代主要崇尚儒学,打击儒教;宋、明是冷落儒学,崇尚儒教,等。就是说,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四、将儒学与儒教分离的意义
应当说,把儒学与儒教相分离,对儒文化或儒学与儒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为儒学与儒教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儒学与儒教是儒文化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二者相分离,再对其分别进行解构,解构儒学时,不引入儒教;解构儒教时,不引入儒学,只有这样,才能使儒学与儒教研究走上正轨。以往的儒文化研究,儒学与儒教不分,囫囵吞枣,难怪无法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第二,有利于从理论上加深对儒学与儒教的科学认识。儒学是人文学说,儒教是信仰学说;百家争鸣的儒文化主要是儒学,董仲舒和宋明理学是儒教;研究儒学用人文方法,研究儒教用信仰方法;儒学与儒教既有联系,又有矛盾和斗争,二者在历史上交替起主导作用。
第三,有利于对儒文化的批判与传承。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儒文化也是这样,只有将二者相分离,并对其分别解构,精华和糟粕才容易明了,批判也不会无的放矢,传承亦不会错位。如:过去,儒学与儒教不分,将董仲舒、朱熹的“三纲”当孔子思想来批判,既制造了孔学冤案,又妨害了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38]
第四,有利于儒学与儒教的重建。儒学是儒教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历史上儒教每次重建的思想基础。要重建儒教,必须先重建儒学,要重建儒学,就必须要肯定儒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长期以来,在二者的研究上,儒学被儒教侵吞,主流观点一直坚持:“董仲舒和宋明理学既是儒学又是儒教”、“汉武帝尊儒就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将儒学逼入了绝境。没有儒学的重建,儒教重建绝无可能;儒教必须要向儒学让世俗地盘,儒学要为儒教清除历史垃圾。现在双方都要实事求是,避免内讧,携手共建。只有这样,儒学复兴才有希望,儒教重建才会出现曙光,否则,二者都会在死胡同中徘徊!
[1][8][10][13][14][18][29]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J].晋阳学刊,2009(6).
[2][4][5][7][32]儒教[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42994.htm.
[3]孙蕴,刘建忠.刍议儒教的中国特色[J].沧桑,2012,(2).
[6]李晓洁,李婧涵.浅析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J].商业文化,2012,(1).
[9][23]解光宇.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学与儒教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J].世界宗教研究,2010,(5).
[11][30][32]沈伟华.儒教之争考[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3).
[12]任文利.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J].中国哲学史,1998,(4).
[15][27]孙景坛,孙丽淑.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新论[M].香港:天马出版社,2010.191.
[16]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1);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6).
[17][26]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J].江海学刊,1995(4);宋明理学非儒家论[J].南京社会科学,1996,(4).
[19]卢植.王制[A].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69.328.
[20]孙景坛,孙丽淑.《史记》之汉武帝正读[M].香港:天马出版社,2010.273.
[21][28]孙景坛.荀子与孙卿子是两个人,《荀子》应为《孙卿子》[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2,(2);顾兆禄,孙景坛.荀子的学术性质之我见[J].南京社会科学,2001,(12).
[22]孙景坛.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3).
[24]名教[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717.htm.
[25][36]孙景坛.“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J].南京社会科学,2013,(1).
[31]孙景坛.关于信仰基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增刊).
[33]孙景坛.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南京社会科学,1993,(6).
[34]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A].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3.
[35][37]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A].张义生.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C].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38]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J].南京社会科学,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