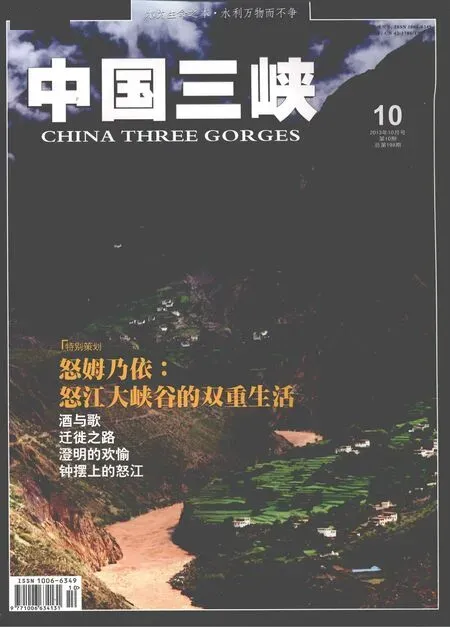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
本专题策划/柳向阳 任红 黎明 罗婧奇
酒与歌
迁徙之路
澄明的欢愉
钟摆上的怒江
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到云南怒江州的首府六库,怒江在东侧的碧罗雪山和西侧的高黎贡山夹峙下,形成三百多公里长的大峡谷,在不同的季节里和不同的江段,他时而温柔舒缓,时而浊浪滔天,貌似轮回中,却难掩饰内在的躁动与不安。
就在那峡谷两侧的河谷与山坡上,数百年间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藏族等数个民族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大多数是由碧罗雪山之东辗转而来,刀耕火种,渔猎为食。虽有蜿蜒曲折的数条古道连通峡谷内外,大山却始终是阻隔他们视野的屏障,也让外界对峡谷倍感神秘。如今,道路已然贯通,峡谷里的人们正在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流转而面临千百年来最为深刻和迅速的一次转变。相对于峡谷之外,他们正经历的变迁也许晚了10年,乃至20年,但显然,他们不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速度快得有些让他们不太适应。而对于我,怒江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中国已经走过,和正在行进着的,欲望的追逐与精神流放的缩影。
上世纪初,各教会组织纷纷派员翻越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从内地与缅甸分别进入峡谷里开始传播福音。基督教传教士传为了方便传播圣经,还创制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傈僳文字,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夫妇更是结合当地人能歌善舞的特点,改编了几十首多声部赞美诗,几十年来传唱不绝。如今,怒江流域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和谐相处,尤其是基督教,影响范围最为广泛。在社会转身的刹那,当大峡谷无法承载更多物欲的时候,信仰却让许多徘徊在贫困线上的人找到了宁静与平和。
2003年7月,我第一次走进已经不再神秘的怒江,做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和徒步,几个月后,我因为峡谷里赞美诗的召唤第二次去了怒江。再一年,峡谷中的歌声和面孔依然不能让我释怀,而关于怒江建坝,开发水电的争论也不绝于耳。我突然意识到,一场深刻的变迁已然拉开帷幕——旋即,我回到了峡谷。
多年来,他们依然迷惘着,依然期待着,怒江的前路似乎还不明朗。怒江,正在时代的钟摆上,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