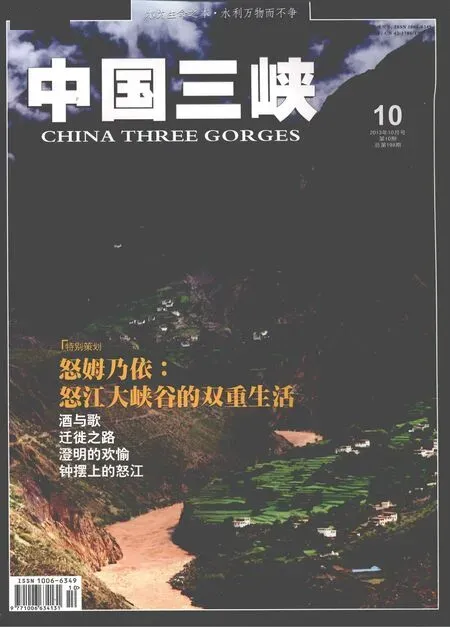重遇怒江
文/任 红 编辑/柳向阳
多年前,读雨果的《笑面人》,看到他写“暮色从谷底升起”,讶异之余,更多的是不解。对于一个积习于平原经验的人来说,暮色总是自上而下地降临。大自然拿着巨幅的黑色大氅,先从顶部打开,然后渐趋推进,直到四野微合,衔接处仍浮动着最后的光;然后那光也消失了,世间的一切,终被抹平彼此的差异,沉浸在一片无尽的昏沉中。
恰是在怒江,我第一次见到了从谷底升起的暮色。那个始自《笑面人》的疑惑,竟是在这次偶然的旅行中得到解答。怒江的暮色是自下而上的升腾,当谷底的村镇早被浓黑拖入长长的夜色,笔直的天顶处却还亮得透明。然后暮色缓缓地升腾,升腾,直至在最高点,完成黑暗的结界。
那是2003年的7月,我在怒江住了一个月。跟本期特别策划的作者周伟去怒江的时间约略相同。我们总以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却不料只是在平行的世界各自行走。本可以有过无数次交集的怒江,我和周伟却从没有过正式地擦肩而过。而真正的相遇和引荐,乃至同桌吃饭,一起喝酒,却是在十年以后。然后互动他的微博,细读他的文字,观看他的照片。十年前,不小心踏进的怒江那个文化场,十年后,突然得到一个回响。
那些傈僳族人的特殊面孔,那些群山中闪耀的银色或者红色的十字架,那些隐在灵魂深处的人名、地名,那些边舞边唱出的一拉秀的行酒词……我的关于怒江的几乎死去的记忆,突然在周伟的记录中复现了。
为怒江,我也曾经写过一些文字,我说那里“初夏的阳光,把六库的主街晒成金子。但这不过是灰姑娘的马车和舞裙,当正午的钟响过之后,这梦幻的怒江之都,顷刻间恢复了它的低调本色,沉浸在午后的昏黄和大榕树的浓荫之下”。
但是,周伟告诉我,我记忆中的怒江已经一去不返了。
周伟说:“怒江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中国已经走过,和正在行进着的,欲望的追逐与精神流放的缩影……在社会转身的刹那,当大峡谷无法承载更多物欲的时候,信仰却让许多徘徊在贫困线上的人找到了宁静与平和。”
记录,观看,思考。请打开你手边的这本书。观看他们,只为遇见自己。
——以福建省儿童医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