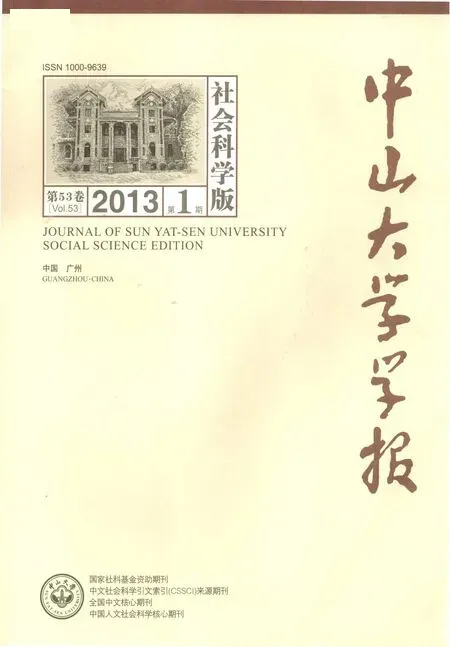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葛晓音
刘长卿是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按理在唐诗史上应划入盛唐,但历代诗论对他的诗歌尤其是七律的定位,几乎一面倒地“列之中唐”。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也随即能找到解释的理由。当代学者则都倾向于将其视为在盛唐与中唐之间承上启下的作家,这一定位说明刘长卿虽然是盛唐人,却在风格体调等方面开启了中唐。既然结论不存在多大争议,似乎也没有再作探究的必要,但如果细察古人的有关评论,不难看出,究竟怎样认识刘长卿七律介于盛唐和中唐之间的特点,还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而且由于学界公认刘长卿七律的风格不同于杜甫七律的“变格”,倒是更接近盛唐七律“正宗”王维、李颀的风貌,这就引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刘长卿七律被划入中唐,究竟依据什么诗学标准?今人的有关研究虽然也曾从某些角度提及刘长卿“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尚不足以回答以上这个较真的问题。因此本文拟联系宋以后诗论中的盛唐与中晚唐之争的诗学背景,辨析其划分诗人时代的诗学依据,并从七律体式建设的角度,对如何为长卿七律在诗史上定位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一
在历代诗论中,少数学者认为刘长卿属于盛唐的主要理据是其实际生活年代。如宋张戒说:“(随州诗)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①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0页。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列举盛唐诗人谓:“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復继出……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他如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取法建安。”②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也是将刘长卿置于高、岑、孟、杜等开元天宝诗人之间的。清阎若璩《题刘随州诗集》说:“刘长卿之为盛唐也无可疑,而分刘为中。尝推其故,盖高棅误读《中兴间气集》,以‘中兴’为‘中唐’,于是所迁钱起、刘长卿等二十六人,除孟云卿外,尽从而‘中’之。此致误之由。水心犹未核及。”①阎若璩:《潜丘劄子》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509—510页。又赞叶水心疑刘长卿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为“具眼人”。潘德舆也说:“盖随州开元间进士,论诗必分时代,当系盛唐。以文房为中唐者,误也。”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4,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63页。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说:“昔人编诗,以开元、大历初为盛唐,刘长卿开元、至德间人,列之中唐,殊不解其故。”③《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331页。但他随即对盛唐和刘长卿的诗歌声调加以分辨,自己解释了其中缘故。可见,他们认为如根据刘长卿的生活年代,是应当将其视之为盛唐诗人的。
另一种将刘长卿和盛唐王、李并提的看法,则是出自神韵派的王渔洋。他认为:“七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玩刘文房诸作。”④王渔洋口授,何世璂述:《然灯记闻》第十八条,见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录:《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120页。并批评高仲武没有眼光:“中兴高步属钱郎,拈得维摩一瓣香。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⑤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八,张健注:《王士祯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91页。指出钱起、刘长卿都是能承王维风格的中兴诗人。赞成此说的不乏其人,如乔亿说:“文房固五言长城,七律亦最高,不矜才不使气,右丞、东川以下,无此韵调也。”⑥乔亿选编,雷恩海笺注:《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3页。方东树说:“七律宗派,李东川色相华美,所以李辅辋川为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辅东川者也。”⑦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19页。贺贻孙《诗筏》也说:“刘长卿诗,能以苍秀接盛唐之绪”,“其命意造句,似欲揽少陵、摩诘二家之长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处。”⑧《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185页。这些学者多从神韵风调着眼,将刘长卿的七律看作是王维、李颀一路。而王、李的七律在明代诗论中,是一向被视为盛唐之正宗的。笔者曾在《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一文中梳理过当时的七律审美取向之争,指出以李攀龙、高棅、王世贞、胡应麟、胡震亨为代表的明代诗家虽然在推尊王、李还是杜甫的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实际上都认为王、李代表的盛唐七律是风雅和平的正调,杜甫的七律相对王、李而言是变格⑨参见拙文:《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那么刘长卿七律究竟是否属于盛唐正格呢?
与王渔洋等有所不同的是,明清诗论中更多的学者虽然承认刘长卿七律能接盛唐余绪,却还是认为“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⑩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4页。。高棅的《唐诗品汇》在“总叙”里首先把刘长卿列入“中唐之再盛”的大历贞元诗人群中,各类诗体都排在“接武”的名家前列。此后多数诗家均承此说,刘长卿七律遂被列为中唐之首。如胡应麟说:“七言律以才藻论,则初唐必首云卿,盛唐当推摩诘,中唐莫过文房,晚唐无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诸体皆然,由其才特高耳。”⑪《诗薮》外编卷4,第187页。同为盛唐派,评价之间却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标准并不一致。众所周知,李攀龙等推崇盛唐重在气象格调,王渔洋等推崇盛唐则基于神韵。如果从气象格调来看,刘长卿就比王、李要差一等。各家论长卿,还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列之中唐的原因,综合观之,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气象不如盛唐高浑雄整,所以比盛唐降一格。以高浑为盛唐七律正格,是很多盛唐派的共识,如明方以智说:“近体因陈隋之比俪,而初盛以高浑出之,气格正矣。”①方以智:《通雅·诗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46页。贺裳也说;“盛唐人无不高凝整浑。”②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见《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331页。刘诗虽然工秀而渐失浑厚元气。如沈德潜所说:“大历后渐近收敛,选言取胜,元气未完,辞意新而风格自降矣。”“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奡之气不存。”③分别见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清诗话》下册,第540页;沈德潜选编;刘福元等点校:《唐诗别裁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乔亿也说:“随州‘五言长城’,七律亦最佳。然气象骨力,降开、宝诸公一等。”④乔亿:《剑溪说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224页。
其二,工于炼意炼句,思致新巧。明清盛唐派诗论家多认为这是中唐诗的基本特点,如沈德潜说:“中唐诗渐秀渐平,近体句意日新。”⑤《唐诗别裁集》,第40页。刘长卿则以隽巧见长,如陆时雍说:“刘长卿体物情深,工于铸意,其胜处有迥出盛唐者”,但“巧还伤雅,中唐身手于此见矣。”⑥陆时雍:《诗镜总论》,见《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418页。贺贻孙《诗筏》谓刘诗:“亦未免以新隽开中晚之风。”⑦《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185页。吴乔说:“盛唐不巧,大历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陈浊麻木之病,渐入于巧。刘长卿云‘身随敝履经残雪’,皇甫冉‘菊为重阳冒雨开’,巧矣。”⑧吴乔:《围炉诗话》卷3,见《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56页。不过刘熙载认为刘长卿虽长于练句,却不损娴雅大方:“刘文房诗以研鍊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截断晚唐家数。”⑨刘熙载:《艺概》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1页。这样的看法在清后期诗论中也有代表性。
其三,虚字增多,开中晚唐诗乃至宋诗端倪。谢榛认为律诗“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虚字多则意繁而句弱”⑩谢榛:《四溟诗话》卷1,见《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47页。,所以“中唐诗虚字愈多,则异乎少陵气象。刘文房七言律,《品汇》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虚字者半之”,“凡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岂独始于元白”⑪《四溟诗话》卷4,见《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224—1225页。。
刘长卿诗被归为“中唐第一”⑫《刘随州文集》韩明跋语:“昔人评品随州诗为中唐第一。”(国家图书馆藏弘治十一年本。),其气象骨力不及盛唐,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和他本人的遭遇所决定的,这一点不少学者都已提及。如明汤所说:“随州之诗,其衰世之哀鸣者也。”“岂亦长卿嗟世不如意,不觉其过于伤,犹屈平之《离骚》者欤?”⑬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集部《刘随州集十卷外集一卷》汤序,上海涵芬楼用明正德刊本影印,第1、3页。李东阳也说:“《刘长卿集》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谪故。”⑭李东阳:《麓堂诗话》,见《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79页。这种悲哀凄怨的调子确实已经异乎雄浑壮丽、和平温厚的盛唐气象。
不过从大多数论者的观点来看,时代和个人遭际的原因并非人们关注的重点。许多盛唐派将刘长卿划入中唐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其艺术表现的特点,尤其是以上三点中的其二。由于新隽工巧而导致其诗不同于浑朴宏丽、不求工巧的盛唐诗,这是盛唐、中唐诗气格体调的主要差别。联系明清诗论中的唐宋诗之争的背景来看,盛唐派对中晚唐诗虽也有一些公正的评价,但审美取向大体是偏重于盛唐正格的。因此将刘长卿列入中唐,尽管标为第一,仍不免带有些许贬意。可见随州七律在唐诗史上的定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据的是明清诗论划分初盛和中晚的审美标准。
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争贯串于从南宋到近代的诗学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诗学批评中各种理论派别、理论概念的生成和演变。其中包含着许多诗学问题的争论,例如唐诗研究中的盛唐和中晚唐之争,各种诗体的正宗与变格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诗学批评中的多种审美标准之争。这一争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风貌、格调、神韵等等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也因其带有褒贬的倾向乃至于门户的偏见而掩盖了某些更深层面的问题。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正是如此。虽然由于盛唐派各家评价标准和角度不同的缘故,随州或被列为中唐第一,或置于盛唐和中唐之间,或仍属盛唐王、李一路,但评论者的注意力都是集中于以区分盛唐和中唐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其每首作品,而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在盛唐七律成熟不久、作品不多的这个特定阶段,刘长卿和杜甫各自以其可观的数量成为天宝、大历间七律成就最为突出的诗人。他们对于七律的建设和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笔者曾在《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一文中指出: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优雅平和、高华壮丽,具有成熟初期的不可复制的特殊魅力,但由于题材品种和创作数量较少,也带来了艺术表现的单一性。由此探讨了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的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其意义不仅在于题材、作法之多“变”,更在于其建设七律体式的重大贡献,为后人指出了继续探索七律独特表现规律的方向。那么被视为能接王维、李颀余绪的刘长卿,对七律表现潜力的进一步发掘又有什么贡献呢?这是本文希望能够跳出初盛、中晚之争的思维框架给刘长卿的七律重新定位的主要思路。以下试图从随州七律意境的营造、抒情的结构、情景组合的变化等三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
二
明清一些论者视刘长卿七律为王、李之余绪,主要是取其意境清空、句调流畅这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不在气象的雄浑壮丽。王维七律计二十余首,有将近一半是应制颂圣及应酬之作,以“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为代表,是典型的盛唐气象,李颀也有少数庄严宏丽的作品。但这类诗在刘长卿的七律中极少见,仅一首《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被称为“堪入盛唐者独此”①《唐诗归折衷》:“唐云:文房七律,秀雅清新,骨力欠劲。堪入盛唐者独此。”见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除了这一类以外,王、李的七律多为送别、访客、隐逸类题材,声调流畅,意境清新,格调优雅。刘长卿主要继承了这后一类七律的艺术特色。所以从格调来说,与杜甫七律的雄深浩荡、超忽纵横相比,随州七律基本上是属于“正宗”而非“变格”的。
刘长卿七律最明显的特点是善于写境,保持了盛唐诗以直寻兴会为主的创作传统。再加上其诗歌意象相对单调,多为青山、白云、芳草、夕阳之类,似乎在造境方面没有突出的创造性,只是王、孟等盛唐山水诗境的延续。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孟、李颀等盛唐诗人的山水送别诗中的空灵清秀的意境营造,主要见于五言律诗,而并非七律的主要特点。王、李七律处理情景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人景融合、景中寓情,且以送别为多,虽有写景鲜明清丽的佳句,但像王维五言律和五言绝句中那样空静清幽的意境,则较罕见。而诗风以秀雅清新为主的刘长卿不但善于在五律五绝的山水描写中营造清幽的意境,更将其移植到七律之中,从而进一步发掘了七律的艺术表现潜力。
在游览山水或送别的题材中,随州七律的意境内涵主要是欣赏自然或借景寄托离情,大体上与盛唐诗相同。山水游览诗如《上巳日越中与鲍侍御泛舟耶溪》:“兰桡万转望汀沙,应接云峰到若耶。旧浦满来移渡口,垂杨深处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乡心万里赊。君见渔船时借问,前洲几路入烟花?”②刘长卿著;杨世明校注:《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此诗兴象与盛唐五言诗中描写若耶溪优美景色的篇章类似。但利用七律四联的结构分四层叙述泛舟耶溪的全过程:首起舟随汀转、水接云峰的游程;次截取水漫渡口、绿杨人家的画面;三用东晋永和九年兰亭雅集的典故,将耶溪千年不变的春色和眼前感触连系起来,又在抒发万里乡情的同时关联到当年曲水流觞的雅兴;最后借问路延伸出前洲更有无限烟花的想像,于是在动态的游览中再现了耶溪清幽的美景,又暗含了从王羲之兰亭诗到盛唐山水诗中内蕴的玄趣。又如《送惠法师游天台因怀知太师故居》:“翠屏瀑水知何在?鸟道猿啼过几重?落日独摇金策去,深山谁向石桥逢?定攀岩上丛生桂,欲买云中若箇峰。忆想东林禅诵处,寂寥唯听旧时钟!”①《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535,88,365,395,311,369 页。题目虽为送别,内容却是想像对方游览天台的情景。全诗以一连串的问句想像惠法师游天台的去向和踪迹,串连其沿途的青山、瀑布、石桥、岩桂,以东林寂寞的晚钟作为反衬,构成深山幽寂的意境。七律在初唐宫廷兴起时,也有不少山水游览诗,如武则天时期带领大臣们游览嵩山所写的一批《石淙》诗,还有中宗时期一些游览大臣别业的应制诗,但都是选择典型景物对仗罗列,且多颂圣之词,结构也都雷同,还谈不上意境。这两首诗四联的关系处理都采用了最能保持七律流畅声调的顺叙和罗列的线性结构,类似王维的《送杨少府贬郴州》和李颀的《送魏万之京》,均以行进的指向串连旅途景物和客游心情。但王、李均重在离情,而刘长卿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动态的旅程来写景造境,便扩大了七律在山水游览题材中的表现力。
除山水游览以外,刘长卿更进一步在登望、送别等题材中,探索了七律在空间构图和营造空境方面的潜力。许学夷曾以“体尽流畅”、“语半清空”来概括其五七言律诗②许学夷《诗源辨体》:“五七言律,刘体尽流畅,语半清空,而句意多相类。”见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312页。,感觉是准确的。流畅指声调的特点,“清空”则指意境的营造更为合适。但五律和七律相比,虽然每句只差两个字,两种诗歌体式的发展途径和创作传统却并不相同。五言律每句只有五个字,便于以实字勾勒画面,减省意象。而且从齐梁到盛唐,在虚实、动静、远近、繁简等方面的处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巧,善于用四联的对仗关系组成静态的空间,在构图中尽量简化和淡化意象,以少见多,由虚见实,以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想像的余地,很适宜表现各类清空的意境。七言律则是由乐府歌行和应制诗发展而来,成熟初期只求律赋式的全面平铺,不以取境为意;文字多妆点夸饰,风格富丽典雅,在体调上尚不易和古诗乐府区别开来。加上每句七个字,一般由两个语法独立的词组构成,如都用实字,意象便较五律为密;如要简化意象,则要多加虚字赘词,在空间构图方面还缺少五律那样丰富的经验。
刘长卿充分利用七律自应制诗以来往往以中间两联铺写景物的传统,化用了五律构图写境的原理,善于通过以小衬大、推远视野、简化和淡化意象等处理手法,拓展出空阔寥落的意境。如《登松江驿楼北望故园》:“泪尽江楼北望归,田园已陷百重围。平芜万里无人去,落日千山空鸟飞。孤舟漾漾寒潮小,极浦苍苍远树微。白鸥渔父徒相待,未扫欃枪懒息机。”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535,88,365,395,311,369 页。首联和尾联点出动乱的时局,而中间两联则将微小的孤舟和飞鸟推到天边,反衬万里平芜和苍茫极浦,以落日千山、隐隐远树勾勒远景的轮廓,便在空阔无人的天地中暗示了诗人极目远望而无法北归的无限伤痛。《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汀洲无浪復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④《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535,88,365,395,311,369 页。背岭的孤城和独泊的小舟与水天相连的洞庭秋色相互对照,夕阳衬托出飞鸟斜渡的剪影,又在最远处为这幅空茫的图景画出了边际,使被贬至此的楚客更形渺小可怜。《青溪口送人归岳州》:“洞庭何处雁南飞?江菼苍苍客去稀。帆带夕阳千里没,天连秋水一人归。黄花裛露开沙岸,白鸟啣鱼上钓矶。歧路相逢无可赠,老年空有泪沾衣!”⑤《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535,88,365,395,311,369 页。远帆带着夕阳隐没在天边,沙岸的黄花、钓矶的白鹭等近处的细景又反衬出天连秋水的苍茫。由于强调了近景和远景的对比,凝望中的空间也被远远拓展到视野之外。七言倘用实字,一般每句要两个以上的意象,这三首诗由于将景物构图集中于中间两联,一句一景,意象得以减省。凡一句有两个意象者,都能自身组合成小大对比,如落日千山与飞鸟、夕阳与飞鸟或帆影、连天秋水与一人等,或是取远处视平线的淡淡景物勾勒轮廓,如极浦与远树、去客与平芜等,因而能像五律一样在简淡空远的构图中容纳无边的离情。此外如《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春草连天随北望,夕阳浮水共东流。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⑥《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535,88,365,395,311,369 页。《送孙逸人归庐山》:“彭蠡湖边香橘柚,浔阳郭外暗枫杉。青山不断三湘道,飞鸟空随万里帆。”⑦都是着意用中间两联取景构图,兴象和视野大体近似。
如果说以上几首诗例中清空寥落的意境主要是活用了盛唐五律山水送别诗构图处理空间的原理,那么《吴中赠别严士元》则是对盛唐诗处理动静关系的创新:“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①《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276 页。此诗第三联的意象与上述几首基本相似,但“草绿湖南”一句中高朗的青春气象在长卿七律中比较少见。“细雨”一联因体物之新、感受之细,向来被推为“高妙”的名句。其实细雨、闲花的兴象在王维诗中也是常见的,这里巧妙地利用了七言句后三个字的独立性及其对前四字词组的补充关系,用“看不见”强调细雨的微濛滋润,以“听无声”强调落花的轻柔闲静,传神地表现了春风春雨无声无息的动态,而且将悄然沁透在离人心头的别愁和默然相对的静境也一并烘托出来了。可见刘长卿七律在化用盛唐五律造境原理的过程中,会因适应七律体式的需要而自然地促成艺术表现的变化。
刘长卿诗歌中的兴象虽然大体延续盛唐,但其诗歌中所营造的空境的内涵已悄然变化。盛唐山水诗的审美观照方式和精神旨趣继承东晋而来,典型的空境一般是因澄怀观道而形成的空明虚静之境,又与佛家的空性相印证,其内涵是面向自然的玄趣或禅境。而刘长卿由于身处乱世和自身遭际的原因,其清空意境颇多因怀古伤今而形成的萧瑟空漠之境,其内涵是面对人事和历史的空幻虚无感。如《登餘干古县城》:“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②《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276 页。兀立在楚水西岸的孤城只剩下空芜的官舍、女墙上哀鸣的夜乌和溪水上飞迴的沙鸟,使独对平江落日的远客在这空渺的意境中更易感受到万古的荒凉。《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276 页。诗人独自寻访贾谊故宅,惟见斜阳下的秋草寒林。当其被贬到这草木摇落的湘江边上,才更体会到与贾谊万古相通的逐客之悲。“秋草”一联渲染故宅一片冷落荒凉的景色,“人去后”、“日斜时”又化入贾谊《鵩鸟赋》中“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野鸟入室,主人将去”的语义,巧妙自然地写出了诗人与先贤同命相怜的黯然心境。刘长卿特别善于在怀古和怀人诗里表现这种人去室空的怅惘。如《过裴舍人故居》:“惨惨天寒独掩扃,纷纷黄叶满空庭。孤坟何处依山木?百口无家学水萍!篱花犹及重阳发,邻笛那堪落日听!书幌无人长不卷,秋来芳草自为萤。”④《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裴敦复被李林甫害死,孤坟不知所在,家人流离他乡,惟见故居黄叶满庭、书幌不卷、篱花自开、秋草生萤,山阳闻笛的典故化为落日中的笛声,更增添了物是人非的感伤。有时这种人事变迁的落寞之感充溢在诗人谪宦的行程中,如《使次安陆寄友人》:“新年草色远萋萋,久客将归失路蹊。暮雨不知涢口处,春风共到穆陵西。孤城尽日空花落,三户无人自鸟啼。君在江南相忆否?门前五柳几枝低?”⑤《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276 页。诗人的旅程虽然有新年萋萋的草色和春风一路相伴,然而在满怀失路之悲的楚客眼里,暮雨中的孤城只是一个空有花落鸟啼的无人之境。有时诗人将自己辞别的悲凉融化在友人居处的空寂意境中,如《赴南中题褚少府湖上亭子》:“种田东郭傍春陂,万事无情把钓丝。绿竹放侵行径里,青山常对卷帘时。纷纷花落门空闭,寂寂莺啼日更迟。从此别君千万里,白云流水忆佳期。”⑥《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276 页。这个湖上亭子绿竹遮径,青山对户,门闭花落,日迟莺啼,这固然是赞美主人褚少府吏隐所在的清寂远俗,但结尾设想别后彼此空对白云流水相忆的情景,又似以人去室空的景象烘托出友人独留湖亭的闲静落寞。《送皇甫曾赴上都》则是在行者的回首和送者的凝望中将两地的荒路、暮江连成了一片:“东游久与故人违,西去荒凉旧路微。秋草不生三径处,行人独向五陵归。离心日远如流水,回首川长共落晖。楚客岂劳伤此别?沧江欲暮自沾衣!”⑦《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5,200,214,49,24818676 页。行人在西去的旧路上日行日远,归向三径就荒的五陵故园,回首虽然不见沧江边独自洒泪的楚客,但彼此的离情都像落晖中的长川流水,愈远愈长。于是,沧江日暮、三径秋草、五陵旧路这些不在同一视野中的景物,在两地同对夕阳和长川的互相思念中构成了清空悲凉的意境。其余如《送灵澈上人还越中》、《将赴岭外留题萧寺远公院》等也大都类此。
以上这类诗中的清空萧瑟的意境,都不是依靠拓宽空间的构图处理,而是组合最能表现物是人非之感的若干景物,或是离人心目中共同的伤感印象,烘托出深刻的人事虚幻之感。这种空境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失落空漠在山水景物中的外化和放大,在盛唐五律山水诗中并不多见。其表现则不限于七律中间两联构景的传统,而是可以利用四联的变化更自由地处理情景的关系。所以归纳刘长卿营造意境的上述几种特点,不难见出他对七律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五律山水送别诗营造清空意境的原理,以空茫廓落的境界抒发失意惆怅的情怀,并不露痕迹地将怀古伤今的人事感触融入静照自然的空寂境界,使七律具备了构造内涵更为丰富的意境的能力。
三
刘长卿的七律善用景物营造清空意境,固然是他最明显的特色,但还有一部分七律却是纯粹抒情而不依托景物,故其和杜甫一样开拓了七律抒情的表现功能。初唐七律与乐府歌行同源,在应制诗中成熟,抒情或为应付颂圣的需要,或为游子思妇的代言,少有个人真情的抒发。盛唐诗人提高了七律的抒情能力,使七律进入送别、访客、述怀、杂感、隐逸、登临等私人感情的表现范围,但是不借景物的纯抒情表现还很少。因此刘长卿在这方面的探索值得重视。
刘长卿的七律虽然大多是送别应酬之作,但其中包含的“羁人怨士之思”融合了身世之感和伤时之悲,不同于盛唐七律中常见的离情别绪、乡思旅愁。如《狱中闻收东京有赦》、《非所上御史惟则》、《送侯中丞流康州》等诗诉说下狱和被贬的冤屈;《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赠袁赞府》、《送李录事兄归襄邓》、《谪官后卧病官舍简贺兰侍郎》、《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送耿拾遗归上都》、《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等诗直抒乱离中的谪居之悲,都是他开辟的情感主题。这类抒情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刘长卿特殊的遭际和心境,而且在衰世的哀鸣中寄托了深刻的人生感触,在不遇的怨叹中蕴含着虚度光阴的焦灼无奈。如《北归入至德界偶逢洛阳邻家李光宰》:“生涯心事已蹉跎,旧路依然此重过。近北始知黄叶落,向南空见白云多。炎州日日人将老,寒渚年年水自波。华发相逢俱若是,故园秋草复如何?”①《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33页。在到处播迁的人生长途中,重过以前的旧路,偶遇昔日的旧邻,不能不惊觉生涯蹉跎,人已老去。展望前程,如北路黄叶之飘落;回顾往日,如南去白云之虚浮;光阴在贬谪炎州中日日消磨,流年如寒渚之水空见逝波。这类光阴催人、人生易老的感触虽然是汉代以来诗歌中的老调,却历来是五古咏怀诗的主题,初盛唐七律很少触及。在同时代的诗人中,只有杜甫的七律有相类似的人生感怀,但因境遇与刘长卿不同,也少见逐客骚人之怨。因此前人评刘长卿七律“意深”②方回《瀛奎律髓》卷28评《(经)漂母墓》:“长卿意深不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382页。)方东树:“文房言近而意皆深,耐人吟咏。”(《昭眛詹言》,第422页。),首先应理解为其含意的深刻复杂超过了初盛唐七律传统的抒情内涵。
抒情内涵的拓展和加深,必然要求七律进一步寻求自由地直抒情怀的表现方式。而直抒胸臆本来属于古诗之长,近体之短。自从近体诗在南朝初步形成之后,五言诗在律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古诗不同的创作传统。一般而言,古体结构容量较大、层次变化较多,便于自由直白地叙述、抒情和铺陈,而近调则结构简单,便于大幅度的浓缩概括而缺乏叙述功能;立意聚于一点、避免尽情直陈的创作方式,又发展了思致含蓄、求新求巧的表现倾向③参见拙文:《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七言律诗在初唐形成的过程中,虽然因为与乐府歌行的同源性而不易在句调上区别于古诗,但其结构篇幅的限制与五律相同,也难以像古诗那样尽情直陈,而是要求立意集中,思致含蓄。因此早期七律的结构和表现方式都较单一,不能自由地抒发较为复杂深刻的思想感情。为此,杜甫探索了七律抒情结构的多种变化,刘长卿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他的变化是含而不露的,没有形成杜甫那样明显的“变格”。前人评其“工于炼意”、“研练字句”,已经注意到其七律不同于盛唐七律的特点。所谓炼意练句主要表现为以构思带动抒情结构的变化,这是他和杜甫不约而同的一致追求。
刘长卿直抒情怀的七律看似句意平直顺畅,没有杜甫的拗折腾挪,但大都有一个构思的切入点,使全篇便于围绕立意调动各联各句的配合关系,形成不同的抒情结构,这个切入点便是“炼意”的结果。因此这类诗往往打破七律首揭事由、中间铺展、结尾抒情的传统结构程式,四联的安排顺着抒情逻辑自由展开。如《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赠袁赞府》:“却见同官喜复悲,此生何幸有归期!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湘路来过回雁处,江城卧听捣衣时。南方风土劳君问,贾谊长沙岂不知?”①《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39,436,487,457页。此诗作于上元二年秋,刘长卿由贬所播州南巴县北返,有敕令重推旧案,于是得以回到长洲县官舍。此时正遇扬州刘展之乱刚刚平复。如此复杂的背景和心境,在诗里凝聚为庆幸尚能归来的悲喜交集之情,这也正是此诗的切入点。因此一开头就急不可待地先向同官倾诉见面的激动,然后才由近到远倒叙其归路:颔联交代摇落时节回到旧任官舍,此地刚经过一场动乱的荒凉情景,空庭冷落和旧邑人稀的描述中隐含着回归的喜悦和乱离的悲哀。颈联由旧邑再倒推至贬所的路途:“回雁”、“捣衣”既点秋季,又抒发了自己被远贬至回雁岭的凄凉,以及卧听捣衣所引起的羁愁客思。尾联与首联呼应,在答问中再次抒发了自己与贾谊被贬长沙相同的心情。这种先倾诉后倒推归程的结构,清晰地表现了与同官重逢的激情稍微平息之后才能慢慢自道经历的感情逻辑,又借一路归程概括了自己在乱世中谪宦三年的生涯,在七律结构中颇为新颖。《谪官后卧病官舍简贺兰侍郎》:“青春衣绣共称宜,白首垂丝恨不遣。江上几回今夜月?镜中无复少年时!生还北阙谁相引?老向南邦众所悲。岁岁任他芳草绿,长沙未有定归期。”②《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39,436,487,457页。此诗作于被贬睦州司马任上,也是直抒谪宦之悲,但着眼点在老年被贬、青春不再的绝望。首联以青春衣绣和白首垂丝的对比,画出自己垂老的形象。颔联更进一层,以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和感叹句再次强调来日无多,已非少年。颈联再用问句点出北归无望的处境,尾联直抒不见归期的悲哀,芳草岁岁变绿与首句“青春”呼应,将全篇的嗟叹归结到唯恐在长沙贬所消磨余生的焦虑。全诗形成前四句叹老和后四句伤贬的对称结构,每一联的意思对比都进一步强化上一联的抒情,最终才见出立意,于是产生了古诗般层层深入的抒情效果。《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旧业已应成茂草,余生只是任飘蓬。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此去行持一竿竹,等闲将狎钓鱼翁。”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39,436,487,457页。德宗建中四年至五年,连续发生李希烈、朱泚、李怀光叛乱,朝廷瘫痪。原任随州刺史的刘长卿先居蔡州,后至扬州。贞元元年,贼将李惠登以随州降,朝廷便封惠登为随州刺史。失去原职的诗人心情之愤懑可以想见,所以此诗的切入点集中在失路飘泊的感叹,各联均围绕此意展开。首联以“长安路绝,万里孤云”兴起失路之悲,颔联直陈旧业荒芜,余生唯任飘蓬,点飘泊之感。颈联以比喻和典故暗示失路飘泊的原因:正因朝廷不能高悬明镜,才使自己失落随州刺史之职。“却使他人得楚弓”句用刘向《说苑·至公》篇中楚共王遗弓而不求,任楚人得弓的典故,既暗讽了朝廷的不明,又表达了自己难以明言的怨怼,用意相当微妙。最后联系“避地江东”的题目道出意欲隐居的无奈。全诗结构的特点是:一三五单数句均写长安无路,二四六偶数句均写自己失路,形成三层兴、赋、比的不同对照,层层紧扣立意。可见同是写谪宦之悲,由于立意的切入点不同,各首诗的结构也自然各不相同。
由于结构随立意变化,增加了句联安排的自由度,刘长卿的不少七律还能达到古诗那样曲折尽情的艺术效果。如《送耿拾遗归上都》:“若为天畔独归秦?对水看山欲暮春。穷海别离无限路,隔河征战几归人!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④《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39,436,487,457页。此诗切入点在友人乱离之中独自归秦的不易。诗人将送别诗首联一般先点事由的格式转化为突兀的问句,先问对方为什么独自归秦的理由,惊诧、欣羡、担忧等等复杂的心绪都从中涌出。然后再感叹穷海相别,路途遥远,尤其在北方征战未息之时,能有几人归去,这就更强调了“天畔独归秦”的艰难。颈联因含义丰富而成为人所激赏的名对:诗人欲“借”回归长安的友人传递万里之外的“双泪”,不仅是惜别之泪,更是报国无门的忧时之泪;而寄一身于建德千峰之中的对照,也不仅是夸张离别之后的孤独,更有无法离开山中的忧伤。至此意思似乎已经完足,尾联又跳过一步,添出一层忧虑:设想对方在途中邮亭驻马时定将愁绪满怀,此愁固然是“穷海别离无限路”之愁,更是隔河西望战争烟尘的家国之愁。全诗在万里相别的悲哀和穷海失路的凄凉中,交织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对友人独自归秦的羡慕和途中风险的隐忧,多重含意由首句之问领起,表达得曲折尽情,而又天然清健。《送李录事兄归襄邓》:“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①《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58,437,536,236页。同是抒发乱离中的送人之悲,此诗着眼于行者和送者命运的分合和心境。前四句将两人相同命运合写,后四句以两人不同去向分写,形成递进的两大层次,而前后半首中的两联又自成递进:十年多灾多难,共同遭逢乱世,都似转蓬流离失所。等到战后相逢,却以白首相对,青春已在乱离中消逝。颔联中的人生况味只有亲身经历长期动乱的人才能体会,因此被方东树誉为“圆警精美,气味沉厚”②《昭昧詹言》,第422页。。然而短暂的重逢之后是更远的离别,所以“此别”之“恨无穷”,不仅因为云水阻隔、天涯相望,更承担了十年乱离的感情重压。其抒情的深度就非一般的离别可以相比。《戏题赠二小男》写老来得子的心情,虽是日常生活的题材,还是归结到流寓的身世之悲:“异乡流落频生子,几许悲欢并在身。欲并老容羞白发,每看儿戏忆青春。未知门户谁堪主?且免琴书别与人。何幸暮年方有后,举家相对却沾巾。”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58,437,536,236页。首联为全诗立意所在。以下三联都围绕悲欢交并的意思,抒发自己的矛盾心情:流寓之中得子固然可悲,却又因儿戏的天真而带来青春的回忆和欣喜;不知二子将来谁主门户的猜测,既有对后辈琴书传家的期望,也暗含着自己见不到幼子成人的悲哀;所以暮年有后虽值得庆幸,但举家流落异乡,又令人流涕。全诗句意淋漓,不断转折,使悲喜之情反复交错,可谓尽“曲折顿挫之致”④纪批:“三句不明晰,五六极曲折顿挫之致。”纪晓岚批点,方回原选:《〈瀛奎律髓〉刊误》,台北:佩文书社,1960年,第1352页。。
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刘长卿用七律直陈其乱世谪宦之悲,虽然多首情感主题类似,但因为切入点和结构多变而各有新意,且都能曲折尽情,这就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自由度。除此以外,其他主题的诗篇也往往能根据抒情的逻辑讲究结构的安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诗加大了七律中间两联对比的力度和跨度,不但强化了抒情的效果,其顿挫感亦与杜甫七律相近。如《送开府侄随故使君旅榇却赴上都》:“征西诸将莫如君,报德谁能不顾勋?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擒生绝漠经胡雪,怀旧长沙哭楚云。归去萧条灞陵上,几人看葬李将军!”⑤《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58,437,536,236页。此诗立意在于赞美其侄护送开府李使君之棺木回京归葬,能不顾勋功而知恩报德。中两联先以其侄赴边万里的豪气与披草看坟的凄凉造成反差极大的对比;接着以绝漠擒敌的经历和长沙哭主的情景再度进行同样的对比,两次起落顿挫,突出了“开府侄”豪勇雄毅而又深重情义的形象。结尾以李广闲居灞陵为人欺辱的典故为喻,感叹已故使君身后的寂寞和世态的炎凉,更反衬出“开府侄”品格的可贵。又如《送侯中丞流康州》:“长江极目带枫林,疋马孤云不可寻。迁播共知臣道枉,猜谗却为主恩深。辕门画角三军思,驿路青山万里心。北阙九重谁许屈?独看湘水泪沾襟!”⑥《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58,437,536,236页。侯令仪原为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被冤除名,流放康州。此诗首尾两联化用屈原《招魂》和宋玉《九辨》句意,同情其被流放岭南的命运,中两联直接为侯中丞大声叫屈。颔联将为臣的冤枉和君恩的寡薄加以鲜明对照,既为逐臣辩诬,又揭示了君主的信谗多疑,尤其大胆激烈。颈联以辕门画角所流露的三军之思和流放者途中的悲凉心情再作一层对照,军中对中丞的爱戴与君主的猜谗也形成一种对比,这就更进一步强调了诗人对“臣道枉”的深深不平。以上两首诗都因中二联对比的强烈而使诗情更加跌宕起伏,而中间两联确实是七律结构的重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长卿善于强化七律体式的特长以拓展其抒情容量的努力。
四
刘长卿对七律表现潜力的开拓,部分重在写景造境,部分重在直陈其情,但并不等于说这两类诗将情景截然分开,只是在表现的探索上有所侧重而已。其实,他更多的作品是在融合情景的表现中追求深刻的思致,故考察其善于炼意的特点、情景组合的创新和变化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前人称刘长卿七律“皆有余味不尽之妙”①方东树:“七律宗派,……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余味不尽之妙矣!”见《昭眛詹言》,第419页。,特别是像《过贾谊宅》这类名作,因用典不着痕迹而特别耐人寻味。但除了擅长用典的原因以外,笔者认为还与他在写景中别有寓意的探索有关。这里所说的寓意,不是指他营造的清空意境中自然蕴含的失意落寞或人事虚无的感触,这类诗固然能做到兴在象外,但仍属于盛唐传统的表现。笔者所指是他另有一类诗,善于借助景物的组合表达特定的用意,亦即写景取象在兴会之外还别有其他意思可以体味。有时其兴象含义之深可以使诗中立意得到进一步生发,如《汉阳献李相公》:“退身高卧楚城幽,独掩闲门汉水头。春草雨中行径没,暮山江上卷帘愁。几人犹忆孙弘阁?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还丞相印,十年空被白云留!”②《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51,534,141,532,529页。李揆于乾元二年后罢相被贬,在江淮养病十余年。此诗前四句粗看只是写李相公幽居环境的清空幽雅。但春雨濛濛,草没行径,可见李揆罢相后门庭冷落,无人到访,令人想见世态的炎凉。江上卷帘,独对暮山,夕阳和江水的意象中又暗含流年之叹和迟暮之愁。这就使结尾惋惜李相公在闲居中白白消磨十年的感慨更为深沉。《酬屈突陕》:“落叶纷纷满四邻,萧条环堵绝风尘。乡看秋草归无路,家对寒江病且贫。藜杖懒迎征骑客,菊花能醉去官人。怜君计画谁知者,但见蓬蒿空没身!”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51,534,141,532,529页。诗里通过环境描写,刻画了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因此前四句都围绕着与世隔绝这一点来安排景物:四邻落满黄叶,家中环堵萧条,可见隐士的住所周围不见人迹。所住之乡只见秋草,不见归路;家对寒江,又增加了一道隔离世俗的深堑,说明隐士与外界的交通也已断绝,颔联两句将“乡”和“家”两个字置于句首,更突出了写景中的用意。《送陆灃仓曹西上》是一首用意委婉的名作:“长安此去欲何依?先达谁当荐陆机!日下凤翔双阙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从故里难移棹,家住寒塘独掩扉。临水自伤流落久,赠君空有泪沾衣!”④《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51,534,141,532,529页。诗人对陆灃西上投靠何人、能否得到推荐持有疑虑,因此首先连设两问。次联想像对方西上途中日远路遥、雪大人稀的景色,似乎只是渲染中原的萧条冷落。但“日”通常喻帝,凤翔双阙之远,不仅指唐肃宗行在的遥远,更有前途艰难无助、到达日边恐怕遥不可及的含义在。这一联实际上是用写景暗示了首联中的担忧之意。
有时其取景的意象可令读者在抒情主线之外产生更多的联想,如《双峰下哭故人李宥》:“怜君孤垄寄双峰,埋骨穷泉复几重!白露空沾九原草,青山犹闭数株松。图书经乱知何在?妻子移家失所从。惆怅东皋却归去,人间无处更相逢。”⑤《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51,534,141,532,529页。全诗哀悼李宥埋骨穷泉之凄凉,双峰下孤垄周边一片空芜萧瑟,已足见其身后的幽独寂寞,而妻儿移家、图书散失,更可见与李宥有关的人事遗迹也一并化作空无。所以人间无处再相逢的悲哀就更加深切。颔联中取白露沾草的意象,固然是描写秋草凋零的荒凉,但也令人想到诗人空对坟茔、泪洒秋草的情景;几株青松,或是墓边实景,但“青山犹闭”四字不但关联到死者长闭于青山之中、与世长绝的意思,还隐约寄寓了诗人对故人品格的赞美以及对其命运的痛惜,其中深意颇耐寻味。《题灵祐和尚故居》:“叹逝翻悲有此身,禅房寂寞见流尘。多时行径空秋草?几日浮生哭故人!风竹自吟遥入磬,雨花随泪共沾巾。残经窗下依然在,忆得山中问许询。”⑥《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51,534,141,532,529页。刘长卿怀人悼亡,善以空境烘托,但此诗中的逝者是一位僧人,所以取景中暗含禅意。首句直抒伤逝之情,却不悲逝者已去,反悲自己有身。因反观存者此身,本来如同禅房中之流尘,也将归于空无真境。于是首联次句就不仅仅是描写禅房寂寞,惟余积尘,而是包含了以佛家之空观看待生死的深微含义。由此再看禅房之外当初行径空余秋草,更加感叹尚有几日浮生可以痛哭故人。同样,风竹自吟,与寺里的钟磬之声遥相应和,固然是感慨景色依旧,斯人已亡,又似乎是借以警醒存者参透大化。全诗表面意思只是睹物思人,但如果联系写景中的这层似有若无的禅意来看,诗人又像是极力以禅理解脱,却终究不免伤情,这样理解就比一般的叹逝之作更加深刻。由以上诗例可见,长卿七律写景中的寓意或显或隐,有时须细读方能意会,有时虽能意会,也不易言传。这类深刻的思致在盛唐七律中较为罕见,且较之同样“意深”的杜诗更加不着痕迹。《唐诗镜》对五七律艺术表现感觉的区别有一个精要的说明:“五律贵响亮精工,七律贵深沈(沉)蕴藉。”①陆时雍:《唐诗镜》卷29,附《经漂母墓》后评。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第602页。刘长卿七律因善于炼意而形成深沉蕴藉的特色,正是他在探索七律独特的艺术表现感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情句和景句的组合方面,长卿七律的句式变化虽不如杜甫明显多样,但也有一些创新之处。如前引《题灵祐和尚故居》前六句分别以一句写景和一句抒情对仗,景句和情句的内在含义互相生发,对法比较少见,难度也大。《送马秀才落第归江南》“南客怀归乡梦频,东门怅别柳条新。殷勤斗酒城阴暮,荡漾孤舟楚水春。湘竹旧斑思帝子,江蓠初绿怨骚人。怜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泪满巾!”②《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79,486,488—489页。从第二句到第六句,每句都是半句情加半句景。但颔联使春水暮色成为离别场景的烘托,颈联以骚人的失意移入湘竹江蓠,使对仗错落有致。《郧上送韦司士归上都旧业》:“前朝旧业想遗尘,今日他乡独尔身。郧地国除为过客,杜陵家在有何人!苍苔白露生三径,古木寒蝉满四邻。西去茫茫问归路,关河渐近泪盈巾!”③《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79,486,488—489页。韦司士祖上原封郧上,如今却成他乡过客,而独归上都旧业,又无家人可依。此诗从韦司士的这一特殊境遇着想,前两联分别以郧上封地和上都旧业交替对仗,强调其两地都有祖业却无处栖身的可伤。然后借颔联对句自然转折,扣住送归上都的题意,引出杜陵旧业的荒凉景色,使后两联顺势而下,情景过渡自然流畅。《喜朱拾遗承恩拜命赴任上都》:“诏书征拜脱荷裳,身去东山闭草堂。阊阖九天通奏籍,华亭一鹤在朝行。沧洲离别风烟远,青琐幽深漏刻长。今日却回垂钓处,海鸥相见已高翔。”④《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79,486,488—489页。全诗之意不过是祝贺朱拾遗被征为官,但句联关系的处理独特。四联将朱拾遗接受朝廷征辟与离开隐居所在的情景分四层对照:第一层为接受征拜,离开草堂;第二层写当初华亭一鹤,现已身列朝行;第三层再强调他已远离沧洲,身在宫廷;最后以垂钓之处海鸥高翔的比喻说明其旧居已经没有可与海鸥相狎的隐士。各联用不同句意将朝堂为官和在山隐居的两种生活情景反复对照,在顺叙的脉络中因不断回顾而形成顿挫。如果不看题目中的“喜”字,这样来回对比,尤其是嵌入华亭鹤和海鸥的典故,很容易使人猜想诗人在贺喜之外似乎还别有讽意。刘长卿像盛唐诗人一样只用浅近的常见语和习见字⑤方东树评《青溪口送人归岳州》:“文房只用眼前习见字习见语,而无一意不深,无一字不灵。”见《昭昧詹言》,第423页。,因此在句式结构方面的这些变化往往不易觉察,与他的构思一样巧而不露、深意内敛,所以前人又以“新隽”称之。可见他虽然能继承盛唐王、李的传统风韵,但只要继续探索七律的表现潜力,就必然走向工于炼意、研练字句的方向。
综上所论,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接续了王维、李颀的余绪,其清空的风格、流畅的声调,更多地保持了盛唐七律“正宗”的风貌。在此基础上,他将盛唐五言山水送别诗写景造境的原理用于七律,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以构思立意调动句联的配合,形成变化多端的抒情结构:既将古诗直抒胸臆、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又深入探索了情景关系的多种处理手法,从而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明清诗论因其“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将他列入“中唐”,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未能着眼于七律体式建设的历史趋势。刘长卿的创变虽然含而不露,没有明显改变“正宗”的韵调,但与杜甫的“变格”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构思和炼意,这就证明无论“正”、“变”,“工于铸意”其实是七律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