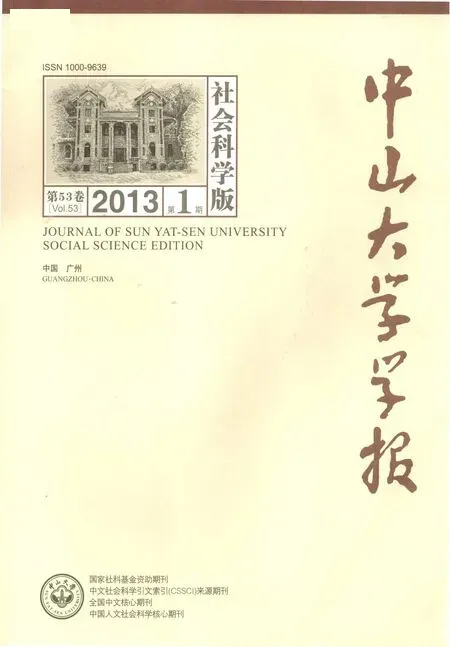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及其庸俗性*
朱富强
一、引 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着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从而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日益偏盛:它不仅基于“无形的手”、科斯中性定理、帕累托效率原则以及“似乎”假说等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甚至还进一步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构建数理模型或计量实证,使这种理论“客观化”和“精确化”。而且,即使面对着市场机制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也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原则鼓吹市场并否定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教条,以及对市场机制想当然的肤浅理解,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贯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信条,往往把时下社会工资水平等都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从而将现实合理化并激烈反对受到社会大众和社会改革者们欢呼的《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等。同时也否定收入再分配的正义性,主张实行所谓的“平税制”。
实际上,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人的需要及其变化,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康芒斯指出:经济学是处理人类努力谋生或努力致富时的各种问题。因此,经济学者首先关心有财富的市场和收益的分配所阐述的各种问题①[美]康芒斯:《集体行动的经济学》,朱飞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9页。。尤其是,经济学要关注穷人福利的提高:一者,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满足;二者,富人的快乐和幸福也需要以社会生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否则就会面临着安全、交往等方面的负体验效用。正因如此,经济学不仅应该关心市场和效率,而且也应该关心公平、正义、自由和人的尊严,应该将市场竞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既然如此,社会经济制度的设立和改进不应该关注弱势者的诉求吗?人类社会不应该制定向穷人倾斜的分配制度吗?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都只是伦理和道德的,而非经济科学研究所应涉及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从而推出了一系列对穷人非常危险的政策。本文基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二分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因“伦理不及”而产生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困境进行剖析。
二、经济思想史中两个代表性案例阐释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将世界看成是和谐一致的以及存在即合理的,因为社会个体都是理性的自利者,个体互动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预定协调”功能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为此,它强调经济学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伦理学和讨论福利问题,而是要建立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纯经济理论体系”。显然,一旦将经济学中那些“不科学”的伦理学命题消除掉,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此时,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正是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偏爱和选择:它刻意地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靠拢,试图通过大量使用数学来使得经济学更加客观和科学,甚至认为经济学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使用更高阶的数学工具,来将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逻辑化、严密化。问题是,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强调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的“经济”,“经济”总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环境中并打上特定背景的烙印①[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同样,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总是“嵌入”特定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环境中,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道德约束下完成的,离开道德环境,就不可能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有效的解释。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往往相去甚远,依其结论而推行的政策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了社会业已存在的问题。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运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推理的数理逻辑越来越严密,但是,其思想深度却并没有多大实质进展,基本上还是沿袭和继承甚至是停留在19世纪中叶以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以及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和巴斯夏等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那个阶段。科斯曾指出:在过去两百年里,我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分析当然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并没有显示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的更高明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方法还不如亚当·斯密②[美]科斯:《国富论》,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同样,亨特也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已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形式,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学学生可能花了多年时间仅仅学会了这种分析根据和技巧,并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变得一无所知……深奥的数学“烟幕”并未掩盖这些价值观。但是,这些在现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模糊的但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基本上与明确反映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作品中的那些观点相雷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作品开始逐渐地掩盖了这些价值观,最终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③[美]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3页。。为了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思维及其相应政策上的缺陷,这里以古典主义后期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学说为例加以剖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者,他们是当时最主要的经院派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说史的重要人物,大师们的思想和认知比一般学者更值得关注;二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比目前一些学者更为大多数经济学人所熟悉,从而使得这里的分析更便于读者理解。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反社会救济的观点
马尔萨斯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一个主持东印度学院有关历史、政治、商业与财政的讲座,也被认为是最早、并且是他那个时代惟一的专业经济学家;其研究思维不仅直接地指向了马歇尔体系而成为马歇尔体系的真正先驱,而且潜含的自然选择思维又产生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尽管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涉及到对货币的分析、分配理论以及一般过剩理论等众多方面,但他主要以人口理论出名,而且,他的其他理论几乎都是以人口理论为基础。基于人口学说,马尔萨斯几乎反对任何类型的社会救济和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强烈反对英国自1601年开始实施的由教区向穷人提供粮食、衣物、住所等物质帮助的旧济贫法。在马尔萨斯看来,给穷人更多资助的济贫法不仅会鼓励懒惰和浪费,而且会促使他们建立自己不能赡养的家庭,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下来,从而进一步“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①[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页。。相应地,马尔萨斯主张应该将穷人收容到“贫民习艺所”;而“贫民习艺所”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制度,在那里穷人生存的条件是彻底放弃做人的起码尊严。事实上,后来马尔萨斯提出的济贫法修正案获得了采纳,而该修正案对被救济者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这包括全部财产的抵押,甚至家庭的拆散。同时,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也影响了他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尽管马尔萨斯先驱性地洞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使得社会产品总值不能实现,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但是,他却极力否定通过收入分配来提高有效需求,因为他认为,改善劳动者生活将会刺激人口增长,最终依然会陷入社会贫困。基于这种思维,马尔萨斯强调,要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最好的办法是维持不生产者的消费,从而强调了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只买不卖的阶级;增加有效需求的另一途径就是增加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阶级的支出,如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②[英]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厦门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显然,马尔萨斯的政策主张与当时绝大多数社会改革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大多数社会改革者都继承了启蒙运动所激发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人类会逐渐走上成熟、人性可以不断完善,只是邪恶的制度限制了人类理性的成长而降低身份和带上枷锁;理性使人类有能力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平衡,从而最终使人类逐渐走向进步和光明,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例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出版的《政治正义论》就强调:德性依赖知识和理性,一个人的性格取决于他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由遗传决定的,一个完美的社会可以创造出完美的人,因而通过不断培养更高的理性及不断增加福利就可以促使人类不断完善;而人类理性进步的主要障碍则是财产私有、经济政治不平等和国家的强制,社会的灾难和不幸也源于私有制,因而废除私有制后人类理性将得到完善,此时人口过剩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样,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提出:人性是可以完善的,社会终将走向进步,战争将被消除,不平等将被平等取代,教育将普及;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将会增加,但借助于技术和知识的进步,食物的供给增长会快于人口增加③[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一直成为社会改革者和文人的批判之薮,甚至其本人也被视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例如,葛德文女婿、诗人雪莱就批判马尔萨斯抑制人口的措施违背人类的道德良知,斥责反对济贫法的马尔萨斯是富人的传道士。托马斯·卡莱尔在一次演讲中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抨击: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这门科学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④转引自[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二)西尼尔的纯经济理论与其政策主张间的悖论
西尼尔是牛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被认为是李嘉图之后惟一一位深入探究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其经济思想力图摆脱古典经济学而倾向于1870年以后取得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西尼尔时代,由于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发展,经济学家被卷入了反映社会冲突中各种利益集团地位的规范化或伦理学的阐述中,比较注重研究社会福利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学理论存在许多的争论。与此同时,学院派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向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理论化”方向发展,经济学家也在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势下,西尼尔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从而成为纯理论的倡导者。在西尼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是论述自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科学”,而不是有关福利问题的讨论;相反,只要伦理学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构成部分,科学进步就永远也不可能使经济学家达成一致。同时,一旦将经济学中那些“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消除掉,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此时,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而这些结论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伦理学家和立法者所关注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应该是目前所谓的实证经济学,而不是规范经济学,对财富、善行和制度改革进行讨论不在经济学范围之内,而应留给国会议员去讨论。然而,西尼尔又热衷于为政策开出药方:不但在几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工作过,而且也曾从事数量颇为可观的事实调查工作。结果,在西尼尔提出的政策主张与其纯经济学理论主张之间,往往就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
事实上,西尼尔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强调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他的“方法”要求经济学层面的分析要撇开福利和伦理因素,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与其他学科割裂开来。因此,他的政策主张往往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劳动者或穷人会非常危险和“不伦理”,而明显体现了为现实制度和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的性质。第一,西尼尔极力反对当时社会改革家提出的对雇佣童工进行限制的奥尔索法案。其理由是,这个法案把经济损失强加给了9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不能在纺织厂劳动更长的时间,从而就失去了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机会。但问题恰恰在于,正是由于大量劳动的供给,使得雇主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工资,从而最终损害了这些家庭的利益。所以,奥肯指出,社会禁止你出售权利,这显然是侵犯了你的自由,但同时也保护了你,以防他人夺走你的权利。在奥肯看来,正因为法律禁止将权利作为最后求救手段,从而堵住了陷于绝望和困难者的某些潜在出路,因而社会就必须有更好的方式来防止或减轻那些绝望。譬如,当禁止使用童工后,寡居的母亲和残疾的父亲想从年轻的子女所挣的工资中得到收入的机会被剥夺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就是一个援助困难者的更好方式①[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9页。。第二,西尼尔极力反对当时法定的10小时工作日,其所持的理由就是“最后一小时工资”理论。问题在于,西尼尔错误地认为,一个劳动日减少一个小时将减少变动成本和产出,但却不影响固定成本;其实相反,劳动的减少将迫使厂房和设备闲置,从而增加每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负担。熊彼特甚至指出,西尼尔是能干的,但是,打瞌睡的时候太多了,也即蠢话说得太多了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6页。。第三,在济贫法上,西尼尔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并作为“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主笔完成了制定新济贫法的报告,提出了严苛的改革建议。实际上,他的提议与其说是一个经济解决方案,还不如说是一个压迫的和退化的机制。例如,作为对贫困的惩罚,它强制劳动者进入像监狱一样的工厂,强行分开丈夫、妻子和孩子,甚至打消他们生育出更多贫民这一危险的诱惑。
总之,从欧洲诸国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改良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景象:一者,许多关注社会进步和完善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社会的改革,并成为一系列法案的积极支持者或推进者;二者,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却反对社会改革家提出的各种改革,而极力维护原来的秩序。事实上,禁止棉纺厂雇佣9岁以下童工并规定所有16岁以下童工的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最早就是社会改革家欧文推动的,但这些规定曾遭到棉纺厂雇主们的强烈反对,而注重福利经济学分析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则往往为雇主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例如,马尔萨斯就反对扶助穷人、反对济贫法、维护既存的谷物法;同样,西尼尔不仅在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援助上反对奥尔索法案,而且在弱势群体的力量联合上反对行业工会运动。那么,学院派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待社会改革的思维上为何存在这种差异呢?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正体现出:经济学本身的无道德性或“伦理不及”性。纯经济学理论强调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以致即使其政策主张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劳动者或穷人是如此危险、甚至有悖于基本人伦,他们也能够基于所谓的“客观”和“科学”分析而心安理得。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就强调,经济分析应该基于理性逻辑之上,而不能由社会大众的投票决定。而且,正是基于所谓的逻辑分析,他们理直气壮地提出一系列的有悖于基本人伦的政策建议。问题是,难道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意味着反道德性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是否已经成了社会实践的制约呢?沃勒斯坦指出:正因为把价值排除于社会研究之外,因而19世纪的研究是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9页。。
三、现代经济学“能够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
上面从两个例子来说明主流经济学家所开出的社会政策之荒唐性,为什么说荒唐呢?因为他们的思维与民主社会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是相左的,政策主张与社会发展也是明显背道而驰的,对社会大众更是危险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又似乎都是建立在“严密”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逐利的本能、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棉纺厂的雇主们之所以反对改变现行的法规,也就是从经济上寻找依据的,如新的禁止童工的法律将使得产品更为昂贵,乃至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竞争力下降、工厂倒闭和失业,也会降低那些无法再利用小孩工作之家庭的收入。经济学家只不过将雇主的这些关注理论化和系统化,并赋予了效率思维。正是基于静态的经济计算,学院派经济学家就起而反对这些制度变迁。事实上,正是基于效率和经济考虑,马尔萨斯对穷人总是抱有一种极端冷漠、残酷甚至有些变态的“理性”态度,他为此甚至被认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然而,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为马尔萨斯进行辩护,因为他们基于同样的效率原则。例如,施蒂格勒就强调,经济学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他们只能“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因此他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善意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就算提供了坏的消息、作出悲观的预期或者对政策作出尖锐的批判②[美]施蒂格勒:《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前言。。而马尔萨斯之反对济贫法,所应用的不过是经济学的逻辑,即使他的主张违背了穷人的利益,却符合社会进步的原则,因而应该得到支持。
显然,基于效率原则为那些引起社会大众反感的社会现实进行辩护也是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的特性。譬如,当社会大众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房价高涨等现象极度不满时,一些经济学家却热衷于为此类现象提供合理化经济分析乃至鼓吹。而且,这些经济学者还宣称,自己的结论都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而那些批判者则是无理性的愤世者。问题是,经济学根本上不是要关注人们的福利吗?而福利本身不是与人们的切实感受联系在一起吗?那么,经济学又如何撇开社会大众的感受而强调其研究的理性和客观呢?学院派经济学者从效率角度来论证诸如限制童工、减少劳动时间以及提高基本工资等制度变迁和改造的无效性,而社会改革者却质问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让孩子们仍待在棉纺厂里而不是在学校读书,难道符合文明的进步吗?让那些农民工们冒极大的危险来取得微薄的生存工资,难道符合社会正义的发展吗?其实,效率本身只是一个实现特定目标的速度指标,从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出发,以多大的成本来实现孩子的学校教育和农民工的应得权利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此权衡过程显然就涉及到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布罗姆利指出:制度变迁考虑的是特定的制度安排会使哪些人的利益提高,哪些人的利益受损,这些选择本质上就具有分配的性质①[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姚洋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显然,这些都揭示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犯了巴斯夏所称的“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的错误。
(一)如何评估庸俗经济学家及其学说
巴斯夏的长篇论文《人们看到了什么和没有看到什么》虚构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顽童不小心打碎了一家面包店的橱窗,一帮看热闹的人开始从经济方面思考这一事件,他们得出结论:这个开始看起来是一个有害的破坏行为,却由于玻璃装配行业可获得额外的收益而成为从经济上看是一积极性的事件。因为店主会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就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亦即,从破坏中诞生了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但是,巴斯夏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些人仅仅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因为,此事的全部积极效应只是对玻璃装配商而言的,因为被打碎玻璃的主人现在要为装修付钱,而这一支出不是为了有益于经济的目标。例如,面包店店主本可以用那笔钱来购买新书或新鞋,现在则不去买新书或新鞋了,结果,书商或鞋商就成为了牺牲品,这却永远也不为人们所知。显然,那些好心的、涉足经济过程中的人从来没有比较准确地描写这种看不见的副作用,没有考虑到除表面当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书商或鞋匠——的利益。显然,“破窗理论”揭示出了某些经济学家在研究视野上的狭隘,因为他们往往是在既定的框架内提出并分析问题,他们的思维经常被成见所禁锢,从而这类视野狭隘的经济学家就不是“好的经济学家”。为此,巴斯夏指出:一个坏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经济学家的惟一区别是:坏的经济学家局限于可见的影响;好的经济学家则既考虑可见的影响,也考虑那些必须被预见的影响②转引自[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即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③参见[德]多林:《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载[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许明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按照巴斯夏的“破窗理论”,好的经济学家往往表现为深刻的认知和深入的洞察、广阔的视野和透彻的理解;而坏的经济学家则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一般地,一个经济学家视野的广阔程度往往取决于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认知能力层面,这主要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二是意识形态层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态度。同时,人的大脑及社会实践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认知的有限性,对于客观真实的世界,人的认知只能停留在相对的水平。既然人的认知的局限性是客观和必然的,人的视野的狭隘也即是客观而绝对的。因此,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努力追求突破这种局限性并能够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而坏的经济学家也不过是甘于屈从或者无力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④赵峰:《坏的和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6月6日。。显然,按照巴斯夏关于好的或者坏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马尔萨斯和西尼尔都是有着严重视野局限的经济学家,因而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关于这一点,我们主要以马尔萨斯为例加以剖析。
其一,就认知能力的局限而言。马尔萨斯对人口发展的观察仅仅体现了当时的一般现象,而这一现象早在其150年以前就为威廉·配第在《人类与政治算术》一书中详细描述过。同时,他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也为很多学者提出过,如坎梯隆就认为如果缺少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就会像仓中的老鼠一样倍增,而孟德维尔则提出了用罪恶来限制人口增长,并把外科医生和吸毒者都包括在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措施之中。中国清代的洪亮吉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人口增长问题,并断言生物界相杀的现象“不过恃强弱之势,寡众之形”,并提出了比马尔萨斯更为全面的两类措施:天地调剂法(即水旱疾役)和君相调剂法①(清)洪亮吉:《意言·百物篇》《意言·治平篇》,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年,第431、434 页。。显然,马尔萨斯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仅仅论述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只是从自然层面来认识贫困和饥荒的原因。他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没有探究影响供求的结构因素,从而无法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贫困和饥荒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马尔萨斯对现象的分析还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一者,他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是根据当时美国的数字,而当时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是外来移民激增而不是自然繁殖;二者,他关于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基础是西欧诸国日益显现出来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因为西欧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而呈现出日益的有限和稀缺性。正因为马尔萨斯一方面利用了美国的人口数据,另一方面却利用欧洲的土地数据,从而在数据上就存在严重的张冠李戴现象。
其二,就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言。马尔萨斯学说中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他所持的意识形态上:一者,马尔萨斯是一个自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只有最优者才能生存,而政府救济则会导致那些“不适者生存”,从而违反了自然法则;二者,马尔萨斯信奉人类的不幸是源自上帝对“原罪”惩罚的宗教信仰,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层”没有能够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而改进人类境况的那些措施如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其实无济于事,社会进步方面的每一种努力往往都会导致不可抑制趋势的灾难。在马尔萨斯看来,尽管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但上帝并没有承诺给予人类充分的理性。例如,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上帝赋予人们生育的能力,同时给予人们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但他从来没有承诺二者的平衡。马尔萨斯强调,如果上帝必然要惩罚人类,那么,灾难就是人类的宿命。因此,马尔萨斯终身都是富人利益的辩护士,他对穷人的艰难处境似乎从来没表示过同情。而且,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马尔萨斯对当时的社会改良措施和学说持有强烈的抵制和反对态度。例如,早在马尔萨斯之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已经关注人口问题。孔多塞认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他们的生存手段”就会导致“或是幸福和人口的持续下降的一种真正的退化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某种徘徊”。但同时,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并且,孔多塞还展望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这种类型的理性思维主要是通过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来促使人们自愿选择这么做②[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在此之后,西斯蒙第也强调资本主义人口过剩只是相对人口过剩,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就可以为防止“与收入不成比例的人口增加”。而且,西斯蒙第还主张,通过教育等形式来降低或停止生育,强调“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③[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8页。。在很大程度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作为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一种科学贡献,而是作为对葛德文、孔多塞和欧文等关注用社会立法手段来改善人类社会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并为维持生存工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为何现代主流经济学说如此狭隘
正是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经济学家往往反对国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反对任何改变当前社会力量结构的政策和行动,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马尔萨斯和西尼尔身上,也广泛出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身上。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都与西尼尔一样,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反对集体劳动权,这可以从近年我国制定和推行《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所遭受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和反对声中窥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只是继承了以“导师”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道:最低工资法也许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其影响和善意支持该法规的人们的意图恰好相反的最明显事例……事实上,如果最低工资法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它们的影响显然是增加贫穷。国家能够通过立法制定一个最低工资率,但它很难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资雇佣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资率以下被雇佣的人。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雇主利益的。因此,最低工资的影响是使失业多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况。就低工资确实是贫穷的象征而言,那些因之而失业的人们恰恰是那些最经受不起放弃他们一直在拿收入的人①[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3页。。显然,这里弗里德曼和西尼尔一样没有看到那些不能看到的东西:一者,实际生产并不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收入分配也不是决定于劳动贡献而是力量结构,最低工资立法只是提高劳动者的一点谈判力量,减少雇主的一点收益;二者,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对立的,而且两者的总和生产力以及相应的总收益往往取决于两者的关系状态,更为公平的收益分配往往有助于总和生产力的提升。事实上,从纵向比较来看,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设有不同程度的劳动保护法,但失业率显然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而且,即使横向比较来看,那些收入更为平等的国家也并非会产生更高的失业率,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生产率往往更高。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不仅严格限制了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发现,而且也限制了他们对问题解决的视野宽度,这里举一例说明。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几家电台搞了一个访谈,一位节目主持人问卢卡斯:你认为美国经济怎么样?卢卡斯马上说道:还可以(It's okay)。而没有再往下说一个字。节目主持人呆了,问他:没有任何话要讲了?卢卡斯回道:我已经说了It’s okay。于是,一分钟不到节目全部结束。但实际上,当时美国社会经济潜含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作为一位对社会经济问题应该保持敏锐性的经济学家竟然说:一切都没问题。当时,经过里根时代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降低富人的税收,削减穷人的社会福利等,使得社会不平等持续上升,贫富之间的鸿沟已经逼近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桑德尔指出: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变糟了。财富分配也明显日益不平等。1992年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拥有全部私人财富的42%。10年前这一数字还是34%,现在美国人的财富集中程度比英国高出两倍还多②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刘训练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4页。。但是,卢卡斯却完全看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还宣称,“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最终导致了2007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即使如此,卢卡斯依然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由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卢卡斯警告道,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并且,他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视为“次品经济学”,认为这些激进政策只能使一切雪上加霜③[美]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为什么连现代经济学大家都会对那些明显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呢?关键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选择。一般地,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就源于自然主义思维,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刻意地向自然科学攀亲: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大量使用数学手段,试图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简洁和优美的经济规律。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它逐渐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艺术创造;二是,它日益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经济研究也被等同于故事编造。但显然,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科的本质和经济研究的根本宗旨。它混淆了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异,而是热衷于以形式逻辑这一静态平面的眼光去审视应该反映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现象之理论,从而无法真正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采取局部分析的思维而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热衷于静态地考察其着力分析的具体个案,而没有将之置于历史的和整体的框架中进行动态分析,所以,它就普遍地只能看到能看见的或愿意看见的一面,而无法考虑到看不见的或不愿意看见的一面,从而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被马克思称为19世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狄更斯就将利益计算的经济学视为一门邪恶的学问,因为理性计算疏离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而经济学家是一群冷冰冰的理性动物,“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①[澳]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方钦、梁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总之,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排除了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乃至文化心理等的考虑,而极端地崇尚基于个体力量博弈的纯粹市场机制。同时,由于舍弃了各种社会性因素的考虑,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将丰富多样的人抽象为原子时的个体,他们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在上帝式的拍卖人的引导下形成社会的和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因为它已不再是为了发现现实中的问题,不再是追求人类的理想,而是基于理性选择行为或供求分析框架对现实的描述和合理化解释。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只是建立起诸如单一货币供给、单一税收、单一教育券、单一负所得税等一般的抽象规则,而不再关注人类社会的起点是否平等正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缓和不平等和不正义。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逐渐兴起,而且,这种思潮在当今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更是甚嚣尘上。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极端地崇尚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而这明显地与自由主义日益复杂化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自由主义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复杂的过程:早期自由主义主要关注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但现代自由主义则更加关注贫困和社会保障,关注社会正义,因而自由和平等已经不可分离。显然,浸含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政策主张上都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倾向,没有深入剖析人类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多样化协调机理,甚至也很少有人知道市场化伦理本身就是市场机制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一事实。赫希曼(Hirschman)在1991年发表的《反对的修辞》一书中就指出:那些保守的批判家正沉着自然地撰写“百无一用”的论文②Hirschman,Albert O.,1991,The Rhetoric of Reacti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四、结 语
自古典经济学后期经济学转向所谓的“纯理论”研究开始,主流经济学就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拢,并呈现出日益庸俗化的趋势:一者,它日益偏重于工程学的内容,并刻意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二者,它日益强化自然主义思维,并刻意地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把存在的视为合理的,从而忽视了对弱势者诉求的关注和对福利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上述特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坚持市场机制有效的信条,并将市场经济中的初始分配收入和市场交换所得视为正义的,等同于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承认分配正义的存在,而仅仅承认存在交换正义;而在交换正义方面,又只是关注交换程序是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不关注在交换起点上是否地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在特定引导假定以及由此产生的解释共同体下进行思维和分析,从而只是看到了它能够或愿意看见的一面,却看不到它不能或不愿看见的一面。但是,如果放弃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信条,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广的视野,更容易看到现实中的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门学以致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是根本上离不开伦理学的,因为人的生活行为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受意识形态所支配。琼·罗宾逊指出:无论是否可以把意识形态从社会科学的思维范畴内消除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的行为范畴内确实不可或缺①[英]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页。。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将意识形态、伦理价值等因素纳入其中来考虑,经济学理论才能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从而走上一条与社会历史保持逻辑一致关系的健康发展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一段布鲁姆的评论: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经济安排的价值评估,涉及政府应如何管理引导经济事务的判定,这就要对经济问题中的好与坏、对与错进行判断,进行这些判断需要标准,而标准必须源于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为自身目的而发展形成的一些严密的分析方法,结果证明在伦理哲学中也是很有用的,它们不仅可以帮助解决伦理学实践中的问题,还可以帮助解决伦理学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经济学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存在于资源稀缺迫使一个社会为这些资源权衡可供选择的可能途径,因为经济学自称是关于匮乏的学科。事实上,在这个领域,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在福利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寻求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在伦理学中,哲学家寻求实践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已经发现他们在处理相同的问题:平等有价值吗?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未来人的幸福?我们应确定什么价值标准来保护自然或保护人类生命②[英]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纯理论取向而极力排除伦理学的内容,但实际上,它也并非真的是“伦理不及”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一元论伦理观,这就是伦理自然主义。伦理自然主义赋予自然主义以一定的价值信念而形成:将自然存在的就视为合理的,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之提供理论支持。问题是,源自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就充满了逻辑缺陷。例如,有学者就举“狐狸去偷一只鸡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为例进行说明:进化论者看到的时候仅仅只有狐狸的脚印,为此就将这件事解释成为狐狸是为了在雪地上留下脚印才去偷鸡的。这不是很荒唐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唐的解释呢?就在于,进化论者没有观察到全部的事物,而只观察到了生存下来的事物,但它却用这些生存下来的事物的合理性去建构整个自然界的过程③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例如,弗里德曼等就用“as if”假说来说明市场机制中生存的企业都是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这明显忽视了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决策错误,而有的错误决策则最终导致那些一直被视为高效的企业突然倒闭。而且,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它就不再探讨社会合理性问题,不再辨识社会伦理问题,而专注于个体理性行为的分析,集中于市场的交换行为。卡莱尔很早就嘲弄说: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亮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或者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④转引自[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事实上,自20世纪初,摩尔等就认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认为进化论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社会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已经整体性批判和放弃了进化论的社会学解释。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却依旧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从而就产生了诸多反社会和不伦理的论断。显然,就当前日益狭隘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更应该认真地听听来自伦理学的声音,认真汲取伦理学的新洞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