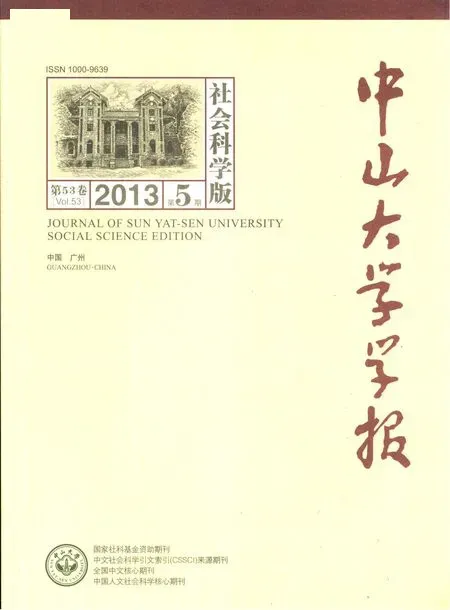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
倪梁康
一、引 论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学术身份在一般人看来十分复杂:他被视为德国的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但在哲学界,他更多被看作是当今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生命哲学家。说他是历史哲学家,理由在于他所受的训练主要来自哲学、历史学和思想史领域,他的老师中有菲舍尔(K. Fischer)、兰克(L. von Ranke)和特兰德伦堡(F. A. Trendelenburg)等人;而说他是生命哲学家,则是因为他的全部思想系统都可以用生命哲学的线索来贯穿。与此相关,狄尔泰也是解释学家和理解心理学家、描述心理学家、文学思想家,如此等等;或一言以蔽之:精神科学家。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他一生中与瓦尔腾堡的约克伯爵(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以及与胡塞尔的交往也是引人注目的论题。
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最后一个论题,即狄尔泰与胡塞尔的交往。对这个交往的性质可以先做如下的概括:如果胡塞尔与布伦塔诺的关系涉及现象学与心理学以及心理主义的关系问题,与弗雷格的关系涉及现象学与逻辑学以及逻辑主义的关系问题,与冯特的关系同时涉及现象学与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两方面的关系问题,那么胡塞尔与狄尔泰的关系便涉及现象学与历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
狄尔泰与胡塞尔的直接交往起始于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之后,大致从1905 年开始,至1911 年狄尔泰去世为止,前后只有六年时间。当时的狄尔泰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于1870 年发表的《施莱尔马赫的生平》奠定了他作为历史的精神科学家的基础。1883 年的《精神科学引论》以及《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的著述,则意味着他在精神科学的体系与方法方面的思考已渐趋成熟;尤其是他明确主张人类的精神生活不同于外部自然进程,有其自己的独特规律,据此而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活动。在这个问题上,狄尔泰与胡塞尔有十分一致的想法。
狄尔泰从1882 年起接任哲学家海尔曼·洛采(R. H. Lotze)的教椅,在柏林大学任教至1905 年退休。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便是于此期间发表的。这部著作对狄尔泰的影响程度可以在狄尔泰自己的一个说明中找到。他在后期《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的修订中加入了这样一个致谢辞:“如果我现在于此要尝试继续构建一个实在论的或带有批判性的客观趋向的认识论之基础,那么我必须一劳永逸地在总体上指明:我有如此多的方面要感谢胡塞尔在对认识论的描述利用方面的划时代著作《逻辑研究》(1900、1901 年)。”①[德]狄尔泰: 《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狄尔泰全集》第7 卷,哥廷根,1992 年,第14 页,注1。除此之外,他在1911 年7 月10 日致胡塞尔的信中将胡塞尔称作“哲学分析的天才”,并且为始终处在外在职业困境中的胡塞尔提供帮助,设法使他能够在图宾根大学获得一个较好的教席( 参见书信 VI,51—52) 。
很可能狄尔泰是第一个公开认可胡塞尔《逻辑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思想家。他不仅仔细地研读这部著作,尤其是其第五和第六研究,而且还在柏林开设了关于《逻辑研究》第2 卷的讨论课。当时课上旁听的人还有一位美国人瓦尔特·皮特金(Walter B. Pitkin)。他在听课过程中对《逻辑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来到哥廷根拜访胡塞尔,希望能获准将其《逻辑研究》翻译成英文。胡塞尔允准了这个翻译计划②这个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以实施。胡塞尔《逻辑研究》的英文版,1970 年才由芬德莱( J. N. Findlay)翻译出版。,并从皮特金那里得知狄尔泰对《逻辑研究》的兴趣与评价。他于1905 年3 月中旬来到柏林拜访狄尔泰和西美尔(G. Simmel)等一行人。胡塞尔在1929 年6 月27 日致狄尔泰女婿米施(G. Misch)信中曾回顾这次拜访说:“1905 年在柏林与狄尔泰少数几次谈话(并非他的著述)意味着一个推动,这个推动将《逻辑研究》的胡塞尔导向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胡塞尔,而不完整地展现出来的、并且实际上是在1913 至大约1925 年期间才得以具体完善了的《观念》的现象学——尽管在方法上有本质不同的形态——导向了与狄尔泰的一种最内在的共同体。”(书信VI,275)
根据胡塞尔妻子马尔维娜的回忆,狄尔泰此后也到胡塞尔居住的哥廷根回访过胡塞尔③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一文的编者卡尔·舒曼曾说明:“关于狄尔泰而后做了回访这一点,目前没有其他渠道的证明,但肯定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狄尔泰的兄弟卡尔·狄尔泰曾在哥廷根任考古学和古典语言学的教授;狄尔泰有可能常常去拜访他,并且而后也造访胡塞尔。诚然,卡尔·狄尔泰在1907 年便已去世。”( “编者说明”,[德]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同上书,第124—125 页) 也就是说,狄尔泰对胡塞尔的回访很可能是在1905 年至1907 年期间。。马尔维娜在其《胡塞尔生平素描》的“哥廷根”时期结尾处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在我回忆中的一个空缺,我要尽快填补它,这便是狄尔泰。”④[德]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同上书,第117,117 页。狄尔泰是马尔维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专门谈及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些人不仅与胡塞尔有学术思想方面的交往,而且还是家庭的朋友,并且在生活、信仰上与胡塞尔有过相互的影响,如马塞里克、魏尔斯特拉斯、布伦塔诺、施通普夫、康托尔、阿尔布莱希特、阿尼姆、格拉斯曼等等。马尔维娜在这里写道:“很快他便表示要来哥廷根访问,而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老先生的那双闪烁着敏锐精神的小眼睛、他对一个伟大成就的友善承认、他的个性的素朴单纯,所有这些都证明他属于德国研究者中的最高尚类型。他私下里对我说:‘仁慈的太太,《逻辑研究》是哲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引导。这部著作还会经历很多次再版,您要运用您的全部影响,使它不被修改,它是一个时代纪念碑,必须始终将它如其在被创造时的那样保存下来。’”⑤[德]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同上书,第117,117 页。
当然,胡塞尔本人最终并未接受这样的建议。他在《逻辑研究》的“第2 版前言”中曾记录下自己对此的考虑:“完全放弃修改,仅仅机械地重印,这对我来说虽然舒适,却缺乏认真,它与我出《逻辑研究》新版的目标相距太远。我能允许所有那些疏忽、彷惶、自身误解(尽管它们在第1 版中难以避免而且可以原谅)再次去迷惑读者,给他在对本质的明确把握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困难吗?”①[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 卷,同上书,BX—XI,BX,B XI。问题既然以这种方式提出,答案便不可能是肯定的。可是在修改的进程中胡塞尔已经意识到彻底修改的不可能:“内行会一眼看出,要想把这部旧著完全提高到《观念》的水准是不可能的。这将意味着重新撰写这部著作——意味着一种永无兑现的拖延。”②[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 卷,同上书,BX—XI,BX,B XI。因而在几经周折之后③关于其间的周折,马尔维娜回忆说:“尽管有此智慧的告诫,胡塞尔仍然还是能够和愿意冒险做出加工的尝试,尤其是对第六研究。在已经印出四个印张之后,他让人将它们化成纸浆。”( [德]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同上书,第 117 页),胡塞尔最终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即对第1 版进行尽可能的加工,由此产生了现有的、内容差异较大的第1、2 版。
狄尔泰并不像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如纳托尔普(K. Natorp)或冯特(W. Wundt)]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论战气氛较为浓厚的第1 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于《逻辑研究》第2 卷中“精密地探讨了一组基本问题”④[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 卷,同上书,BX—XI,BX,B XI。的那六项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六研究。这里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指“意识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它们常常被视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会引起一些读者(如海德格尔)的困惑。实际上这些研究虽然本身不是心理学的研究,但它们的所有结论都可以运用在心理学上⑤关于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可以参见[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9 卷,海牙:奈伊霍夫出版社,1968 年;也可以扼要地参见胡塞尔的文稿《现象学与心理学(1917 年) 》,[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6—129 页。。狄尔泰无疑把握到了这一点。因此胡塞尔能够确定:“除了冯特先生之外,在较老一代的研究者中惟有狄尔泰认识到了这卷的各项研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⑥[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 版“序言”草稿的两个残篇(1913 年9 月) 》,《逻辑研究补充卷》,多特雷赫特: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2002 年,第318 页。
但可以看到,在对待《逻辑研究》再版的态度问题上,狄尔泰与胡塞尔已经产生分歧:前者认为它已经完善,无须大改;后者则认为,尤其是对第2 卷需要进行彻底的修改。这个分歧在此刻还显得无伤大雅,后来则表明它植根于基本的方法与立场的差异之中。
二、胡塞尔对狄尔泰的影响
如前所述,按照狄尔泰自己的表态,胡塞尔通过《逻辑研究》而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一个实在论的或带有批判性的客观趋向的认识论之基础”⑦[德]狄尔泰: 《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狄尔泰全集》第 7 卷,哥廷根,1992 年,第 14 页,注 1。的建构方面。作为一位始终偏重思想的历史与发生向度的哲学家,狄尔泰在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分析中首先发现的是现象学在认识论方面的奠基,这个奠基自身表明为一种对认识行为的意向性结构的明见把握。如果狄尔泰的理解心理学乃一种在内容上是生命历史的、在方法上是发生说明的心理学,那么他在胡塞尔那里发现的恰恰是另一种心理学:对稳定的意识结构进行本质描述和把握的心理学。也就是说,心理学的发生研究在这里得到了结构研究的补充,从而不仅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丰满和完备的形态,而且有可能获得更为稳定的基础。因而他晚年所做《精神科学之奠基研究》中的第一研究便是“心理的结构联系”⑧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同上书,第3 页及以后各页。。如果心理活动是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流动是一个发生研究的课题,而它的横截面则是一个结构研究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前者是后者的发生研究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构研究基础。狄尔泰原先在结构心理学方面的缺失,如今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得到了弥补,他的喜悦之情当然也就溢于言表。在1907/08 年期间的手稿残篇中,他曾就结构心理学记载下自己的思想:“我现在将结构称作在一个体验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类型是体验在一个群组中被构造起来的最简单方式。有如此结构的东西而后出现在进一步的结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最终构成一个范式、一个定位,这是在那个构成生命单位的心理流程中完成的定位。”①[德]狄尔泰:《精神世界》( Die geistige Welt) ,《狄尔泰全集》第6 卷,哥廷根,1994 年,第318 页。狄尔泰自己随后也承认,他是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范围内使用这些表达的。事实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2 卷中所把捉的意识体验中的本质要素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应当是狄尔泰的“结构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启示的来源。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中特别指出:胡塞尔的纯粹语法学概念就是对结构关系的富于启示的表达②[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同上书,第322 页。。
从心理学的发生维度到其结构维度的转向,在狄尔泰那里是借助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完成的。这个转向在其后期著作《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中得到表达。正如兰德格雷贝所言:“狄尔泰之所以对他早年的研究进行修改,并在晚年时着手写作《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与《精神科学之奠基研究》,其动因皆来自于他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研读和理解。”③[德]兰德格雷贝:《自述》,《哲学自述》第2 卷,汉堡,1975 年,第137 页;中译文参考张慎等译:《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中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年,第139 页。兰德格雷贝于1926 年在胡塞尔指导下以《威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它的基本概念分析》( 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Analyse ihrer Grundbegriffe) 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28 年发表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 辑。该辑还有胡塞尔另一位学生弗里茨·考夫曼的论文《瓦尔腾堡约克伯爵的哲学》( 任教资格论文?) 。此后,兰德格雷贝和考夫曼作为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尤其在现象学的历史哲学路线的开拓方面卓有贡献。
而在胡塞尔这方面则可以说,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已经给他日后从现象学的结构维度到其发生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转向埋下了伏笔。只是在此时,胡塞尔本人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潜隐的影响。二十多年后,在《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的引论性说明中回顾和总结这段思想关系时,胡塞尔曾对狄尔泰与自己的相互作用关系做了较为客观和周到的评价,但仍然没有顾及历史哲学的向度。胡塞尔在这里写道:“狄尔泰高兴地采纳了《逻辑研究》,并认为它是对他的《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的第一个具体阐述,尽管《逻辑研究》的产生与他的所有著作无关。狄尔泰自己建立起这个联系,因为当时我很不幸地处在埃宾豪斯那篇出色的[对狄尔泰的]反批评④海尔曼·埃宾豪斯( Hermann Ebinghaus) 的反批评,发表于1895 年10 月的《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 。的影响之下,它认为阅读狄尔泰的伟大著作并非必要,再加上我在那些年里也很少感受到狄尔泰著作的意义。在我为从原则上克服实证主义所做的内心激烈斗争的过程中,狄尔泰较早著作《精神科学引论》所表现出的那些实证主义倾向使我产生反感。当我亲自听到狄尔泰说:现象学,即在《逻辑研究》的第二部分、亦即专门现象学的部分中的描述分析与他的《[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本质上是和谐一致的,并且可以被视作在成熟的方法中对观念地浮现在他面前的心理学真实阐述的第一基础时,我大吃了一惊。狄尔泰自始至终都极为重视这一点,即:我们的研究从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出发而达到了会聚,并且,他在晚年几乎是以青年人的激情再次从事他一度曾放下了的对精神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是他与此有关著述中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一篇文字:登载在《柏林科学院论文集》上的《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1910年),可惜他此后不久便去世了。我自己在现象学方法的完善过程中以及在对精神生活的现象学分析中走得越远,我就越是必须承认,狄尔泰事实上对现象学和描述分析心理学的内在统一所做的使我惊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包含着天才的现象学前考察和前阶段。这些著作决非是陈旧过时的,甚至在今天,对在方法上有了发展、并且在其总体问题上有另一种构造的现象学的工作来说,它们仍然富有最珍贵的具体推动作用。我愿意最热心地向你们建议,研究这位极其伟大人物的所有著作。它们提供了在历史联系中直观指明和描述的真正宝藏,而且,在所有那些真正纯粹的描述与真正直观的被给予性最忠实地相吻合的地方,现象学家获得了一个已开垦了的、富饶的工作基地。”①[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9 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8 年,第34—35,34—35 页。
不言而喻,胡塞尔在这里已经看到了狄尔泰当年所看到的东西,这也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共通之处:对心理现象的直观、描述与分析的方法。当然,他并不认为狄尔泰所设想的描述心理学可以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现象学心理学。这一方面是因为狄尔泰没有来得及展开这方面的思考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除了描述分析方法的共性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根本分歧。因此,他补充说:“但是,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并不能获得在那种纯粹内向的心理学中进行的深造,这门心理学只是曾浮现狄尔泰的面前,他自己尚未用概念严格的方法和坚定实施的确定而赋予它以严格科学的形式。尽管狄尔泰后期的巨大影响令人欣喜,但这种影响由于对他的方式的外在模仿也可能造成不利的结果,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所以,我在几个主要部分之后想要引入的这门心理学不是一门直截了当地带有狄尔泰烙印的心理学,而恰恰是,如我已宣告了的那样,一门现象学的心理学。”②[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9 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8 年,第34—35,34—35 页。
概括地说,胡塞尔在《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的引论性说明中对狄尔泰的思考在总体上持一种“矛盾态度”,即如奈农和塞普所说:“胡塞尔赞同狄尔泰的历史学识和‘天才的直觉’,他认为,狄尔泰反对那种想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在精神科学之中的精神态度,这是合理的。然而,胡塞尔像在‘逻各斯文章’中一样怀疑,狄尔泰的描述—分析心理学是否能够为那些精神科学之科学奠基所要求的问题提供一个实际的答案。”③[德]奈农和塞普:《附录二:全集本编者引论》,[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78 页。
但是,如果胡塞尔在1905 年与狄尔泰遭遇时仅仅赞赏后者的历史学识,发现了描述分析方面的共通之处,并且因此而从狄尔泰那里获得了学理上的支持,那么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的关系就仍然还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狄尔泰在此期间对胡塞尔也有重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当时尚未、甚至可能始终未被胡塞尔明确地意识到。
三、狄尔泰对胡塞尔的影响
有一个历史事实应当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胡塞尔自己曾在文稿中记载:“在《逻辑研究》首次发表时,我尚未获得在历史方面的自明性。”(手稿F III I/136b)与后来的年青海德格尔一样,此时的胡塞尔也一定会追随柏拉图强调:“我们不叙述历史。”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开篇不久便引录了柏拉图在《智者篇》(242c) 中所说的这句话。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尼迈耶出版社,1979 年,第6 页。真正的真理不会今天产生,明天变化,后天消失,因而是无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直到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的问题才成为他思考的主要课题。但是,从胡塞尔本人的授课表来看,他在1905 年夏季令人诧异地开设了一次历史哲学的讨论课,讨论狄尔泰的“理解的心理学”以及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相关思想(年谱89)。也就是说,胡塞尔突然开始关注历史哲学问题。这与他在此期间与狄尔泰的交往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巧合。而后在1910 年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长文中,胡塞尔开始考虑“历史主义”的问题并对狄尔泰提出批评,尽管他在这个时候如比梅尔所说还不具有“历史的眼光”⑤[德]比梅尔( Walter Biemel) :《关于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导引说明》( Einleitende Bemerkung zum Briefwechsel Dilthey-Husserl) ,《人与世界》( Man and World) 第 1 辑,1968 年,第 433 页。。但无论如何可以说,现象学在历史哲学方面的首次关注是在狄尔泰的影响下发生的。此后,在狄尔泰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胡塞尔基本放弃了对历史哲学的系统思考。直至30 年代中期,胡塞尔才重新回归这个思想领域,并撰写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这样的历史现象学著作①《胡塞尔全集》第6 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2 年,第381 页。。
当然,在前引1929 年6 月27 日致米施的信中,胡塞尔在谈及狄尔泰对自己的影响时并未说明:狄尔泰在何种意义上将他从《逻辑研究》引向《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但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里所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并不是指《观念》的第1 卷②胡塞尔在《观念》第1 卷中对狄尔泰只字未提。因此可以说,狄尔泰对胡塞尔的影响并不体现在作为第1 卷内容的“纯粹现象学”上,而是主要体现在作为第2 卷内容的“现象学哲学”上。此外,舒曼( K. Schumann) 认为,《观念》的书名可能借鉴了胡塞尔尤为看重的狄尔泰《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的报告名称( 参见《编者引论》,《胡塞尔全集》第 3 卷,同上书,XXXIII) 。,而应当是指《观念》的第2 卷和第3 卷③《观念》第1 卷出版于1913 年。这两卷的文稿后经胡塞尔的助手埃迪·施泰因和兰德格雷贝的整理和加工。胡塞尔计划出版《观念》的第2 卷和第3 卷。第2 卷的文稿是与第1 卷文稿同时完成的,但对第2 卷的加工修改一直延续到1924 年,而后基本停止( 参见玛丽·比梅尔:《编者引论》,《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 卷,《胡塞尔全集》第3 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2 年,XIV—XIX) 。《观念》第2、3 卷都是胡塞尔去世后才作为遗稿出版的。,它们构成胡塞尔在信中所说“在1913 至大约1925 年期间才得以具体完善了的《观念》的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尤其是《观念》的第2 卷,它以“现象学的构造分析”为题,包含三个篇章:1.物质自然的构造;2.动物自然的构造;3.精神世界的构造。第3 篇“精神世界的构造”问题直接与狄尔泰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科学”问题相关,因而胡塞尔在该篇引论的一节中基本上是从“具有天才的直觉,但缺乏严格理论化的狄尔泰”开始谈起的。狄尔泰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被列入现象学构造分析的三个主要对象之一。易言之,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构成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三分之一领域。当然,尽管胡塞尔在这里谈及动机引发、联想、人格形成、权能主体等等问题,但他的总体考察仍然是在结构方向上而非在发生方向上的展开的。
在《观念》第2 卷的修改结束的同时,胡塞尔在大约写于1924 年的一份文稿中表露出他在历史哲学方面的一个基本想法,而且是具有浓烈的狄尔泰影响痕迹的想法:“狄尔泰曾公正地指责说,康德的理性批判没有尝试对历史的理性进行批判,根本没有尝试对精神科学的认识进行批判,而且根本没有看出进行这种批判的必要性。在哲学的意义中,不仅存在着对一切可能的超越的认识问题进行超越论考察中的普遍性,就是说,按照一切可能的超越的科学的问题进行超越论考察中的普遍性,而且还存在着一种彻底精神,这种彻底精神通过从这种认识退回到这种认识在绝对内在性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又退回到一个更远的阶段,而且必须将这种认识活动,作为认识论者的认识活动,因此一般而言,将纯粹意识的和意识自我的认识活动当作课题。”④[德]胡塞尔:《第一哲学(1923/24 年) 》第一部分,《胡塞尔全集》第7 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6 年,第376 页;[德]胡塞尔著、王炳文译:《第一哲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493 页。
胡塞尔在这里显然已经开始接着狄尔泰的思路来展开自己的发生现象学思考。他所说的两种“普遍性”,一种是指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方面的结构“普遍性”,一种则是指认识活动本身的发生“普遍性”。后一个向度至迟在1920 年便开始为胡塞尔所关注。通常认为这是胡塞尔受纳托尔普的影响所致。但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的号召在这里无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发生的向度在这里是对时间意识的向度和历史的向度这两者的衔接。从时间到发生再到历史,意识现象学的这个思考走向最初也被胡塞尔称之为“纵意向性”,它与意识结构方面的“横意向性”一同构成意识现象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思考走向或研究方向⑤对此的详细论述,参见笔者的长篇论文《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第 1 卷第 2 期,2010 年 8 月,第 60—79 页。。正是在这个双重方向的意识研究的意义上,胡塞尔能够在后期《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说:“在科学中,真正的历史说明的问题,是与‘从认识论上’进行的论证或澄清相一致的。”①参见《胡塞尔全集》第6 卷,同上书,1962 年。胡塞尔在这里将现象学的发生说明与结构描述以本质直观的方式结合为一,为自然与精神的本体论系统研究奠定了一个方法论的基础②G. Simmel,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tudie,Leipzig 1892.笔者会另外撰文专门讨论现象学作为精神科学或精神哲学的意义。。
除了这篇1924 年文稿之外,胡塞尔在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方面还做过一次相关问题的讨论课:根据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助手兰德格雷贝(L. Landgrebe)的回忆,胡塞尔在1924 年夏季学期的这门讨论课上曾以西美尔的《历史哲学问题种种》③笔者会另外撰文专门讨论现象学作为精神科学或精神哲学的意义。一书为课堂讨论的文本基础④参见[德]兰德格雷贝:《自述》,《哲学自述》中册,同上书,第124 页。。但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在此期间对历史哲学问题的讨论既不连贯,也不系统。具体说来,从1905 年至1934 年的二十年间,我们在胡塞尔那里只是偶尔可以把捉到狄尔泰的影响线索。例如,1927 年2 月,兰德格雷贝在胡塞尔这里完成了以《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论文答辩(年谱321);1928 年胡塞尔在夏季学期还再次开设过现象学心理学讲座,并在其中讨论狄尔泰(年谱334);如此等等。
直到30 年代中期,在1934 年11 月26 日致其挚友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胡塞尔才忽然写道:“我现在遭到普全历史哲学问题的突袭,这些问题对我极为重要。”(书信IX,111)这个思想袭击应当就是导致胡塞尔后期开始撰写《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历史现象学著作的直接原因,而它是否与狄尔泰的影响直接有关,对此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胡塞尔遗稿中可以找到一个文件夹(手稿K III 9/1—23),其中含有写于1935 年6、7 月的关于历史的精神科学、历史世界与生活世界(关于狄尔泰和布伦塔诺)的手稿(年谱)。这是胡塞尔后期历史现象学思考的开端与部分延续的内容。胡塞尔在1937 年因病才中断了这方面的思考,并于次年言犹未尽地辞世。
这里会禁不住地产生一个疑问:没有狄尔泰,胡塞尔会不会像康德那样最终带有历史理性批判方面的缺失?没有狄尔泰,胡塞尔还会谈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历史世界以及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吗?当然,历史不能借助假设来重构,思想史尤其如此。
四、两人之间的表面误解
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关系史不只是由双方积极的相互影响所组成,而是还具有消极与冲突的一面。冲突的起因从表面上看是胡塞尔于1910 年发表在李凯尔特(H. Rickert)创办的《逻各斯》杂志第1辑上的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胡塞尔在这篇做“通俗”考虑的文章中展开对作为严格科学之哲学的两个对立面的批评: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狄尔泰在这里被胡塞尔视为后一种思潮或倾向的代表人物。这不仅是因为狄尔泰学派在1911 年出版了《世界观。对哲学与宗教的阐释》的文集⑤参见 W. Dilthey,Bemhard Groethuysen,Georg Misch u.a.,Weltanschauung.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in Darstellungen,Berlin 1911.,而且更多在于胡塞尔在总体上对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解释学、世界观学说,作为精神科学基础的心理学、生命哲学等学说所持的怀疑态度。
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长文中多次提到狄尔泰,赞赏他对各种文化形态的历史研究,但批评他在其理论中隐含的历史主义趋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怀疑主义的结局:“狄尔泰在前面所引书[《世界观》]中同样否认历史主义的怀疑论;但我不理解,他如何会相信,从他对世界观结构和类型的富于教益之分析中,他可以得出反对怀疑论的决定性根据。因为正如在这篇文字中已经阐述过那样,一门还是经验的精神科学既不能对某个提出客观有效性要求的东西提出反对的论证,也不能对它提出赞成的论证。如果将这种旨在经验理解的经验观点换成现象学的本质观点,那么事情自然就会是两样的,而这似乎正是他思想的内部活动。”①[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50 页,注2,第48 页。胡塞尔在这里提出的一个原则性批评在于,狄尔泰将经验科学的方法运用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中,最终无法为精神科学提供客观有效的规律论证和真理把握。这是胡塞尔与狄尔泰在本质直观方法上的一个基本差异。胡塞尔在这里暗示,狄尔泰虽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看到了与自己描述分析方法相一致的东方,却还没有真正把握现象学本质直观或本质描述方法的真谛。而方法的误差会导致历史主义及其怀疑主义的结果:“显而易见,如果将历史主义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会像所有观念一样失去其绝对有效性。一个观念具有有效性,这将意味着:它是一个事实的精神构成,它被视作有效的并在这种有效性的事实性中规定着思维。这样也就不存在绝然的有效性或‘自在的’有效性,不存在那种即使没有人实施,或者,即使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类曾经实施过,它也仍然是其自身所是的有效性。这样也就不存在对矛盾律和所有逻辑学而言的有效性,反正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处在完全流散的状态中。也许这就是终结,无矛盾性的逻辑原则由此而转向其对立面。”②[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50 页,注2第48。与此相一致,胡塞尔也隐含地批评:狄尔泰虽然关注了《逻辑研究》第2 卷的各项研究,却忽略了其第1 卷对心理主义、相对主义、人类主义、怀疑主义的批评。
但这里产生出一个问题:狄尔泰此前恰恰是在《逻辑研究》第2 卷中看到了胡塞尔的心理行为的结构描述的方法,认为它与自己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观念不谋而合,并且相信它在心理学中的运用可以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甚至可以说,他后期在世界观类型以及其他文化构形方面的研究正是采用了这种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只是将它进一步运用在历史的维度上。因而这里的分歧,是否出于某种误解?狄尔泰在1911 年6 月29 日给胡塞尔的信中便曾将此视为“误解”,并且检讨自己,“我在这个误解上无非没有过失”(书信VI,44)。他解释自己在《世界观》文集中发表的文章乃是对多年前关于世界观学说的一个讲演稿的汇集,或是对这些文稿的扩展,因此有可能会导致胡塞尔的误解。但他无论如何否认自己的立场会导向怀疑主义,因此他从这封信的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不得不对胡塞尔的说法提出异议:“坦率地说,这样一种表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重的,因为您将我的立场刻画为历史主义,它的合法结论是怀疑论,这种描述不得不使我感到相当惊奇。我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奉献给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它应当为精神科学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内在的整体联系。”(书信VI,44)
胡塞尔在1911 年7 月5/6 日致狄尔泰的回信中也谈到“误解”:由于他在《逻各斯》上的阐述过于简短,不够清楚,实际上他的论证并非针对狄尔泰而发,并且承诺:“我也会在《逻各斯》上立即发表一个附注,以预防进一步的误解。”(书信VI,48)此外,胡塞尔还认为,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指出他们二人工作的共同点:“我们从不同的研究出发,受着不同的历史动机的规定,经历过不同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和研究的东西是一致的和共属的:现象学的基本分析和现象学的总体分析,借助于由您所开辟的大文化构形的形态学与类型学。”(书信VI,51)事实上,狄尔泰在前引信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我们一致认为:完全一般地说,有一种普遍的知识理论。我们此外还都赞同,通过一些研究才会开启通向这门理论的入口,这些研究对那些首先为这样一门理论所需、而后对哲学的所有部分都必要的标识的意义做出澄清。而后我们在对哲学的进一步建构中分道扬镳。”因此他认为:“实际上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您所以为那样远,我们在极具争议的要点上是同盟军。”(书信VI,43、47)
此后,狄尔泰1911 年7 月10 日给胡塞尔的回信中感谢胡塞尔对他的误解的澄清,并且对胡塞尔计划发表这样一个附注的提议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强调,可以“保留”他们之间的“分歧”,“直到您以后论述的发表”(书信VI,52)。然而狄尔泰于1911 年10 月1 日便突然辞世而去。胡塞尔后来也就没有在《逻各斯》上发表这样的附注。但他在1929 年8 月3 日致米施的信中还谈到此事:“根据狄尔泰的愿望,计划在《逻各斯》上发表的附注应当纳入到这样一项研究中去,一项与《[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相联结的、探讨狄尔泰意向与我的意向之内在共属性的研究中去。在深入研究《建构》的过程中,狄尔泰突然离开我们而去。但我尚未完成对我与狄尔泰的关系的清理,最后应当由《[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二部分(它的初稿已经与第1 卷初稿一同完成)来做出这样的澄清,它会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进行广泛的分析。但是……!”(书信VI,278—279)这里的“但是……!”,是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二部分①如前所述,在其中以“精神世界的构造”为题的第3 篇的引论第48 节便是从“具有天才的直觉,但缺乏严格理论化的狄尔泰”开始谈起的。胡塞尔在这里显然想对他与狄尔泰的思想关系做出一个清理。同样如前所述,胡塞尔在1925年夏季学期《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座引论中对自己与狄尔泰的思想关系的清理要更为详尽周密。一直尚未发表,而且事实上直至胡塞尔去世也未发表。
五、两人之间的深层分歧
胡塞尔未能在《逻各斯》期刊上发表这个附注当然有其深层的原因:在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但更多地存在着深层的分歧,因而他们两人既不可能像胡塞尔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一次详细的交谈便可以导致理解”(书信VI,48),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可能像狄尔泰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一个附注的发表便得以完全消除。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留意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编者比梅尔的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狄尔泰与胡塞尔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之间的对立就在于他们对历史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对于狄尔泰来说,历史是精神展开的本质场所,精神在其中实现它的自身理解,而对胡塞尔而言,观念只是含糊地显现出来,并因此而必须通过撇开所有实际历史的本质直观而得到纯化。”②[德]比梅尔:《关于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导引说明》,同上书,第433 页。比梅尔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抓住要害的。但这里应当更准确地说,狄尔泰与胡塞尔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对作为哲学本质的历史把握方式上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即:如何以本质的方式把握历史。当胡塞尔在前引致米施的信中说到他与狄尔泰“在方法上有本质不同的形态”时,他所指的也正是这一点。
狄尔泰虽然认为对历史的理解应当是一种本质的把握,但他明确反对用“概念思维”③[德]狄尔泰:《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引论》第一部分,《狄尔泰全集》第5 卷,哥廷根,1990 年,第405,405 页。的方式来把握历史。他将这种“概念思维”方式称作“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体系”,并且一再强调:“我觉得一门致力于通过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以有效的方式来陈述世界联系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④狄尔泰在信中两次引用了自己的“世界观的类型种种”的两段类似的表述来强调这一点( 书信VI,第43 页,参见第 45 页) 。历史的流动性和变化性决定了无法用概念将它固定下来的:“从不变的一出发既不能领会变化,也不能领会多。”⑤[德]狄尔泰:《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引论》第一部分,《狄尔泰全集》第5 卷,哥廷根,1990 年,第405,405 页。事实上在这里隐含着他对胡塞尔的历史把握方式的批评:胡塞尔的历史本质把握就是一种概念把握。因此他可以对胡塞尔的反击说:“真正的柏拉图!先是将变化流动的事物固定在概念中,然后再把流动这个概念补充地安插在旁边。”⑥转引自[德]米施:《编者前报告》(1923 年) ,《狄尔泰全集》第5 卷,同上书,CXII;以及[德]米施:《生命哲学与现象学——狄尔泰学派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分歧》( 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iltheyschen Richtung mit Heidegger und Husserl) ,达姆施达特,1967 年,第136 页。米施在“前报告”中没有给出狄尔泰原话的出处,在《生命哲学与现象学》中则引述了“前报告”中的这段话。很可能这是狄尔泰的某一次在与米施谈及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文章时所做的口头表述。
可是,如果本质直观不是在概念中进行的⑦严格说来,胡塞尔并不会认为自己的本质直观方式是在概念中进行的。对于狄尔泰的这个批评,他可能会反驳说狄尔泰混淆了“概念”和他所说的“观念”或“含义”。但这里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合适场所。,又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呢?这就像米施在其《生命哲学与现象学》一书中所说:“如果他[狄尔泰]自己在描述生命联系的过程中就回溯到柏拉图的表达上,并且将完整体验的‘形式’称之为一个‘观念的统一’,它是由时间上分离的各个生命部分组成的,并且‘具有一个含义’,那么人们会询问这样一种反击的权利究竟何在?”⑧[德]米施:《生命哲学与现象学》,同上书,第136 页。
反过来说,如果如前所述,比梅尔认为胡塞尔至少在这时还没有历史的眼光①参见[德]比梅尔:《关于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导引说明》,同上书,第433,433 页。,那么问题在于,胡塞尔何时才获得了历史的眼光呢?如果胡塞尔是自20 年代起有了发生的眼光,或者自1934 年起有了历史的眼光,那么我们重新面临的问题又在于,这时他的眼光与狄尔泰的历史眼光的异同究竟何在呢?
或许只要将狄尔泰在《全集》第5、6 卷《精神世界》与第6 卷《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之建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 卷的第3 篇“精神世界的构造”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相关研究加以仔细比较和对照,就可以看出狄尔泰与胡塞尔在对历史的本质直观方法或纵向本质直观的方法理解与运用上的基本差异。
从总体上说,狄尔泰对生命形态、文化构形、世界观类型的描述是以一种类型学的方式进行的,胡塞尔认为这仍然属于经验综合的历史把握,而非他的意义上的历史本质直观或纵向的本质直观。尽管他在致狄尔泰的信中用“现象学的基本分析和现象学的总体分析”以及“大文化构形的形态学与类型学”(书信VI,51)来概括他自己与狄尔泰的共同努力方向,但他始终不认为他们已经确定地行走在这个方向上。他并不认同狄尔泰的类型学的方式,但实际上最终也不完全认同自己的精神本体论与历史现象学的把握方式,这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的《观念》第2 卷的主要原因。胡塞尔在纵向本质直观的思考上并不只是在苛求别人,同样也在苛求自己。
这里已经涉及比梅尔在狄尔泰与胡塞尔的历史理解之差异方面所提到的第二个看法。如果他的第一个看法严格说来与两人在对历史的本质把握的方式上的不同理解有关,那么他的第二个看法便与两人在对历史的本质把握的对象上的不同理解有关。比梅尔认为:“胡塞尔实际上是从逻辑构成物的有效性出发,这种有效性在他看来是非历史的;而狄尔泰的出发点则是艺术作品和精神构成物,它们只能被理解为历史生成的、通过某种风格而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即理解为生命的表露,生命自身通过这种表露来领会自己。”②参见[德]比梅尔:《关于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导引说明》,同上书,第433,433 页。
毫无疑问,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观念》第1 卷中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是在横意向性方向上的本质直观:目光反思地转向意识体验自身并对其“非历史的”、稳定不变的本质因素及其结构联系进行本质直观。但这只是他的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在胡塞尔《观念》第2 卷的第3 篇,他的目光已经由反思—横向的转变为反思—纵向的。他在这里讨论“人格”的构成、动机的引发、权能的积累、他人同感的形成等等发生现象学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他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交互主体性、生活世界、社会、文化、科学等等的起源和构造,正如他后来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危机》中所做的那样。但他当然会认为,在所有这些历史中把握到的本质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否则哲学家与历史家的区别就仅仅在于,前者记录自己的历史,后者记录别人的历史。
狄尔泰在对“文化构形”或“历史的生命形态”进行类型论的研究时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家,他可以回顾、思考、发掘、研究所有人类感兴趣的历史事实,无论是自然史,还是精神史;他可以在所有人类思想与文化系统的名称后面附加“史”的后缀,例如哲学史,而后可以尝试去把握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如黑格尔也曾做过的那样。由此类推至诗歌、文学、修辞、艺术等等。但作为哲学家,一旦他要求在这种历史发生中发现某种即使人类灭亡也仍然有效的客观真理、某种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某种胡塞尔意义上的“观念存在”、某种弗雷格意义上的“第三王国”,那么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所有这些由人类精神构建起来的东西,是否只是与人类有关的,只是对人类有效的,因而最终是人类的和相对的。设果如此,那么对它们的思考和研究也就将必然具有人类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性质。柏拉图曾将诗歌、文学、修辞、艺术逐出哲学的领地③参见[德]狄尔泰:《精神世界》第一部分,《狄尔泰全集》第5 卷,同上书,第370 页。,理由可能不外乎此。
但即使做这样的退让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人类的精神构成、文化形态或世界观类型并不仅仅是由诗歌、文学、修辞、艺术等等组成,而是还包含着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等等广泛的领域。植根于这些领域之中的真理与法则也仅仅是人类的和相对的吗?“历史的眼光”就只能意味着人类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眼光吗?
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也可以这样来提出:胡塞尔所坚持的在逻辑构成物方面的非历史的客观有效性究竟有多大的范围?它仅仅局限于逻辑、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还是也延展到某些历史的精神构成物的领域之中,例如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历史的领域?胡塞尔在算术、几何、逻辑起源方面的成功研究是否可以引入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中?
胡塞尔本人对此确信无疑:“以此方式,所有历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在其‘存在’特性中‘可理解的’、‘可解释的’,这种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就是一个意义所具有的各个内部自身要求的因素的统一,并且在此同时也是那些根据内部动机而合乎意义的自身构形和自身发展的统一。即是说,以此方式也可以对艺术、宗教、道德等等进行直观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对那个与它们相近并在它们之中同时得到表达的世界观进行直观的研究,一旦这种世界观获得科学的形式并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对客观有效性的要求,它便常常被称作形而上学,或者也被称作哲学。”①[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46—47 页。而且,看起来狄尔泰也会乐于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赞赏有加。他自己也希望并相信可以发现“精神科学中的逻辑联系”:“因为如果不对这些在精神科学中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成就,历史世界的构建就是在这些成就的共同作用中进行的?”②[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同上书,第323 页及以后各页。狄尔泰在这里似乎十分倾向于用“逻辑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就像黑格尔曾经以思辨的方式做过的那样,也像胡塞尔后来以发生说明的方式所做的那样。
一方面是逻辑构成物、稳定不变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是精神构成物、发展变化的历史关系,对这两者及其相关关系的构成研究花费了狄尔泰与胡塞尔毕生的精力:狄尔泰是从对历史关系的探讨走向对结构关系的思考,胡塞尔的路向则正好反之。
六、回顾与总结
黑格尔之后,狄尔泰再一次强有力地倡导了历史意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为历史意识的真正兴起做准备。在此意义上,他站在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的对立面,并因此而站在了维柯和黑格尔的一边。哲学对他而言首先是历史哲学,以及在此意义背后的精神哲学和生命哲学。
在狄尔泰与胡塞尔的三封通信的编者比梅尔看来,这些通信之所以弥足珍贵,就是因为在这个书信中表达出来的思想交流“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通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这是两位思想家的个人意见交换,而更多是在这里展示出他们各自对哲学本质的理解”。而且他们两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想在科学面前拯救哲学的本质”③[德]比梅尔:《关于狄尔泰—胡塞尔通信的导引说明》,同上书,第430、433 页。。
什么是“哲学的本质”?④这是狄尔泰1907 年长文的标题,载《狄尔泰全集》第5 卷,同上书,第339—416 页。这里的“哲学”不是狄尔泰所说的在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或形而上学,而是他所说的“哲学的哲学”,即以“历史的和心理学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方式进行的哲学反思⑤参见[德]狄尔泰:《世界观学说——关于哲学的哲学的论文》,《狄尔泰全集》第8 卷,哥廷根,1991 年,第13、234 页。。这里的“本质”,在狄尔泰这里也已经不是传统的名词的“Wesen”,它更多是后来海德格尔常常使用的动词的“wesen”或动名词的“Wesung”⑥[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哲学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272 页及以后各页。孙周兴在这里将这个意义上的本质译作“本现”和“本质现身”。。可以说,从狄尔泰开始,哲学的本质发生了一次从名词到动词的转向。它在胡塞尔这里相当于哲学的反思目光从横意向性到纵意向性的转向,或者说,从超越论的结构现象学到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的转向①这个转向甚至导致后人如哥德尔或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暗暗放弃了本质哲学”。参见[美]王浩著、康宏逵译:《哥德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77 页。。在海德格尔这里则相当于从名词的“存在”到“动词”的存在的转向,或者说,从“存在者”向“存在本身”的转向②“存在( Sein) ”在狄尔泰和胡塞尔那里还以传统的方式被理解为某种同一的、普遍的、基础的、固定的和包罗万象的东西。例如,狄尔泰将存在理解为与生活、活动相对的东西:“自我在向自身的努力沉浸过程中会发现自己不是实体、存在、被给予性,而是生活、行动、能量。”( 《狄尔泰全集》第7 卷,同上书,第157 页) 胡塞尔亦如此: “只要它是‘存在’,即经验有效性的相关项,它就受制于观念法则,而这些法则限制着这个存在的意义( 或自然科学真理的意义) ,作为一个原则上相对的东西但在其相对性中仍然同一的东西。”( 书信VI,48)。
这里一再提到海德格尔,并不是偶然的顺带。他的哲学基本出发点就是从狄尔泰而来的。可以说,海德格尔比胡塞尔更多地受到狄尔泰的影响,并且更多地继承了狄尔泰的遗产。这也是他从一开始便维续了狄尔泰对胡塞尔的批评的原因③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现象学及其效应》一书的第11 节“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哲学观”( 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161 页及以后各页)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共同学生兰德格雷贝便认为:“海德格尔力图将《存在与时间》理解为对狄尔泰所开创道路的彻底激进化发展。”④[德]兰德格雷贝:《自述》,《哲学自述》,同上书,第139 页。可以看出,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黙尔的思想发展,在思考的目光上都是纵向的或历史的,在思考的方法上都是理解的或领会的(verstehend)。当然他们在思考的内容上各有差异。就最后一点而言,胡塞尔的努力与狄尔泰最为接近。
胡塞尔在狄尔泰的影响下于1905 至1911 年期间已经开始将目光关注于“可理解的(verständlich)”“精神存在”⑤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46 页。,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存在领会(Seinsverständnis)”。胡塞尔自20 年代起在发生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方面的探讨,表明狄尔泰等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入和持久。实际上,当狄尔泰试图进行历史理性批判的工作时,他已经默认了一个前提:历史是理性的。历史在何种意义上是理性的?例如,在有历史的东西中存在着某种可以为理性(精神科学)所把握的规律?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何种规律?如何把握?⑥海德格尔1924 年期间便已看到了这一点:“狄尔泰的所有工作之动力都来自这样一个努力,即:使人的精神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使‘生活’得到科学的理解,并且为这种理解的科学性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 参见海德格尔:《时间的概念》,《海德格尔全集》第64 卷,法兰克福/美茵,2004 年,第7 页)狄尔泰面临这个问题,而且通过他的影响,胡塞尔后来也将这个问题摆到了自己前面。
从总体上看,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在狄尔泰与胡塞尔那里都徘徊于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理解论之间,它们构成历史解释学的两极。历史认识论是狄尔泰本人后期和胡塞尔的相关思考特点⑦狄尔泰本人早期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上偏向施莱格尔、诺瓦里斯等浪漫派的代表,后来还具有在进化论、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科学主义的趋向,直至他后来找到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方法,并试图用它来为精神科学奠基。,它也可以被称作科学的解释学或精神科学;而历史理解论则是海德格尔后期和伽达黙尔的相关论述风格和思考方式的写照,它更多是一种艺术的解释学或解释的艺术。
解释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在狄尔泰引发的历史哲学转向后分化出来的两种思潮。而在其中的一种思潮那里,历史哲学或精神科学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衍变为对历史和精神的解释艺术。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也会被宣告终结。
因此,现代哲学随着狄尔泰的出现和作用而完成了两次实际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当代成为了一个历史意识尤为强烈的时代,一个历史哲学或发生的形而上学的时代。这是从横意向性、结构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对横意向性的本质直观的路向转向纵意向性、发生的形而上学、历史理性批判、对纵意向性的本质直观的路向。第二次则是上述从精神科学的解释学和历史哲学到后哲学时代的可能转型。这里之所以加上“可能”二字,乃是因为这个转型还在进行之中,结果还难以预测。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第一个业已完成的转型中,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有分有合。他们之间的分,在当时看起来十分醒目,而如今在与更后来者的比照中却显得是小异而大同。尤其是在方法的层面上,胡塞尔与狄尔泰都在坚持历史理性的批判,他们都试图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扩张面前用严格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来拯救哲学的本质。简言之,他们都还具有哲学的普遍性诉求。前面曾提到胡塞尔赞同狄尔泰对两种普遍性的追求①参见[德]胡塞尔:《胡塞尔全集》第7 卷,同上书,第493 页。:一种是指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方面的结构“普遍性”,一种则是指认识活动本身的发生的“普遍性”。现在看来,“普遍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表达。它们实际上更应当是指两种必然性:一种是历史的、实际的、个体的必然性,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实际性(Faktizität);另一种是结构的、观念的、普遍的必然性,或胡塞尔意义上的总体性(Generaltät)。或者还可以考虑,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是否更应当将这两种“必然性”称之为两种观念性(Idealität):个体的观念性和总体的观念性?
胡塞尔曾批评狄尔泰将描述和说明的对立混同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认为在任何领域中,即无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精神领域中,都存在着这个区别。无论是描述还是说明,都指向一个“客观的东西”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 卷,《胡塞尔全集》第4 卷,同上书,第393 页。。这个“客观的东西”就是上述意义上的必然性或观念性。只是在这个限定了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赞同前引胡塞尔的观点:“在科学中,真正的历史说明的问题,是与‘从认识论上’进行的论证或澄清相一致的。”③[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同上书,第381 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危机》对早期《逻辑研究》的呼应。在后者中我们已经可以读到胡塞尔的这样一个信念:“假如我们能明察心理发生的精确规律,那么这些规律也将是永恒不变的,它们会与理论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一样,就是说,即使没有心理发生,它们也仍然有效。”④[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 卷,I,A 150/B 150。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