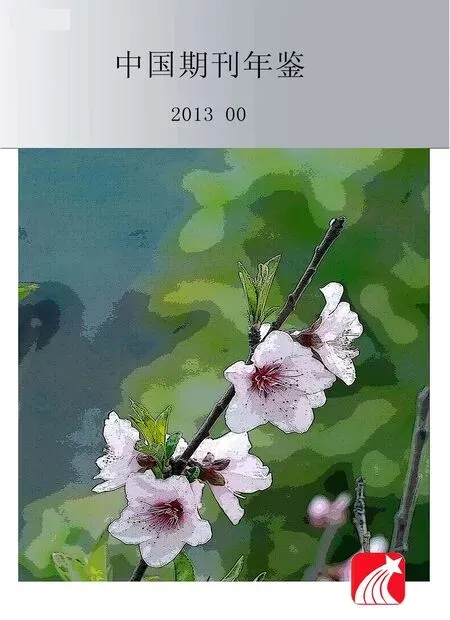从莫言获奖谈英文文学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以《中国文学》和《人民文学》英文版为例
肖 娴
从莫言获奖谈英文文学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以《中国文学》和《人民文学》英文版为例
肖 娴
文学的译介和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有独特的作用。在我国,相比海量的英译汉文学作品,汉译英显得极其单薄。一直以来,国人通过翻译家之笔,知道了莎士比亚、高尔基、雨果、拜伦,了解了西方文学的源流,也能及时地读到世界当代文学新作,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又有多少呢?答案是,中国文学在世界的眼中是模糊的。国外的读者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愿望,而我们却缺少主动的诉说。乐黛云认为,通向世界的文学渠道之所以一直不畅通,主要原因是“发送和接受的双方缺少真正的沟通”。[1]今年10月。我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是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学大家,中国的文学作品亦不乏可与获诺奖作品比肩的杰作,获诺奖如此不易,究其原因,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稀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及交流传播为何步履艰难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课题。
事实上,中国文学界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文学走出去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急于找到一个让世界了解自己的窗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也就显得尤为迫切。1951年,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文学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创刊;1952年,外文出版社成立,先后定下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文学对外翻译的书目,这是新中国国家机构首次有计划地出版、译介中国文学;1963年,制定了《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出版规划》和《现代文学作品出版规划》;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图书的国外发行机构纷纷倒闭,之后,一些中国作家通过出让版权等方式开始自己与海外联系出版作品。新世纪之初,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作协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新闻出版总署与清华大学也有类似的中国文学英译计划[2]。201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创办、编辑的《今日中国文学》在美国出版,向全球发行,这被称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三大工程。继文学杂志《天南》推出英文版后,老牌的权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也于2011年11月推出名为Path Light(《路灯》)的英文版试刊号,该刊有望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并广泛参与世界文学共建和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
期刊以它的连续性和时效性的优势,在对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文学》半个世纪文学译介的风雨历程,在翻译人才、翻译选材、传播渠道和市场运作等方面或许可以为《人民文学》英文版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一、《中国文学》译介的成就与反思
纵观1951—2011年60年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历程,《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51年创刊到2001年停刊,《中国文学》共出版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1981年,当时的新任主编杨宪益先生受到“企鹅丛书”的启发,提议出版“熊猫丛书”,将此前《中国文学》上刊载的译作结集出版,并增加了新译的、主要介绍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新作品。“熊猫丛书”广受好评,发行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上日文、德文版及中、英、法、日对照版等共计200余种,其中许多被重印或再版。198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承担出版《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和中文文学书籍的任务。
当时的外文局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外翻译家,如作为主编的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当代女性作家的翻译作品几乎都出自戴乃迭的译笔,她还专门撰文着重介绍当时的女作家和艺术家,如谌容、新凤霞、张洁、宗璞、戴厚英、遇罗锦、张辛欣、王安忆等。沙博里、葛浩文等优秀的外国专家长期供职于外文局,翻译了大量的作品。《中国文学》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大陆唯一一份面向外国读者及时、系统地翻译、介绍新中国文学发展动态的外语国家级刊物”[3]。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停止出版的原因是由于资金及市场渠道方面的原因,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1989年以后,发行中国图书的国外发行机构倒闭,作家们开始通过出让版权的方式自己联系国外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对《中国文学》也是不小的冲击。而“熊猫丛书”也因翻译队伍的流失而逐渐不复了往日的盛况。外文出版物的销路不广,但印刷质量和出版发行的成本却很高。曾任外文局副局长的黄友义说,汉译外出版物要经过17道工序,费用远高于面向国内发行的刊物。此外,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的隔膜等都成为文化输出的掣肘,这种输出与输入间的巨大逆差,一直影响着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二、《人民文学》英文版
英文名称为Path Light的《人民文学》英文版,寓意“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上的灯”,计划以季刊形式发行。自此,《人民文学》杂志将是英文与汉语同轨,创作与翻译并行。2011年11月的试刊选取了文学界近期的大事——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为主题,及时地反映了国内文学的新动向。推出的作家既有毕飞宇、张炜、莫言这样的实力派,也有笛安、李娟这样的新锐作家。涵盖的体裁包括茅盾文学奖作品选段及访谈录、短篇小说、诗歌及新书介绍。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PathLight在装帧、设计和编排上与国际阅读欣赏习惯保持一致。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瓶颈便是翻译问题。Path Light的编辑阵容由中外编辑及译文审定者共同组成。译者是热爱中国文化、中文水平较高的外籍翻译家,他们的译文会更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选材也更契合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此外,为了更好地进行市场推广,拓宽营销渠道,《人民文学》英文版将尝试电子刊物,“通过亚马逊做电子收费阅读,以保证杂志的定向抵达。”[4]主编李敬泽说。
三、英文文学期刊“走出去”的困境
《人民文学》推出英文版,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以及世界对中国文学了解依旧不多的前提下产生的;是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影响,让外国文学读者触摸到中国文学的脉搏。从这一层面来说,《人民文学》英文版与《中国文学》有着相似的诉求。但是,在如今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人民文学》英文版显然比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有更多的话语空间和表达自由。本文将从翻译选材、翻译人才与译文质量及海外出版发行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讨论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英文文学期刊“走出去”所遭遇的困境。
(一)翻译选材
《中国文学》作为外宣刊物,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般选择宣传新中国形象、反映建国后人民生活的作品译介宣传我国文艺政策,配合政治外交的需要,或者介绍一些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作家的作品。而6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选题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思想、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工农兵英雄形象等方面,一份纯文学期刊几乎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而“西方学者并非严肃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他们常常只是将此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5]。因为国内其他中文文学期刊的停刊,《中国文学》几乎无稿可选,只能靠发毛泽东诗词、样板戏和鲁迅文章来勉强维持,这对日后杂志的销路也产生了影响。70年代末,《中国文学》刊载了很多反映解冻后的“伤痕文学”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这些作品在今天来看,其历史意义要超过其文学价值。《中国文学》几乎不接受投稿,而是通过中文部编辑选取当时国内文学刊物上有影响力的、艺术性高的作品,主编负责审稿把关后交由外文部负责翻译,办刊原则是:发表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作品;在保证不出政治性错误的前提下力求高质量的译文;并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学艺术素养,以提高办刊质量。
我们也注意到,在杨宪益担纲《中国文学》主编时,他从未放弃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宣传和译介,对于向国外介绍我国传统文化和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总是不遗余力。通过增设栏目,拓宽选材范围,将相声、游记、回忆录、民间故事和寓言都囊括其中,并及时报道中国作家、艺术家和文学、文艺的最新动态,体现了时代感和民族特色。既译介了从维熙、蒋子龙、高晓声、陈忠实、贾平凹等当代现实主义作家,也选取了莫言、残雪、阿城等先锋作家和古典文学作家蒲松龄、沈括、袁枚等。[6]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很多优秀作品得到译介,其中古华是典型的通过译介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他的《芙蓉镇》《浮屠岭及其他》因其地方色彩和历史感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关注。
新创刊的《人民文学》英文版旨在通过及时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新动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界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让中国作家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去向世界推介中国的文学作品。例如,2011年11月的创刊号选取的作品主要是当代文学,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选,一格、笛安、蒋一谈、李娟等新锐作家,香港诗人王良和,新锐诗人雷平阳等,以及新书介绍,包括王安忆的《天香》、贾平凹的《古炉》、方方的《武昌城》等;2012年2月底出版的第2期则集中介绍伦敦书展中受邀的中国作家,对古典文学几无涉猎。
(二)翻译人才与译文质量
《中国文学》出版时期的外文局集聚了一批优秀的外国专家如戴乃迭、詹纳、沙博里、葛浩文等。他们的译文地道、流畅,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而中国译者如萧乾、杨宪益等,都是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他们深谙中国文化,忠实于原文,不遗余力地传译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译文质量高。然而,随着老一辈翻译家相继辞世,国内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目前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曾经作为《中国文学》主要译者和主编的杨宪益先生的辞世引发了翻译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讨论与反思。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学难以“走出去”并得到英语世界认同的主要原因是翻译质量,是译本的“水土不服”低估了中国作家的声誉及中文写作的特质。其实不尽然,对外翻译不仅是文学的传译,文学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最复杂最深层次的表现形式,其形态包罗万象,有时很难用另一种异质文化恰当地呈现,因此,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也常常遭遇挫折。在一种文化中能深深打动本民族读者的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后,却很难被译入语读者理解,并使其得到感同身受的审美共鸣,这在英语世界以外的其他少数族裔文学中也是常有的现象。《人民文学》英文版的译者全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翻译家,这些翻译家对隐藏于文字背后的中国式表达,深层的文化内涵如何传译,是翻译质量的关键。
(三)海外出版发行
在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时期里,《中国文学》英、法两个版本的总印数超过6万份,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亚非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在欧美地区也有不少订户。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化对外传播文学刊物,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中译外(中译英为主)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桥梁,而自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便走入低谷。虽然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也不断地通过丛书的形式向海外发行,如“大中华文库”“经典的回声”“中国经典文库译丛”等,新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能够通过向海外出版社出售版权等方式得到及时的译介,但像《中国文学》这样及时反映中国文学动态的连续出版物的停刊,却让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阵地丢失近10年。
四、对英文文学期刊出路的思考
诞生时间比《中国文学》晚60年的《人民文学》英文版显然拥有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商业推广环境,业界也对《人民文学》英文版的创刊寄予了厚望。外文期刊的销路一般不会很广,例如在西方,真正卖得动的中国作品不是诗歌,而是民国时期的带有中国“地方色彩”的传奇小说或者历史小说,这符合西方人对神秘东方文明的审美期待。通过文学期刊输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人才是关键,政府应扶持,译者需潜心,出版界当开拓市场。
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提高翻译人才质量都需要政府的支持,甚至给予一定的补贴,毕竟文学译介不同于对外贸易等的翻译,可以立竿见影,文学翻译需要时间去酝酿,好的译本需要读者和市场去检验,名著往往诞生于译本之后,因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名著多源于经得起读者检验的译本。政府部门除了财力上的支持,如果进行有序的组织,逐渐培养一批对中国文学译介有兴趣的译者,便能产生“集群效应”,营造更好的外译氛围。作为文学外译的译者,要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好的译作是译者潜心经营的结果,急功近利是产生不了好译本的。
此外,出版界在推介外译作品时,需要更好地了解国际市场对中国文学的需求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出版外译文学作品。在开放的今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渠道更加开阔,通过网络、电子书等形式进行营销和推广不失为一个解决纸质媒体长途运输难题的办法,也能使日渐小众化的文学刊物有更多的受众和生存空间,关键是出版界要有对海外图书市场的充分了解和对西方读者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的深入分析。当然,翻译质量也是短板之一。中国翻译界目前几乎处于断层的状态。首期Path Light的译者几乎全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翻译家,他们在理解和传译中华文化时会不会因其母语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偏差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需要时间来检验的难题。
[1]乐黛云.通向世界的文学渠道— —祝《今日中国文学》创刊[J].中国比较文学,2010(2):143-145.
[2]吴自选.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86-90.
[3]何琳,赵新宇.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材— —以“文革”为分期的《中国文学》选材对比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6):29-33.
[4]《人民文学》杂志推出英文版Path Light[N].人民日报,2011-12-29.
[5][6]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J].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3):67-76.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