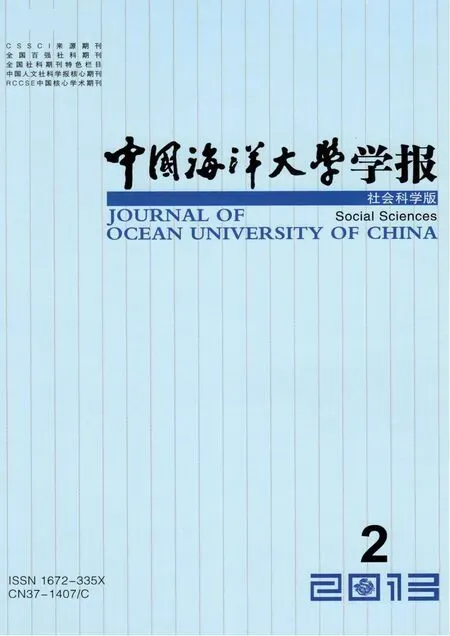论主管机关的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
刘长霞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4)
一、引言
海难救助直接关乎海上人命与财产安全。我国海上搜救工作遵循“政府领导,社会参与,依法规范”的基本原则。①《 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1.4条。在我国,有关国家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国家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过程中,往往要调用各种设备,组织和使用各种救助力量,费用支出巨大。海难救助结束后首要解决的便是这种费用支出的有效偿付问题。我国《海商法》第192条规定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海商法》第九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但该条的规定过于笼统,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也不尽一致。
主管机关作为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和维持的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在本身即具有救助义务的情况下,运用自身力量所从事的海难救助作业,②《海商法》第192条将国家主管机关的海难救助作业分为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作业,一种是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控制的救助作业。前者是指国家有关主管机关运用自身力量直接开展的救助作业;后者是指国家有关主管机关进行指挥、组织和协调其他救助力量开展的救助作业。主管机关救助费用的偿付问题主要存在于其运用自身力量从事的救助作业中,这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议题。能否构成《海商法》上的海难救助?其能否依据《海商法》主张救助报酬?如果承认其救助报酬请求权,其救助报酬数额的确定与一般救助人有何区别?在当前司法实践不统一,国家救助经费存在巨大缺口,政府负担过重的大背景下,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显得极为迫切。
二、主管机关海难救助之于一般海难救助的法理障碍
海商法所调整的海难救助法律关系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纯私法关系。海难救助法律制度作为海商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从产生之初便以鼓励海上救助为基本价值追求。海难救助报酬作为对救助危难中的船舶或其他海上财产的奖励,成为人们自愿开展海难救助的极大动力。自愿原则可以说是传统海难救助的一项核心原则,也是海难救助的基本构成要件。自愿原则要求救助行为的实施不能是出于任何公共义务(例如法律义务)、准公共义务(例如某人的职责)或者合同义务。[1](P273)救助方开展海难救助的直接目的在于通过救助遇险船舶及财产以获取救助报酬。而被救助方接受救助的主要考虑在于,与其让灾难将船货吞没,不如请他人救助,在获救财产的价值内给予对方相应的报酬。
关于海难救助的国际及国内立法主要是通过救助报酬的设定以鼓励救助作业的开展。目前,关于一般海难救助报酬的实现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例如,“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已经成为海难救助领域的一项习惯法原则。对于海难救助报酬的确定,各国国内法都规定了类似的考量因素,如:我国《海商法》第180条规定了十项确定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1989年救助公约》第13条也详细列举了确定救助报酬的考量因素。
海商法所谓的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在我国,与海难救助有关的主管机关,通常指港口消防队、港务监督与港航监督机关、海上安全指挥部等非营利性的国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2](P404)这些主管机关,由国家配备公务人员,并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和维持,负有保障国家管辖水域内船舶航行及其他海上活动安全的职责,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具有公法上的行政管理职能。
主管机关从事的海难救助之于一般海难救助的最大区别在于,主管机关开展救助作业是其本身的义务与职责。如,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主管机关接到求救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救助。《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海事管理机构收到船舶、浮动设施遇险求救信号或报告后,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救助遇险人员。主管机关开展海难救助作业的根本目的不是营利,而是实现其法定职责,即:保护海上人命及财产安全,维护海洋环境及航道通畅。主管机关本身救助职责的存在,引发了其从事的海难救助作业适用海商法调整的理论障碍:一是,其所从事的海难救助作业难以满足一般海难救助的“自愿性”要件。二是,海难救助报酬包含极大的奖励因素,救助人开展救助作业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利,而主管机关开展海难救助具有强烈的公益性。三是,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具体救助作业中,主管机关与被救助方之间处于不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
主管机关海难救助与一般海难救助构成要件的差别,使得其存在适用一般海难救助报酬取得规则的法理障碍。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的法律地位,探讨主管机关能否成为我国《海商法》上的救助方,进而为其救助费用补偿方式的确定奠定理论基础。
三、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的法律地位
我国《海商法》第192条规定: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作业中,存在主管机关、被救助方、其他救助参与人等多个法律主体。根据第192条的规定,在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中,只有成为《海商法》上的“救助方”,才能依据《海商法》第九章的规定享有救助报酬请求权。作为私法主体的其他救助参与人,在自愿与被救助方达成救助协议的情况下成为本条所称的救助方,并享有《海商法》第九章规定的救助报酬请求权一般不存在问题。而主管机关能否依据《海商法》第九章的规定取得救助报酬请求权,主要取决于其能否成为《海商法》上的救助方。
影响主管机关成为《海商法》上救助方的两大因素分别是:第一,主管机关开展海难救助时所使用的船舶及设备具有政府公务属性;第二,主管机关的特殊行政主体身份及其本身救助职责的存在,是否影响其以平等的救助方身份开展救助作业。本部分将结合《海商法》第172条的规定,并通过梳理有关主管机关开展海难救助作业的不同情形,对主管机关能否成为《海商法》上的海难救助方做出分析。
(一)《海商法》第172条对船舶的规定与主管机关的救助方地位
《海商法》第172条规定:“船舶”,是指本法第3条所称的船舶和与其发生救助关系的任何其他非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海商法》第3条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很明确,用于军事的或政府公务的船舶被排除在《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中所指的船舶。据此,有些学者提出,依《海商法》第172条的规定,用于军事的或政府公务的船舶不得依据《海商法》第192条享有权利和补偿。而鉴于第192条的立法用意及我国当前救助经费欠缺、救助力量严重不足,专业救助站点分布不均衡,相当一部分海难救助仍需要依靠主管机关组织协调的非专业救助力量,如军事船舶、军用飞行器、公务船舶等的现状,有必要协调其与第172条的关系,以避免产生歧义。同时考虑到海难救助一章适用的船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建议对第172条做出修改。[3][4]
笔者认为,《海商法》第172条对船舶的规定与主管机关依据192条享有权利和补偿并不矛盾,第172条的规定并不影响主管机关作为海难救助方的法律地位,即使主管机关使用军事的或公务的船舶从事海难救助。
《海商法》第九章对船舶的规定,主要是从海难救助标的的角度加以规范。一般认为,海难救助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四个要件:被救物必须是为法律所承认的标的、被救物处于危险之中、救助是自愿行为、救助有效果。《海商法》第172条的规定表明,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舶在海难事故中作为被救助物获救时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海商法》的调整范围,须要其他法律制度加以规范。而对救助方采用何种性质的船舶开展救助,《海商法》第九章并未做出要求。也就是说救助方可以使用商业船舶及设施从事救助作业,也可以使用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舶从事救助作业。救助方使用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舶从事海难救助作业,并根据第192条享受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与《海商法》第172对船舶含义的规定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至于是否应该扩大作为救助标的的“船舶”的范围,并对《海商法》第172条加以修改,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二)主管机关的行政主体属性不影响其作为救助方的法律地位
关于海难救助的形式,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所作的分类稍有不同,但均承认海难救助存在纯救助、合同救助及雇佣救助三种主要形式。[5](P334-336)[6](P273-274)[7](P190-192)
其中纯救助是指在海上财产遭遇危险之后,在未曾请求外界救援的情况下,由救助人自行提供救助的行为。纯救助是海难救助早期所采取的主要形式,目前,这种救助形式已不多见。但由于海上情况复杂多变,也不能完全排除纯救助的方式。比如,遇难船上无人,过路的主管机关船舶施救了此遇难船。
雇佣救助,又称实际费用救助,是指救助人根据海上遇险财产所有人的请求,以提供海上劳务的形式所提供的救助服务。雇佣救助的救助指挥权在遇险船一方,并且无论救助是否成功,都要按救助方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支付救助报酬,雇佣救助更多的体现海上雇佣劳务的性质,由《海商法》以外的民法、合同法等法律加以调整。而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作业,其救助指挥权都在主管机关一方。因此,有关主管机关从事的救助作业不存在雇佣救助的情况。
合同救助,是依据救助方和被救助方所订立的协议,以“无效果、无报酬”为原则进行的救助。合同救助是现在海难救助所普遍采取的形式,且为《海商法》所调整。合同救助以救助方和被救助方之间达成救助协议为前提,救助方和被救助方在救助协议下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法律主体。有关主管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在其从事救助作业中,其与被救方是否存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可能?其能否自愿与被救助方签订救助合同?
传统行政法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从行政权的控制与保障两翼展开。随着行政与行政法的发展,权力理念越来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合理和片面性。而契约理念则正好与之相反,体现了平等性、双方合意性、自愿服从性、双方的合作性以及权利义务的约定性和对等性。契约所蕴含的这些精神,正是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与价值所在,是现代行政法的目标追求。
在行政法学中,我国学者大都承认行政契约的现实存在及其积极意义。也有学者已经开始倡导契约的普适化,即不仅在行政法中确立契约方式,而且扩大契约在行政法领域中的适用范围,使行政性、过程性的契约由特定或有限的行政领域走向普遍性的行政领域。[8](P345)
在行政法理论上已经广泛认同契约理念的大背景下,我们没有必要在海商法领域否定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的缔约权。赋予主管机关这种契约缔约权并不会减损主管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一方面,赋予主管机关缔约权,主管机关与被救助方以平等的地位签订救助协议开展救助服务,与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为维护航道安全、海洋环境等公共利益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强制措施,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主管机关本身具有救助的法定职责,不影响其自愿签订救助协议。主管机关与被救助方就救助事项签订救助协议,并按照协议的内容开展救助作业,有利于双方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增强救助作业的可预期性。而救助作业的顺利开展,正是主管机关履行其保护海上人命与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的具体表现方式。
通过对海难救助开展形式的梳理可知,有关主管机关从事的海难救助作业可以以纯救助及合同救助的形式存在。由于纯救助在实践中已不多见,主管机关的自愿救助主要体现为合同救助。其主要特点是主管机关与被救方达成救助协议,并依此开展救助作业。此时,就具体救助作业的实施而言,有关主管机关处于与被救助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满足《海商法》第192条规定的“救助方”要件,享有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
四、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的取得与确定
在确定了主管机关的海难救助方法律地位后,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海商法》上的救助报酬包含了巨大的奖励因素,而主管机关主要由国家配备公务人员及设备,并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和维持,且其本身即具有保护海上人命及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在依据《海商法》确定主管机关具体救助报酬数额时是否应将其中的奖励性因素排除?
(一)《海商法》第180条规定的奖励因素
我国《海商法》第180条规定了确定救助报酬的十项考量因素,指出确定救助报酬应当体现对救助作业的鼓励,并综合考虑下列各项因素:
1、船舶和其他财产的获救的价值;
2、救助方在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
3、救助方的救助成效;
4、危险的性质和程度;
5、救助方在救助船舶、其他财产和人命方面的技能和努力;
6、救助方所用的时间、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
7、救助方或者救助设备所冒的责任风险和其他风险;
8、救助方提供救助服务的及时性;
9、用于救助作业的船舶和其他设备的可用性和使用情况;
10、救助设备的备用状况、效能和设备的价值。
尽管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十项因素基本上指明了确定救助报酬的考量方向和指标。仔细观察这十项因素可知,救助方的成本费用支出仅是确定救助报酬考量因素的一小部分,如:第6、9、10项是从救助方的救助费用支出角度来确定救助报酬。而如第1、2、3、4、5、7、8项则具有很大的奖励性,体现了鼓励救助的原则,在救助报酬的确定因素中占很大比例。因此,仅仅依据救助费用支出成本来确定救助报酬的具体数额,与同时考虑救助报酬的奖励性因素来确定救助报酬的具体数额,将存在较大差异。
(二)我国司法实践的不统一
在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的案例中,法院确定救助报酬的具体标准不尽一致。如在“汕头海事局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东石油分公司救助合同纠纷案”中,广州海事法院认为,“原告对‘明辉8’轮船载货油的救助行为是基于履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职责的行为,该救助作业属于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并进而根据《海商法》第192条的规定确定原告汕头海事局享有《海商法》第九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在确定具体救助报酬数额时,除了风险费外,广州海事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按照国内市场价格标准计算救助费用的基本主张予以确认,认为原告汕头海事局所主张的救助报酬中,除风险费外,均在救助成本范围内。相对于本案中广州海事法院主要考虑主管机关的救助成本,在“烟台海事局诉宁波港龙海运有限公司海难救助纠纷案”中,在承认烟台海事局的救助报酬请求权之后,确定具体救助报酬数额时,青岛海事法院认为“救助报酬具体的数额计算,应体现对救助作业的鼓励”,并逐项考虑了《海商法》第180条的全部十项因素。
(三)美国做法的借鉴
美国海岸警卫队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在战争时期听从海军的指挥,在和平时期则听从交通部的指挥。自18世纪组建以来,海岸警卫队就按照法定的授权一直提供施救服务。根据《美国法典诠释》第14卷第88条的规定,其目前的服务范围是:“对在公海上和美国具有管辖权的任何水域的遇难人员、船舶和飞行器以及因水灾而受到危险的人员和财产提供援助”。在美国,海岸警卫队作为负责海难救助的专门机构,对施救过程中获救的财产,其传统的方针一向是不主张救助报酬。[9]6-20-24这 一 判 断的主要理由在于,海岸警卫队所用的救助工具属于政府所有,其从事的服务不具有法律关系上的自愿性,因此不能享有救助报酬。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承认海岸警卫队救助报酬请求权的案例,如在American Oil Co.(United States American Oil Co.—The Amoco Virginia)案的上诉中,[10](P732-736)海岸警卫队背离了其传统的方针提出了救助报酬的请求。该案中,Amoco Virginia轮系泊于休斯顿运河的某一码头,在装载汽油并加热燃油时发生了火灾。海岸警卫队负责此次灭火工作并得到了城市消防部门的协助。次日,火势尚未得到控制,而当地用来灭火的化学泡沫灭火剂已告罄。海岸警卫队随即指示海军和空军组织一支空运队伍,并将50多万磅的泡沫灭火剂运往休斯顿,从而使这场大火得以在该日晚间扑灭。随后,海岸警卫队提出89676.66美元作为救助费用,这个数字是指泡沫灭火剂的价值和海军、空军的运输费用。第五巡回法院撤销了地区法院的原判决,判给海岸警卫队主张的全部金额。
该案中,海岸警卫队提出了救助报酬请求,上诉法院也超越常规创造了只要海岸警卫队作出选择,就可允许其主张救助报酬的理论。但在具体救助报酬数额的确定上,法院主要考虑了海岸警卫队超出其职责范围支出的救助费用成本,即其仅限于海岸警卫队使用空军和海军提供的服务和物料范围之内的请求。
这种以救助成本为基础确定救助报酬的方式,在海军的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在 Tampa Tugs and Towing,Inc.V M/V Sandanger案中,针对海军扑灭Sandange轮火灾主张救助报酬,法庭最后以“按劳计酬”的方式赋予了海军相应补偿,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救助报酬。尽管海军并没有局限于其费用支出主张救助报酬。[11]
在我国司法实践对主管机关救助报酬的确定标准尚未统一的情况下,美国这种以救助成本支出为基础确定主管机关救助报酬的方式,既能满足主管机关获取救助报酬以弥补巨大救助费用支出的现实需要,又能兼顾主管机关开展救助作业的公益性目的追求,值得我国借鉴。
五、结语
现在社会在追求“服务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政府负担过重的问题。在海难救助领域,这一表现尤为突出。海上活动以“风险”著称,相对于陆地救援,海难救助面临更大的风险,救助费用支出巨大。当前国家救助经费缺口大的矛盾十分突出,日常救助和训练任务繁重,设备老化严重,都亟需大量维修资金。[12]如果海难救助的全部资金都由国家承担,一方面政府负担太重,另一方面也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在相对于国家救助的私人救助中,被救助方要根据获救财产的价值向私人救助方支付救助报酬。如果针对同一海难救助,只因救助人的不同,被救助方负担就差异巨大,会增加被救助方过度依赖国家力量的救助,而拒绝私人救助力量救助的可能性。
主管机关开展海难救助时所使用的船舶及设备的政府公务属性及其特殊的行政主体身份,并不影响其以平等的救助方身份开展救助作业。主管机关成为《海商法》上的救助方,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承认主管机关救助报酬的背景下,结合我国救助费用面临巨大缺口的现实,应承认主管机关的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同时,鉴于主管机关主要由国家配备公务人员及设备,并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和维持,在确定主管机关救助报酬的具体数额时,应将《海商法》第180条中的奖励性因素排除,主要考虑主管机关的成本费用支出。
[1](加拿大)威廉·台特雷著,张永坚等译.国际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林于暄.国家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J].水运管理,2008,(2):29-30.
[4]郭传光.海事主管机关的救助报酬问题探讨[J].交通科技,2008,(2):113-114.
[5]傅廷中.海商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张丽英.海商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8]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9]Steven F.Friedell,Benedict on Admiralty(V.3A)[M],New York:Matthew Bender,1997.
[10](美)G.吉尔摩,C.L.布莱克著,杨召南等译.海商法(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11]Bruce D.Landrum,Salvage Claims for the Navy and Coast Guard-A Unified Approach [J].Naval Law Review,1989,(38):220.
[12]孙富民.东海海域救助统计,分析与对策研究[A].中国国际捞论坛组委会.第五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