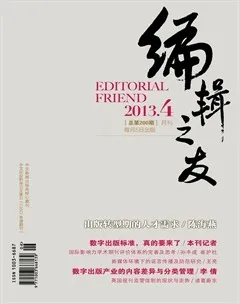从翻译权谈中文简繁体授权的合理性
摘要:
本文拟从翻译权的定义出发,通过分析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相互间的关系,指出简繁体只是不同的中文书写形式,且二者间在使用上也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因此中文的简繁体授权明显具有不合理性,与翻译权的定义相悖。基于此,若内地出版社与港台出版社在版权贸易中只承认中文授权的方法,是目前解决中文简繁体授权不公的一种有效方式。
关键词:
翻译权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授权
一、中国内地出版社版权引进日益频繁
目前,版权贸易几乎与编辑、校对一样,成为出版社的一项常规业务。尤其是2000年后,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且每年都会出现畅销品种,成为推动零售市场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当我们望向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图书出版市场时,不难发现,那些进入内地年度畅销书榜单的简体版图书,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繁体版图书也是高居排行榜前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系列以及《暮光之城》系列等等。因此不管是内地的出版业,还是港台地区的出版业,在图书版权引进已经进入稳步增长通道的当下,业内和相关行业人士关注的版权引进问题已是需要理性对待的问题,而无暇或者未曾去关注简繁体版权引进的合理性问题。且内地与台湾和香港的图书版权贸易自身也处于持续增长中。根据《201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发布》一文,2011年全国出版物版权引进数量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分列第4位和第8位。内地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分列首位和第4位。[1]但在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版权贸易日趋频繁的今天,对中文简繁体授权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少人关注。
二、中文简繁体授权的不合理性
中文的简繁体授权的基础是著作权许可使用的一种——翻译权的授权。原作的翻译权是原作著作权人的一项财产权利。《伯尔尼公约》第8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在对原作享有权利的整个保护期内,享有翻译和授权翻译其作品的专有权利。”著作权人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内将翻译作品的权利授予一个被许可翻译作品的人。因此拥有中文翻译权的出版社或者著作权人即使同时将同一作品授予内地简体版权和港台繁体版权,也与版权公约并不冲突。但是我们若就其中简体版或者繁体版单一授权来看,这种同时将同一作品授予内地简体版权和港台繁体版权的做法明显存在不合理。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5项规定:“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这种另一种语言文字包括译成外国文字和其他民族文字。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文简体和繁体的关系。内地使用的中文简体字是怎么来的呢?据《辞海》,简体字就是汉字中因简化繁难字体而构成的一种笔画相对少的字。其中一部分为国家已颁布推行的简化字。而汉字简化始于清末,大规模的汉字简化则是发端于1949年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化运动。汉字简化就是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化运动的三项基本任务之一。与此相适应,1952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也于1956年1月通过。该汉字简化方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不能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230个;第二部分收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285个;第三部分收用于简化的偏旁54个。[2]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235个,为使用简化字确立了明确的统一的规范。[3]1986年国务院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这些公布的简化字使用至今。因此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86年的《简化字总表》可以说是对千百年来流行在民间的俗体字、减笔字、手头字的规范,是对清末以来汉字简化工作的总结。
从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内地现在使用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规范的简体字有部分是在繁体字简化或者偏旁简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一部分简化字实际上是古已有之,是传承字。[4]这些部分的传承字吴玉章先生在《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中提到:“汉字远自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简体,以后各个时代简体字都有发展。我们的工作只是比较系统地来进行简化,并且使简体成为正体。”因此在汉字由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变迁史中,都有简体字。1949年后的汉字简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历代以来的简化字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而这种整理和总结而来的一些“简体字”,也并非全部简化,而是部分简化。且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还规定了繁体字的许可使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且汉字的简化也是处于一个过程中,远没有结束,有时还根据现实情况,对一些简化字又恢复其对应的繁体。因此就内地目前简体字的使用情况而言,传承而来和简化而来的简体字与繁体字并不是截然分裂,而是处于相互交错的状态。因此中文简体授权就内地实际使用的文字而言,并不科学,因此也就不合理。
在翻译外文时,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中存在一些外来语汇的译名差异,如数码与数位,里根和雷根等,这些大多是由于翻译方法不同或者定名原则、来源不同,对同一外来语采用不同的中文译名而造成的,与是否采用简体或者繁体字无关。因为就同一外来词而言,中文简体的译名也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大哥大、移动电话和手机等对应的都是同一英文词汇。使用这些不同的翻译名词,只能界定为不同的翻译文本,而不构成不同的翻译语言文字。
综上所述,简繁体的授权,其实是不同的中文书写形式的授权。若以此类推,我们是否还可以有隶书字版、草书字版的授权?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中文的简繁体授权其实就是中文的重复授权。只不过现在的图书版权合同严格规定简体版和繁体版的范围,而不至于公开与版权公约相冲突。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字发展史。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行假名规范化,实行全面的汉字注音,经历了整理字体和简化笔画的运动,发起罗马字运动,但日文的翻译授权目前也是基于现在使用的日本文字,从来不曾授权日本历史上存在的其他文字。对照其他文字翻译权的授予,中文简繁体分别授权明显地体现了另一种标准,这与《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 “本联盟各成员国,受到尽可能有效地和尽可能一致地保护作者对其文学艺术作品所享权利的共同愿望的鼓舞”是有冲突的。这种状况不改变,实际上也违背了《伯尔尼公约》。
三、解决简繁体授权不公问题88f95b53842a227769613edd2f5e7455的一种较好方式
翻译权的所有者能简繁体授权是基于事实上内地和港台地区所使用的中文的不同书写形式,而要想避免这一不公正,除非是客观上不存在简体和繁体的使用,就是让简体阅读市场和繁体阅读市场统一趋于一个阅读文本。但综观现实,历史的原因形成的文字书写形式上的不一致,客观上要统一,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在此基础上简繁体分别授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使得授予权利的外方坚持不肯让步。但我们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做到,即所谓“求同存异”。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说,应在与港、台方面协商的基础上明确简繁体分别授权之不合法理。在实际操作上,内地和港台地区出版社真正携起手来,一起与国外出版社或者著作权人统一谈中文授权,即任何一方获得中文版权后,可以自行确定使用何种方式(简、繁)翻译,不应承认简、繁分别授权。已出某种形式(简、繁)的中文本后,再出另一种形式(简、繁),可以是该出版社自己(因为一般外方授权后,被许可方不能转让),也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或者自己的子公司出版另一个版本,数量计入外文授权的印制总数,也确保了翻译权所有者的经济利益。而在取得翻译权授权的时候,只需支付一次预付版税,在翻译报酬上,也不用多支出一笔。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图书生产制作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共同策划营销,扩大图书市场宣传的力度,共同推进图书的销售。这样的做法,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中文图书市场的整合。因此这种内地和港台地区同一家出版社签下中文翻译权的做法不失为目前解决简繁体授权不公问题的一种较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张洪波.201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发布[EB/OL].中国新闻出版网网址.http://data.chinaxwcb.com/epaper2012/epaper/d5368/d5b/201208/25433.html.
[2]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7.
[3] 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9.
[4] 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序)[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