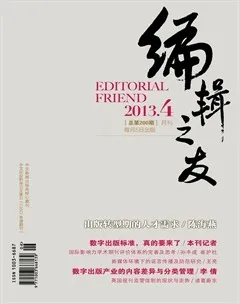清末“新政”与新式官报

摘要:
清末“新政”期间,新式官报迅速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了报刊与社会变革间的能动关系:一方面,急剧的社会变革为官报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和土壤,官报的功能、内容和形式、体系均迅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官报不断为“新政”摇旗呐喊,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政”的发展。但归根结底,官报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作为一种舆论控制的极端手段,在清王朝覆灭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关键词:
清末“新政” 新式官报 舆论控制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遭遇空前危机。为挽救统治,清廷实行“新政”,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全面展开。为配合“新政”的推行,清廷创办官报,掀起了晚清报业的又一轮高潮。与传统官报不同,这一时期的官报在功能、内容和体系上都呈现出近代化报刊的特征,是为“新式官报”。以往对于新式官报的评价,学者多是从文本内容的角度来衡量官报在近代报业发展中的地位,难免有些偏颇。清末新式官报在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乃至中国政治运动史上,都应有着不容回避的一席之地。表面看来,是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官报的消亡,但通过研究不难发现,作为舆论控制的一种手段,新式官报在清王朝覆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一、新式官报是“新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
清末新式官报肇始于1896年,于“新政”期间达到顶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敏在《新式传媒应对无方与清朝的覆灭》一文中道:“从1902年12月《北洋官报》创办到1911年底,清政府至少办有106种官报,分别由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军政机关创办。”清末何以兴起一股官报高潮?除与外报的传播密切相关外,最主要原因在于“新政”的推动。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使清王朝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慈禧太后被迫举出改革大旗。1901年1月29日,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声称变法之不可缓,并要求各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1]4月21日,清政府设立政务处,作为议商变法条陈、制订新政措施的机关,标志着清末“新政”正式启动。“新政”期间,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采用多种渠道、方式表达对“新政”的态度和看法,呈现出一派舆论鼎沸景象。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为新式官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前提。概括起来,“新政”期间沸腾的社会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政”期间,新旧矛盾的冲突异常强烈,普通民众对于“新政”持排斥态度,“新政”的各项措施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导致国内谣言四起。“新政”之“新”,在于“平素所未见未闻”,改革力度之大远远超出想象。加之官方信息传播渠道封闭而单一,上情下达通道不畅,民间难免将其“传为异事,演成不经之说”。有学者研究发现,“新政”时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谣言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新政”乃清廷奉列强旨意为洋化中国而举办;“新政”专与人民为难,是害人之举、虐民之政;“新政”是封建迷信所致的奇谈怪论。[2]这些谣言逐渐汇聚为一股强大的反“新政”的社会舆论,且多数最终演化为暴力形式的“民变”。在此形势下,清王朝专制统治下的舆论一律与政治控制面临着严峻挑战,官报的创办成为大势所趋。
二是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也不同程度地发出对“新政”的质疑之声。言禁、报禁放开之后,报刊数量大增(如表1所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末报刊表现出严重的“去官方化”倾向。在众多报刊中,“为清廷控制者不足10%”。[3]相反,由民间人士创办、民营资本介入的民办报刊数量多、比重大,在社会舆论中居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些具有合法身份的民间报纸,或对“新政”心存质疑,或隔岸观火,有的干脆明目张胆地与清政府“唱反调”。
以“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事件为例,国内舆论对此反应强烈。一些报纸围绕考察政治的上谕,陆续发表社论、评论、专论,对此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对考察的目的、考政大臣的选拔程序等存在质疑。《民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考政”的本质在于粉饰“新政”,不过借考察政治之名“掩人耳目”罢了。[5]《大陆》也痛斥出洋考察目的不明确,“本意不在考求而在功名”。[6]《申报》更是撰文指出,考政大臣的选拔范围太窄(仅局限于宗亲、枢臣、户部堂官、督抚),其选拔程序有悖于立宪精神,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强国,而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专制政体。
可以看出,“新政”期间谣言泛滥、各种负面舆论充斥媒体,社会舆论已至失控地步。这些失控的舆论一步步侵蚀着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根基,一点点地掏空着“新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使得清廷意识到抢占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廷对于官报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内外创办官报的呼声日益高涨。创办官报,抵制民间报刊,钳制舆论,已为内廷与外朝共识。
清末新式官报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分布之广,可以说创下了官报历史之最。但归根结底,官报是“新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级官报的创办是在“新政”三道谕旨的推动下实现的,即变法上谕(1901年1月29日)、预备立宪谕(1906年9月1日)、立宪施行方法谕(1907年7月8日)。这三道谕旨,是官报在陈述开办理由及其宗旨时再三引申的。三道谕旨的核心,是在指出变法必然性的前提下,强调沟通上下之间和国内外之间的信息交流,培养“新政”人才,达到立宪自强的目的。 围绕这三道谕旨,统一社会舆论并论证官方政治变革的合法性,是官报承载的重任。然而,新式官报未能担负这一职责,反而在与民间、外报等媒介系统的对话和冲突中,消解了清王朝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二、客观地看待新式官报对清末“新政”的作用
1. 新式官报直接推动了“新政”的发展。如前所述,新式官报是清末“新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是“新政”的舆论阵地。官报不仅成为传递新政思想、发布政令、推行“新政”的重要媒介,同时,其官方喉舌的舆论强势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间舆论的影响力,对“新政”的推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清廷通过创办官报、颁布法律等手段,赋予官报法定的权威地位,逐步确保官报在“新政”进程中的舆论领袖地位。从1851年咸丰帝严斥江西学政张芾刊刻新式官报之请,到1898年光绪帝下诏动员各级官吏“劝办”报纸,到1907年拟写官报章程,一改过去不直接办报的传统,身体力行,表明了对于报刊舆论的重视,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1902年《北洋官报》创办到1911年10年间,清廷通过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始官办而终归商办、始商办而终归官办等方式,至少控制了111种官报,占当时创办近千种报刊的11%。与此同时,清廷还通过查禁和制订新闻法规,进一步加强对新闻舆论的规范和控制。自1906年至1911年的5年时间内,有关部门先后制订了一大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或含有调整与规范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与法令。以巡警部1906年10月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为例,共有9条内容,基本上属于禁令性质,其中有8条都属于防范报刊宣传危及其统治地位的规定。如此一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清廷将创办官报作为疏导民意与控制舆论的居心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从内容结构看,官报还不忘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北洋官报》《南洋官报》《河南官报》《湖北官报》的内容看,官报报道始终以“新政”为中心,为“新政”的推行提供官方的信息引导,充当了清廷“耳目喉舌”的角色。以《北洋官报》为例,该报强调其宗旨是“通上下”,通过刊载圣谕广训、上谕、本省政治、本省学务、本省兵事、近今时务、农学、工学、商学、兵学、教案、交涉、外省新闻、各国新闻等内容,[7]以普及“新政”知识。《湖北官报》登载内容也大同小异,包括圣谕、谕旨、抄、辕抄、要电、要闻、政务、科学、实业、杂业、图表、论述、国粹篇、新说、纠谬篇、校勘、衔名、商标。[8]可以看出,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是官报刊载最多的三项内容。这一方面是服务于“新政”的需要,另一方面,官报也期望以此规范民间报刊,“勿以狃习旧故之见,疑阻上法”;[9]而要规范民间报刊,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有官报以纠正其失,示之准绳”。[10]
尽管官报以服务“新政”为宗旨,体例和内容大同小异,但依托其“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11]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有关“新政”的各项举措、法令、最新进展得以通过行政系统直接发往地方衙门和学校。特别在一些偏远地区,信息闭塞,民间报刊发展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官报便成为人们了解消息的主要“窗口”,在引导舆论、推动新政实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 新式官报的创办,扩大了新政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央级的官报还是地方官报,都以启迪民智、通上下内外之情、宣传“新政”为宗旨,其发行市场主要在国内。但也有少数官报将发行市场延伸到了海外,如创办于东京的《官报》和《远东见闻录》,均以留日学生为读者对象。客观地讲,这些官报虽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甚至对改良派倡导的自由、民主思想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新政”不遗余力的报道和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阶层的看法,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较之以往相对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象,为“新政”的顺利开展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
以往对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学界多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对“新政”持片面化的否定居多。事实上,国外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从“新政”发轫之日起,就表现出一种“同情式的理解”。这与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不无关系。有学者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倾向塑造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并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从传教士的著作中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看法的转变,如明恩溥的《中国概况》(1903)、梅子明的《巨人觉醒》(1906)、明恩溥的《中国的进步》(1907)、丁韪良的《中国的觉醒》(1907),以及蒲鲁士的《新中国的发展》。上述著作中,传教士对“新政”的改革措施虽时有批评和质疑,但总体上持同情、支持态度。“新政”还引发了海外报刊媒体的关注。韩国《皇城新闻》用大量篇幅报道清末“新政”,内容涉及“新政”的方方面面。值得一提的是,该报还撰文肯定“新政”的积极意义及其对中国前途乃至东亚大局的贡献,称赞 “新政”是清政府在危难之际穷则思变、“豫机奋图”之举,表明“清国之人心不至瓦解,清国之时势不至土崩”。[12]《大韩每日申报》则对“新政”实施后的一些新变化,尤其是清廷的预备立宪,给予了高度肯定,即不管内容真假如何,实际效果如何,预备立宪都可称为“文明前途之初启轫也”,[13]无疑给政治改革带来了一线生机。
结 语
清末“新政”,政府大力倡导官报,既有识时务的一面,更有利用官报来控制社会舆论导向的一面。但归根结底,官报以“挟清议以訾时局”为使命,根本目的在于“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反动性注定了它必然是一项失败的活动。原本期望通过建立官报系统与民间报刊系统、外报系统争夺舆论主导权的清王朝,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在舆论压制和操控的极端手段下,逐渐丧失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垮台。
参考文献:
[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中华书局,1958:4602.
[2] 黄珍德.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3] [4] 刘增合.试论晚清时期公众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J].江海学刊,1999(2):132-133.
[5] 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N].民报,1906(01).
[6] 论五大臣出洋事[J].大陆,1905(10).
[7] 唐臻.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与演变[EB/OL].载成舍我先生纪念馆网站,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id=294.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55.
[9] 教育·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J].第二年第三期.
[10] 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3.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文教类(第2号)[M].
[12] 李斯颐.清末10年官报活动概貌[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3).
[13] 清国有革新之善策[N]//皇城新闻第4卷61号(第2版)光武5年(1901-03-22).
[14] 清国立宪问题对所感[N]//大韩每日申报第6卷第778号,第1版,1908-04-11.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