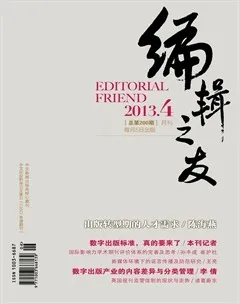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舆论引导必要性的思考
摘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众媒介素养不高,而且舆论界也呈现出相互竞争、冲突甚至对抗的乱象,政府舆论引导变得必要而迫,在此方面,发展新闻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舆论引导 发展新闻学
发展新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应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应根据国家利益引导舆论,在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利益、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到“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1]发展新闻学的这一理念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舆论“乱象”的存在是舆论引导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大规模重构,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但也必须看到,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这些新事物、新思潮可谓鱼龙混杂、良莠难辨。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西方意识形态更是裹挟着各种社会思潮进入中国舆论领域,使舆论显得多元而混乱。
不仅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受西方新闻理念影响,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弥尔顿“意见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机制”理念崇尚有加,积极践行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由于不能完全洞察西方意识形态实质,许多新闻记者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对西方设置的议程框架亦步亦趋,却从不做认真判断与思考,致使生产出的新闻报道完全丧失了国家与民族的立场。
鉴于此,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乱云飞渡”的舆论“乱象”中,新闻人必须透彻理解发展新闻学倡导的建设性舆论引导,明白建设性舆论引导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难免受到外来舆论攻击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不仅借此歪曲、丑化中国,还借机向中国输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是基于当时苏联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的现实。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不改革就会出现严重社会问题,所以戈氏推行改革符合彼时苏联经济发展要求。但为什么改革会中途夭折并导致一个执政党的覆亡和国家的解体?为什么执政的苏共在覆亡之际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与帮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停滞与衰败。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提高,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得人民与共产主义信仰渐行渐远。苏共给执政党以警醒: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该国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度,也决定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及话语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与此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富足,中间阶层规模不断扩大并由此发挥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成为全社会认可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状态,成为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保证。经济富足与“集体意识”使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有效维护了国家社会稳定,社会舆论因此一般不会危及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对媒体管控相对宽松也就在情理之中。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使迅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在人均指数面前显得颇为尴尬。经济实力不足使部分民众艳羡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物质丰裕,加之发展不平衡和腐败等问题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民众对于国家的忠诚,如果再有各种思潮和敌对势力的浸淫与蛊惑,民众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与迷茫就在所难免。事实上,就功能而言,新闻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议论国是、监督执政,更应该是支持执政、实现政通人和;媒体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批评和促退,而是建议和促进。新闻人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用通达上情、正面说理、激励前进的正面报道为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媒体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必须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必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发展新闻学强调,新闻媒体应配合本国政府完成发展的任务。因此,“新闻一定要服从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没有说一个非开放的政治能够承受一个开放的舆论,舆论一定是政治的一部分,舆论的进程一定要符合政治的总进程,它才是理性的,过度的自由对中华民族是一场极端的灾难……现在的社会背景之下,在适度自由的条件下从事中国的新闻”。
总之,以发展新闻学的视角看,当一个国家还未发展稳固到足以抵御各种外来势力干扰之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并引导舆论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利于国家稳定,而且能够有效地维护民众利益。媒体必须承担引导舆论的责任,用建设性的新闻理念补充甚至替代以解构和批判现实为追求的报道理念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一种共识。
三、公众媒介素养不足以辨识参差不齐的舆论信息
媒介素养简单说就是鉴别、选择、解读媒体信息的能力,其状况“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文化发展的水平相关”。[2]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十分重视公众媒介素养教育,从小学或中学就开始教育学生如何识别选择和解读媒体信息。[3]这种教育使西方公众从小就懂得媒体的信息需要鉴别与选择性接受,要经过头脑批判性地解读。良好的媒介素养,使公众不会轻易受媒体左右与影响,并能够理性综合判断新闻信息的真实性。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公众媒介素养正处于培育和形成过程。由于长期忽视媒介素养教育,很多公众对媒体信息盲目信任或否定,缺乏批判解读媒体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即便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公众,对于新闻的产制过程也知之甚少。一份来自美国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其中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仅为41%。[4]该报告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公众倾向于相信和传播负面信息,而且在传播负面信息的过程中不去思考、不做求证、不加判断,结果就是不自觉地进入西方媒体设置的议程——西方更倾向负面报道中国,在思想和行为上盲从媒体舆论。对此,政府和媒体不能不高度警惕。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众媒介素养不足以辨识新闻信息,看不清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不能客观理智解读信息中含有的“刻板成见”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基于公众媒介素养不足及西方媒体的偏见,我国媒体必须突破西方媒体对中国设置的议程框架引导舆论,向公众传达符合中国利益的声音。正如麦克马那斯所言:“社会的健康状况和它所消化的信息的‘营养价值’息息相关”“新闻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5]因此,对舆论进行适度引导与管理应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
四、舆论引导的历史借鉴
回顾苏联和俄罗斯新闻历史,教训不能说不深刻。苏联斯大林时期,政府对媒体管控极严;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原则”;进入叶利钦时代特别是普京掌控俄罗斯以来,俄罗斯政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重新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总体看,俄罗斯新闻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紧-松-紧”的变迁过程,而后一个“紧”——政府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强化对新闻媒体的集中管理——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舆论问题的全新认识:“这样做有利于维持政局稳定,也有利于推行各种改革措施。”[6]
舆论与社会发展需要相一致就会加速社会发展进步,舆论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背离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甚至破坏作用。“当舆论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破坏作用积聚起足够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7]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政府对舆论的引导和管控是必要的,媒体必须担负起舆论引导责任,营造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舆论环境,建构并引导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念,强化社会主流价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闻媒体必须摒弃西方新闻价值观中对“反常”“冲突”等负面报道的过度追求,强调新闻传播的正面、健康、和谐,将新闻传播置于社会大系统中。从社会发展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考虑新闻信息的传播应成为媒体的不二选择。
社会控制论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认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在各种社会控制中,政治控制作用最为突出。政府为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就需要获得公众的忠诚和拥护,即对其合法性的肯定。[8]要肯定这种合法性,就需要一个正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舆论,因为“舆论具有为政权合法性补给能量的功能”。“但是,舆论也可以从反方向释放能量,质疑、消解、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9]基于此,发展新闻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并倡导媒体的社会责任,反对不受约束的无限制的新闻自由。
实践证明:舆论引导与管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在分化、多元、碎片化的舆论格局中营造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主流舆论,发展新闻学所强调的建设性新闻理念显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61年,国际新闻学会出版的《积极的新闻屋》要求“现代记者改变新闻价值的观念,要生动、综合、系统而有意义地报道社会的正常现象,将人类重新导入一个和谐而幸福的世界”。[10]毫无疑问,发展新闻学的理念为“将人类重新导入一个和谐而幸福的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形态及其当代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2001ML)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45.
[2] 段京肃,杜俊飞.媒介素养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0.
[3]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69.
[4] 调查称中国民众偏好分享负面评论[EB/OL].http://news.163.com10/0804/07/6D7P84LD00014AED.html.
[5] [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M].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5.
[6] 程曼丽.“松”与“紧”的变奏——现行俄罗斯新闻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J].国际新闻界,1996(4).
[7] [9] 赵强.舆论安全:一个务须重视的现实课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8] 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591.
[10] 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J].今传媒,2010(8).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