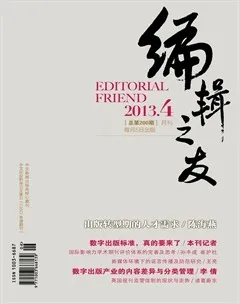媒介融合时代记者个人微博叙事的伦理困境
摘要:
媒介融合趋势改变了传播领域的生态环境,传统媒体的记者开始在商业网站的微博平台中亮相,然而,个人微博叙事是否也应遵守职业伦理?个人微博的私人属性、组织属性和公共属性到底如何区分?文章从记者、受众和媒介三个不同层面来解读。
关键词:
媒介融合 记者微博 伦理 困境
互联网语境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即来自传统媒体的记者以实名身份在商业网站开设个人微博,既发布各类新闻信息,也公布一些私人生活与情感的内容,更有对时事的关注与点评,叙事风格上一改传统媒体的严肃刻板,呈现出随性活泼的鲜明个性特征。据新浪网2012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上开通的媒体人账号已经超过7万个,[1]媒介融合时代记者个人微博已具相当规模,其作为信息平台的重要功能及在舆论中发挥的影响力均不可小觑。
按理,记者以个人身份开设微博,其嬉笑怒骂均属个人自由,理应受到尊重,但是,一方面,记者在个人微博上也发布新闻信息,那么受众必然对其有一定的职业伦理期待;另一方面,由于记者业已存在的影响力,其周围已聚集大批粉丝,这些网民在接受其发布的即使带主观倾向的新闻信息时也易受其左右,由此导致的种种后果往往为记者所始料未及。如此,记者进行微博叙事时往往遭遇伦理困境,笔者试图从记者、受众和媒介三个不同层面来解读其深层原因,并提供建议。
一、记者个人微博遭遇伦理困境之深层原因
(一)记者层面:多重身份背景下角色定位的模糊化。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如一个成年男子,就可能有父亲、丈夫、儿子、公务员等多个身份,这些身份很多时候并不冲突,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可能因利益取舍而发生矛盾,从而使当事人处于伦理困境。关于记者身份,早些年因为先拍照还是先救人的问题曾引发大量争议,如《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发表骑车人在暴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照片,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为抢救落水者,果断放下采访任务为其做人工呼吸的事件等,这些在新闻实践中发生的职业责任与社会公德的冲突现象,归根结底表现为特定情况下角色定位的困境:定位在“记者”还是定位在“普通公民”,由此采取的行动会大相径庭,后果也必然不同。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存在已久的身份冲突被进一步激化。其一,记者跳出传统媒体的束缚进入商业网站开设私人微博,就是为了能够轻松自由地书写,此时,他更多地是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在叙事。其二,记者又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媒体的影响,毕竟网上网下他都是以实名的身份在叙事,聚集在微博周围的大量粉丝们,很自然地将其言论看做其职业活动的延续,此时,他更多被看做以记者的身份在叙事。实际上,很多传统媒体正是借专业记者开设的微博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推向深入,由此来抢占社交平台的制高点,延伸自己在社交平台中的领地。其三,某些记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利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来达到影响舆论的效果。如2011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李铁在微博中发表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妥言论,引发笔仗与“内讧”;又如有些记者在姓名前署上所属媒体的名称或在微博中有意提及媒体名称,此时,博主身份的定位更加模糊化,其私人微博更像一方介于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无法彻底廓清。这种语境下,记者在微博上发布信息或发表言论时便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这就是麦奎尔指出的媒介职业角色的困境之一——“积极地参与与中立地传输信息之间的矛盾”。[2]在这二者的纠葛中,记者为模糊化的多重身份所困扰,陷入一种伦理的困境。
(二)受众层面:碎片化传播背景下对信息的误用与误读。微博短小精致,由于受字数上的限制,更像一个拉长版的标题,更多的信息被切断或隐匿,尽管可以通过设置超链接来拓展信息容量,但在微博以秒为单位刷新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只是停留在“首层信息”的了解上。微博主为迎合这种趋势,也尽量以更少的文字来阶段性地呈现关键信息。如此,微博平台整体呈现出碎片化传播的态势,并在无数次“转播+评论”的过程中再次被碎片化,一篇微博被多人转播和评论后,有时很难分辨出谁在“说”、“说”了什么,以及谁在“被说”。
在碎片化的信息海洋中,微博受众往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们在转发记者微博信息时,更多地衡量的是该信息是否符合其对新闻真相的自主预期,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客观审视,由此便可导致受众对记者微博信息的误用。《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曾对微博中碎片化信息传播对事实真相的掩盖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并认为,倘若受众“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只是选择性地撷取能证明自己偏见的信息和所谓‘证据’”,那么,寻找真相的过程便只是“强化自身偏见的过程”,只是“依赖既有的碎片化信息,去还原一个符合自己期待的真相”。[3]此外,由于微博具有即时发布的特点,一些需要整体来审视的系列微博往往被受众关注的其他微博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又容易导致受众对记者微博信息的误读。
不论“误用误读”还是“正用正读”,都属于受众对记者微博信息的关注,并可能推动新闻事件的进程。据研究者石扉客对微博的调查发现,经由微博的介入,焦点事件“完成一个公共话题所必须的社会情绪酝酿和发酵”,并由此发展成为“公民动员”,其中每一环节都只需要24小时。[4]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开放的叙述场中,多元叙述主体均可参与叙事,但是,作为公众人物的记者,往往成为其中的“优势叙述者”,会聚集大批支持者,在不断“转播+评论”的过程中为舆论推波助澜。在此过程中,舆论可能被引向正确的方向,也有可能被误导,造成媒体逼视或媒介审判。
(三)媒介层面:微博作为一种叙事媒介的“无意识”助推。媒介往往被视为一种中介因素在各种场合被忽略,然而,媒介并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一种工具,它一旦进入各类社会现实,就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内容的品格,尽管它无自主意识,但是为叙事提供载体的同时,其鲜明的媒介特征将改变新闻叙事的表意行为及过程,为其带来全新的模式和形态。
1. 微博模糊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界。尽管记者开设的是私人微博,拥有的似乎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在其中可以随意书写。但他不可能总是停留在“自言自语”的阶段,会关注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人,也会被更多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关注,正是在这种“看与被看”“说与被说”的过程中,微博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它的价值。如此一来,经由无数次“@”,私人微博已不是“一言堂”,而是成为一个颇具公共空间特征的“群言堂”。空间界限的模糊化为身份定位的模糊化提供了发酵条件,从而对记者微博叙事的伦理困境形成“无意识”助推。
2. 微博的嵌套性话语结构容易导致信息的被误解。微博的特色体现在单条信息的有限容量,及非常便利的“转播”与“评论”功能。正是在层层转播与评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微博的嵌套性话语结构。有研究者认为,微博的传播特性可界定为“结构上的拼图性、话语上的嵌套性、时间上的扩散性”,并认为“嵌套话语”之下,“微博的信息内容、消息来源得以完整、清晰地呈现。由此带来了信息甄别上的便利性”。[5]然而,这种信息甄别的便利性并非总是存在,一旦转播与评论的层次增加到一定限度,便极易造成信息结构的混乱,倘若不仔细加以分辨,一个没有受过良好微博技术训练的网民很可能对信息误解。
3. 微博的传播性能易于信息的快速扩散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微博的巨大效应正在于叠加了内容与用户,既有内容的聚合,更有用户的聚合”,[6]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传播的四种方式——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聚合到了微博的单一应用上;从技术角度看,微博是一种节点共享的即时通信网络,对信息资源的凝聚力和整合力超越以往任何媒介,这种技术性能通过互联网自然嫁接到新闻报道上,使微博新闻具备核裂变式的传播效能。
记者作为公众人物在这个舆论场中显然处于“意见领袖”的位置,倘若不能秉承客观公正的叙事风格,随性随意发表言论,则很有可能在粉丝的拥护下经由微博技术平台的“无意识”助推导致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已进行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即便记者声明“言论与所在媒体单位无关”,也是无法全部免责的,原因在于:(1)公众关注记者微博,包含着对新闻人的期待和对其所在媒体公信力的信任;(2)微博运营商在给记者微博实名认证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优先权。[7]因此,记者一旦开设实名微博,就须以职业伦理为规约,恪守表达规范。
二、记者个人微博伦理困境中的策略选择
对于记者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更多是聚焦于传统媒体环境,当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结合改变了传播领域的生态环境,便需要对该问题重新审视,尤其是大量记者在网站集体亮相的今天。
1. 媒体层面。制订可操作化的细则进行管理并培养记者的归属感。记者所属媒体应制订可操作化的细则对记者个人微博叙事的行为进行管理,明确其身份所属,如对记者的实名微博进行备案,提醒记者时刻保持反思。美联社某记者就曾因没能把握好这种身份平衡遭到高层谴责:他擅自将该社摄影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捕的消息发布到Twitter上,美联社高层在内部邮件中严厉指责该行为,并规定一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图片或视频都要首先提交给美联社,而不能自行在Twitter之类的社交媒体上发布。[8]针对这种越来越普遍的记者使用社会化媒体从事新闻活动的行为,路透社很早就制订了详细的规范,其2010年起在《路透社报道手册》中专门列出的《网络报道守则》[9]可资借鉴。此外,传统媒体在鼓励记者实名开博的同时,也应着手树立威信,使记者对其有强烈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自觉规约自己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开设私人微博的方式来实现对媒体约束的“逃离”。记者微博其实相当于所属媒体的一个子媒体,其言行会对所属媒体形成一种辐射效应,二者倘若能实现良性互动,其结果必然是互惠互利的。
2. 受众层面。提高网民素养,理性审视网络信息。互联网实现了媒介的大融合,然而,网民的媒介素养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网络中侵犯隐私权、名誉权的事件屡屡发生,更有各种对信息的误读所导致的网络谣言。网民应仔细甄别信息真假,不妄加评论;对于记者微博中明显的个人化戏谑观点不恶意转发和评论;在事实真相尚未澄清时,应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各种观点,不轻易定论;在网络中维护个人表达权的同时,更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各种权利为前提。
3. 记者层面。把握新的叙事语境,把慎言谨行当做一种义务。媒介融合时代带来的是全新的叙事语境,习惯了传统媒体叙事方式的记者们,一旦转移阵地进入互联网的微博平台,就应对新的叙事方式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全新的认识。微博平台模糊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那么,一场所谓“内部”的讨论则很有可能在无法预知的情况下被无限放大,直至成为“公开”的矛盾。毕竟,记者更多的是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他往往因掌握更多的事实信息而自成意见领袖,其言论也更多的被网民当做其所属媒体发出的声音,所以应自觉遵守新闻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1] 新浪头条新闻.微博粉丝突破一千万[EB/OL].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2-02-27/181924012511.shtml.
[2]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2.
[3] 曹林.调查者越多,真相越模糊?[N].中国青年报,2012-09-05(02).
[4] 石扉客.鸿忠抢笔:两场24小时微博传播战[J].南方传媒研究,2012(23):119-126.
[5] 罗昶.拼图结构、嵌套话语与扩散时间: 叙事学视域中的微博传播特征分析[J].现代传播,2011(7):118-121.
[6] 詹新惠.网络新闻写作与编辑实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08.
[7] 张志安.记者微博的价值和规范[J].中国记者,2012(5):95-96.
[8] 彭兰.记者微博: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碰撞[J].江淮论坛,2012(2):154-158.
[9] 路透社网络报道守则:规范使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EB/OL]. http://news.sina.com.cn/m/2011-02-19/113821980415.shtml.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