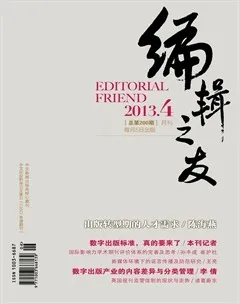谣言传播与微博辟谣
摘要:
随着微博传播效力的日益扩大,谣言开始借助微博这个平台大规模传播。怎样建立一个良性的言论机制?本文认为微博辟谣是一种社会言论自我净化的机制,但在对于谣言的判断和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体系,构建起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舆论环境。
关键词:
微博 谣言 辟谣 言论体制
2010年,微博开始了井喷式的发展,众多门户网站和媒体网站相继推出微博,知名网友的主要活动阵地纷纷向微博转移,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微博发展的元年,但是,在微博的传播效力日益扩大的同时,谣言也借助这个平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显著方式大规模传播,如从“金庸去世”到“抢盐风波”;与此同时,微博的管理被提上议事日程,微博辟谣随之成为热门话题,几大微博运营商都不约而同地开设了官方辟谣账号,各种民间微博组织和人员也纷纷开展了辟谣工作。时至今日,微博辟谣机制已渐成体系,初有成效,但对其删除、禁言等措施,很多网民颇有微词。现代社会中,怎样才能建立一个良性的言论机制?本文通过分析微博辟谣的内容及机制,认为微博辟谣是一种社会言论自我净化的机制,但在对谣言的判断和处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要真正实现媒体的社会协调和监测功能,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体系,构建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舆论环境。
一、辟谣微博的现状
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微博辟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辟谣微博,于2010年11月18日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到2012年7月20日已经被90万余人关注,共发表309条微博。此外,2011年5月18日在新浪微博注册的另一个辟谣账号——“辟谣联盟”,因其与官方姿态对立的自发性和民间性,也备受关注,至2012年7月,“微博联盟”的粉丝量已近8万,共发表197条微博。与新浪辟谣微博并行运营的还有腾讯的“谣言终结者”、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等,它们的关注度也都分别达到25万和10万之余。各大微博运营商纷纷开设官方辟谣账号,各个社会组织联手在微博上注册辟谣账号,一时间“辟谣”之声高涨,打击制止谣言的行动如火如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辟谣。新浪“辟谣联盟”成立宣言中这样指出:“在新浪微博,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实现自己龌龊的目的,在微博上肆意造谣传谣,大量网民由于缺乏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成为被忽悠、被欺骗的受害者,许多人还在无意识下成为谣言的传播者。这些被转发了成千上万次的谣言,让一些网民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充满怀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忧虑,侵害了无辜者的正当权利,伤害了整个社会的诚信,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辟谣联盟”的宣言认为,谣言是一些有着“龌龊”目的的人制造,并由不理智、容易上当的民众轻信并传播,进而制造了社会混乱,造成严重危害。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辟谣,就成为一种正义的力量。在辟谣者眼里,信息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不实的虚假信息,另一方是准确的真实信息。只要传播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在民众中间传播较广、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信息)不准确,有不实之处,就是造谣,就需要纠正,就需要驳斥,否则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微博辟谣者还进一步认为甄别、核查信息的真伪虚实是一个带有专业性质的技术活。普通民众并不具备鉴别信息准确性的能力,专业的机构有人才和技术上的优势,有能力把真相公之于众。
2. 辟了什么谣。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11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统计,2010年经由新浪微博曝光并证实的谣言有21起,而2011年这一数字迅速升至176起。[2]这个数字显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差不多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条规模较大的谣言出现。那么数量如此之多,被辟谣者认为造成严重影响的究竟是些什么谣言呢?笔者通过对“微博辟谣”“辟谣联盟”“谣言终结者”“谣言粉碎机”“科学松鼠会”等微博辟谣账号以及辟谣组织主要发起人的个人微博包括“吴法天”“点子正”和“尼德兰苹果”等微博的内容进行浏览和粗浅的统计,认为这些微博所辟的谣言中,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谣言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关涉名人的不实消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就是得益于在公众中极高的知名度,因此关于名人的新闻(生死、婚恋、言论甚至一举一动)历来就有着极高的新闻价值,极易引起众人的围观。靠名人吸引眼球,已经是许多媒体、企业和个人宣传、推销自己的一剂良药。许多关于名人的新闻报道,重点其实不在“信息”,而是重在“名”了。所以,名人和谣言自古就形影不离。微博辟谣也自然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名人新闻上,除专业的辟谣微博,名人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个人微博都是辟谣的主力军。
围绕突发事件的谣言。突发的新闻事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在事件突发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人往往不是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所以,报道信息的人要么不专业,要么不亲历,都给突发事件的报道带来了难度。所以,突发事件新闻也往往都是谣言的“重灾区”。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及核辐射事件和之后出现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都出现了谣言满天飞的现象。
关乎社会生活的谣言。这类新闻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和民众的亲身体验息息相关,属于社会这个大肌体的神经末梢既琐碎又分散,是社会中某个细节的特写,因此在这类新闻中也极易滋生谣言。比如“2011年湖南隆回县高考考生因迟到被拒入考场而跳楼自杀”“上海东华大学食堂电风扇落下削死学生”“老人被城管殴打受伤”等都是转发量较大的此类谣言。
科普知识谣言。一些以科学研究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内容的科技新闻,既有趣又实用,往往也是人们关注的内容之一。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科技新闻报道比比皆是,这类信息往往打着“最新研究成果”的旗号,驳斥以往的信息,但同时又往往成为让后人批驳的谣言。在当下的辟谣微博中,以“辟谣”的名义,传播科普知识的不在少数,腾讯和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都是以此为主要内容的。
3. 怎么辟谣。据新浪微博“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总结,新浪微博的辟谣机制包括:24小时不间断监控、建立用户举报参与体系、多方位核实保证证据绝对可靠、虚假信息查证后严格处理、多渠道进行信息澄清等五个步骤。[3]从中可见目前的微博辟谣行动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专业辟谣团队为本,更多地依靠民间力量。目前的辟谣微博一般都以几个人构成的团队小组为主要构成形式,这些人都是网络技术或信息处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对网络信息24小时不间断监控,能较早发现引起大规模传播的谣言,并找到传播源头。但由于某些专业领域知识的缺乏或者人力的不足,谣言的发现以及证实阶段仍需依靠更广泛的社会力量。“金庸去世”谣言的最早的发现和求证者就是非辟谣小组成员,“微博辟谣”作出反应已到了第二天。在这方面,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表现得更为明显。“辟谣联盟”本身就是由几个志同道合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辟谣团队,其中有媒体从业人员,也有律师,还有大学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此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自发性和民间性可以说是微博辟谣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二,以核查新闻要素为主,对信息进行纠正和完善。辟谣微博大都认为,谣言之所以造成负面影响,是因为不实信息的误导。所以,辟谣微博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信息的核查上,根据信息中包含的新闻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一一证实,对于谣言进行批驳。如针对“2011年隆回县高考考生因迟到被拒入考场而跳楼自杀”这条谣言,新浪“微博辟谣”指出,事件发生地点不是湖南隆回县“第二中学”而是“第一中学”,同时强调指出“早晨8∶57时警方就接b8861930d4c3814d36e6bc6484732812到报警”,这个时间考试尚未开始,而非谣言中的因考试迟到。“微博辟谣”纠正了谣言中包含的地点、时间两个要素,但其中的原因仍然只有语焉不详的“坠楼原因正在调查中”几个字。这样的辟谣方式能否从本质上消除谣言,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三,对不实信息发布者、传播者进行严肃处理。当证实一条信息虚假之后,辟谣微博,尤其是微博官方的辟谣账户会对该信息进行删除,造成恶劣影响的,会对用户进行暂停发布、暂停关注、删除ID等不同处理。2011年7月29日,著名打假人王海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铁道部又一奇迹,殡仪馆大约零下10℃的冷库里存放了21小时的男子,突然尖叫救命”,并配了一张刊发此新闻的报纸版面图片。这则新闻来自于当天的《南昌晚报》“世界新闻”版中一则发生在南非的事件报道,在一片关于动车事件的声浪中,这则与动车事件毫不相干的新闻居然模仿铁道部前发言人王勇平的语气制作了肩题“这不是奇迹,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这样的制作方式无疑是一种误导。而王海不幸成为其中一员。几个小时后,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账号针对此事发布辟谣消息,并宣布:王海及其他发布了此新闻的4名用户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4]
4. 微博辟谣的影响。在如此这般的辟谣攻势下,微博辟谣又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呢?
首先,辟谣微博作为一种信息的监管机制,对于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起到了积极的“净化”作用。辟谣微博坚持寻求真相,新浪“微博辟谣”组长谭超说:“我们不替任何人说话,只要公众有疑问,小组就尽一切力量寻求真相。”“微博辟谣”做的这些工作,得到微博用户的极大认可,向“微博辟谣”求证、举报不实信息的,每天可达数百条。[5]其次,在这个机制下,广大的社会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言论体制中来,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微博辟谣”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和协调力量。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者说是平民主义的社会,许多学者称之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比较完美的社会自治状态,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与国家进行民主的、有效的交流,让社会拥有更多的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协调的权力。当下的微博辟谣,正体现出这一点,这无疑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微博用户对微博辟谣颇有微词。首先,“辟谣”这个词本身就引来了一番争议,这种对于信息的立场预设,就一些传言和质疑中的瑕疵全部斥为谣言的做法,似乎更像是戴着有色眼镜。其次,微博辟谣对于发布或传播的“谣言”及用户进行处罚的权力和方式的随意性也遭到了质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曾指出,按照传统方式的过分干预,一旦辟谣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时,微博恐怕就失去它存在的本意了。这里的“传统方式”,显然与现代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的言论体制背道而驰。
二、树立理性谣言观
微博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的交互平台,是公众广阔的“话语场”,所以平等参与、营造合意就成为它的基本精神。微博辟谣的出现,这也是根本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对谣言的认识理念的局限。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学科角度深入地研究谣言,就会发现,在“不实信息”的外表之下,谣言还有着许多重要的本质特征。更加理性地认识谣言,是建立科学的言论体制的基础。
关于谣言,心理学、社会学、舆论学等学科都有不同角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树立一个理性的谣言观。因此,有必要从学科的角度对辟谣微博中指涉的谣言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1. 谣言是一种心理平衡机制。最早关于谣言的研究出现在荣格的心理分析研究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中,他们透过谣言内容来解析散布者的行为动机。研究认为,谣言其实只是人们把压抑于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以消除心理不稳定所造成的紧张感。在人的心理上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通过对美国二战期间的谣言进行细致分析也认为,“任何人类的需求都有可能给谣言提供推动力”。[6]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人们的某种强烈愿望是造成谣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原因,谣言就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7]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人的某种心理需求的外显,而并非人的主观臆造,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了谣言的客观自然属性。
由此可见,有很多谣言都具有这样的特性。比如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和核辐射事件中的“谣盐风波”,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每个人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在无所适从的时候,人们相互之间都要彼此慰藉、关心,以此来释放恐惧,“碘盐能够防辐射”的谣言就不胫而走。与其说民众在传递信息,不如说民众在传递一种情感,在释放一种情绪。那么,如何安抚民众的恐慌心理,就不是一两句“辟谣”就能解决的事了。
2. 谣言传播体现了不同利益关系。心理学家研究了谣言产生的心理动机,还对谣言传播的动力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谣言的消息成分在传播过程中会被不断增删或篡改,使其包含了很多错误的信息,这其实是人的选择性记忆心理现象的体现,这样的选择性源于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异。许多著作中引用的“金夫人生病”这则谣言就最好地证明了民众的利益差异性是导致谣言产生变形、讹传,以致有害化的重要原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王海所发布的关于动车事件的一则谣言,《南昌晚报》出于让新闻吸引读者注意的目的制作新闻标题,而根据一般的阅读经验,“标题党”大有人在,也就是读新闻只浏览标题,于是包括王海在内的许多读者很有可能就是只读了新闻的标题,甚至连新闻所在的版面都没有注意到。在当时那个敏感的时期,民众的生死、民众的利益已被大规模唤起,于是,王海这条微博的出现以及被大量转发也就成为必然。在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了王海及民众与《南昌晚报》之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诉求,正视这些言论,进而去追问产生利益差异的原因,才是社会管理者们更应关注的问题。
3. 谣言背后关涉的是隐性的社会问题。与心理学家把谣言看做是个人的心理问题不同,社会学家则把谣言看做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他们普遍认为,谣言中虽然有许多臆想的成分,但都与社会现实相关,所描述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真实,是社会的集体记忆。对此,法国谣言学者卡普费雷指出,用“真与伪”的标准来界定谣言,本身就是一种“完全主观性质的判断”。他进一步指出,谣言揭露了许多隐藏着的真相,对官方的质疑无形中会增加政权的透明度,因此,卡普费雷把谣言比作“第一座自由广播电台”。[8]社会学家之所以如此比喻谣言,其实就是认为谣言描述的“社会真实”“集体记忆”或者“隐藏着的真相”,是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湖南高考考生因迟到拒入而跳楼自杀”的谣言,反映出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令人担忧的现状;“老人被城管打伤”谣言唤起了人们对城管暴力执法的记忆;“红十字会将无偿献血转卖给医院导致有偿用血”的谣言,更是暴露了我国在处理慈善、募捐及医患关系等方面的不透明和腐败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仅仅指出所谓的事实不准确来进行辟谣的话,也许就隐藏了真相。
综上,当我们把目光放在谣言背后所关涉的心理、利益及社会问题时,表层的事件信息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人们不再关注事情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也不会去追问某个数字是否准确,民众关心的只是“存在”。这时,把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的认识,就显得局限和浅显了。也正因为如此,辟谣对公众来说,只是“又多了一条信息而已”,[9]甚至适得其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谣言,辟谣就不再具有辟谣者们所言之凿凿的必要性,而且单纯的纠正信息中的错误成分也往往无法消除谣言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对待谣言,我们需要更理性的态度和方式。
三、建立科学的社会言论体制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不仅需要理性地认识谣言,更需要在一种民主而开放的社会言论体制下理性地对待和处理谣言。谣言不能一辟了之,微博辟谣还需要完善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把谣言当做社会常态,赋之以宽容之心。谣言从表面上看,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或事,而事实上都是与一定的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事件只是问题的偶然状态,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随着显露程度的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谣言就是其中最敏感的反应,也许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也许连传谣者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但它起作用了,这更像一种社会潜意识。由此,可以认为,谣言并不是危机事件出现后的应激状态,而是一种社会常态,既然如此,对待谣言也要有一种平常心。
真相的暴露本身是过程性的,用100多年前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 “用今天的报道来纠正昨天的错误,再用明天的报道来补充今天的不足”。[10]因此,在信息的流通过程中,我们不妨宽容一些,允许这个接近真相的过程的存在。在微博所辟之谣中,“金庸去世”的谣言就充分显示了一种在信息自由流通过程中所带有的一种自净功能。2010年12月6日20时19 分,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用户“中岛”发布的“金庸去世”的信息瞬间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震惊、猜测,纷纷转发,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新闻媒体,相关讨论在1 小时内超过5 万条。在最为混乱之时,也就是消息发布的22 分钟后,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在微博上辟谣并给出证据。当晚,中新社、香港媒体、金庸先生友人等也多方证实,此消息为虚假信息。而新浪官方账号“微博辟谣”直到第二天才正式辟谣。我们可以看出,针对不实之言,微博用户的反应是最灵敏最迅速的,在公开的平台中,完全能够自我发现、自我更正,让谣言不攻自破。而微博辟谣虽然不能说毫无用处,却也意义不大,反倒是删除、封号这些善后措施容易让人不禁心生反感。
2.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监督协调功能,平衡利益矛盾。20世纪初,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一文中就提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三大作用,环境监视;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联以适应环境变化,社会文化世代相传。[11]在传统社会里,大众传媒是缺乏的,或者说是低效的或不发达的,这样的状况直接造成社会底层民众的声音缺乏便捷的表达渠道。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信息的传递已构建了一套高效率的运转机制。大众传播媒介能够把分散的、杂乱的民众议论整合起来,并与国家的信息平行传递,这种处于社会中间、协调上下的作用是大众传媒所特有的。
在这一前提下,大众传媒需要明确自身作为社会组织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身份,需要从民众议论中寻找新闻线索,发现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社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在“随时随地发微博”这个便捷的传媒技术平台的感召下,一些政府要员、管理机构都开辟了官方的实名账户,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倾听民众的声音。当然,倾听并不是为了管制,而是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
基金项目:山西省社科联2011-201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项目:“新媒体提升山西媒体传播影响力研究”(SSKLZDKT2011077);中北大学2010-2012年校级课题“当代大学生对主流媒体宣传报道的接受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辟谣联盟.辟谣联盟宣言[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9053a20100qxhm.html.
[2] 上海交通大学.2011中国微博年度报告[R/OL].中国舆情新闻网.http://wenku.baidu.com/view/d8edbd1d10a6f524ccbf8508.html.
[3] [5] 谭超.微博谣言分析及新浪辟谣机制[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11/11/c_122267486.htm.
[4] 方可成.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EB/OL].南方新闻网.http://news.qq.com/a/20110812/000873.htm.
[6] [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7]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沈阳:开明出版社,1993:475.
[8] [法]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8.
[9] [法]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喻国明.微博辟谣是个伪命题[EB/OL].http://tech.sina.com.cn/i/2012-01-06/12576609750.shtml.
[11] 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3.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