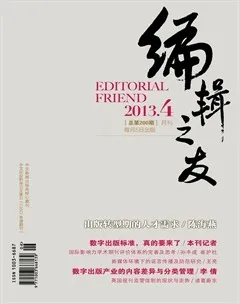数字出版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知沟效应
摘要:
数字出版应用于我国当前阶段的基础教育,会产生知沟扩大的负面影响。知沟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通过经济基础、知识和技术、内容特征和个人动机4个方面的因素产生作用。本文认为通过调整数字教育资源分配秩序,努力激发较低阶层孩子应用数字教育资源的积极性,可缩小知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数字出版 知沟 数字鸿沟 教育资源
一、数字出版的知沟及其层次
数字出版应用于基础教育正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目前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出版企业的经济利益,关注的是出版企业如何把握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盈利机遇。而对这一应用的对象——基础教育所产生的效应关注的还不多,有限的讨论集中于阅读方式的改变对学习效率的影响。出版和学习天然相关,出版物带给人类知识和信息,但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公众中分布并不均匀,“知沟”于是出现。
知沟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说,“社会经济地位高者一般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故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1]产生知沟效应的因素分为宏观和个人两个层次。宏观层面的因素最初由蒂奇诺等人提出,他们从社会结构层面审视不同社会地位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地位、地区、民族、职业和教育,统称“社会经济状况”(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2]S.E.S状况直接决定了社会不同群体中知沟的存在性。艾特玛等学者从个体层面对S.E.S决定论提出修正和批判,他们认为在相同的S.E.S群体内,个人接受信息的主观动机决定了知沟的存在性。总体来看形成知沟的宏观因素特别是经济水平是主导因素,个人主观能动性则是突破S.E.S状况的积极因素。[3]
数字化时代知沟又被称为“数字鸿沟”。数字出版作为数字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也会在公众中产生数字鸿沟,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产生的知沟有何特点,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数字出版衍生基础教育知沟原因分析
今天学界普遍认可知沟的产生受以下4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基础(Access)、知识和技能(Basic skills)、内容特征(Content)和个人动机(Desire)” 。[4]就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在ABCD四个方面的效果很不理想,甚至产生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1. 经济基础。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经济投入。目前我国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扩大,早在2006年我国基尼数已突破0.5的“差距较大”上限,接近“收入悬殊”的最高水平(2006年后我国不再发表基尼数)。[5]产生知沟效应最重要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我国现阶段非常明显。与收入差异相匹配,我国社会数字化资源占有的差距也日益显著,以互联网的普及率为例,根据人口统计的资料,其在地区、城乡、职业和学历上都呈现巨大的差距: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达70.3%,远超云南25%的水平;占人口数过半的农村人口仅占总网民数的26.5%;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达96.1%,而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人群中只有8.5%。[6]因此,我国目前数字化资源占有水平的差异,为数字鸿沟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基础教育领域,数字化资源的分配同样极不平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已普遍接通互联网,电脑也成为基本的教学工具;但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这些硬件设施普遍缺乏。数字出版是高投入产业,它和我国基础教育结合的前提是现有的中小学已具备较好的数字化硬件基础,但受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我国目前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资源分配还很不均衡,这一前提基础还未能较好实现。
目前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结合的试点,电子书包就是典型代表。电子书包的定价一般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加之内容资源和网络的使用费用价格不菲。目前的试点地区因经济发达,政府财政能够为电子书包的成本买单,但试点之后的推行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是否能享用这一免费午餐尚不得而知。因此在其成本不能很好地从受教育者身上转移出去的前提下,电子书包的推广必然导致基础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知沟也随之扩大。
2. 知识和技术储备。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经济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对数字化教育所需的软硬件的拥有水平产生差异,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通过早期使用、熟练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比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孩子拥有更大的数字化技术优势。教育部制订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规定,要在2005年前,所有的初级中学以及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并争取尽早在全国90%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但受长期教育投入不足特别是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不足的影响,该纲要的落实的现状并不理想,软硬件老化、专业师资欠缺导致落后地区的孩子在数字化技术掌握方面存在普遍不足。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教育如电子书包所需要的技术并不十分复杂,但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比掌握技术更重要的是应用。因为缺乏其应用的生活环境,僵硬地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并不能使其真正获益。因此从纸和笔的传统学习方式过渡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数字化学习方式,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3. 内容指向。数字出版服务于教育的效益最终要通过内容体现出来。今天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它们承载的内容无论是内容特征、服务对象,甚至话语体系的取向都有明确的指向。这种指向主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所构建的语境是适合主流社会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对现代媒体的传播内容耳濡目染,掌握程度较落后地区的孩子要高。个体的知识占有差异影响因素遍及生活的每个过程,而既有知识的累积又影响着新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结果导致知沟的持续扩大。
虽然教育内容的设定,会兼顾不同层次孩子的特点,但教育内容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去适应落后地区孩子理解的需要。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精心制作了一部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试图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水平。然而,研究表明该项目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富裕儿童对节目内容有更多的事先体验,因此接触和利用更多。虽然该节目的播出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富裕家庭的儿童获益更多,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反而扩大了。
今天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更加严重,而社会也更加复杂多样,远远超出孩子特别是落后地区孩子直接经验理解的范围,电子书包等数字出版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所承载的内容如果以落后地区孩子的理解为底线,不但无法发挥数字出版的优势,也会造成教育和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端;如果以发达地区的孩子的理解来考量,则可能造成落后地区孩子的学习障碍,从而扩大知沟,由此形成一个悖论。
4. 个人动机。这里的个人动机指个人寻求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意愿、目的和寻求信息模式的差异。美国学者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递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谓的传递社会遗产就是教育。数字出版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电子书包,本身就是融合媒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是综合“内容+终端+平台+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性、多媒体、网络化的教育服务平台,在侧重教育的同时,兼有教育信息服务、娱乐、社会交流等多种功能。当孩子在应用这个数字平台时,个人动机的不同,会导致他们更多的应用这个平台的某一个功能,或寻求知识,或游戏娱乐。
美国学者温德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表明:收入低的家庭接触现代传媒的资源量并不少于高收入家庭,但更多关注的是娱乐资源而非对其发展更有利的新闻资讯。[7]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因所受教育的他律和自律的要求较高,从中获取知识的主动性相对于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孩子较强,由此导致知沟的扩大。
三、缩小数字出版的“知沟”效应——需要跨层次的结合
1. 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基础功能。数字化资源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数字出版技术应用于基础教育天然具有扩大知沟的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会积累。就个体的发展来看,知沟最初表现为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的差异,进而表现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和高考入学率上的差异,最终表现为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早期教育资源的分配对于知沟有基础性影响。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的知沟,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关键的影响。
知沟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宏观的S.E.S结构,其中收入水平又占主要部分。因此要缩小基础教育阶段不同阶层孩子的知沟,主要取决于社会不同阶层经济差距的缩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直接效果来说,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对于缓解知沟效应有现实意义。国家应以调节和补助的方式维持教育资源分配的平衡,以弥补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在数字化软硬件如设施、师资和教学内容上的差距。许多国家现行的经验值得借鉴:如英国的“缩小数字差距”计划,免费为低收入家庭接入互联网,并提供二手电脑;美国的“信息技术平民化”计划在加大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大力扶持那些研发平民化技术的公司,取得了积极效果。
2. 个人动机的能动作用。相对于调节难度较大的宏观S.E.S结构,个人动机属于微观层次的因素,改变的难度较小。近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人动机的因素在缩小知沟方面的作用,美国学者夏普因此指出:“当寻求信息的动机非常强烈时,‘知沟’就会缩小而非扩大。”[8]虽然个人动机无法突破S.E.S结构的限制,但却是最现实和积极有效的突破因素。因此在农村加大数字化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培养低S.E.S阶层孩子获取数字教育信息的兴趣,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数字教育技术和资源对其将来参与社会、发展自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动积极地利用这些资源,以最大限度达到缩小与高S.E.S阶层孩子知沟的目的。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勒纳将现代传播技术称为“现代人格的放大器”,以此来描述数字出版技术在基础教育的作用再合适不过。这种放大,如果是建立在既有不合理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基础之上,则放大的是不同阶层孩子的知识鸿沟和将来分化的阶层鸿沟。因此,在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融合的起步阶段,合理分配这种新兴资源,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可能产生的基础教育阶段孩子的知沟,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善莫大焉。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当前社会条件下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受2012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P.J.Ticheno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Summer,1970:158-170.
[2] [日]儿岛和人.现代大众传播理[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52.
[3] J.S.Ettema,:Deficits,Differences, and Ceilings: 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J].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4,No. 2,April,1977.
[4] 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J].1999:89.
[5] 王星.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警戒线[N].文汇报,2010-08-25.
[6]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29次)[R].8-21.
[7] B.Dervin and Bradley S.Greenberg: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Urban Poor,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M].,Sage,1972:195-233.
[8] Hester. J & Gibson.R.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National Versus Local Media: A Time-series Analysis for the Issue of Same-sex Marriag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J].10(3):299-317.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