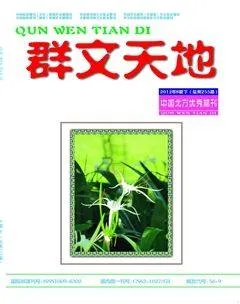品读音乐中的文化
摘要: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回归其本体,探求根源。确实,音乐做为人自身的原始本能,最初的本质属性为娱乐,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不是简单的音乐。
关键字:音乐;文化
在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中提到,“音乐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声音,还有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即人类行为”。从这句话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地理解到,音乐不能做为一种独自存在的个体,超出人类自身的控制与行为之外存在;反之,它与人类行为有关。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进行扩展,音乐产生的先决条件是身体行为,即生理因素,包括身体的姿势,姿态,还有运用特点肌肉将手指放置在某一乐器的键盘上,或收紧声带和横膈膜的肌肉以进行歌唱的行为。观念,构思或文化行为包括某些音乐观念,它们必须转化为身体行为才能产生声音。此外,我们也应该进行社会层面的分析,某些人按特定的方式行为做其音乐观念的准则,因为他们是音乐家,而且社会也对此行为进行定型,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不是音乐家的人也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影响,因为音乐本身具有感染力,不仅表现在情感上,甚至在身体身体上。紧接着,又因为文化习俗方面的原因,某一音乐活动中的行为不同于其他音乐活动中的行为。如祭祀,傩戏的现象。最后,还有为了成为一位音乐家,一位感悟力强的听众或者一位非职业的音乐活动参与者而进行的学习行为。这些都可以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部分。如同布来金在《人的音乐性》中所说,“非音乐专家根本无法理解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的对音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行为问题等的忽视,则会对此学科有损坏。因此,民族音乐学不可对音乐,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一体进行脱离,人的终极兴趣始终为自己,音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研究音乐也是对自身的研究,同样,在研究自身的同时,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等因素而独立存在。所以,民族音乐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为探求人类行为的原因。
一、文化中的音乐
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中,笔者读到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回归其本体,探求根源。确实,音乐做为人自身的原始本能,最初的本质属性为娱乐,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不是简单的音乐,这个时候的音乐则是被组织成社会所认可模式的印象,音乐制造可以被看做一种习得的行为方式,而且,音乐风格成为人类文化表达方式的一部分,是以人类决定从天性中精选出来的,而不是天性强加给人的东西为基础。然而,人类从中精选出自己音乐风格的这种天性,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外在的,还包括人的本性—他的身心能力以及通过跟人和事物打交道而构成这些身心能力的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在文化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到一个结论,对音乐的功能分析,不能脱离于其社会功能的结构;如果不考虑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构和生物学体系的结构,那么音与音间的相互作用,就会被成为一种孤立的状态,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人的音乐性》所说:“民族音乐学不单是对外来音乐进行一种表层的研究,民族音乐学也不是一种民族的音乐学—它是为更深刻地理解所有音乐提供可能的一个学科。”因此,音乐不能做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它做为人类体验的声音表达方式,也应该被放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结构中进行分析和理解。
二、音乐本体的研究
尽管在民族音乐学中,文化中的音乐做为极其重要的部分,值得我们下苦功去深入研究,但是不能太过迷信于其中,做为音乐的本体,我们还是要对其音乐性进行分析,并一次为基础,对其文化性以及社会性做进一步分析。如在《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中,托马斯·图里诺的《秘鲁排箫风格的历史和诠释的策略》,对排箫声部进行一定的剖析,并把分析出的结论与社会环境等进行相关联。
三、研究方法
(1)对歌词的研究
音乐影响着语言,因为一般的说话模式必须有所改变才能满足音乐的需要。因而歌曲中的语言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表达方式,这是需要对歌曲所藉以表达的语言有特别的知识,在《音乐人类学》中,引用了贝斯特的一段话“为了谐音而产生的词语形式变化,是人们在翻译这些歌曲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于是元音可以被插入,省略或改变,一个单词也可以被加入一个额外的音节。同样,歌曲作者不仅使用古老的表达方式以及重新启用废词,他们有时还造词”。
(2)用途与功能
音乐的用途与功能是民族音乐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在观察音乐同时,音乐可以做为特定社会中以特定方式加以利用,也就是音乐做为其自身或同其他活动相结合的习惯或传统方式。
参考文献:
[1]梅里亚姆著.音乐人类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2]伯尔曼等著.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刘小凡(1988-),男,汉族,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