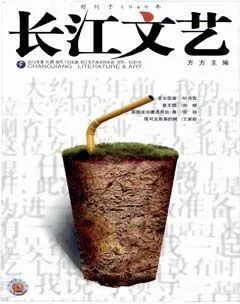张翎:站在彼岸书写家族史诗
张翎,浙江省温州市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获英国文学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著有长篇小说《睡吧,芙洛,睡吧》《金山》《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余震》《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得台湾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首届中国华侨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小说曾六度进入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并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
范宁,80后,武汉媒体文化记者。来自三湘四水,遍访文化名家,问道、修业、解惑,从文化的视角看世界,乐得其所。
曾经载着华人驶向彼岸的航船,今天载着华语文学回到此岸。
横亘世纪百年,一批中国人,从漫长的海岸线出发,执帆回望的身影消失在乡人视野。彼岸是传奇,是金山,是美丽新世界,然而他们的故事被海风吹散,罕有只言片语,能随海潮漂流而还。
所幸,怀中那抷乡土未冷,耳边那一曲乡谣未逝,胸膛中跳动的那颗龙心未止。黄皮肤黑眼睛的乡愁,在大洋对岸恣肆生长,被人收割,堆积成一串一串的文字,淬炼成一行一行的离歌,一支华语文学的脉系,把百余年来的飘零、闯荡、奋斗串起,用一部部小说带回故国。
张翎的书写,汇入这漫漫潮流之中。近年来,有关海外华语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的对话、对照,活动日渐增多。今年4月,张翎就出席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的相关主题论坛,讲述她眼中的华工往事。她的作品如《望月》、《交错的彼岸》、《金山》等,展开家族史诗画卷,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一
张翎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任职17年,她面对着不同族裔不同阶层人的耳朵,声音从那些耳朵里飘入又传出,经过大脑的演绎,成了一个个故事。张翎要做的,是打开心灵的耳朵,感受这些故事后面那个讲述的灵魂——它或许曾经游荡在战场上,或许曾经目睹颠沛流离。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就是一道彼岸。张翎从中国到加拿大,是从此岸到彼岸,但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岸与岸之间的摆渡。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是一位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张翎(以下简称“张”):我在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任职17年,这两年为采风之故,离开诊所休假。选择成为听力康复师,其实是我的“作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在国外,靠写作维生的专业作家为数不多。英国著名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名言对我一生影响至深。她的大意是,一个女人要想成为作家,必须具备500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指的是一个女作家——其实对所有作家都适用——应当具备的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特质。这句话一直以来都被人诠释为女权主义宣言,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忠告。
我很佩服作家和诗人们能在极端艰难的生活环境里,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之类的传世之作。但我也相信,如果头上有一片哪怕很简陋的屋顶,盘中有一勺热汤面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更加从容地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耗费十年的时间去铺设一条维生之路,然后再展开我的业余写作设想。当然,这个设想的巨大代价是时间和精力的严重透支。
听力康复师的职业不仅为我铺垫了一个可以不用为基本生活需求分心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精彩多元的视窗,使我和各个族裔各种社会阶层的人,有了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我的病人中间,有许多人经历过各样的战争和灾荒,他们对生命疼痛等母题的真切感受,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灵感。
范:什么机缘触发了您的创作激情?
张:很小的时候,我就渴求成为作家,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想不起来是哪一件具体的事使得我产生写作的热情。如果一定要追踪,可能就是好奇感。
我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温州。当时的温州,是个交通和通讯都十分闭塞的小城,不通火车,没有机场,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途径是海路,周围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普通话。小时候坐在瓯江(钱塘江的支流)边上,看着远处水变成了天的地方,就琢磨那到底是什么地方?那里的人和我们是否长得一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后来第一次离家去上海上大学,看到黄浦江时,心情异常激动。我一直在想:水的尽头在哪里?那些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景象?就是这样的好奇感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北上,从温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去了加拿大。每一次离家,都越走越远,再回首,故乡已经是文字了。
范:加拿大是一个华人特别多的国家,尤其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当地华人的生活是不是您创作的主要对象?
张:我迄今为止的作品,大多是家族史诗类型的作品。比如长篇处女作《望月》,写的是大上海一个资本家大家族三代女性在大洋两岸的生活。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写的是以温州人文历史为背景的家族故事。《交错的彼岸》和《金山》,其实也是这个类型的故事。
这些小说时间跨度通常都是一个世纪,情节在大洋两岸延伸拓展,虽然也涉及了一些当下北美移民的生活状态,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故事的主要脉络是历史至当下的延伸。
我很少书写只涉及当下生活或与自己的直接生活经历紧紧相关的题材,因为我觉得这些题材还没有经过时间和距离的沉淀及过滤,让我有些“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惶惑和迷茫。
范:中国文学当中其实很少有“彼岸”这个意象,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移民文学当中,“彼岸”就成为一个非常基础的元素。您被视为中国文学领域的拓展者,那您觉得“彼岸”的人生和生活,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的意义在哪里?
张:首先我绝对不敢承受“拓展者”这个称号。我的经验告诉我,一套上“××者”的称号,基本就是找抽了。我不过是一个热爱文字和文学,想真诚地书写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的作家而已。
随着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移民潮已经成为全球化的现象。移民文学(或者称“离散文学”)的内涵,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近12年中,诺奖的获得者超过半数都不在自己的出生国写作,但他们书写的,大部分依旧是关于故土的小说。难怪2008年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过:“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大意)。”
故土和移居地,其实是互为彼岸的。站在“彼岸”来看“此岸”,一定会有隔靴搔痒不知冷暖的疏隔感,但也会由此产生理性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冷静和客观。在文学的大版图里,边界线在不停地变换。多一种声音多一个视角,总是一件好事。
范:引发您创作灵感的一般会是什么事件或情境?(比如我知道您写《余震》来自读到的一本书以及产生的联想等)您的日常创作状态又是怎样的?
张:一般来说,阅读、旅游或者交谈过程,能带给我一些非常偶然的灵感,很可能会成为我一部小说的创作冲动。
比如,一次加拿大北方印第安部落之旅,引发了小说《向北方》;一段与母亲关于外祖父尸骨回乡的谈话,就成为小说《雁过藻溪》的骨架和精髓;一次偶然的误机经历,使我“撞上”了一本特殊的回忆录,而回忆录里关于地震孤儿的描述,造就了《余震》这部小说的由来。
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作家,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创作计划”,只是任由星点的灵感将我带入一种心境——也许就会有文字由此生出。我一直很享受这样的随意,它会使我不受市场干扰,较为纯净地进入一种创作状态。
二
2010年,张翎的新作《金山》,卷入一场文字风波。这部在中国大陆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作品,被人指出有抄袭之嫌。为此,张翎发表严正声明,表示《金山》是自己多年孕育锤炼之作,该书参考了大量史料,这些史料都有迹可循。
而跳出文学之外,张翎为大众熟悉的另一个话题,是冯小刚的卖座电影《唐山大地震》,其原著便是她的小说《余震》。这部写于2006年的小说,微妙地“书写”了两年后的汶川,在震后忽然拥挤一片的灾难题材小说中,《余震》傲然耸立。
范:《余震》写在2006年,2008年发生了汶川地震。真正的灾难到来时,您当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张:汶川地震发生的那阵子,我天天下班就是看电视,每天都哭,几乎得了轻微的抑郁症。唐山大地震的中国,处在一个很不同的社会环境,由于新闻管制,南方的许多城市(比如我的家乡),几乎对北方灾区的真实状况所知甚少。我在为写《余震》而作的案头调查中,除了众多的建筑物坍塌、地貌改变的图像外,我几乎没有找到一张受害者的照片。一张由官方媒体拍摄的几个孤儿穿着新衣手拿苹果,坐在通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里的照片,几乎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受灾人群的图片。
而32年后的汶川地震,社会环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国外可以即时看到灾区的状况。几百页的文字叙述,也比不上一个实地画面带来的震撼。在那样的灭顶之灾面前,我再次感受到了人在巨大的宇宙力量面前的无奈,对从前那些“人定胜天”的虚浮口号,产生了更深切的警惕和反思。
我感到欣慰的是:2008年的地震灾难来临时,在尽快重建家园的计划里,心理干预也成为了一个相关话题。唐山大地震中,我们只注重了“外伤”,然而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都在学习和成长,懂得了“内伤”是一种不易觉察却更持久更致命的创伤。
范:您与冯小刚一定就这个题材有过交流,您觉得冯导表达出了您原著的意思吗?他心目中的大地震又是怎样的?
张:我和冯导曾去新西兰外景地一起工作过两个星期。当时剧组曾有设想把国外场景放在新西兰,我们在途中有过一些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他想要在影片中表达一种大灾难中人性的温馨,以及这种温馨带来的医治力量;而我在写小说时想要表达的是,天灾给心灵带来的创伤,不一定会随着城市家园的重建而完全消失,心灵的余震可能会比地震本身持续得更久远。
小说和电影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一些脱胎换骨的蜕变。电影《唐山大地震》成功地诠释了冯导对地震的理解和他所要表达的理念,我们不必强求小说和电影在视角上的一致。
范:《唐山大地震》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您认为这个票房表达出怎样的含义?
张:《唐山大地震》电影的票房成功,可能代表了老百姓对一些似乎被时代颠覆了的传统家庭观念的向往,对牺牲谅解包容等善良美德的渴望。当这部电影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映的时候,我很担心一些典型的中国式观念和幽默会由于文化隔阂而丢失,可是那天的大剧场里几乎每个人都是红着眼睛离开的,大家的笑点似乎也非常合拍,这使我相信了有些民族的元素也可以成为国际的元素。
范:《余震》之外,您还有其他的有关中国今天现实的作品或计划吗?
张:其实《余震》的主题也不是关于当下的中国。它涉及的是一段30多年前的历史,尽管它的影响延续至今。虽然我经常回国,也一直非常关注祖国发生的一切,但毕竟我已经不再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不具备像国内作家那样对脚下的土地的第一手坚实感觉,所以我不会去书写我不熟悉的当下中国生活的作品。但是,我会一如既往地书写我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故土往事,关注“此岸”和“彼岸”之间生活的那些人群,记录他们的特殊状态和感受。
范:《金山》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是什么引发了您的创作动机?在此前已经有许多同一题材的作品时,您写作这一题材,想要表达自己怎样的想法?与此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张:我并没有读过太多的华裔北美历史方面的小说(因为我作案头的重点是在学术和历史专著上),也没有任何想“超越”此前作品的野心。我唯一的野心(假如有野心这一说的话),是超越自己。
尽管所有关于华裔北美群体的小说,不可避免都取材于一段共同的历史和这段历史所产生的丰富史料,但每一部小说在自己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上应当是独特的,彼此不可替代的。在调研和写作的过程里,那段历史中的无数个故事使我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亢奋激昂的状态中。我直面了这份感动,也努力试图真实地诠释这份感动。
范:在《金山》后面列了参考书的名单,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尤其是历史题材,不可避免要接触到参考书,但是又必须要跳出参考书。您是怎么基于材料又不局限于材料的?
张:所有的史料只是骨架,而留在书页上的文字则是皮肤。骨架和皮肤中间,必须要有丰厚的肌肉。如何在骨架和皮肤中间搭建真实可信的血肉,这是我最大的挑战。
《金山》一书横跨了一段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书中光有名字和对话的人物,就有七十三个。这些人物生活在大洋两岸的十数个城镇。这样的一部小说,是不可能依赖并受限于任何一本参考书的。细节对话人物心理描述,这都是史料所无法解决的巨大困难。我必须独自地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到一条叙述之路,使得干巴巴的史料化为活生生的人物。我的重点始终是人物和细节的可信度,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和历史真实具有同样重要性的。
三
中国文学要拓展海外阅读并不容易,文化背景的差异,题材关注度的不同,甚至是翻译问题,都会成为华语文学被世界接受的“门槛”。张翎也与读者分享了她眼中的海外阅读,以及海外读者的个性和习惯。
范:作为一个作家,对于阅读情况应该非常关注。国外普通读者的阅读情况您是否了解?
张:我想,阅读群体的多元化,和纯文学作品的边缘化,应该是目前世界读者市场的一个总趋势。
我这几年关注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外读者和作家群体的划分似乎比较偏重于类型,比如科幻小说、魔幻小说、历史小说、年轻女性爱情小说、刑侦小说等等,而国内的读者和作家群似乎更愿意以年龄划分,比如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等等。
国外读者市场很大的一个板块是读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成员,有的是以喜爱的作家来划分的,比如简·奥斯丁俱乐部、罗伯特·彭斯俱乐部等;有的是以阅读兴趣来划分的,比如侦探小说书友会等。这些人定时聚会,彼此分享阅读体验。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一种很有效的以文会友普及文学欣赏的方式。而现在国外的年轻人和专业人士也开始喜欢使用电子阅读器来享受阅读的乐趣。纸质图书的销量和出路,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范:您现在经常在欧洲旅行,能谈一下欧洲或者美国加拿大在文学方面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吗?
张:这两年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行走,由于我早年英国文学的背景,我对欧洲人文历史一直情有独钟。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人的生活态度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接触到的法国文人群体,是一群似乎不太受北美“追星追梦”文化所污染的天真单纯之人,对文学艺术充满着一种远离功利的景仰。
他们对自己认知经验之外的东西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而对充溢北美大陆的基于物质标准的“成功故事”兴趣寡然。去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法国作家节,活动完毕之后和一群法国作家坐同一趟火车回巴黎。在火车上,一位作家弹着吉他即兴唱起了自编的歌曲,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地唱出了他对编辑出版商评论家的种种不满,而那些被他指名道姓地编排了的人,就坐在同一车厢。他卓越的才华和幽默赢得满堂喝彩,那些被他嘲讽甚至恶骂了的人,非但不以为忤,反而为他热烈鼓掌。
这群作家中间,有好几个是七十年代狂热的文革追随者。这群人在酒吧里回忆往事,用各种欧洲语言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我和他们聊起这一段心路历程,他们依旧热血沸腾。他们对我说:“假如你在20岁之前没追求过一种完美社会体制,你是个没有心肠的人。假如你40岁之后依旧追求理想社会体制,那你就是个没有脑子的人。”法国文化人中间那种崇尚心灵自由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淡然超脱,对于我这样被北美的物质文化和发展理念深深影响了20多年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震撼。
责任编辑 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