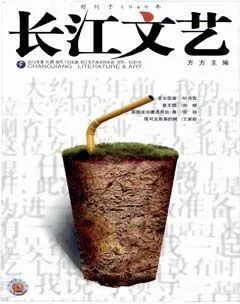飞廉的村庄
1
村中的树有楝树、杨树、榆树、椿树、泡桐、柳树、桑树和刺槐。后来又有人家到集上买回来冬青与水杉栽,没几年,也亭亭如盖,但看起来总觉得很别扭,像讲话古怪的外乡人。楝树在其他的地方少见,在村上却几乎每家都有。四月里光秃秃支开的枝桠上开出细细的紫花,全村都会有苦涩的香气。花落后结出楝果,像手掌一样的一串串绿莹莹的小果子,正好做小孩子们玩双陆、玩“点窝”的器具和满村巷追赶掷人的武器。可惜苦涩难当,不能食用(要是楝果能吃该多好啊,小时候我常这样想)。杨树也许就是书上讲的枫杨,长得又高又大,也少生虫子,夏天里一团浓阴,正好盖在房顶上。三毛家的门前,有七八棵大杨树,就像七八把巨大的伞一样,八月里刮西南风的时候,大杨树下面,岂非就是天堂。杨树会在四五月挂出一串串嫩黄的种子,像往南飞的野鸭那样,排在一起,所以村里人取名叫作“鸭娃”,它的柔嫩与可爱,需要特别的通感,才能将之与呱呱呢喃的小鸭子联系到一起。榆树飘榆钱的时候是很好玩的,如果村里飞满榆钱与柳絮的时候,一定会是春末的四月。金龟子也特别喜欢榆树,它们常在树干上凿出伤口来,好几只聚在一起,像吃酒席一样喝着由伤口渗出的树汁。椿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们好像不知道椿芽以后可在城里做成一道席间的美味,它一身怪怪的臭气实在是令人难以亲近。而且许多又大又肥的毛毛虫特别喜欢它的枝叶,常常趴在它厚厚的叶片上,一不小心,就滑下来,掉到你身上,让人又疼又痒。
2
泡桐的花与叶子都很有意思。泡桐花又肥又大,像紫色的喇叭,它的枝干也是很有用的,村上熬麦芽糖的作坊里面,一定要取泡桐的树干来做转送糖汁的管道。泡桐的干是中空的,用铁条一捅,就是现成的水管。当然,村上人说一个人没有用,也会用泡桐来形容,其意几近于饭桶、空心草包之类。讲一个小孩长得快,也是用泡桐来形容,泡桐像把伞,三年就锯板,一个小孩由满地飞跑的顽童,变成能挑水割麦的少年,也就是三五年的工夫。柳树也是常见的,不过种柳树,可不是为了分别做诗,为了看它垂下丝绦的样子。柳树的枝干是用来做椅子的,所以过几年,柳树的枝条就要被砍一回,男人们劳作一天,家里又会多几把白簇簇的新椅子。因为没有专门拜过师傅,所以这些准木匠按心中的样子做起来的椅子,看上去就有一些古怪了。古话讲,房前柳,屋后竹,河边桑树一片绿。又讲究门前不栽桑,门后不种桃,所以,只有一排桑树,种在村后的小池塘边上。村子里没有养蚕的人家,桑树好像是专门为五六月里小猴子一样的娃娃们去爬树吃桑子,为那些爱臭美的丫头摘桑叶洗头发而生长的。在清堂家的后院里,还有一些刺槐,象牙一样细白的槐花香气扑鼻,但是槐枝上的尖刺,却让人敬而远之,就像孩子里面的坏家伙,这样的树,当然是少的。说到美中的不足,也许村里,还应种一些竹子。春天里,可以去挖笋子吃,孩子们想做钓鱼竿,也用不着千方百计去别的村子里讨要。一种树在村里扎下根,繁衍不绝,相信也要特别的运气。但是周围的村子里都有竹子,却一直未传到我们村来,这件事,的确令人费解。
3
三四月份,谷雨时分,将萝卜籽撒到菜地里去。萝卜籽是绯红色的,像飞尘一样细小。一二周后萝卜秧子生长出来,绿色的嫩叶,红色的茎,像此时正在换羽的半大的鸡身上的羽毛一般,所以又被叫作鸡毛菜。
由密集的细秧中挑出来的鸡毛菜是初夏里饭桌上的一道美味,有一点儿苦,细小的绒毛微微地扎着舌头。一块菜地上,也只能挑出一二碗菜来吧,与这些过早成为盘中之餐的鸡毛菜们相比,幸运的兄弟姐妹将留下来,继续向下生根,向上成长,直到长出红艳艳的萝卜。
萝卜适合在沙质的地里生长,对于小孩来讲,沙地里的萝卜,轻轻一拔,就能拔出来。所以在■与小河的河滩上,在夏天的洪水退去后成长起来的萝卜,常会被来此放牛的小家伙们偷偷拔出尝鲜。要是在种过水稻的胶结的田地里,想拔起一只深入土里的萝卜,倒是一件麻烦事呢,有时候,将外面的萝卜缨子拔断了,也未必请得出里面的萝卜来祭你的五脏庙。
无数次去菜园里看萝卜长成没有,真正吃到萝卜总要等到七八月份,得到父母的恩准,拔出自己菜地里的一只萝卜,到池塘边将萝卜身上的泥洗净,坐在草丛里享用。将红艳艳的皮一圈一圈剥下来,拉出长长的一条,也可以用衣袋里的小刀子,将萝卜皮刻出几瓣,取出去皮的萝卜后,将几瓣皮收拢来,好像一盏莲花灯一样。好吃的红萝卜,上半截的脖子上,有淡淡的绿色,下面则如白玉一般洁白,甜甜的,又有一股淡淡的辣味。也有的萝卜特别的辛辣,强忍着吃下去,那也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了。
4
秋天的时候,一担一担将长成的萝卜挑回家,将萝卜缨子剪下来,切碎喂猪。萝卜就如同一堆小山一样,堆在堂屋里,听候家里的女主人处置。
一部分会被埋到屋角的沙堆里,在漫长的冬天里,取出来做菜。埋在沙地里,是让萝卜不要过早地生出芽来,干掉水分,成了空心萝卜。不过沙子虽然有用,萝卜却是迟早会花心,所以腊月里拿出来烧肉的,多半是花心的萝卜,没有办法的事。
一部分会被切成条块,晒干,脱尽水分,然后拌上盐与辣椒,装入瓦瓮里。过上几天,就可以吃上用腌萝卜丝做的咸菜了。
还有一部分,会被放到腌菜缸里。一口腌菜缸,下面是小半缸红萝卜,上面则是小半缸长杆的白菜。为了将红萝卜压结实,缸顶还会压上一块长长的石块。
腌菜缸就放在灶屋里,慢慢地沁出盐水,发出酸涩的气味,但是要将缸底的萝卜压熟,总得等到窗外飞起雪花的时候吧。这时候,好像又回到了红萝卜在地里成长的时节,每一次你路过菜地时,嘴里都生出了津液。当窗外开始落下第一场雪,母亲同意在这样的寒冬里,奖赏你一只淡红色的压萝卜,你不会畏惧腌菜缸里刺骨的冰水吧,将棉袄袖子卷得高高的,将光裸的手臂探下去,由如麻的腌菜杆下面,捞上圆润的萝卜来。压萝卜结实、清脆、酸甜,又有咸鲜的香气,如果不是母亲的管理有方,一定会被孩子们当成零食吃得精光。
以上讲的是红萝卜,还有白萝卜,长长的体型巨大。还有胡萝卜,红彤彤的更深地钻在地里。这些在菜地里也是有的,它们像远房的堂兄与表兄弟一样,没有红萝卜来得亲切。
无论如何,在菜地里,总会有几棵萝卜最后留下来,没有被拔掉。春天来到的时候,拔起苔,开出花来,在此时油菜金黄的花海里,露出一枝粉白的细花,然后结出红色的种子,如飞羽一般又被撒入谷雨后温暖的菜地里。
5
九月也是菜园兴旺的好时候。不过这时候,池塘里会有菱角。菱角生着吃,得吃那种一下子就可将角掰断的菱角。那种像牛角一样坚硬的老菱角,煮熟后用刀剁开好吃。不过我还是喜欢将生菱角去皮切片炒菜,觉得特别有滋味。
十月里已经是秋风阵阵。园中的蔬菜也许只有大白菜、包菜与胡萝卜了,长过丝瓜、瓠子、豆角的绿藤也会枯萎,不再有生气勃勃的样子。我记得有一种白茄子,茄子已经快摘光了,矮矮的茄树最后竟长得像棉花树一样,不过在扯起来之前,摘下的最后几只茄子,比月前结出的茄子稍小,也许是在秋风里吹过了一些时日,做成菜,总觉得特别好吃,有一点涩涩的味道,像木片一样有韧劲,我们叫炒秋茄子。这时候,正好大蒜也由地里刨出来,所以可以将新鲜的蒜瓣作佐料。十月的大蒜,又结实又鲜辣,再过一个月,就会生出芽,塌下肚皮去。
冬月与腊月的菜园是空旷的。整天端上桌子的会是大白菜与胡萝卜。还有小白菜。小白菜有许多种类,像母亲讲的高脚白、上海青之类。我最喜欢吃的一种小白菜母亲却不知道名字,深绿,叶子很细,一层一层地排着叶子,长在地里,就像一朵花一样。好在冬至到了,年关已近。池塘里要起鱼,家里也要杀年猪,无论如何,一年上头难见到荤腥,一下子大鱼大肉摆上桌子,再怎么好吃的蔬菜这时候也比不上鱼肉吧。
6
我家有七个人。爷爷,父亲,母亲,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我们住在村子中间,一幢由六间房间组成的瓦房里。这一幢瓦房是我弟弟保力出世时建起来的,所以保力长到多大,这一幢房子就建了多少年,门前的树,也就是长了多少年。在这一幢瓦房之前,我们家是青砖黑瓦的四合院,院中有小小的天井,下起大雨的时候,雨水就潴积在天井里,像一个小小的池塘,雨水在上面溅起水泡。六间砖瓦房是由爷爷与父亲盖的。
六间房坐北朝南,屋顶上铺着檩条,檩条上铺着黑瓦,四面是砖墙,大墙上敷着白灰。每一间房由梁柱与板壁分隔开来,每一间都向南开着木头窗子,好挡住北风,又让常在南边的太阳能射进来。自西往东,由六扇小木门相通,第一间,是爷爷与我们兄弟的房间。爷爷的床放在北边,一张黑沉沉的雕花床,雕花床上的木雕都在“四清”时期被敲下来了。床前是放鞋子的床踏。左边一张宽大的木桌,右边是一张茶几。在木桌上面的木壁上,挂着由生产队里牵进来的广播。我还记得,晚上,能站在木桌上的油灯前,听到由广播里传来的队长的讲话。床前右边,从前是一块空地。爷爷过了六十岁以后,就由父亲主持,给他打了棺材,黑沉沉的棺材,就放在空地上,用塑料布蒙着,将我们兄弟的床与爷爷的床隔开。二十余年后,这一只棺材终于派上了用场,将坐在床上去世的爷爷带去了蔡家河的坟地。上面讲到的雕花床,床踏,木桌与茶几,全被父亲按规矩烧化了。我与弟弟的床,在窗子下面,父亲自己钉的木板床,并不结实。冬天的时候,我与弟弟在被子里蹬架,会将床弄坏,因此被母亲怒骂。我与弟弟在这张床上,由六岁睡到十四岁。后来去孝感读高中,弟弟终于得到了一个人睡在上面的机会,再后来,他也去孝感读高中,这张已经摇摇晃晃的床,也结束了它的使命。
推开我们的房门往东,是一间堂屋,我们叫小堂屋。六间房里有两间堂屋,父亲做新房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所以计划着,等他们长大后,一人三间房,娶来媳妇分家过日子。所以有两间堂屋。小堂屋,是备用的,还未启用。所以被当作柴草间,母亲扎好的草把子,就堆这里。有几年,偷猪贼盛行,还将这里彻了一半去养猪。家里的农具,板车,簸箕,锄头,挖锄,镰刀,长条凳,也堆放在这里。家里养猫的时候,猫也将它的家安在那草把子里。我从小学校里得回的奖状,在大堂屋里贴不下了,也有部分移过来,贴在两边的木壁上,以供生儿育女的猫,和猪圈里的猪瞻仰学习。小堂屋向南开着大门。大门下面的门廊下,挂着枯干的丝瓜与瓠子。门廊的椅子上,爷爷去世之前,常坐在那里,晒太阳。
由小堂屋的侧门向东,是厨房。厨房最北,是一张灰黑的睡柜,我们叫它“老睡柜”。睡柜有四个隔子,里面装上五谷杂粮。睡柜上面,家里来了客人,可以铺上被子睡觉,我记得我也曾在这个睡柜上睡过一二年。在上面看完《西游记》,看到DAsL49ChzpiCqBNezEwRxQ==半夜,可以听到隔壁小堂屋里猪的哼哼声,觉得是猪八戒前来超生,又担心这边墙上的缝隙,将油灯的光透过去,让母亲看见。睡柜向前,两边是好几口大缸,用来装黄豆与谷麦。还有一口小缸,冬天用来泡腌菜与腌萝卜。再向前,右手边上,是我们家吃饭的桌子。桌子低矮,四方形,黑漆漆的,被油烟浸渍。除开过年家里来客,去堂屋里摆上大桌子吃饭,三伏天里,将饭菜端到门外的竹床上,我们都要在这一张桌子上吃饭。桌子对面,摆着碗柜。碗柜上,挂着筷篓。在厨房朝南的窗子下,是灶台。灶台的左边是柴草堆,右边是水缸。母亲每天就站在灶台前,在水缸与柴草堆之间做饭。这一间灶屋,自然是我们一家人饮食温饱的地方,父亲在这里喝酒,教训孩子,我们坐在灶凳上,往红火的灶膛里塞进草把子烧火,每年过小年、除夕,或者元宵节的晚上,母亲还要在灶里点灶灯,提醒那黑脸的灶神往天上去报告降到我们家的平安与福祉。
7
由灶屋向东,第四间,是父亲与母亲的卧室。他们的结婚时的家具,都摆在这个房间里,一张雕花床,还是红色的。一张桌子。一只睡柜,顺着放在挨着灶屋的墙下,我们叫这个睡柜是新睡柜。新睡柜上,放着两只箱子。这个一定是母亲的嫁妆。过年的时候,表弟表妹们来玩,就是睡在这只睡柜上。睡柜对面,是两个立柜,我们的衣服,都是装在这两只柜子里。朝南的窗下,放着一溜小瓮。过年时节的零食,就是放在这些小瓮里。
由父母的卧室往东,第五间,是大堂屋。这是六间房里面,最大的一间屋子,与其他的房间比较起来,未免显得空空荡荡。堂屋朝北的墙上,挂着画与对联,最早的画,我记得,是毛泽东与华国锋的头像,后来换成了福禄寿星之类,下面是一个条柜。条柜前面,是黑色的八仙桌。在堂屋的东北角上,是一只鸡埘。鸡埘之上,有两个稻草搭的鸡窝。有时候,父亲将卖菜的担子与自行车放在堂屋的西北角上。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四时八节的祭祖,固然是由父亲在堂屋里烧纸。除夕之夜,大家一起烧火守岁到新年,家里来了客人,也是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摆酒吃饭。家里兄弟姐妹过十岁的生日,也要将亲戚请来,在堂屋里吃饭。这时候,一张八仙桌不够用,还要去别人家借,这一间堂屋里,可以放下四张八仙桌,坐上二三十人吃饭。当然,很多时候,父亲与母亲请人来打麻将,也是在这一张八仙桌上。至于那只鸡埘,早上的时候,家里养的鸡由里面出来,跑到村子里去觅食;黄昏的时候,回来,径直往里面投宿。中途母鸡们匆忙回来下蛋,伏在鸡埘上格格大格格大地鸣叫,好像是要为这平日里空荡、年节里热闹起来的堂屋添加一点生气。
大堂屋往东,最后是姐姐与妹妹的房间。她们与我和弟弟一样,一起在一张床上,也睡了很多年。直到十余年后,分别嫁到张家湾与楚家湾去。因为是女生的宿舍,看起来,比我与弟弟的房间要整洁,父亲特别挑了土,将地面夯平,墙上也特别地用泥糊了一次,将漏风的墙缝,都填掉了,姐姐与妹妹去肖港镇上,买回来明星的画,俊男靓女,贴在墙上。
每到春上,快要进入梅雨季节,父亲就要搭上梯子,去屋顶上检瓦,将风吹猫踏弄乱的屋瓦摆好,即便是这样,房间里还是漏得很厉害。下大雨的时候,家里的盆子与桶,都得摆出来接漏。冬天北风怒号,风由墙缝与瓦缝里吹进来,一直吹到被窝里。老鼠跳浪,有时候会有蛇爬进来,蜜蜂、壁虎也常出入其中,虽然不能免乎风雨,但是这六间房,依旧是那样的结实与温暖,能将绝大多数的积雪、寒霜、大雨、狂风、夏天暑热的阳光,挡在外面,由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里面出生,成长。这风雨中的故巢,就像是鸟雀在树上搭成的窠。
8
在前面已讲到秋山啦。秋山是一个矮胖矮胖的老头,鼻头上长着一个瘤子。他本来是做了周巷镇山里一个寡妇的上门女婿,没有生养出子女,又一个人回来,自己过日子。他养了一头牛,与这头牛相依为命,却常常与这头牛吵架,用想得出来的最脏的话来骂它,牛当然是没有办法还嘴的,就低着头往田野里走。到冬天,秋山与其他的老头儿一起做糖坊。他一个快活的老光棍,通晓男女之事,知道一堆荤笑话,让村里那些年轻人冬天的晚上,一吃完饭,就将碗一扔,飞快地跑到糖坊里去听他传道解惑。他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承担打锣的差事。每次新娘子拜堂,他站在后面打锣,一大半的锣棰都要落到新娘的屁股上。
秋山还能吃,他与人打赌一口气可以吃下十几个肉包子,一口气吃下一小锅米饭,人家办红白喜事,他可一人吃下一大碗红烧肉。这些都是村里关于吃的最高纪录,秋山老了,这些年轻时的纪录他未必能再破了。
没有子女,所以秋山只好自己去弄棺材与寿衣,六十岁左右,村里的老人这些东西都要备齐了。秋山靠他的牛,他的糖坊,靠夏天挑着自己种的菜到金神庙卖,也庶几乎完成了这个愿望。他向人吹牛,说他晚上有时候爬到棺材里去睡,大家未必相信,但他的棺材漆得黑黑的,就摆在离他的床几尺远的地方。
那年初冬的一个早上,秋山牵着他的牛出门。经过西边新港上的小石桥到他的田里去。小石桥上结着浓霜,秋山脚下一滑,矮胖的身体就像一根红萝卜一样滚落入水,冬天水浅,所以秋山还可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咒骂他的牛。没想到这时候牛也脚下一滑,摔下桥来,正好压在秋山的身上。
秋山死了。好在他已备好了棺材与寿衣,不消劳烦别人。他埋进蔡家河后,村里人议论他的牛该怎么办,有人讲它弄死了秋山,也要杀了才对,将肉分给全村的人过年吃。这头牛终究还是卖到外地去了。它害死主人的新闻,也未必落实到了它身上,不然它如何卖得出去呢?
9
我们村上的剃头匠名叫华清。在我十四岁出门读书之前,我的头就是他剃的,事实上,不光是我,全村的人,头发大半也是他剪的。天气好的时候,他拎着他的小木箱子,一家一家地剃头过来,先是老爷子坐在门口的阳光下面,围上那块又黑又滑的围裙,眯着眼睛,由华清剃出一个鸡蛋一样浑圆的光头。然后是中年的汉子出来,剃出撮箕头。然后是小子们,被他剪出滑稽的桃子头。华清的顶上功夫只有这三样了,就像程咬金的三斧头,所以村里男人们的头发,也就是光头、撮箕头与桃子头三种了,中间的区别,无非是头发的深浅不同而已。
年复一年的光头撮箕头桃子头对老头中年汉小孩子无所谓,村里的年轻人可就有所谓了,人家正是找媳妇谈恋爱爱臭美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华清那由磨刀石上取出来的剃刀在他们头上,造出鸡蛋、撮箕和桃子形状来。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不惜骑自行车,或步行到肖港镇上去,找理发店的师傅理发。那里的师傅,剪得出分头来,头发可以剪得像被风吹开的麦地。这样的分头,才配得上他们新买的牛仔裤,去准丈母娘家见羞答答的未婚妻才会有面子吧。
华清却对分头不屑一顾,觉得这不是正经的剪法,那些小伙子一个个看上去,活像电影里的叛徒和汉奸。他的保守,也让他失去了垄断全村的剃头市场的机会。一个名叫银堂的小伙子,长得又瘦又小,腿也有一些跛,到镇上去学了理发的手艺,学成出师后,在村里开了一个理发店。他的理发店也贴出了镇上理发店里才有的明星的图画。银堂当然也会理出麦浪一样的分头来,他还买了一张可以放平躺下的椅子,让男人们躺在上面刮胡子,他还买回了摩丝,他第一次将摩丝喷到大家头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神奇极了。银堂的理发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他也由此发了一点小财,娶到了媳妇,生下了一堆孩子。再去理发的时候,就由他媳妇端来热水,他的孩子,则由着他的喝骂,在那张庞大的已破败的椅子旁边奔跑。
我慢慢地也长到了年轻人的队伍里面,也不满意由华清来剪出桃子头了,从某一天起,也投入到银堂的理发店里,一边看着香港明星,一边由银堂为我剪出汉奸一样的分头来。再过几年,离开乡村,我连银堂的顾客也做不成了。
10
无法想象,一户人家没得堂屋。也无法想象,一个村子没有稻场。由保明家门前的土坡上下去,就是飞廉的村庄的稻场。稻场有十来亩地的样子,南边是小池塘与田野,北边也是小池塘与田野,东边是村子,西边是一长溜生产队的仓库,一九八四年分田之后,拆掉了。经过历代的打夯、辗压与修葺,稻场平整如镜,东高西低,夏天的暴雨一直下到夜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稻场上也不会有积水。太阳与月亮由东边升起来,要在村子的树影里攀爬许久,才可照到稻场上,所以,要到早上八九点钟,才可去踢开谷堆,或者摊晒小麦。夏天的早上,也可坐在稻场上聊天,吃完早饭。而落日,一直要落到■堤上,贴近地平线,才会由稻场上收起余晖。月亮也是这样,如金盆,如银钩,掉入■里。
小麦、早稻、晚稻的脱粒,都要在稻场上。这将是村子里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稻场中间的变压器边的电杆上,电灯在晚上亮起来。每一家都排好队,依次将田野里挑回的草头子排入脱粒机里,在它巨大的轰鸣中,将麦粒或者稻粒,由腹下的铁齿里咬下,将麦秸或稻秆,由铁口里吐出来,积在一边,再捆成捆,堆成草垛。一场打稻,总得有五六个人参加。一个人来喂脱粒机。一个人将草头子解来,推给喂稻的人。一个人将草头由稻谷垛上搬下来。一个人,用木杈子将脱粒机吐出的稻秆挑走。一个人将挑来的稻秆捆好。一个人将稻粒由脱粒机腹下推出来,形成小丘一般的谷堆。一般的人家,得有二三个小时,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将收获的稻子打完,得互相换工协作,才能够凑足对付一台脱粒机的人手。之后,当家的男人,才能在家里人的帮助下,将谷堆扬去灰屑,装入麻袋,趁天气晴好的时候搬出来摊晒。打小麦,也是这般。所以一场麦收,夏收与秋收下来,稻场四周草垛林立,稻场中央,各家轮流摊晒谷麦,稻场四周,满是新谷与新麦的气味,一派收获的繁盛景象。谷麦打下摊晒完毕,农家一年的劳作,差不多是大功告成,谷子磨出米吃饭,麦子磨出面粉做粑,谷糠与麦麸喂猪,稻秆养牛,麦秆与棉梗扎成把子烧灶做饭,全家的人与牲畜可得十分温饱。
谷麦之外,其他的作物,也应在稻场上收获。倒芝麻。用连枷拍黄豆。打油菜。打绿豆。这些小作物,一二个人就能够对付,而且只用占去小小的一块稻场。另外就是摊晒棉花。打完早稻,晚稻还要在水田里生长的时节,稻场被用来晒棉花。在实行生产队制度的时候,会将稻场钉上木桩,一行一行拉上铁丝,将竹子编出的箔子摊在上面,将棉花摊出来。盛夏三伏天的早晨,站在保明家的坡上往下看,一层一层的棉花铺开在稻场上,与天上铺开的鳞鳞白云,差不多是一个样子。
所以一年之中,自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稻场最忙,真正是收了桑麻又种田,连枷声声不停息。我们的汗水,固然是滴落在田野上,稻场应承接得特别的多吧。我还小的时候,记得参加打稻的小分队,只能够担当分草头与推谷之类的工作,在满天的灰尘里,汗水落到眼睛里,没得办法擦去。稻芒钻入衣袖与脖子,又痒又疼。等到打稻完成,尚有青气的草垛堆积成山丘,月亮由三毛家的杨树上升起,一天星斗。吃过饭,乘着凉,晚上就在稻场上架起床铺蚊帐看谷,心里的怡然与快乐,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十一月后,入冬,稻场才得有清闲。这时候,村里老死了人,会在稻场上办丧事。死在外面的人,固然是不能在家里做法事,必得在稻场上搭起孝棚。在家里的床板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往世的人,放到棺材里,抬往蔡家河的坟地,也必得在稻场上停灵,由道士做法。据说,死人应将生前留在田地上的脚印尽皆收回,那么稻场上的脚印,也会特别的多吧,因此才会有特别的停留。黄昏时分,村里主持丧事的人,还会为死者来稻场上烧垄,就是在一层稻草上,铺上黄裱纸扎成的钱箱,里面装上死者带往阴间里的钱财,然后烧成熊熊的大火,还有人用扫帚拍打着蝴蝶一般飞升起来的灰片。
也在稻场上放电影。有一段时期,电视机很少的时候,新婚,考上大学,小孩子过十岁生日,庆祝的办法,除了是在家里请客,还会请镇上的放影队到稻场上放电影。这时候,四面村子里的人,都会扛着板凳来看。我与我兄弟考上大学,都请过放影队。至于到底放的什么电影,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稻场就有一点像全村人的堂屋了。平日里,大人在上面劳作,小孩子们在上面游戏。蜻蜓、蝙蝠与春燕在上面飞,牛在四周的草堆下吃草。这个就不用讲了。
11
立冬之后,做裁缝的晏矮子就要忙起来了。父母到他家里去,讨他来做衣服的日子,总要排到腊月里去。在约定的日子的前几天,母亲就将扯来的的确良蓝布与自己纺出来的棉布取出来清晒,又与父亲商量,要做哪些衣裳。等到这一天清早晏矮子挑着他的裁缝担来到了,父亲卸下两扇大门,用板凳在堂屋里搁成面板,转眼家里就成了一个裁缝铺。
晏矮子先要将我们一家人叫出来,一一量出尺寸,爷爷与我父母也就罢了,每年的尺寸差不多不会改变,我们兄妹四人,都在成长之中,每年的身高都会不一样吧。量过尺寸,他就要将布匹在木板上推开,取出又薄又圆的粉饼来,在布匹上划线。这时候,堂屋里面是布料崭新的香气,父亲在外面干活,常常会回来敬烟给晏矮子抽。晏矮子有时候很忙,就将烟夹在耳朵上。
吃过了中饭,差不多已做好了设计,晏矮子就可以在他那一台神奇的缝纫机上面,开始缝制衣服。我们可以整整一个下午,都待在他的缝纫机前面。随着他的穿着解放鞋的脚不停歇地踩动,带动那轮子飞快地旋转,将闪闪发光的缝纫针上下穿过移动的布料,那扎扎的声响令人沉醉。
像我们这样的七口人的家庭,每人都要缝一套新衣,晏矮子一天没有办法做完,所以他晚上要留在我们家吃饭,与父亲一起喝酒。晏矮子是朋兴镇那边的人,到我们村来做上门女婿,他个子矮小,窄小的国字脸黑黑的,喝过酒就变成酱红色。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不错,一边讲论世界上的大事,一边喝酒,可以讲到很晚才回去。
我们却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回家去。等他走了,我们就可以去玩他的缝纫机,将地上的布条,在缝纫机上,嗒嗒地缝到一起。将地上用断的缝纫针找到,好用做以后钓鱼用的鱼钩,将他没有用完的粉饼找出来,攒在一起,好用来写字与画画。我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去金神庙学裁缝,这未必不是因为晏矮子的缝纫机令她着了迷。可惜这时候,大家差不多都要去肖港镇买衣服穿了,姐姐的裁缝手艺终究是没有学成。
第二天清早,晏矮子即可将余下的几件衣服缝完,然后取出他的熨斗交给我妈妈,让她拿到灶间,去将熨斗中的木炭点着。红红的木炭在熨斗中啪啪地烧起来,晏矮子用他灵巧的手将衣服一件一件地烫好,叠在铺板上。干完之后,就可以收拾起他的裁缝担子,离开我们家,去为排好日子的人家做衣服,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忙到腊月二十几,新年来到的时候。
晏矮子走后,母亲才能取出新衣让我们试穿,看一看是否合身。晏矮子的手艺,其实当得起查验,不然,母亲也不会要等他离去后,再让我们试穿。新衣裳试过后,就被妈妈锁到柜子里,与我们一起等待着新年。
好在新年很快就要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守岁的时候,据老人们讲,也就是在守絮,守候着新衣,熬到眼神■,瞌睡虫发作,爬到床上,关下蚊帐,钻进被子里。这时候母亲就会进来,将柜子里的新衣取出,盖在我们的被子上;将她做的新鞋子,放在我们的枕头边,让我们兴奋地,在新衣新鞋的气味里进入新年的梦境。
那时候,家家户户,每年都要请裁缝做衣裳吧。不过有一些人家,会有人在外面,没有办法赶回来过年,所以诗中讲:“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有在外面不能回来过年的人,家里做下新衣的人,在大年初一,也未必会开心。好在我们家里的七口人,每年初一都可相聚在一起,都可换上晏矮子为我们制成的新衣裳过年,这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12
冬至之后,踮起脚就可看见年关。要将年过好,必得有周详的预备。这一个多月里,风雪无阻,要做的事情是:有一些人家,要将媳妇娶回来,这样吃年饭的时候,就会增加一个新人。将村子里的池塘用抽水机抽干,按人头将鱼分掉,好让人家腌鱼。杀年猪。腌肉。腌鸡。将白菜与萝卜由地里挑回来,腌上满满一缸。接裁缝来给全家人做新衣。母亲为全家人做新鞋。学校放寒假,学生们除了做寒假作业,还要再买来墨汁与毛笔,练毛笔字,准备写对联。打豆腐,一半晒制臭豆腐,一半留成白豆腐入油锅炸成底子、三角、豆腐元子。做一坛米酒,用棉衣裹起来发酵,或者是放到温暖的糖坊里,这样才能在大年里,让客人吃上米酒煮鸡蛋。去糖坊里订一二十斤麦芽糖。爆米花的老头挑着爆米花机来了,要将家里的米取出来去排队,爆出大半缸米花。打糍粑,将糯米蒸熟,借来砥窝,打出一长条一长条砖头一般又厚又重的糍粑来。烫豆折。将大米、蚕豆、绿豆磨成粉,调成浆,在锅里摊炕出豆皮,切成丝,晒干。打阳尘,扎起扫帚,将家里的板壁上的灰尘与蛛网扫除干净,将碗橱搬出来,放在门口洗刷干净。约华清来剪头发,将爷爷刮成光头,父亲与我们剪平头。去金神庙赶集,买生姜、卤料、香烛、鞭炮、门神、画子、红纸。爷爷在要烧给祖宗的马粪纸上打出钱印子。反复告诫小孩子们,过年要讲吉利话,不能犯忌讳,说到鬼啊什么的,就像嘱咐狗子过年似的。小年一过,年关的最后几天,更见忙碌,动油锅炒锅卤锅,父母成天在厨房里忙碌,姐姐与妹妹在井边卷起袖子清洗白菜,胡萝卜,藕;洗晒被子。转眼就会到三十除夕,一大早关门吃完年饭,全家洗澡,将水泼出门外,将房间清扫一空。下午写春联,摊放在堂屋里,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熬出浆糊,举着灯,搬着木梯将春联、门神、说帖四处张贴,此时就可关门守岁,一家人团坐在电灯下,打牌,烤火,看电视,等候新年的来到。
责任编辑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