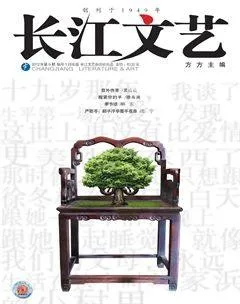乡村纪事(三章)
我时常想起这种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是从心底喊出来的歌谣,这种歌谣会让宁静的乡村顷刻间活跃跳动起来。
榨匠——远去的歌谣
父亲是个榨匠,因此对打榨,我便有比别的行当更多的熟稔。时至今日,父亲那拼尽力气吼出来的“嗨哟”,以及叮叮当当的牛铃、吱吱呀呀的碾声……常常进入梦里,以至于我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种听一首老歌、欣赏一出舞蹈的感觉。
今年二月,我回到老家,想再看一看榨坊,可没能如愿。那里,别说碾子、榨已没有踪迹,就是想找到一点踪迹一个零件也难。那里早已是一片蒿草。
榨是用来榨油的。油茶籽、芝麻、桐籽、漆籽这些油料植物要变成油,就要通过榨榨出来。榨的构造很简单,四块圆木组成的榨身,固定和支起榨身的榨脚,悬吊在榨一旁的撞杆,以及往榨身里添加的种种楔子(排楔、倒楔、上扦、下扦、油饼、坐狗脑、行狗脑、泡子)等。这一切都是木质的。当然这些木头的材质是硬度和韧度很好的枇杷木、梨木、核桃木、油杉等,而且榨身还需要木头足够宽大,使其能够在中部掏出一个弧,在四块圆木合起来时,能形成一个直径一尺多的圆形空间,用来放置油饼及各种楔子。因此,一合榨便可以装满整整一间屋子。这在乡村,算是庞然大物了。小时候,榨身常是我们“作战”的战场,我们爬到榨身上面,以直伸向上的榨腿为掩体,向对方投射泥土做成的炸弹。可见榨是多么宽大。
撞杆的材质比榨身更要坚实,一般用核桃木做成,两头细,中间粗,像一条巨鲸,打击的一头,装有嵌着铁质十字的铁圈。它重达三百斤左右,垂吊在一根专门的“门”字形的木架上,距地面约半人高,当它从高高的地方划下来时,正好可以打击插在榨身里面的扦脑。平常,不打榨的时候,它一头抵在地上。我们会骑马一样骑上去,享受摇篮一般的摆动,或者几个同伴骑到两边,像坐翘翘板儿一样玩耍。想来,这也算是我们成长的道具和摇篮吧。
在榨坊里,除了榨,还要有锅、碾、甑等配套设施。锅是用来炒菜籽、芝麻、花生、漆籽的。一般而言,榨食用油,都需要先炒制植物籽实,这样油才更容易榨出来,而且油才香。这也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
碾子就是将用来榨油的菜籽或花生等油料碾烂的工具。它由碾架、碾槽组成。碾架酷似一辆装有两个轮子的架子车。只不过两个碾子是青石打制的,而且一前一后装在碾架上。碾槽装成一个圆圈,碾架的一端固定在这个圆圈的圆心。一般而言,碾架运动的动力是牛、马,或者水能。
碾子也是十分有趣的。在牛和马拉着碾架绕着碾槽盘旋时,碾盘和碾槽会发出一种咯咕咯咕的声音,碾架和几处转动的地方也有声响,吱吱呀呀地,就像一首舒缓悠长的歌谣。假如那天是一头颈项上佩戴了牛铃的老牛拉碾的话,叮叮当当的牛铃声就会像小河中的浪花一样美丽。这就成了一曲由金、石、木的声音共同组成的绵延不断的交响。
大人说,给牛赶蚊子去。我们就会爬上碾架,坐在上面,挥舞着一匹棕叶,驱赶那些在牛、马的屁股上乱咬狂叮的蚊蝇,贪婪地吸着从碾槽里发出来的浓得像稠稠的油一样的芬芳,直到碾槽里的东西碾好了。
一架常用的碾子,碾盘的边缘和碾槽的底部都是光滑透亮。那是它们被油浸泡了许久许久的缘故。好像它们里面贮满了油,用手一拧,就可以拧出金灿灿亮晶晶的油来。
花生和芝麻碾好了,就上作甑了。作甑比蒸饭的甑子要大若干倍,圆周大约两米多,要两人合抱。它被泥巴和土砖“砌”在锅上,不能活动。一般而言,作甑蒸一甑可以装满一榨。为便于操作,它打在地面上,榨的旁边。
这样大的甑子,就需要与此相匹配的大锅和大灶。大灶因其蹲在地上,形似一只卧虎,人们就叫它老虎灶。这样的大灶,就有较大的灶门,有很粗的烟囱。因此,作甑一丢火,灶前便是一片火红,灶里发出呼啸的声响,伸到屋脊上的烟囱冒出阵阵幽蓝的炊烟。一会儿,甑上冒气了,气越来越大,像云雾一样在榨坊内翻滚。
这就是一座榨坊的几大件。有了这些设备,榨匠就可以从花生、芝麻、漆籽等籽实中榨出亮晶晶香喷喷的油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炒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是碾、蒸、打。这些工序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假如火候和力度掌握不好,就会影响出油,以及油的质量。
譬如说炒。炒是在另一口灶里。先将锅烧热,烧干。待锅内达到一定温度,将被炒的东西倒进锅里,一个人站在灶台边,用木抄子不断地在锅里搅动,使之受热均匀。待锅里发出一种香味,炒制的人从热锅里抓几颗出来,用拇指和食指一捻,看看翻炒的程度。如果手指上有了油,壳容易捻碎了,估计好了,就迅速将东西铲到事先摆好的晒席上。炒的关键在于火候,过了,出油少,油老;欠火,油嫩,也差香味。
打桐油是不需要炒制的,但要退壳。桐籽是坚壳类植物,这种坚壳掺杂其间,可使其具有一定的涩性。所谓退壳,就是要退去一定量的坚壳。但退壳的多少也有学问。壳退得少了,壳碎在里面,要裹油;壳退多了,打的时候,容易从草衣里面挤出来。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油就榨不出来了。
又譬如包。包,在家乡称作“包箍”。“箍”的音,在坊间能指称几种东西,一种是包箍的铁圈,一是指榨过油之后的渣饼(可能此箍写作“枯”更合适),还指要上榨的蒸好的箍面。包箍就是用铁圈、草衣将箍面包成圆饼。包箍也是有奥妙的。首先,每个箍必须是等量的,即每个箍里所包的箍面分量要基本相等,不能有厚有薄。薄了,打的过程中,铁圈靠在一起,油就榨不出来了;厚了,箍面就从草衣里挤出来了,油也不能完全榨出来。所以,榨匠一般都会重视这个环节,而且练就了较好的手感和眼力,三瓢半或者四瓢就是一个箍的分量,而且误差一般不会超过几两。其次,包箍要把衣子铺好。所谓“衣子”,就是稻草,将一头扎了,四散抖开,便成了一个圆。把这个圆放在一个圆形模具里,然后就倒进箍面,包起来。
会包箍的榨匠们事先是把三道铁圈放在一块干净锃亮的石板上,然后罩上模子,放入衣子,均匀地打开,放入模具里,这才开始舀作甑里蒸得滚烫的箍面。然后,人站进去,用脚踩紧,待箍面舀到一定高度时,拉上第二道铁圈,再踩,舀满时,拉上第三道铁圈,最后将留在模子外的一段衣子折过去,将箍面包得严严实实。包得好的箍,每个箍的厚度都是一样的,铁圈之间的间隔也是等距的,衣子的每一根稻草都很均匀,没有箍面会漏出来。它们一个一个码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人高,好像一筒拆开了包装的酥饼放在那里。
当然,打榨最有技术含量,最像舞蹈表演的劳作便是打。所谓打,就是把沉重的撞杆高举起来,然后猛力击打插进榨身里的大扦。
箍包好后,榨匠把它们一个挨一个放入榨中间的一个凹槽里,然后再塞入排楔、倒楔、狗脑、上扦、下扦等。这些东西,就是挤压箍饼的。排楔是一个约两丈多长的前窄后宽的楔子,就是它,被撞杆打击,一点一点钻进榨身里,因为越进越宽,里面越挤越紧,油便被挤压出来了。打榨打的就是上下两根扦。而倒楔的形状恰与此相反,它前面宽,后面窄,主要是用来抖榨(使挤紧的排楔松开,以便把排楔和箍取出来)。
打有不同的方法:一个人打和多个人打。但无论是几个人打,都需要力量和技巧。撞杆很重,约三百多斤。举起它除了力量,更要技巧。因此,打榨,即使一个人打,也需要手、脚、眼、气息、声音之间的完美配合。一般是这样:打榨的人左手薅住栏杆中间的吊担,右手贴在身体前方的撞杆上,侧身横推着撞杆,让撞杆与榨身成垂直方向游动。这时的游动相当于助跑,为的是更轻易地把几百斤重的撞杆举起来,为后面猛力一击蓄势。这样来回游动两次之后,打榨者就要举起撞杆来了。这时是撞杆回游的瞬间,他贴在撞杆的右手,“哧”地一下抠住了撞杆前端的一个凹处,脚下快速地横向远处移动,就在移动到最远处时,“嗨”地一声,双手将撞杆高举起来,使撞杆与地面垂直,再猛地转身,快速向前,“呀”地一声吼,将撞杆稳稳地打击在扦上。
这是富有力度的,又是轻盈而灵巧的。在这一击中,打榨人吼出的号子嘹亮而悠远,气吞山河,撞杆与扦的撞击声,干脆而响亮,常常会唤起山谷一波一波的回音。我时常想起这种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是从心底喊出来的歌谣,这种歌谣会让宁静的乡村顷刻间活跃跳动起来。似乎宁静的乡村就是被这打榨的声音叫醒的。
打榨的动作更是美妙绝伦,分开来看,脚下有踮、转、跨、跳,身体有伸、倾、仰、俯,节奏有快、慢、急、徐,臂有屈、伸、弯、展等若干种。也就是说,这一击,一个人身体的肢体都在协调动作,人的力量和美,也在这一流畅的动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这种打法,主要是用于打花生、芝麻、菜籽、桐籽等。打漆籽是不能这么打的,因为漆油太容易凝固。因此,榨漆油时,就不允许撞杆还有游动的间歇。
打漆籽是众多人一齐揪着撞杆,紧促地去打。这种打法叫“拉抱”。
父亲小时候就开始打榨了,在仓坪一带,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榨匠。仓坪一带盛产桐籽、漆籽、菜籽。清末民初,桐油的出口使得这一带榨油业十分繁荣。一般大户人家,瞄准了桐油和漆油的利润,想方设法开榨坊。那47077294905177bfa1f47e040345bd1e时的仓坪,时常可以听到山谷里传出打榨的“嗨哟”声,此起彼伏。父亲的“榨艺”正是得益于感觉中漫山遍野的榨坊。
解放后,父亲因为一身打榨的功夫,被当时的粮店请去打榨。我二月份回去的时候,专门问了问父亲在粮店打榨的情况。这时的父亲眼里放出光来。他说,当时粮店里同时请了几个榨匠,榨菜油和桐油。但是那些人都没有他榨出的油多,一榨相差五斤。粮店的负责人问那些人原因,他们总是说榨有问题,或者说灶有问题、菜籽有问题等等。粮店负责人于是举行了一次打榨比赛。他们把四合榨摆在一起,把灶也打在一起,用同一杆秤称重,然后用同一杆秤称油。结果,父亲打出的油还是比别人多五斤。别人不得不服。因此,这便成了父亲一生引以为豪的事。他谈到这件事时,脸上微红,像喝了酒一样。
现在想起来,格外觉得这种劳动竞赛很生动,很有气魄。想想看吧,四合榨摆在一起,四口灶筑在一起,这是多么盛大的劳动场面啊!而且,炉火熊熊,蒸气升腾,牛铃当当,歇斯底里的“嗨哟”声、撞杆与木楔的撞击声响成一片,这是多么壮观、火热!
当然,在父亲的这个辉煌时刻,我还没有来到人世,没能亲眼目睹这个盛大得令人振奋甚至惊心动魄的劳动场面,我看到父亲打榨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父亲从粮店里回来,又在队上打榨。那时候,各个小队都保存了一座榨坊。我们队里的榨坊支(设)在小队仓库的下面。父亲去打榨的时候,常常会带着我。
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饥饿。因为我至今记得我们那常常装着野菜粥的饭碗。
也许是因为看打榨有趣,也许是因为饥饿,到榨坊可以奢侈地闻一闻油香,这时候的榨坊是一个大人小孩都喜欢去的地方。每到放学,或者社员放工,小孩大人三三两两地就前去榨坊,在那里看打榨、聊天或吸烟。
大人们会打谜语我们猜:“婆婆儿横睡起,老头儿直睡起,老头一使力,婆婆尿直滴。”
猜不出,大人们就笑起来,指着正在哗啦哗啦流油的榨说,真笨,这不是吗?
原来这谜语是说打榨的。于是我们就高喊起来:“婆婆儿横睡起,老头儿直睡起……”嘻嘻一片,乐趣无限。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学到的第一个谜语吧。
当然,我们之所以如此喜欢榨坊,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原因:揩油。
大人们揩油的办法是拿烟叶。他们坐在灶口或者榨边,把烟口袋掏出来,把烟叶放在油碗里浸,然后又用这截浸过油的烟叶去濡染别的烟叶。说这样的烟香。
我们揩油的办法和大人不同,是从碾槽里面抠一点花生末子或芝麻末子吃。我们都知道打花生油、芝麻油时,都是需要炒熟碾碎的。圆形的碾槽是一段一段有弧度的石槽拼接而成的,碾花生、芝麻时,石槽的拼接处往往会积压一些细末,塞得很紧,刷是刷不起来的。因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空间。我们放学后,书包都来不及放回屋里,就直奔榨坊,等大人们把东西舀起来。这时,我们就一个个趴在碾槽边上,伸手去挖塞在接缝里的花生、芝麻末子吃。我们人很多,一下把碾槽占满了,大人们便笑我们像井台边的蛤蟆一样。
有时,手抠不上来了,有人干脆把脑袋抵进槽里去,用舌头去舔。有大人吼起来了,“哎,东子,你舔什么舔,别人还吃不吃油啊?”又有大人出来说,“人娃子的,舌头干净,又不是猪娃子、狗娃子。”有大人站出来这么说,舔的就大胆而欢畅了。现在想起这件事,好笑,可是心里酸酸的。
说到这里,偶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碾花生、芝麻要在下午?
一般而言,打榨是早晨开始炒,冷了就碾,碾了蒸,蒸了就打。也就是说,按照程序,碾花生、芝麻应该是在上午。那么,父亲为什么要放在下午来碾呢?是否有意让我们回去抠碾槽里面的花生末子吗?
当然,因为父亲打榨,我自然地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譬如我给父亲送饭,母亲不让我在家里吃饭,而是要把饭送了再吃。母亲会把父亲的饭盛得很满。而我把饭交给父亲时,父亲端起碗吃一大半,然后望着同伴杞叔笑一笑说,吃不完了,又望着杞叔笑一下,就会从锅里舀一点点油倒进碗里,把拌了油的饭递给我。
这时是“干集体”,我知道父亲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是我分明感觉得到,父亲吃过饭后,打榨的时候更卖力了。他的脸膛和颈脖一片鲜红,叫喊时,颈上的青筋粗壮突出。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是想用他的力气把淋在我饭碗里的油榨出来吧。
队上的榨坊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拆掉的。这当然是因为体制的改变和一种新榨的出现。这种新榨人们称为红榨,铁质的,以电为动力,体积很小,但榨油的效率却是木榨的好几倍。
因此,木榨,这个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芳香和滋润的工具,这种最像原始舞蹈的劳作,像一支古老牧歌一样,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队上这合榨原是没收地主老杨家的,这合榨要处理,会计说,五十元钱吧,优先老杨购买。老杨最后五十块钱把这合榨买走了。后来,他当木柴卖给了一个木匠。他自己家里只保留了一个撞杆。老杨已在十几年前死了。他的后人觉得撞杆放在家里占地方,没用,就劈了当柴禾塞进灶膛里烧了。
这一缕青烟已在几年前飘过。
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闪动在农家的熊熊炉火,听不到那些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而农家的餐桌上、火塘里,也鲜见那种铜质的充满富贵气和精致生活味道的金黄器皿。
铜匠——闲坐说玄宗
找到岳魁刚是因为老冀。这是因为很偶然地听说给他做工的人中,有几个人是铜匠。老冀本来是个公务员,退休后,自己办了一个三峡植物园,聘了一些人,把三峡工程蓄水要淹没的荷叶铁线蕨、梳花水柏枝、三峡纹母树等一些珍稀植物抢救性地挖回来,移栽在自己的植物园里。我打电话给老冀,问他那里是不是有几个铜匠。他说是啊。于是他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铜匠岳魁刚、岳魁金家里。
打铜,我小时候见过。我们家曾经打过一个71ea3028f786ffa975b5280d181f271e铜耳锅。打这个铜耳锅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到吊在火头的那把浑身结着一层烟壳的铜炊壶,说是某年某年,用多少粮食换来的。那两年,一家人多吃了一些草。
母亲为何宁可让一家人多吃一些草也要添一把铜炊壶?
铜炊壶烧水很快,相比鼎锅和瓦罐,也好看、卫生(置不起铜炊壶的人,一般用鼎锅烧水。鼎锅是用铸铁制成的,是当年可以买到的商品。因为锅底和锅壁厚,锅上端是敞口的,因此受热很慢;而且取水不便,要取水,必须把瓷缸伸进锅里,而这时火星或灰尘也趁机落入鼎锅里了,因此烧出来的水总有一股铁腥气、烟垢气。而铜炊壶,因为有弯曲的长长壶嘴,取水方便、也卫生)。而更重要的是,铜炊壶在当时就是一户人家的一件大家当。它甚至还是一个庄户人家殷实和面子的标志。
当时,一般的家庭会有这几样铜器:铜炊壶、铜茶罐、铜耳锅、铜汤匙。富裕的人家,还会有铜脸盆。它们取代了铁鼎锅、陶锅、铁耳锅、木盆等等,使庄稼人的生活变得轻盈闪亮起来。特别是用铜炊壶烧水,用铜茶罐泡茶,简直就是乡村生活的一道风景。
客来了,主人家在火塘里添些柴禾,把炊壶提到灶房里盛上水,挂到火头烧着,然后把铜罐拎出去洗涮一下,放在火塘边炙烤,待铜罐烤干,就抓上一把茶叶放进去烘焙。主人让铜罐在火边烤一会儿,再拿在手中摇一摇,摇一摇再烤一阵,再摇一摇,如是者三,直到铜罐里的茶叶发出一阵浓郁的茶香。而这时,炊壶里的水也烧开了。主人就提起炊壶,小心翼翼地把开水冲进铜罐里。只听见“哧”地一声,一股白汽从铜罐里升腾起来,屋里便堆积着浓酽浓酽的茶香。
这种用铜罐泡制出来的茶膏脂般浓酽,十分芳香。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称作功夫茶,是不是山村里一种简朴的茶艺,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有了铜炊壶、铜茶罐,这种最日常的生活也便有了几分迷人的色彩。
母亲坚决地要请铜匠打一只铜耳锅,是因为铜耳锅比铁耳锅好看,而且体积和容量也比铁耳锅小一些。这样,就有另一个好处,待客时体面(假如要弄一点好吃的菜待客的话,较少的份量就会把一只铜耳锅装得满满当当;而且那熠熠闪光的铜耳锅放在桌上,也令整个餐桌显得干净而鲜亮)。
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打制铜耳锅的铜,也没有钱买铜匠的铜,母亲把一把断了把的铜汤匙,箱子、衣柜上的铜饰件(在更早的年代里,姑娘出嫁时做嫁妆,都要请铜匠打饰件,这是钉在箱子、柜子门上的一种饰物,有各种不同的造型,有的上面还镂有精美的图案,这可见早年手工艺人的制铜工艺了)、铜锁聚在一起,放在一个小竹筐里(谁知道积攒了多少时日?),用秤称过,估计差不多了,就去请铜匠。
那个铜匠姓韩,是我们的本家,长得高大魁梧,而且很胖。我至今仍记得他赤裸着上身打铜的时候,挥动锤子或是拉动风箱时,肥厚的肚皮以及腰间的赘肉一抖一抖跳动的样子。他身上搭着一条毛巾,右手拉动风箱,左手不断地拿毛巾擦脸上滚滚而下的汗水。他把炉子支在我们屋场一户姓周的人家家里。
一天,韩铜匠来我们家吃过早饭,就把母亲收集起来的那些铜提走了。到晚上,这些破铜器就变成了一只亮晶晶光闪闪的铜耳锅了。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这次本想去找这位老铜匠,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下落。
岳魁刚和岳魁金、岳魁甲、岳魁同四兄弟都是铜匠。没有铜打以后,他们在老冀的植物园里做点事情,而且自己也学老冀,到巫山一带去挖树蔸子(中华纹母树),然后移栽在门前屋后和自留地里(中华纹母树可作盆景,因此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接到老冀的电话,岳魁刚和岳魁金就在家里等着。
他们住着一栋砖预结构的房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那时能建砖预结构的房子,可见家境不错。我问他们为什么当时能建这样的房子,岳魁刚媳妇嘴向岳魁刚一翘:这都是他一锤一锤敲(鄂西方言读kao)出来的。这就说明这个行当在当时是很来钱的。
四兄弟都是铜匠,我原以为是家传,一问才知道错了。原来他们的父辈并不打铜,而是排行老二的岳魁刚去跟师学艺,然后,再传给老大、老三、老四。岳魁刚说,他学艺是1978年,那时还在搞集体。他之所以要学打铜的手艺,是因为那时在集体做工,一天的收入仅得一块钱,而做手艺可以拿到七八块。他去找队长,说要学打铜,队长要他按规定每月交三百块钱(交钱才能记工分,有工分才能分粮食,这是当时的体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粮食不是拿钱可以买到的,农村人口,是按工分分粮;城镇人口,则是凭供应本子或粮票),他答应了,就去找师傅。
学了三年,出师(手工艺人学成时的专业术语)了。而这时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几兄弟就先后跟他学起打铜来。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俗称钢精壶、钢精锅、钢精汤匙(铝制品)等一些炊具餐具已在市镇和较发达地区使用了,而一些偏远山区则因为休养生息,渐渐有了一些实力,于是打铜的生意在这样一些地方悄然勃兴起来。
岳魁刚说,他们那时绝大多数时间在南漳、保康、兴山、谷城、竹山、竹溪、巴东、神农架等一些地方做。这些地方喜欢铜炊具是有理由的:他们做饭和取暖的燃料一般是木柴,铝制品显然没有铜制品好使。
打铜的工具主要有:风箱、砧子、锤子、钳子、化铜罐、试铜槽、剪子、锉、钻子、秤、机车、灯盏等等。风箱是木制的,约有五六寸宽、一尺多高、一尺多宽。内部分成几个部分,最下面是风箱,上面是两个小屉,主要用于放置一些小工具和原料(如锌、硼砂),再就是充当师傅的钱柜。最上端,四周镶了边,让镶板高于顶端,从而形成一个斗状的没有盖板的盒子,这主要是方便操作,如锉铜,而被锉下来的铜末就落在这个斗里(有俗语云:“铜匠不落铜,锉达眼睛红”,是说锉铜是铜匠赚取东家铜料的一种方式)。而在风箱的两边,分别用两篾片夹起来,再用一根横梁把两边的篾片联结在一起,这样挑或者拎就很方便了。
因此,铜匠行走起来,一般就786fc8e753faef6462e326cac538685df312dcc5060b9c326823cbc4ff066a6c是这样一副模样:一根扁担,一头挑着风箱,一头挑着装着锌和衣物的包裹,头上戴着草帽,有的还在风箱上挂一把雨伞。岳魁刚说,那和逃难一样。
铜匠与别的匠人做艺不一样。是流动的,又相对固定。他们不可能像木匠、篾匠一样,给谁做工,就在谁家里吃住,作业点也摆在东家的客厅里。他们是流动的,又相对有一个固定的作业点。这主要因为:一是他们随时随地要带上很多很多锌,特别到远处做艺的时候。因为在偏远的地方,要买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只好随身带着。一般他们会带上一百多斤。而锌是不能带入东家老板家里去的。东家不懂兑锌是打制铜器时必须配兑的原料,而认为是掺假。因此,他们到一个地方,就要找个熟人,以便有一个放置锌的地方。二是打铜的第一步工作是先立炉子。这个炉子他们叫八卦炉(四个角上砍一刀,把四个角变成八个角,他们称之为八卦炉。因为铜匠认为,他们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而把炉立成八卦炉,就会得到太上老君的庇佑,不会遇到有人架火),虽然立起来并不复杂,但他们并不是走一家立一家,而是能让一个屋场、甚至一个小队(假如他们居住并不十分分散的话)的人都会到这家里来打铜。铜匠本人就会把这一家变成一个作业点,直到把这个村子上的活做完。
这样的事情,在城市或者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是不太可能的。谁喜欢一个铜匠在自己家里给别人做工,成天敲敲打打,烟飞灰漫?可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这就不是一个问题。这自然有铜匠自己的工作,譬如,对东家态度好一点,有时送给东家一只铜簪、一个小汤匙,有时候,给伢儿一点小玩意儿等等,总之,炉子一旦立在谁家里,铜匠就会和谁处得很好。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地人的淳朴。他们对这些不去计较。所谓人情大如天,他们即使心里不愿意,也不愿意得罪村邻。
炉子立好,铜匠就开始打铜了。首先是化铜,把“夫食子”(木柴燃烧后的一种炭)放进炉里,用火引燃,然后坐在一个很矮很小的小板凳上,拉动风箱,炉子顷刻间就会亮起来。再后,把一些破铜器放进化铜罐里化起来。
化铜应该说是打铜的第一道工序。这里的关键是兑锌。兑锌多少要看东家提供的铜是什么样的铜,是紫铜,还是黄铜、白铜,而同是某一种铜制成的器皿,其配比也不一样,因而化铜时兑锌的分量也就不一样。如有一种铜钱,当50的和当20的就不一样。因而这全靠铜匠的经验。化铜的第二个难题是加锌。我们已经知道加锌会被认为是掺假,而一掺假,东家就不会信任了,在一个山村,假如有人认为你掺假,那你这活就做不下去了。而有的东家为了防止铜匠“掺假”,会在化铜的时候,一直守在炉子边上。这时要成功地把锌兑进去,就要费一些脑筋。“老板,能不能帮我倒一杯茶去?”他这样说。山里的人毕竟是纯朴的,匠人给自已做艺,能不倒杯茶吗?于是倒茶去了,这时铜匠迅速地把放在风箱的小屉里的锌拿出来,丢进化铜罐了。
打铜赚钱,赚就赚在锌上。锌的价格只有铜的一半。但如果锌兑多了,打制铜器的时候,铜就会裂口,这样就很难把东西打好了。而且锌偏多,打出来的铜器带红色。
化铜还有一个火候问题。要看到罐子里都放亮了,看到渣子在里面旋转。其实,这可能就是沸点吧。铜化好了,倒进一个模具中冷却。然后按照需要开始正式打制。如打耳锅,就将铜冷却成一个圆饼形状,然后用琢(方言念zhua)锤(一种丁字形的铁锤,形似挖地的镐)打制,一点一点地展开,慢慢打制出一种形状。
岳魁刚说,他们会打的铜器主要有:炊壶、酒壶、锣、唢呐、钵(一种响器)、各式烟袋、耳锅、汤匙、面盆等等。在这些铜质器具中,最难打的是唢呐。唢呐的喇叭口,要有弧度,弧度要合适,否则,吹不出声音。这是其一。其二,唢呐要美观,让人从外面看不到焊接点,就要在铜管里面焊接管缝。铜匠焊接(俗称烧焊)和铁匠不一样,因为炉子的位置相当低,炉面离地面只有二十公分高,而焊接的时候,铜管要放在炉里烧着,这时,人就要趴在地面上,头侧睡在地面上,手里的焊接原料才能伸进铜管里去。
铜匠常年远走他乡,有时半年,有时一年回家一次,因此,铜匠们十分喜欢在作业的地方认“干爹”、“干娘”、“干女儿”、“干儿子”。一旦有了这层关系,陌生的他与他们之间便有了某种亲缘关系。他们就有了一个在异地他乡的落脚之处。他们便把沉重的配料锌放在那里。而在一时找不到活做的时候,也就落在那里吃住。
有些铜匠时间住久后,与他们有了感情。因此,对于铜匠,便有这样的俗言口碑:“十个铜匠九个嫖,一个不嫖是个苕。”(后来,汽车和公路出现后,人们把这一说法张冠李戴到司机头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对铜匠“好色”的夸张,与实际的情形大相径庭。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品味出打铜的艰辛,以及铜匠特殊的生存智慧。
岳魁刚谈到这里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抿嘴而笑,停了一下,说了一句:“我师傅倒是这样。”他接着说,他师傅有一个相好,那个相好的男人在学校里做饭。师傅就一直歇(下榻)在她家里。那个相好,对他师傅相当好。师傅把自己的孩子带过去,相好帮着照看。有时候,他们这些徒弟一时找不着事做,也到师傅的相好那里去蹭饭吃。师傅的相好竟然乐颠颠地。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来,他们脸上有一种庆幸或者说甜蜜的感觉。毕竟这一切都是打铜带来的呀!
九十年代,他们的生意渐渐少了。原因主是要铝制品的普及,再就是铜的金贵,铜价涨了好几倍。过去4块钱一斤,现在涨到20多块,如说一只铜脸盆,现在单铜钱要150元左右,工钱要200元,就是350元。而一只塑料面盆只有几块钱,搪瓷面盆也只要几十元。因此,人们便不怎么打铜了。
没有人请他们打铜,岳魁刚他们只好回到村上种地了。虽然他们明知道时代向前行进,他们从事的这个职业也会越来越落寞,但他们却没有把风箱、砧子这些工具,这些帮他们挣来了砖预结构楼房、这个帮他们挣来媳妇、帮他们成家,给他们生存和快乐的“朋友”(衣钵)丢弃掉。他们把它束之高楼,像某个荣誉一样珍藏着。
铜匠这个职业也几乎消失了。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闪动在农家的熊熊炉火,听不到那些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而农家的餐桌上、火塘里,也鲜见那种铜质的充满富贵气和精致生活味道的金黄器皿。
——那好像是一个梦。
我拿起一把钻子仔细端详,似乎看见原始人在莽莽森林中奔突,拾起石块向前面的一只香獐掷过去,看到他们为了切割香獐的大腿,迷茫地寻找着锋利的石块
石匠——铿锵的挽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的农村,谷仍是用石磙碾下来的,米是用石碓舂出来的,面粉是用石磨磨出来的。石磙、石碾、石磨、石碓……不知道出现于何时,但可以想象,它们陪伴人类走过了十分漫长的岁月。石磙是用来脱粒的。稻谷、麦子、豌豆、葫豆等等作物,就是靠石磙的碾压,籽实才能从禾秆上掉下来,成为粮食。石磙有两种:一种是布条磙,大约两尺长,一头稍粗一头稍细,中间钻有圆孔。另一种是组合磙,由三个厚约五六寸的石饼组合起来,中间亦有圆孔,用木棍穿连起来。
打谷是石磙最主要的用途。一般是这样:人们将从田间背回来的稻子均匀地铺开在稻场(院坝,鄂西一带称作稻场)上,晒到太阳偏西,禾秆枯焦,这时就把牛牵出来,把石磙套上去,让石磙从里到外一圈圈碾压。石磙在碾压时,相互碰撞,发出砰隆砰隆的声音,稻场上也立刻飘出一种裹着青草味的谷香。石磙碾压一遍,大人们便用扬杈(一种“人”字形的木质工具)把碾压过的稻草翻过来,这时稻场上已落了厚厚一层谷了。
打场一般都在太阳下山之后,往往会持续到夜间。这时月亮升了起来,照着拉着石磙的牛和翻动着稻草的人们。这时候,人和牛以及影子活跃在山村的院坝上,组成一幅充满喜悦和恬静的山村丰收图。而我们,常常会在石磙转过去的时候,大胆而恣意在稻草上追逐、打滚、蹦跳,挥洒着山娃子们快活无拘的野性。
石磨,有大磨和小磨(手磨)两种。大磨与北方的磨略有不同。北方的大磨,磨盘上是一个石磙,利用石磙在磨盘上碾压,而把要磨的东西碾碎;南方的大磨,是两块磨盘,磨盘的一面有密集的磨齿。两块磨盘扣在一起,上面一块中间有一圆孔(俗称磨眼an),粮食从此进入磨中。磨盘的两个方向上装有木桩(磨手),以便和动力联结(马、牛和大磨联结的那些工具叫做“套”,人一般用扁担、或一种专门磨杠。这算是大磨的附属设施吧)。大磨一般用来磨小麦、玉米,以马、牛或人拉动上面的磨盘。大磨的直径一般在两尺左右,因为要有马、牛或人转动的空间,因而一般摆在专门的房里。这间房被称为磨房。
大磨一般是大户人家的,在需要较多的麦面和苞谷面的时候(如过节、过事)。一般农家只有手磨,而且必不可少。
推大磨,需要赶磨。所谓赶磨,就是驱赶拉磨的牛、马,或者为它们驱赶那些死皮赖脸追逐它们的蚊子。赶磨者一般由小孩来充当,他们手中拿着一匹捶软的棕叶,在牛和马的身后亦步亦趋,时不时往牛和马的屁股后面挥一下。
磨面时一般是一边磨,一边筛。马蹄得得几声响,磨一转动,一股新麦的香味顿时弥漫起来,雪白的面粉像雪一样一片片贴着磨盘落到干净的磨板上,眨眼间整个磨盘下面就出现一道雪白的线,再推几转,面粉一点点增多,慢慢地变成那种像落满了积雪的山峰。这时,头上包着毛巾的母亲或者姐姐就会用撮瓢把面粉撮起来,端到摆在磨房角落里的一只大腰盆前面,倒在事先准备好的络筛里。她们摇动络筛,精细的粉末便落入盆底。
我就赶过许多次磨。现在想起来,它似乎蕴含了某种特定的意味。
小磨的用途更广泛,除了磨苞谷、小麦,还用来“推浆”:譬如磨黄豆打豆腐、磨玉米浆做浆粑粑,磨玉米浆熬糖,梭(剥)谷壳、荞麦壳等等。小磨的体积小,也是上下两块磨盘,它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架上,人站在一边,用磨抓子(一种“丁”字形的木质工具,它一头放在磨手里,另一头被推磨者抓在手里)推动磨盘。另一边有人坐着,往磨眼里添加要磨的东西(喂磨)。
推手磨需要一定的体力。想一想,我大约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能推手磨了。我记得母亲不断地要我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而我,当时却以自己能推动手磨为骄傲。或许我在显示我的劳力不错。
印象最深的是舂米。大约是过年前吧,姐姐们把谷子用手磨“梭”(将谷壳剥离)了,就大袋小袋的背着去舂。碓是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碗形的碓窝埋在地面以下,一根木梁上绑上一个石柱(俗称碓脑壳),木梁下面有一个支点,人站在碓窝的另一端,踏动木梁,让碓脑壳翘起,落下,翘起,落下……把米舂“熟”(从手磨里梭出来的米粒,表面不白,不易煮。经过碓舂之后,米变得雪白、透亮)。
可能是要过年的缘故吧,我们去舂米的时候,那里等候了很多人。她们(一般是妇女和小孩)在那里说笑。自然就开始了一种劳动的协作。不管是谁的米,都会帮忙踏动木梁。看起来,碓脑壳像一只啄米的鸡……
石器是人类开始时最主要的工具,考古学家从石斧的刃口上判别人类生存的时代。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换一句话说,人类的进步进化,是从利用石器开始的。直到从石头里面炼出铜、铁,人类才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有了另一种文明。人类用从石头中提炼出来的铁器,开始对石头的雕凿和对土地的征服,开始让生活变得轻松和精致起来……
石器伴随人类行走了几千年上万年,作为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的石器现在却越来越稀少。而以制作石器为生的石匠也已几近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我五月份回到老家,终于打听到村里还有一个石匠,于是租了一辆摩的去了。
当然,在此之前,我曾经搜寻过那些我熟稔的石碓、石碾、石磨等等,可是已不能如愿。现在保存得比较完好的是人们甩在屋前屋后的手磨。而石碓和碾槽、碾盘已难觅踪迹了。
乡村石匠主要就是打制石磨、石碾、石碓、石磙。脱粒机、打米机、粉碎机、干湿磨的出现和普及,导致这些石器已不再为人所用,因此,在我去找石匠的时候,心里想着,他可能是末代石匠了,或者说是最后的石匠了。
他叫郑光华,我问他现在还打石头吗?他说打。我问打什么,他说主要是打碑,有时候,也给人家打一打建房的水脚石。打碑,已经是石匠最主要的业务了。这是不是石匠最后的挽歌,或一种无奈的谢幕?
郑光华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学石匠的。那时他14岁。他学石匠的动机很简单,“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因为他们一家五兄弟,家大口阔,生活很困难。他想吃饱饭。相比其他的手艺人,石匠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的作业点常在野外,同种田种地一样,要受风霜雨雪之苦,而且,还需要足够的劳力和悟性。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学石匠。但郑光华却铁了心要学。他想石匠这门手艺虽然辛苦,但毕竟比种田的收入高,而且也不会失业。于是,他装了“盒”(一种长约两尺、宽一尺的长方形木盘,用以放置礼品,礼品一般以烟、酒、糖、面条、猪腿、鸡蛋等,广泛用于拜师、谢师、求亲等),在盒里放了一套衣裳。
首先就是学劈石头。因为石匠要打制器具,首先要有材料,这跟别的艺人也不一样。别的艺人,材料都是东家自备的,而石匠要自己去取料。因为,只有石匠才能辨认哪种石头可以打门槛,哪样的石头能打磨。这是一方石山,上面长满了荆棘。他们先要把荆棘除掉,然后仔细地辨认石头,是青石,还是老娃石、掉灰石、响班琴(这些都是石匠称呼的石头名称,不知它们究竟是怎样的石头),如果正是他们需要的那种石头,就开始取料。
口诀是这样:“掏三钻,打穴眼(an)。”即,先用钻子打眼,约一尺远一个,把眼打好后,把铁锲子打进去,然后用力敲打铁锲子,让铁锲子把石头“胀”开。
取石头,行话叫做“发青山”。如果是建房取大门料,还要先看看日期,择吉2+KEMOzLYBQ2DghDItehPw==日。
和所有手工艺人一样,石匠带徒,一开始师傅不会教你做什么东西,而是熟悉规矩,干杂活,等干到一定程度了,才让你摸家伙,教你使用工具。
石匠的工具主要有:墨斗、曲尺、五尺、龙骨(装置钻头的套子)、锤子、钢钎、扁钻、小钎子。
墨斗是一种丈量工具,由一个墨盒和一个小转轮组成。墨盒里面装有棉花之类的填充物,让墨汁浸透,转轮上绕着很长的线,线从墨斗中拉出,自然就粘了墨汁在上面。这样,要取材料或将材料取直时,就弹线。将两点固定,把线绷起,然后弹下来,一条又直又细的墨线就落在石头上了。因为石头有时候是黑色的,因此,石匠的墨斗,常常用红色的印油。
曲尺和五尺也是丈量工具,它们更多地用于打制器物的时候,上面有精准的刻度。曲尺的作用是量角,要把方形的器物打周正,必须保证角是直角。而五尺是石匠用得最多的计量工具。相传是祖师爷鲁班所传。传说它可以避邪。走夜路,只要带上五尺,火焰很高,神鬼也要避让。
石匠最多的工具是钻头和铁锲子。它们有很多型号,打制不同的器物或在不同的时间里选用。而小钎子就是雕刀,主要用于在石上雕刻。
石匠的工具并不复杂,但用起来却很费力,因为它的对象是笨重而坚硬的石头。所以,没有摸过钻子的人,一开始,钻子上去是钻不动石头的(他们的说法叫“不巴”),只有将钻子的角度、锤子的力度协调合适以后,钻子才可以按人的意志工作。
郑光华学取石料,学了一阵,很辛苦。可是,为了学到真艺,晚上他也不休息,给师傅家里推磨。师傅觉得他能吃苦,爱钻研,教得更认真了。
开始叫他打门墩(放置于石门槛两头,用于固定门槛和大门枢纽的物件),郑光华好像懂了,抄起家伙打起来。师傅也没怎么管。打好一看,完了,打的“顺风”(门墩像鞋一样,左右各一,开口不同。“顺风”就是没分左右)。师傅气得掴了他两耳光。
石匠的手抽在人的脸上,可想力量是不会小的。郑学华两眼直冒金星,想哭。可是怪谁呢。怪自己呀。自己怎么就不知道门墩是一左一右呢?
这回算是吸取教训了。
石匠除了打磨、石磙、碾子、门槛以外,还有一项业务是钻磨(当地上也称为“蚕磨”)。为什么要钻?一是石磨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磨齿钝了,石匠要通过钻、剔等方法,将磨齿打锐利。二是新磨不合适,上面的磨盘与下面的磨盘不能咬合,不能推东西,或者东西推不烂,或者推起来特重。这都要请石匠来钻磨了。
这是在东家家里进行的。一般而言,东家要为石匠准备丰盛的饭食。所以这是石匠最轻松最喜欢的事情。在缺粮吃的时候,有人供吃喝,有工钱,而且又不需要抡大锤。这就很不错了。
因此,石匠很在意别人对于钻磨技艺的评价。因为当时一个村子里有好几个石匠。只有磨钻得好,才有人找你干。而有时候即使用心也难免出问题。这时,石匠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而会说石头有问题,或者说钻磨那天,有什么高人搞“板眼儿”等等。
搞什么板眼?如果推不出面来,石匠就会说,这磨被别人封了口。
其实,这是钻磨有窍门。有口诀:“一指黑,二指白。”什么意思?是说磨沿的宽度(这当然是指内沿)。磨沿两指宽时,磨出来的东西就白,磨沿只有一指宽,磨出来的东西就是黑的。其实道理很简单,磨沿宽,东西放在里面碾压的时候就长,才会细,就白了;窄了,东西碾不碎就落出来,所以黑。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磨推不出面来呢?一是磨沿不能太宽,二是赶齿的走向与弧度。磨齿,不管大磨还是小磨,都是八方齿,大磨一方齿是13-15根,小磨一方是7-9根。大磨有两根赶齿,在磨里被碾压的东西,出得快还是慢,与赶齿有很大关系。如果赶齿的走向不对,东西就不能顺利地出来。当然,决定磨好不好推还有一些因素,如磨齿的深度、锐度、走向等等。钻磨是石匠最简单的业务。以此观之,石匠大概也不那么容易当吧。
钢磨(干湿磨、磨面机)普及后,农家用不着再请石匠打石磨、钻磨了。人们不再记得石匠了。只有在吃馒头、米饭的时候,才会说起石磨:哎,机械推的面到底没有石磨磨出来的好吃,米也没有石碓舂出来的米香……
那么,郑光华,这个想一辈子吃石头饭,在大山里锤炼出了一身侍弄石头的绝技的石匠,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打碑!
农村立碑(墓碑)的风俗勃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原因是农村因为实现生产责任制,得到休养生息的农民们手里有了一些余钱,也应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吧。
墓碑的材料是石头。因而,石匠有了用武之地,石匠也就保留了下来。要不然,我现在也很难找到郑光华了。
郑光华的房前屋后都摆有一些石料,都是打墓碑用的。他的作业方式是这样:哪家要打碑,就先到他这里来预订。然后他就去取石料,请车运到家里,在房子外面搭个棚子,作为他作业的地方。打碑一般要打七块石头,大约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最难得打的是碑面子。它是墓碑的主体部分。首先,要用钻头把表面钻平,然后磨光。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个人配合。程序是先把碑面摆到一个牢实的木架上,然后用夹棍夹住一大块砂石,几个人抬着大砂石,在碑面来回晃动,一边有人往上浇水。开始用糙石,然后再用细石,直到把碑面磨得光滑如镜。一般地,磨这么一块碑面,需要六个工。
现在,因为有了球磨机,磨碑面就变得简单一些了。碑面磨好,就能往上面刻字、雕花了。这时石匠会告诉东家,要刻碑了。但石匠不会急急忙忙刻起来,他要将情况告诉东家。因为有规矩:这时候东家要给石匠封喜钱。
喜钱就是一段“红”(红布、红绸之类)搭在碑面上,或者是一个揩汗的毛巾。收了喜钱,石匠就会把罩在碑面的东西揭开,请先生在上面写字。写字的先生,可以由东家请,也可以由石匠代请。先生把碑文写好了。石匠就开始刻了。
郑光华说,刻字是打碑最难的。要靠手里的力度来控制字的轮廓和锋芒。用力要均匀。尤其是不能刻错。一笔错了,又要重新磨掉,再从头来。
还有一个难题是要雕画,就是在上面雕龙刻凤。这不能请人来画。谁会画呢?只有自己学。郑光华说,为了学这个,他费了不少工夫。
碑打好了,还要立碑。东家会挑选一个日子,把几块碑石都运到事先选好的地点(一般为墓地)立起来。这时石匠就会说几句吉祥的话:“此墓此墓,听我嘱咐,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子孙万代,步步高升,万代发祥。”
这才算把一座碑打好了。多少工钱?八百块钱。打一座墓碑,三十天左右,八百块钱,每天只有二十多块钱。郑光华说,这是他家庭的主要收入。他一年下来,大约可以打八到九座碑,可收入六千多块钱。
郑光华今年43岁。已经从艺近三十年,是个老石匠了。我问他现在有没有人跟他学艺,他说没有。因为这个事蛮苦,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而且在外面打工,比这强。
我拿起一把钻子仔细端详,似乎看见原始人在莽莽森林中奔突,拾起石块向前面的一只香獐掷过去,看到他们为了切割香獐的大腿,迷茫地寻找着锋利的石块,用一个石块去打击另一个石块……
当然也会想起打谷场上的嬉闹、舂米时的欢笑、以及那响彻在春夜里手磨的声音……
似乎只是一眨眼间的事情,从人类用石头去获取野兽野果到石器终于退出工具的行列。
想一想,一种伴随我们走过几千年的东西,就这么没了吗?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责任编辑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