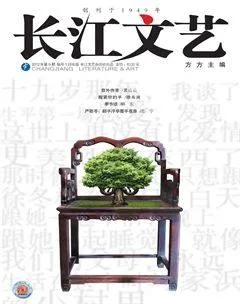“五伦”、“三纲”分梳说
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华文化为解决此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说所昭示的人际间良性双向互济关系的理念。
自两汉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三纲”说与“五伦”说(“五伦”或指仁、义、礼、智、信,或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本文取后义)并列论之(所谓“三纲五常”、所谓“纲常名教”),无论是汉至清对“纲常名教”的推崇,还是近代将其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抛弃,都是把“三纲”说与“五伦”说捆绑在一起的。其实,“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分别代表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不宜笼统处置,而应予分梳,区别对待。
一
中国的人伦观,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系统,形成两种传统。一种传统以“三纲”说为代表,最典型的表述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颖达)
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近人张之洞在《劝学篇·明纲》中说:
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足见“三纲”说作为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抵制民主、平权的诉求。
另一种传统的代表性表述则是“五伦”说,所谓: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这种“五伦说”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
简言之,民本主义的上下关系论要领有二:
第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尚书·五子之歌》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一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三十九》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是以贱为本也。”正是从这种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的认识出发,孟子发出千古名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尚书·泰誓》记有周武王的名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皋陶谟》有另一名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老子·四十九》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如孟子所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警告,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贞观政要》)的名论承袭于此。
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司马光:《家范·夫妇》)。“夫不义,则妇不顺矣”(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双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双向要求;
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
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王肯堂:《交友》),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
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他指出:
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
二
“三纲”说与“五伦”说的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
“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
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
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长者
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时至近代,“三纲”说的元典性成为争论的焦点。
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内篇的《明纲》中亟言三纲说来源于圣人之道。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三纲说”为扬弃对象,如何启、胡礼垣在1899年撰写的《劝学篇书后》尖锐批评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宣扬的“三纲说”,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何启、胡礼垣特别揭示三纲说的非元典性:
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
三纲之说,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释之,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礼纬》之书,多资谶纬。以谶纬解经,无一是处,为其无实理之可凭也。
三纲者,不通之论也。(《劝学篇书后·明纲篇辩》)
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又进而指出,“凡尚理学如希腊等国,亦莫不以五伦为重”,足见五伦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劝学篇书后·明纲篇辩》)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区分“三纲”与“五伦”:
后世动谓儒家言三纲五伦,非也,儒家只有五伦,并无三纲。”(《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第9册,第75页)
这里说的“儒家”当然是指先秦原始儒家。梁氏此一辨析,与何启、胡礼垣相类似。
综上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 “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借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三
“五伦”说有别于专制主义政治伦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互动,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良性双向互动概括为:
父慈子孝 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 长惠幼顺 君仁臣忠
“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这一思路包含“互动”与“双向要求”的合理因素,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与救治,有助于我们今日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如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以构建和谐社会。
以政府与民众关系为例,片面的单向要求,或者是上对下的“专断”,或者是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陷入不和谐困境。
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必将激化劳资矛盾,劳方如果强索超越企业承受力的要求,均有损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以民族关系而论,大民族的沙文主义与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都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谐共存。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肯认,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社会主义的精义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义务问题上的良性双向互动观;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双向互动,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责任编辑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