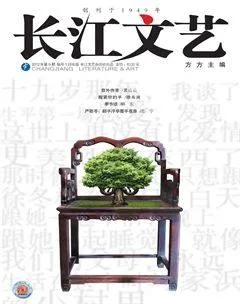辩证法与神秘主义
生活在公元前6~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不仅提出了“火本原说”和“逻各斯”理论,而且还被后世人们誉为“古代辩证法的奠基人”。素以思想晦涩而著称的黑格尔在谈到赫拉克利特时,称他为“晦涩的哲学家”,由此可见其哲学思想有多么晦涩!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之所以显得特别晦涩,主要是由于他那玄奥深邃的辩证法思想。辩证法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关注“背后的东西”的形而上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神秘主义的意韵。
当人们置身于现象世界时,往往很难觉察出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对于一般人来说,能于此物中看到他物,于静止中看到运动,于单一中看到繁多,无疑已经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了。倘若能够更加精进一步,竟至于超越此物与他物之差异,于运动变化中悟出■永恒,从纷繁芜杂中窥见单纯同一,那就更是一种大彻大悟的般若境界了。这种超凡脱俗的般若之识,对于凡夫俗子而言,无疑具有浓郁的神秘主义味道。因此,古代社会中那些具有深邃辩证思维的哲学家,往往会因其思想与大众常识相悖逆而命运乖张。他们不是出于愤世嫉俗而采取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就是由于触犯众怒而亡命他乡,甚至命丧黄泉。前者有如赫拉克利特,后者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师徒。
赫拉克利特是爱非斯城邦的王族,原本可以继承王位,极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却主动放弃王位,遁迹山林。赫氏为人狂放不羁,行为乖僻,平素喜爱与儿童掷骰子为戏,时常说出一些貌似谵妄的深刻箴言。他一方面表示,万物流变,无物常驻,存在之物就如同一条不停流动的河流,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另一方面又认为,纷繁变化之物实际上只是那永恒不变之“逻各斯”的诸多现象,对立之物的相克相生,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之间的相互转化,说到底不过是“同一的东西”罢了。因此,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这种见识才是永恒的智慧。赫拉克利特因为语言晦涩、思想深邃而被同时代的人们所不解,他自己也孤芳自赏地宣称,一个优秀的人抵得上一万个平凡之徒。赫拉克利特晚年因患水肿而去城里求医,他不说自己得了水肿病,而是用诡异的语言询问医生如何可以使洪水泛滥的河谷变得干涸。医生听不懂他的隐喻之言,因此这位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只能在神秘的晦涩中无助地死去。
其实早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就已经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表达了最初的辩证思想。他对其师泰勒斯提出的“水本原说”不甚满意,进而认识到一切有形之物都有其局限性。因为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该物,就在于它已经具有了某种规定性;而一旦当此物具有了某种规定性,它就不可能再是他物了。因此,像水(以及后来的气、火等)这样的有形或限定之物,是不足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本原的。阿那克西曼德不是用一物来取代另一物而作为万物的本原,而是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有限制的东西。针对一些有形有限之物,他提出了一种无形无限的东西,即“阿派朗”(απειρον,无限或无定形)来作为万物的本原。火固然不同于水,甚至与水截然对立,但是火与水都是有形有限之物。而“阿派朗”作为无形无限之物,则从根本上超越了水火之间的对立。在水、火、土、气等相互分殊甚至彼此对立的有形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相的本体,它超越了一切形式或规定性,因此,只有它才有资格成为宇宙万物的真正本原。这“阿派朗”就如同道家所言的“道”一样,它是说不清、道不明,恍兮惚兮、玄而又玄的“万物之始”或“万物之宗”。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大道无形”,表达的都是同一个道理。这无法言说的“阿派朗”或“道”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加以表述,即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却不能说它是什么。这个绝对的否定者,就是一切肯定之物(有形之物)的真正本原。两千多年以后出现的博大精深的黑格尔哲学,同样也是从这个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纯存在”(或者什么都没有的“纯有”)开始的。这个“纯存在”由于缺乏具体的内容或规定性,因此它实际上就等同于“非存在”或“无”。然而“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毕竟是一对直接对立的概念,而从“存在”到“非存在”或者从“有”到“无”的转化就意味着第三个概念的出现,这就是“变易”。因此,“有”(存在)、“无”(非存在)和“变易”就构成了黑格尔逻辑学最初的一个否定之否定三段式。
自从阿那克西曼德以后,西方许多具有深刻思辨倾向的思想家,都喜欢以一种否定方式来指称那至高无上的对象,如上帝等,从而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否定哲学或否定神学。公元2~3世纪著名神学家德尔图良认为,作为创世主的上帝具有无限的奥秘,这些奥秘绝非我们有限的理性所能窥透。他把我们的理智比喻为一个有限的器皿,而把上帝的奥秘比作汪洋大海,如果这个器皿无法盛下汪洋大海,那只能说明我们理性本身的可怜和渺小。20世纪捷克著名思想家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由此可见,我们的理性器皿只能盛下有限的经验事物,但是对于无限的终极实在(如上帝、宇宙本原等),就只能通过一种辩证的否定方式来加以表述了。
辩证法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然而对于沉溺于现象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所揭示的那个与现象世界相Fw95jpjMII+xSuNJhVLz4vWkpwOtf8bUnijQSQXSsjM=矛盾的本质世界乃是一个无法用感官来验证的神秘域界。因此,他们对于这个“背后的世界”的态度,或者是付诸于单纯的信仰,或者是斥之为无稽之谈。但是哲学家们却孜孜不倦地以探究本质世界为人生目的,锲而不舍地试图揭示出终极实在的奥秘。正因为如此,在古希腊社会中,那些哲学家、尤其是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往往都与流行的大众常识背道而驰。当希腊人对宙斯、波赛冬、阿波罗、雅典娜等奥林匹斯诸神顶礼膜拜、讴歌赞美时,一位游吟诗人式的哲学家克塞诺芬尼却公然声称,那些与人同形同性的■其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杜撰出来的一些傀儡,而唯一的真神则是那个不变不动、无形无相、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神”或“一”。克塞诺芬尼所说的具象的奥林匹斯诸神与抽象的“神”或“一”之间的对立,就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和万物与“逻各斯”之间的对立一样,都体现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一般民众注目于奥林匹斯诸神、注目于火和万物之间周而复始的流变,克塞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却把眼光投向了背后的“神”、“一”和“逻各斯”,并且试图用一种辩证的方式把相互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
像克塞诺芬尼、赫拉克利特这样与大众常识相悖逆的哲学家在古希腊社会中不胜枚举,他们都试图通过一种辩证的否定方式来揭示某种潜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理或奥秘。当希腊人尽情地享受着经验世界中的美好事物时,巴门德尼却把处于生灭流变过程中的感性之物说成是“非存在”,而把潜藏在现象背后的不变不动和独一无二的东西称为“存在”,这神秘的“存在”只有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当希腊人热衷于奥林匹亚竞技场上的身体竞逐时,柏拉图却对这种大众热爱的感性活动嗤之以鼻,认为有智慧的人应该在沉思冥想中来展现灵魂的力量,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展示肉体的力量。最具有吊诡性的是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提出的一系列诡辩命题(诡辩与辩证法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它们都指向神秘主义的幽深之域),如“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箭不动”、“谷粒的论证”等等,这位由于反抗僭主暴政而慷慨就义的伟岸英雄,却用这些诡辩命题从根本上颠覆了希腊民众关于运动和繁多的常识。
辩证法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性格之一,它植根于哲学思辨对于“背后的东西”或形上之物的探究冲动中,并且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神秘主义的深深烙印。从赫拉克利特等人那里发轫的古代辩证法,后来通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中介而与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相融汇,最终在近代形成了最具典型意义的黑格尔辩证法。
责任编辑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