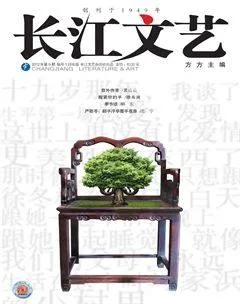严歌苓:翻手浮华覆手苍凉
没有一个人物是宁静的。在命运的漩涡中,在时代的磨砺中,在自身性格的撕扯中,严歌苓觅到人性中的复杂一面,然后赋予笔下的女人们——她并不在乎她们要承受多少坎坷的命运,或者只是在为一部击溃人心的作品而献身。
范宁,80后,武汉媒体文化记者。来自三湘四水,遍访文化名家,问道、修业、解惑,从文化的视角看世界,乐得其所。
美丽的女人在优雅地写作,笔底却是波澜万千心绪缠绵。
严歌苓完成了这样一个画面。她的作品往往如此,收纳琐碎的生活,然后用一种精雕细刻的语气,平静地叙述出来。新作《补玉山居》就是这样。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严歌苓陆续拿出三部小说,《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和《补玉山居》,令人惊叹其创作力。
没有一个人物是宁静的。在命运的漩涡中,在时代的磨砺中,在自身性格的撕扯中,严歌苓觅到人性中的复杂一面,然后赋予笔下的女人们——她并不在乎她们要承受多少坎坷的命运,或者只是在为一部击溃人心的作品而献身。
那些脆弱的灵魂,被她捏在手心里,不动声色地亮出来。初见时满目繁华,细腻温婉,乍然,银瓶竟破,碎光一地,弹起若许尖叫,紧接着是怒放后的苍凉。她笔下每一个女子似乎都要走这一遭,浮光掠过,走进暗影,化成跌宕的传奇。
严歌苓的手,在纸上字间翻覆。而她自己,却实践一种悦目的生活。她是少见的有自带摄影师的作家,她在家里喜欢摆上烛光和鲜花。也许在严歌苓那里,命运,并不等于生活。
一
了解严歌苓,可以从她的作品开始。不过就像所有具有个性的作家一样,一部作品,只是严歌苓的一个侧面。你读《少女小渔》的隐忍,不会明白《扶桑》的平和;你读《小姨多鹤》的认真,未必知道《金陵十三钗》的风流。
不过你可以知道她们的一个共性,那就是“女人”。严歌苓的笔下,极少有男性角色超过女性的光芒。那些风韵各具的女人们,或如一曲苏州评弹,或如一声京韵大鼓,或如一段咿呀昆腔,但总归是纠结而美丽的——酷爱纠结与美丽,大概是女性作家欲罢不能的热望,尽管严歌苓并不喜欢被称为“女作家”,更不喜欢被称为“海外华人女作家”。
范宁(以下简称9F0a7UcUiuXbd1rZn3y5C0stuyxdM9ZE8/CyIIPBYEM=“范”):似乎没有女作家愿意自己被局限在“女性作家”这样一个标签里,您也不例外。但是您笔下的女性的确光芒耀眼、个性斐然。这与您自身有关吗?或者说是一种创作的偏好?
严歌苓(以下简称“严”):岂只是我爱写女性!不说国外的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家,光看国内当代的男作家,包括苏童、莫言、毕飞宇等等,他们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难忘。尤其是苏童。其实我写过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比方我的中篇小说《倒淌河》、《拉斯维加斯的谜语》、英语小说《赴宴者》等等。但是因为自己是女人,写女人对于我更加自然。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诉我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有写不尽的题材。我觉得有趣的是:女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女人,而不是男性。这样我得到有关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过我冷不防就会写一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也说不定呢。
我并不是有意只写女性,也不是说你们都说我是女性作家。写男性、写女性对我来说一样,只是相对来讲,我更喜欢写女性,因为女性在社会里较为边缘,较为边缘的人物身上一定有变数,变数大就容易产生戏剧性,而且女性的一生往往是以情感为主,小说、文学,都是情感越丰富的人越好作为主人公,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这么厚一本书写的就是女性的情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原因。
范:小说《扶桑》里,扶桑让所有男人心生怜悯。克里斯一直都有要拯救扶桑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看上去那么幼稚。她不需要拯救,您小说中的女性都看上去很柔弱,但其实具有女性特有的那种坚韧。您一直在着力表现这个?
严:扶桑的生命很强大,能以那样的平常心来对待仇恨、苦难,使得所有要解救她、给她自由的人都显得那么可笑。扶桑身上沉积着世世代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悲悯。这和我的家世也有点关系。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父亲,或因为战争,或因为疾病、内在的心理状态,早早过世。这两个家都是由女性支撑起来的。靠的是从容和想得开,靠女子胸中无大事的平常心,一直过渡到孩子们都成人。所以我对我的外婆和奶奶很崇拜。
范:《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女人多鹤,大概可以算您一系列与历史和时代有关的小说的代表。潜回时光深处,您如何去还原那样一个时代?对于这样一位异国女性,您又如何解读?
严:在写《小姨多鹤》之前,我还有点畏惧。当时我们那儿有个日本的女制片人,我想不如就以她为原型吧,因为她就是那种地道的日本人。但是真的写,我从她身上找不到感觉。后来去日本,在我住的那家民宿里,70多岁的老板娘给我很大的启发。她是那种传统的日本女人,每天忙于家务,有客人来就深深鞠躬,现在很难找到那种宁静了。
范:《金陵十三钗》写南京大屠杀,您把最孱弱的年轻的女孩子与那个最残酷的、时刻游走着死神的城市并置在一起,让她们的人性从普通到升华。这是您笔下的大屠杀故事。那么十三钗代表了您心目中怎样的女性形象?
严:美丽的、坚忍而娇媚、拥有宽广的情怀,这是我心目中的女性。在《金陵十三钗》中,我写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妓女人物,她们代表了那13个。
二
严歌苓站在历史的前面。
和许多年轻的作家不一样的是,尽管笔下笔墨最重的是女性,但严歌苓并没有让作品失于小情调或小情怀,家国天下这样的主题,人性复杂这样的剖析,依然出现在她的字里行间。
范:《少女小渔》里面的移民主题有点沉重,您也写了一大批移民的故事。
严: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一个留学生,但是真正的故事比这个更加阴暗邪恶。移民是一次战争,非常悲壮,一切既成的道德准则都要受到考验,生命在移植的时候,在存亡大前提下,很多东西都应该重新审度。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发生故事,爱情的,仇恨的,一夜间暴富的,一夜间破产的……所以我写了一大批移民的故事。
范:《金陵十三钗》从历史的细处切入,却往往触碰到历史最疼痛的部位,这似乎是您作品的风格。这本书里藏着怎样的战争和历史的寓言?
严:《金陵十三钗》中的“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预示着主人公、南京城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战争会把一种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一些人会去当叛徒汉奸,一些人突然变成了烈士。也就是说在每个人内心里,你的善恶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直到最后一个极端事件发生了,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人,这是我想通过《金陵十三钗》这样一个讲述战争的故事来表达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各种人物完成了他们人格的成长、转变,最后达到升华。
范:您之前提到过,会有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长篇?
严:是的,叫《无期》,是我从去年写到今年大概花的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作品,一共30多万字。它是写一个男主人公的,而且是用电脑写的,这是我的两个突破。
用电脑写作非常累,它要求集中双重精力,不如我拿铅笔更“绿色”。所以这部作品我写得很吃力,但回头一看,还是为它骄傲。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家里的小小的事情不顺利,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的、人性的,这样想马上就好了。还是让大家看吧,我也不能说我喜欢的就是你们喜欢的。
范:《补玉山居》出版后,依然是一位老板娘当主角,我们期待的严氏男性角色千呼万唤不出来,缘何?
严:其实这个小说写了有好几年了,大概是2009年左右吧,一次朋友带我去京郊平谷的一个农家院,就是这个山居,当时的老板娘身上就有曾补玉的影子,也就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这部作品。我个人的写作习惯是写完之后都会把稿子放一段时间,因为心底里总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自信,所以还要沉淀一下,直到编辑催得厉害了,才会拿出来出版。我想出一个史诗性的、长的、当代的作品,就是所谓的我眼中的中国吧。不断地对中国熟悉起来,但是我记忆当中的中国也必须要写,因为我有这么一种愿望,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出版节奏和策略。
范: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了当下的现实社会?
严:我常年生活在国外,始终是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在国外,我是使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不是主流的写作;而在中国我的故乡,我又是一个旅居国外的人,我也是一个边缘人的身份。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会用自己的时间去书写我记忆中的中国,同时,因为我每年都会有几次回国的机会,也就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审视当下的中国社会。我很庆幸,我是一个使用中文这种占全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在使用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我的作品也可以被这么多读者阅读。我关注着当下飞速转型的中国,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我无法理解和明白。
范:纷纭世相,您用一个小店老板娘的视角串起来,补玉山居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补玉这个人物,您赋予怎样的内涵?
严:我当时就是对山居的老板娘印象很深刻,觉得她身上的个性和形象都很有文学价值。后来就觉得这个形象始终忘不了,萦绕脑海中,所以我又一次回去那个农家乐找到她,在她那住了一阵子。她还笑说:“您要写小说一定得把我名字写上。”但是我告诉她,因为是文学创作,所以不能用真名字。山居里的人物都是想象的。在曾补玉的身上,体现的比较突出的性格就是她的乾纲独断,她有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所以,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义”的成分在里面。
范:现在社会上有种观点叫做“男人没了”,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您心目中的男性应该是怎样的?
严: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我心目中的男性,最起码外表应该具有男性应有的特质和气质,应该有责任心,有担当。
三
与严歌苓聊生活和时尚,是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在这个领域,作家小女人的一面流露出来,像她在家里点亮的星星烛火。
创作是严歌苓每天必须做的事情,生命有新陈代谢,脑子和精神也是如此。她如果不写,就会扰乱新陈代谢的节奏。这是她高产的原因所在。但写作之余,她也在经营自己的年华,“非作家”的严歌苓,是“严歌苓”本身。这种感觉挺好。
范:今天社会有一系列女性被消费的形象,凤姐、干露露、范冰冰、“宝马女”马诺,您认为这些女性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严:非常抱歉,你说的这几个人我不太了解,没听说过。但是,对于目前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可理解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幸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物欲的过分追求,你不要把邻居的幸福强加到自己身上,人家买了一个大电视,我也必须要有,否则我就是不幸福。尤其是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是很痛苦的。但是,对物质的这种追求,我觉得可能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的一个原因,就是太爱物质了,这是它的一个生命力的动力,但得不到的时候就是不幸福。
范:您曾经有段言论关于女人应该保持美丽,让丈夫感到魅力和快乐,后来被洪晃调侃,您觉得自己是否说错了?如何看待洪晃的调侃?
严:我承认我是很爱漂亮的,也有一点小资。即便是老公,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狼狈或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每天在外面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你总得让他回来赏心悦目吧?这样他的心情也会轻松愉快,我也得到快乐。
点点蜡烛、放放音乐、摆摆鲜花,这些事情很有仪式感,我们一家都很在乎。在我们家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桌上摆好四菜一汤,把电视机关上,放上一些优美的音乐,愉快地进餐。
范:我很喜欢您拍的写真。那不是一个作家的写真,那不是海明威也不是福克纳,那是令人喜欢的漂亮写真。
严:我不追求什么品牌和名牌。有时我到朋友家,他们说你穿的真漂亮,我说我做猪八戒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我从来没去过美容院,你看我头发,白的,一直没去染过。我也没敷过面膜,出席活动时人家送给我很多面膜,我发现用了没用也没什么大的区别,就送人了。我觉得吃蔬菜、多喝水最好。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刻意的,到要被采访、要被拍照了,就匆匆化一个妆。
范:您好像是很少见的自带摄影师的作家,为什么要带个摄影师?您对女性的美是如何定义的?
严:我的两位摄影师是两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我觉得读书的女性很美,读书可以让女人变得优雅。
四
严歌苓手中的“翻与覆”,还可以用在小说和剧本上。担任几部大戏的编剧,让严歌苓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声名迅起。但严歌苓对自己改编的作品缺少自信,她几乎从不看自己改编的作品,在这个领域,她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
范: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后争议也不少,您如何评价这部电影?和您的原作相比,还原度有多高?
严:《金陵十三钗》的剧本和原著小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影视改编权转让给了张艺谋导演,所以,我的小说中就不能够再出现相同的情节,为了剧情的需要,电影剧本中对于人物的设置和剧情都进行了很大的改动,所以,我的小说和电影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目前为止《金陵十三钗》是我非常喜欢的自己作品改编的电影之一。因为在与张导合作的过程中,经常会碰撞出一些新的灵感火花,从很视觉的方面来表达故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张艺谋导演是非常棒的,与他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范:您这几年另一部重要的编剧作品是《梅兰芳》。有观众认为它是半部好片,后半部分没有前面那么灵气十足,您怎么看?
严:陈凯歌导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在与他交谈合作的时候可以将自己调动起非常大的工作热情,他是一个非常懂戏的人,在电影方面陈凯歌导演也算是我的一位电影导师。
《梅兰芳》的第一稿我是在美国写的,把稿子带回来给陈凯歌看时,他说让我重写,一共改了7遍才最终定稿,在我们不断的沟通中,梅兰芳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逐渐明朗,我们心里的梅兰芳终于达成了一致。
电影在后期制作中有一些内容被剪掉了,可能后半截观众看起来觉得会有一些比较突兀的地方。
范:作家和编剧的身份,您有时会不会自己混淆?
严:我非常爱文学,也爱电影,好的文学不一定是好的电影的基础,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纯粹为文学写的作品。但还有一半的严歌苓是非常爱电影的,那一半就专门为电影来写。我希望这两件事别混在一起,否则常常要造成巨大的妥协。
我不是圣贤。电影电视给你造成这样大的收益,这样大的影响,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写能够被他们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东西。这是下意识里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主动想写一个东西让他们拍电影。我现在要对自己说:“你写的东西你们绝对不能再拍电影了。”写作之外,我可以专门写电影电视剧,这两件事情我再不混在一起做了。
范:中国的文学佳作不少,但是影视剧往往粗制滥造,您觉得当前影视剧的软肋在什么地方?
严: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如何能把故事讲好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以来都把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严格区分开,我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
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
所以我会很警惕,将来在潜意识里就掐灭那些为电影而作的念头。
责任编辑 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