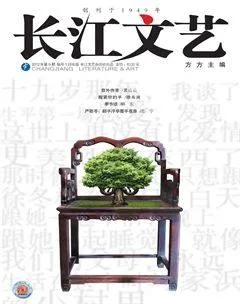春三月(组诗)
桃花源
山路弯弯,流水潺潺。还有十万桃花
一园方竹,叶薄而繁茂,构成了
桃花源。这还不够。推开一片白云
亮出一片宽阔的庭院,几间平房
一头牛,一群鸡,两只白鹅,一条
黑狗,外加一个荷锄的农夫,构成了
桃花源。这还不够。一条古老而
清幽的石径,十几座小石桥,一缕
炊烟,半亩荷塘,还有一条桃花溪
前朝风月,皎洁得一尘不染
构成了桃花源。这还不够。黄昏下
夕阳边。山语、树话、鸟叫、虫鸣
风在草尖上,让谁扶了一把
桃花种在诗里,没有流出一滴血
诗人穷成一只饥饿的空碗,坐着一辆
牛拉的破车,偏写出了《桃花源记》
草民
草民,草一样的人民
比一棵草更卑微更弱小的人民
燕麦草、狗尾草、苜蓿草、三棱草
稗草、稻草、芦苇草、马齿苋草
鱼腥草、鬼针草、伤心草、苦难草
你属于哪一类,哪一株
最接近枯黄的那一株是你么
最倒霉被冰雪压倒又被牛蹄子
踩进泥泞中的那一株是你么
草民,草一样无声无息的贫苦
的农民。在小小村庄的灯盏下住着
依附于一株草或一些草
而活着。住草房,穿草鞋,戴草帽
种草、薅草、捆草、挑草
用稻草搓草绳,给猪割草,给牛喂草
给羊圈添草,给床铺铺草,往
灶膛里填进去许多或干或湿的柴草
风吹草低。他被风吹向更低处
低于半亩禾田。山坳里的草屋
风轻轻地就掀开了一扇门扉
泥巴筑的墙,麦草盖的房顶
他的家像在麦壳里躺着。两个还
很小的儿子,坐在门口
大碗里装的红薯、土豆
或许是在催着他的儿子迅速地成长
一年前他的老婆得病死了
盖房子的钱买了他老婆的棺材
村子里的人都搬了。他还是
住着这间草屋。我见到他时
他正在后山的那片斜坡上
孤零零地弯腰刨地。秋天刚过
菜地里的辣椒秆子,被砍掉了
改种白菜。他带着两个儿子
要在冬季里慢慢完成他们的生活
流水
江南是水做的,水做的江南,到处是流水
一万年前的水,一万年后的水
都朝着一个方向流淌
水从深山流来,从峡谷流来
从云端和高山流水的源头流来
那年,我与黑八爷上山采药,无意中
我追着一条小溪一路跑到山下
水顺着小溪,哪里低就往哪里流
从山谷一直流到低处的民间
把村庄一口快要干涸的池塘填满后
继续向前流淌,流经陈艾草的半亩蚕豆地
经过一座榨油坊的旧址时突然
拐了一道弯,然后继续拐弯
拐过油菜田和几家穷人的后院
沿途无意中收养了几朵野花
和秋天的最后一场秋雨
流到村前堆成一条两尺深的小河
一些水被木桶或水罐取走
一些被农民抽去浇地,一些以平缓的姿势
慢慢流淌。它们去远行又像回家
江汉平原
往前走,江汉平原在我眼里不断拓宽、放大
过了汉阳,前面是仙桃、潜江,平原就更大了
那些升起在平原上空的炊烟多么高,多么美
炊烟的下面埋着足够的火焰
火光照亮烧饭的母亲,也照亮劳作的父亲
八月,风吹平原阔。平原上一望无涯的
棉花地,白茫茫一片,像某年的一场大雪
棉花秆挺立了一个夏天,叶片经太阳
曝晒,有些卷曲。平原人隐藏在下午四点
的棉花地里,露出来的几顶草帽
像路边几间平房的黑窗户。我顺着
一条小河来,逐水、追鱼,像携带流水
黄昏,夕阳如水中游走的活物,游到
七孔桥拐半道弯就消失了。这时候
远处村庄里,点起了豆油灯,大平原变得
越来越小,小到只有一盏油灯那么大
豆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我感觉黑夜里的江汉平原也在轻轻摇晃
铜草花
铜草花,看起来像草
其实就是
一种没有叶子的小花
我的家乡到处生长着这种小花
她在春天悄悄长出
一枝嫩芽,悄悄开遍
荒野和山坡
看见几棵铜草花顺风长高
我就知道,这下面有铜
铜草花是青铜的嘴巴、舌头
和牙齿
告诉世人地底的秘密
扒开土层,就是一层一层
美丽丰饶的铜矿石
那一年,我在隔壁的山上放牛
看见一辆一辆拉矿的大卡车
络绎不绝经过我的村庄
我的一位在鄂钢上班的姨父
告诉我,铜矿石经过冶炼
吐掉杂质
黄亮亮的,那就是铜
然后,我们把一个民族的精魂
植入青铜的体内,打磨光滑
从此,铜就有了精神、光芒
就有了语言、韵律
做成铜锣或小号,敲或者吹
任何时候都有一种震撼人的力量
芦苇荡
走近洪川湖就能听见野鸭的叫声
芦苇在一湾荡漾的湖水里渐渐泛白
水底闪动着一丛丛芦穗的影子
芦苇花像羽毛一样,在天上飞
去芦苇荡,水是唯一的道路
乘船而入,踏浪而行。人坐在
小木船上,像坐在波涛上
水流岸不流。波浪在我眼里
吹开了一层又一层。船拐着
弯儿走,好好的湖,却分了
那么多岔,看过山路十八弯
在这里又让我看到了水路十八折
两岸的芦苇,长得多像我乡下
的穷亲戚,和患难的亲兄弟
弱小而细腰的身子经不住风吹
风吹一下,就颤栗一下,弯曲一下
长在湖心岛上的一丛芦苇只有
补丁大小的祖国。世界早遗忘它了
岛上的一棵光秃秃的树枝
挂着夕阳,像勉强挂着国旗
春三月
三月。吹进村庄的风
刨开了南面山坡上
渐渐裸露的两片麦地
三月。燕子要到咱家房梁上做窠
梧桐树宽大的叶子
经常掉在咱家凉台上
三月。奶奶一边扫院子,一边
把半碗糖球
倒进我们兄弟的口袋
三月。草丛里的几朵野花
开得有些可怜
只有一小点春风吹着它们
三月。大人们去西山岭开荒
深深的地下
掘出地瓜和传说
三月。山坡上一条长长的树枝
长出了绿叶,树枝经过
一个冬天,有些弯曲
看见桃花
我知道这是今年开的
去年的桃花都谢了
葡萄架下
满院子都是葡萄的味道
葡萄架悬在头顶,细密而
嫩绿的藤叶爬在木头上
下面放着一张桌子四条矮凳
我习惯在这里打坐,由于它的
高悬,我也习惯了向上仰望
四野的谷子黄了葡萄就熟了
葡萄从藤叶的缝隙间挂下来
我爱她们的羞怯和含蓄
一颗葡萄是我最小的故乡
我用指尖丈量她
抚摸她完整的血脉和皮肤
下午
村旁拐弯处的那条小河
像70年代一样流淌
奶奶和四婆
下午一直站在河堤说话
爷爷下午顺着河湾去了一趟
老木的铁匠铺
他想给家里打一把好镰
爷爷亲眼目睹了老木如何将一块
不成形的废铁慢慢打薄
打成镰刀
下午,父亲把窑边的地犁了
秋后种油茶还是桑麻,他在犹豫
回到院里,母亲正拍着
旧棉絮上的灰尘。一个下午
她把家里翻晒个遍
薄薄一层阳光
母亲要在深夜
裁剪成我们兄弟过冬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