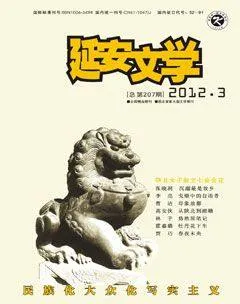陕北太阳
在我心里,陕北有三个太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在人间。
天上的最是火热,每天都是明亮的。这里的父老乡亲都是夸父,从早到晚,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身体到灵魂,都在追赶那个太阳。
因为追赶,皮肤被太阳伤得又红又黑;因为追赶,一身都是阳光。
所以男人都那么阳刚,女人都那么明媚。
这个被古人称之为“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以天为神,以地为道,以太阳为心。
陕北在地球的东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陕北人首次把一个伟大的人物比喻为太阳。
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陕北文化使然。
陕北文化是民间的,自然的,却又是独立的。儒、道、释,伊斯兰,耶酥基督,都没有能深入她的骨髓。
她是火的文化,是革命的天然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有别于中国核心文化的特点;她有游牧文化的风韵,但又区别于游牧文化,可也绝不是游牧文化和黄土地文化的简单叠加。她的实质由陕北长期的苦难和封闭所造成,是天地之间一块金灿灿的炼狱文化,是我所谓的第二个太阳。
土生土长的李自成风风火火没几年便打到长安,建立大顺国,把大量的陕北人带进这座帝王之城,继而又打进北京。毛泽东带领仅剩数千人的中央红军在陕北待了十三年,便把红军扩充到几百万,硬是打出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建国初期,不仅西安,全国各级政治中心都有陕北人。这是陕北人第二次飞黄腾达的时代。
现在是陕北人涌进西安及至全国各大城市的第三个时代,这全是因为陕北又掏出了一个太阳,它就是地下的煤。
因为煤炭,陕北已经成为陕西经济的引擎。陕西十强县中有七个都在陕北。
但陕北看上去依然是荒凉的,尤其在从飞机上俯瞰,更为明显。
但只要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荒凉只是给了它一个坚硬的、布满曲折纹路的外壳,像一颗巨大的核桃。敲开这个壳,一个繁荣、智慧、热烈得像火焰般的陕北便出现了。厚重的煤炭,浓得化不开的石油,红红的剪纸,热烈的腰鼓,飞扬的二踢脚,和那一声声回肠荡气的《东方红》,一曲曲令人闻之断肠的情歌,无不在熊熊燃烧。
“叫一声哥哥揣一揣我,浑身烧成一堆火。”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
陕北是燃烧的陕北。
陕北的阳光资源应是世界之最,它的严寒只是另一种燃烧。一年四季的老黄风也只是燃烧的另一种形态,是金色的焰火。看看著名摄影家陈宝生镜头里的马,一匹奔马分明就是一条火龙,一群奔马就是火山爆发,或者说就是一场沙尘暴,势足以翻天覆地,摧枯拉朽。这就是陕北。
陕北没有宗教,但陕北人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怀,做事跟爱恨情仇一样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一位没有念过一天书的老人,用她一双满是老茧的手和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了一幅幅复杂怪异寓意深刻得匪夷所思的剪纸,一个百年孤独、千年孤独的陕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独特的艺术创造和她简单的生活图景、质朴的外貌、笨拙木讷的语言形成巨大的反差。
陕北少雨,冬季又长,土地大部分时间闲置,缺乏生机,但却把它的子民引到了反躬自问沉思默想的旅途。看起来跟山一样坦然、厚重、蕴藉的陕北人,外在的劳作既少,生命力便向内转化,文化的、艺术的创造便藉此发端。
陕北文化之大概,就是在一群相信天命默默无闻的人手里造成的。他们的创造往往不是出于自觉的使命和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恰恰相反,他们的创造发端于生活的无奈和苦闷,发端于无情的天、吝啬的地对他们的逼迫。他们把反抗的欲望转化为文化艺术的创造。
路遥把生命交给文学这项神圣事业的那一刻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了陕北大地的书写者。《人生》是陕北人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首先是陕北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是陕北式的思索。
他的创作生命表现为一种燃烧状态,他的血变成了燃料。他用生命换取文学,把自己变成了陕北人心目中的一颗恒星,一颗太阳。
在他死后二十年,人们依然在阅读他的作品,在谈论他的人格形象,尤其在大学生中间,影响力持久不衰。
陕北不再是贫穷落后的象征。
陕北人的脸上不是仅有皱纹,而是布满阳光。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