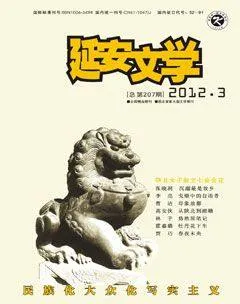失落的传统:诗歌的民间叙事资源
信天游在中国诗坛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六十多年前,当李季的长篇信天游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顿时给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现代诗坛带来了非同一般的震动,被郭沫若称赞为“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
信天游,一种艺术的呐喊……
一、失落的传统
几十年来,陕北的信天游一直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信天游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形态,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并参与新生活的建设,则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霍竹山的信天游体长篇叙事诗《金鸡沙》的出现,可谓是信天游在当代社会的转型之作。
当前的诗歌发展被许多评论家甚至诗人自己认为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对此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辉煌业已丧失,诗歌不断走向小众化,成为各种文学体裁中相对边缘的文体。诗人这个身份也由一个崇高的精神象征转向了病态的嘲讽。这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无疑是诗歌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断裂。当前,我们的许多诗歌过于追求叙事形式、技巧和策略,或者迷恋于词语的玄妙组合和空间的架构,或者片面走向白话和口水诗,往往忽略了叙事的内容,失却了诗歌所应该具有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审美性结构与意义,变得不知所云,难以卒读,甚至走向庸俗、粗俗不堪的境地。
其实,诗歌永远无法脱离生活,尤其是民间生活。自《诗经》以来,无论是创作技法,还是创作理念,我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一直都有一种“民歌传统”。《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的“风”就是主要收集了全国各地的民歌,《诗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汉代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采诗机构——乐府,主要用来采集民间的诗歌。唐诗成为唐代社会交往唱和的重要内容,白居易为了让老百姓能看懂他的诗歌,每完成一首就读给“老妪”听。宋朝更是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可见宋词在民间的流行。虽然今天我们阅读唐诗宋词稍有难度,其实它们就是当时社会的流行歌曲。元代的话本则是勾栏酒肆说书人的讲稿;明清小说很多都是在元代的话本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从文学的历史演变来看,一直就有一条民歌的传统和民间叙事的资源。然而,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这一原本根植于民间、有着良好民歌传统的文学体裁,逐渐走出了民间,走向了四顾无人的“高处”,脱离了生活的土壤。
当我们一再喊叫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候,民间和传统迅速从我们的文本中滑落。霍竹山的《金鸡沙》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信天游是陕北重要的民间文学形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则是信天游这一民间文学形式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关于“三边”这一地理文化变迁的文学样本。与诸如山歌、二人转等民间文艺形式相比,曾经非常红火的信天游的能见度如今显得相对较低了,并不像广西山歌、东北二人转那样逐渐成为大众传媒役使的工具。信天游是一种真正贴近生活、自在性的文学样态,是陕北群体生活的重要拟像性文本。今天,从民间文学到失落的传统,从全球化到地方化,“民间”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词语,“民间”也成为文学重新发明的资源,从而使得一个传统的、内在的、认知的、经典的民间越来越受到各种文化形态的关注。《金鸡沙》正为我们昭示了诗歌失落的传统和丰厚的民间资源。有人说:“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如果现在不赶快地去搜寻,再等些年以后,恐怕一首两首都是很难的了。”因此,《金鸡沙》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掘了失落的传统和民间资源,而且还提醒着每一个写作者:当越来越多的诗人逐渐丢失传统、溢出生活经验的圈子时,诗歌的写作应该指向当下的生活和我们的经验。
二、共同体的建构
《金鸡沙》既葆有了信天游的吟咏模式,也开拓了民间资源的文化内涵,烙上了深深的地域性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三边”和“改革开放”的新鲜文本。回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金鸡沙,变化翻天覆地、有目共睹——从砖瓦土坯房的村庄到小楼林立的新农村、从乡村土路到康庄大道、从沙漠到绿洲、从抱着土地“老家底”不放到自觉外出务工、从外出务工到回乡致富……《金鸡沙》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城乡不断走向融合、生活不断走向富裕的乡村图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乡村视野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从而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乡村共同体的生成模式。
“金鸡沙背靠毛乌素,/庄稼人吃尽了风沙的苦。”改革开放前的金鸡沙因为背靠毛乌素沙漠,每个家庭都靠天吃饭,这使得村庄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庆幸的是,包产到户政策的出台,金鸡沙人说“我们又解放了!”于是,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出现了分地、包产到户的高潮,金鸡沙人甚至分了屈家油坊:“一颗西瓜切了八十一牙,/屈家油坊分起来真利洒!”这是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体化社会的解构,是乡村传统的失落和分化:“分开了土地分散了心,/人人好像害了场病!”如果说分地导致的人心走向分散是一种内在的村庄结构的重组,那么,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冲击则成为乡村变化的另一种力量。“改革开放观念变,/打工闯天下很普遍!//再没什么盲流和游民,/随身只带一个身份证。”改革开放前,“外界”对于这个世界并不重要,因为每个家庭都是封闭的,他们对于外界(城市、他者)基本上是陌生的。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从空间和制度上打破了城市和乡村的阻隔,一群先行者在资本的幻像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塑:“燕娃子离窝翅膀硬,/‘兰花花’服装出了名。//有米不怕蒸不成糕,/服装厂效益真是好!//华成娃深圳当了老板,/金鸡沙传得沸反盈天。”诚然,通过村庄和集镇的交往,乡村面貌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乡村草屋变成瓦房,村民的生活也丰富起来,乡间屋舍旁多了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等“现代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村庄的深层结构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秩序和权力结构悄然发生了“革命”:“屈平王镇长成天醉,/好得一个鼻孔孔出气哩!//马拉套绳驴驾辕,/两个合伙买钻杆。//天上没月亮星星明,/拿到‘井灌’屈平笑出了声://‘天底下就数当官好,/一本万利的生财道。’”这种乡村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正是改革开放对于一个村庄所引发的现代性焦虑。
无疑,在这个热切向往“现代化”的乡村“新世界”里,村民的地位、身份和权力正被重新划分和塑造。而这一切变化,无论是从积极层面,还是从消极层面,都应该归因于“改革开放”,因为正是“改革开放”,让这个封闭静止的乡村与城镇有了交流,让一些农民走出了土地和家乡。但是,这种变化和冲击,导致乡村权力结构、传统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在乡村发展内部,急切需要一个乡村共同体。霍竹山用信天游建构了一个“共同体”——“三边”——的形成过程。可以说,他的《金鸡沙》是一个村庄变迁的民族志书写。这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深入民间的重要意义。霍竹山正是用信天游书写着陕北地域人群的生存状态,不是简单地用生活衡量人物的内心深度,而是用人物内心的最隐秘的情感来衡量个性的心灵变迁,从而形成信天游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的迷人深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潜隐着的生命力的激情的召唤。
虽然民间发展的动力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有意思的是,霍竹山对这个乡村共同体的建构却始终围绕着“华成娃与屈彩英的爱情”。从他们的父母不同意,到“屈彩英跟华成娃私奔了”,到“书记挨个儿打电话,/深圳请回来华成娃”,再到“丈母娘疼女婿疼在心,/‘我们成娃又能干来又年轻’”。从中可以看出,屈彩英与华成娃的婚事成为乡村共同体的叙事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叙事方式。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卫风·氓》)到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红豆》)再到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以及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民间的爱情其实一直成为文本叙事的一种动力和隐喻,它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而暗示了文本的意义指向,推动了文本的发展。霍竹山也借助屈彩英与华成娃的婚事推动着《金鸡沙》的叙事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以爱情叙事缓解语言的紧张,增强叙事的快感,并以此获得普通群众的认同。
三、民间的活力
1946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立即受到热烈的称赞,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项丰硕成果。从《金鸡沙》的题记里可以看出《王贵与李香香》对霍竹山产生的影响之大,甚至在《金鸡沙》里,我们仍然能够读出一些《王贵与李香香》的影子。《金鸡沙》无疑也借鉴了《王贵与李香香》这篇优秀诗歌的叙事模式和方法,但是,《金鸡沙》在反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比《王贵与李香香》更为深刻。《金鸡沙》全景式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金鸡沙”面貌的发展变迁,虽然采用了屈彩英与华成娃的爱情作为叙事的线索,但是,更多地反映的还是一个乡村在改革开放的各种风潮中的世态人心。因此,霍竹山的这篇叙事长诗不能简单取名为“屈彩英与华成娃”。
与《王贵与李香香》相比,《金鸡沙》写得更为细节化、充满韵动感,作品的描写避开了《王贵与李香香》的脸谱化色彩,从人物内心的深层次上表现了金鸡沙人民面对改革开放后各种社会问题时的“小农心态”。对村民算盘拨得贼精的心理描写和深度剖析,是霍竹山的《金鸡沙》更进一步的地方。他写分屈家油坊:“红头山羊分给两家,/赵大炮分了一包旧棉花。//没打的庄稼分捆捆,/一片树林分了七十二份。”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对公共财产的分割,霍竹山也用力地刻画了人物内心的那些小九九:“土地牲畜编成个号,/一家一户按人打分。//屈平婆姨正肚子大,/一道庄跑遍还没生下。//彩英爷爷只剩一口气,/打针输液也要等分了地。”这样的描写将人物的小心眼小算盘写得尤为出色。当屈家油坊分完后,各人又对自己分的东西不满意,以及出现的邻里间的冲突和摩擦:“麻雀雀飞进了鸽子窝,/就数屈家油坊怪事儿多。//他说你占了一铧地,/你告他家把树林毁。//一疙瘩云彩风刮开,/断官司忙坏支书李有才……赵大炮哭‘一包旧棉花’,/‘当时你眼窝又没瞎!’//‘只想娃娃穿暖和,/没想老婆不依我。’”可以看出,霍竹山对乡村人物的观察是极为精到的,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极为传神和准确。因此,我认为,信天游的重要优势不仅仅是适合传唱和生活化,更在于对身边人事绘声绘色的描绘,对人物行为与内心的深度观照。
霍竹山的《金鸡沙》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本是“信天游”的特点。作品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吸收,在具体运用上,也呈现活泼多姿的状态,充分体现了这种信天游独特的的艺术魅力。如“老黄风刮起满天沙,/两个生产队从此把仇结下”、“沙枣涩来油枣甜,/就怕咱二人没有缘”、“上河里发水下河里浑,/有了几个糟籽儿发官瘾”、“随水的莲花迎风的柳,/跑旱船的妹妹实在柔”等,都充分体现了民歌的比兴传统,这个传统更深的源头在《诗经》。其实,《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叙事资源。这就是民间的力量和传统。不过,我更关注的是,霍竹山的《金鸡沙》所呈现出的陕北民间的语言智慧与幽默。虽然这些语言由霍竹山形成了文字,但我相信,这些语言一定是霍竹山亲自跑到田间地头收集来的,来自于活生生的民间生活。比如他写屈家油坊对霍窑乌素的不满,李有才进行说服工作时说:“‘怎不说江南分上二亩稻?/怎不说延安还有你们一孔窑?//怎不说西安分一台犍地机!/怎不说天安门还有三分地!’//打锣听音说话听声,/李有才把众人口塞定。”这样的一些充满机智与幽默的话语,让我们感到民间的语言魅力。再如:“瓢葫芦舀水沉不了底,/怎尽想走路拾金子?”“马瘦毛长尻子深,/谁娘胎里就是享福的命!”“搐鼻子骡子漾尾巴,/浑身尽毛病还说怪话”“玉米芯子装枕头,/气死你这个‘活不够’”“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旧社会的税费数不清”“利益面前人心偏,/公道不过拈蛋蛋”“霍窑乌素人还用娶婆姨?/枕上个馍馍搂水地”……这样的句子数不胜数。这些都说明作者对于这种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的熟悉程度,善于从中吸取营养,致使作品的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的特点,成为真正艺术化了的诗歌语言。这就是诗歌优质的民间资源。有谚云:“信天游就是没梁的斗,甚会儿想唱甚会儿有”,信天游的这种普及性和随意性让我们由衷感叹:诗歌真正来自于民间。而“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则更说明了信天游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乃至生命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写《金鸡沙》的霍竹山不但是一位诗人,而且已是一位民间文化的吟游者。这才是一个诗人在民间资源的藻井里应该有的文化自觉。
霍竹山的《金鸡沙》在立足民间的基础上,在文学性的开拓上比传统的信天游更进一步。毕竟,早期的信天游几乎完全是乡土性的,传唱者或作者的文化知识相对较低。霍竹山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他的写作当然就带着知识分子色彩。他在充分尊重民间基调的同时,也提升了信天游的“文化含量”。这种文化的提升也是今天这个文化膨胀的时代民间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霍竹山的《金鸡沙》对于文学性的把握既有民间的趣味,也有自己独特的阐发,如他描写霍窑乌素的勤劳致富时写道:“恨不得房顶种上一分豆,/恨不得井台撒上白萝卜。//恨不得锅巷种上两畦韭菜,/恨不得水缸沿沿上栽海带。//要是有个梯子能上天,/一犁犍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要是能借来牛郎的牛,/月亮上面也种它几亩。”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提炼,让我们看到隐藏在“土气”中的美:淳朴且苍凉、激情而豪放。此外,“太阳出来好像浇了水,/晴死的天气也有几份霉”、“紫花苜蓿地飘彩云,/蜂飞蝶绕爱死人”、“墙头上跑马为兜风,/咱老陕今天就逞一回能”、“煤油灯上孵了一窝鸡”等语言,也都在民间的染缸里染上了浓厚的乡土气息。然而细心品味就会发现,霍竹山的信天游始终彰显文学的想象,以此表达情感的体悟与释放。
四、结语
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态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他们走到曾经被他们蔑视的民间去寻找希望。洪长泰这样说:“我认为,1918年发轫于北京大学一群民间文学家中间的民间文化运动,堪称是这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退一步说,是由于刘复、周作人和顾颉刚等发现了民间文学,转变了中国知识界对文学、更重要的是对民众的态度。”(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l页)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我们民间文化生命不息的知识分子力量。遗憾的是,在现代化的追求过程中,我们纷纷遗失了自己的传统和文明,地方性的丧失使得我们身份的文化烙印日趋消解。霍竹山深入乡村所创作的《金鸡沙》,很像1918年北京大学的民间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他对待信天游的态度是热烈的、虔诚的。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争取信天游的合法性,这正是信天游在当代社会复兴的真正力量。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信天游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文化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政府、民间组织、各类人群等多个力量共同作业的产物。在西方民族志研究领域,关于家乡民俗的研究,却是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巨大变化、经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学术反思和理论争鸣之后,才逐渐开始为学界所接受的。霍竹山所做的新时代的“信天游”,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作者都应该深入到民间,应该到民间的异文化当中去进行田野作业,以寻找和发现越来越丰富的民间叙事资源。
周根红,文学博士,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南京。主要从事文学与传媒研究。
栏目责编: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