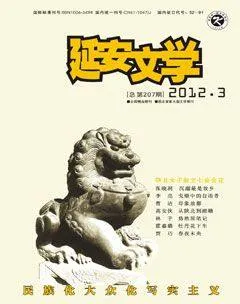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学思考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飞速前进。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结构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对乡村而言,城市化使得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在艰难中进行着深刻的蜕变;对城市而言,大量涌入的农民工给城市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始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对城市化进程中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困境、精神出路给予了及时的关注与书写。
2011年,《延安文学》作为西北的一本大型纯文学刊物,在小说的选取上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刊发了不少艺术性、思想性和时代性兼容并包的优秀作品,有些小说甚至在全国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侯波的《肉烂都在锅里》(《延安文学》2011年第4期)发表后被《小说选刊》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成方的《事当大愧》(《延安文学》2011年第5期)发表后被《小说选刊》2011年第12期佳作推荐。2011年的《延安文学》刊发的小说中有大量作品反映了城市化进程给社会、文化和精神上引起冲击,以及这种冲击下人的生存状态:有反映农民工进城的,有反映进城农民工思乡的,有书写城市底层生活的,有书写农村现状及留守人群的,等等。这些小说都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从一个侧面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象呈现。
2011年《延安文学》刊发的小说作品从总体上来看,其艺术性和思想价值也不尽相同,有高有低,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进行归类。第一层面的作品就是如《肉烂都在锅里》《事当大愧》等艺术精致、思想深邃和鲜活的时代感的小说作品;第二层面的作品就是较好地呈现出艺术性、思想性和时代性的小说,如《无法离开的地方》《城市来了》《我可以叫你幸福吗》《家在城市》《桥洞人家》《鸽子》《黑夜里歌唱》《狗眼爱情》等;第三层面的作品就是那些呈现独特价值或者独特风格的一些小说,如《次危机》《我看见什么了》《我们的非幸福生活》《石榴的镇街》等。
《肉烂都在锅里》是侯波继《上访》后的又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肉烂都在锅里》将艺术视角深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的生存处境问题,尤其是农村人的文化处境问题。小说叙述了一位村支书老杜为了给放电影的亲家丙发子完成上级检查任务,不惜花钱杀羊做羊肉来吸引村民观看电影的故事。这篇小说充分体现出作者感悟生活的灵敏性,敏锐地捕捉到当下农村的2131电影放映工程的尴尬处境,并以此透视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活的尴尬处境。文化追求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需求。但是随着现代化不断深入到农村的方方面面,农民的文化追求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以感官享受的消费文化成为现代化城乡文化选择的新宠。当文化生活需要用物质诱惑来激发,当麻将娱乐轻而易举地完胜电影放映的时候,小说《肉烂都在锅里》留给我们关于农村文化处境一个深深的思考。同时,这篇小说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等方面也有独特的艺术色彩。它大量采用生活化的语言,不但逼真地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农村世界,更对小说人物形象的立体化、情节叙述的合理化、主题意蕴的外向化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这篇小说时间跨度短,空间跨越小,集中在两个晚上的学校操场的时空范围内展开叙事,但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蕴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时空有限性使得矛盾冲突得到集束式爆发,对读者的冲击作用反而更为激烈和震撼。
成方的《事当大愧》以回乡奔丧为小说的切入点,书写了官场沉浮的一幕闹剧。小说犹如一部人物众多而又纷繁热闹的人物情景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有一种憋着口气读完全文,直到结尾才长呼一口气的疲累之感,不光眼累,脑子也跟着高速运转。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又会出现什么人物,姓甚名谁,官阶是何。整部小说借着一个葬礼,让官场那些所谓的领导同志们都走了个过场,露了一下脸儿!主人公也是累得够呛,接待完这个又接待那个,忙得不亦乐乎。整个葬礼的过程仿佛是一个官场运作的另类展示平台,将各方嘴脸都暴露得一览无遗。当葬礼接近尾声,那场换届的戏码也落下了帷幕。结局总是出人意表的。当一切已成定局的时候,主人公方才醒悟,他此番之行是为了奔丧,是为了给父亲尽孝,但是他却模糊了重点,于是乎发出了“事当大愧”的内心呼声。最终他的一番忙乎,也只不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强力推进,任何人都抵御不了大时代的浪潮,都会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着,被迫与其共舞。吕先觉的小说《狗眼爱情》就是写了平静的农村如何被城市化的触角搅动的故事。小说以一个狗的视角进行叙述,将狗和主人的爱情纠葛同时展开,又相互扭结成了一条主线,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小说叙写了石桶村的一个光棍二奎喜欢上了寡妇蓝梅,经常拎着兔子肉送给蓝梅,甚至为了让蓝梅吃上苞谷浆馍不惜动用老母亲推磨,就是这样一种乡村式的爱情方式逐渐赢取了蓝梅的芳心。但是,随着石桶村煤矿的开发,村长摇身一变成了老板,在村长的蛊动下蓝梅当了煤矿的会计,并且误传二奎有乱伦之举。蓝梅在误解和利益欲望的驱动下,毅然投身于村长的怀抱,成为村长的情妇。物质富裕了的蓝梅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寂寞,村长占有她的同时还在外边另找新欢。委屈的蓝梅重新与二奎有了鱼水之欢。事情败露后,村长竟然给蓝梅穿上了贞洁裤,气愤之下的二奎将村长劁了。
城市化的进程如果说对一些偏远的乡村是一个搅动的话,那么对于城市周边的农村则是无情的吞并。李兴义的小说《城市来了》就将艺术的视角聚焦于“城市来了”后周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境遇。当大多数村民欢呼雀跃地呼喊着“城市来了”,自己要成为城里人了时,精明人老杨头却感受到了“城市要把农村给吃掉了”。尽管村子拥有土地,但是村子的生产方式、经济来源已经完全与土地无关,早已融入城市经济发展的链条中了。但是,老杨头认识到个人与时代的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所以要最后利用土地再赚一笔,决定在空地上盖房领取补偿。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纷纷效仿,一时间使拆迁工作陷入困局。作品一方面呈现出城市化进程对于农村无情的挤压同时,折射出城市化过程中人性被利益欲望等逐渐扭曲的历程。应该说这篇小说在这里将矛盾推向了一个高潮,但是很遗憾的是小说的结局没能将这一高潮进一步升华,而是以“救救孩子”这样俗套的结局为故事画上了尾声。
城市来了,无论是周边的农村还是偏远的山村,都逐渐地融入这场大的潮流中。那么,被城市化的浪潮卷席进城的这些农村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入城市、融入城市呢?走入城市、融入城市对于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传统的文化体系和乡间的精神状态的农村人来说并非易事,他们从“无法离开的地方”依依不舍地走来,成为了“桥洞人家”,不得不在“黑夜里歌唱”,最后逐渐地实现“家在城市”的愿望。
毕华勇的小说《无法离开的地方》写了一个农村青年进城的辛酸故事。农村青年毛仓不服气儿时的伙伴三女在城里发达后的盛气凌人,丢掉了老镢把进了城。进城后的毛仓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了建筑工队当了炊事员,开始了他的打工之路。毛仓从淳朴的农村来到了灯红酒绿、欲海沉沦的都市,眼花缭乱的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那种淳朴。他看不起三女身边的“小妖精”,鄙视挣两个钱就去找小姐的打工仔。但是作为这个城市成千上万打工族中的普通一员,生活的贫贱和地位的卑微使毛仓没有鄙视人的权利,他只能受到人们的嘲讽和欺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毛仓没有认清自己的社会阶层,不甘与这个阶层为伍,心里时刻认为“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就是猪,就是狗,谁拿正眼看你们,猪,狗……”。最终老板辞了他。而给自己发工资的恰恰是自己的儿时好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他才发现了三女的发迹之道。既不甘跻身社会的最底层,又不愿意投身城市的游戏规则,这样毛仓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离开城市,要么改造自我。这何尝不是所有农民工进城的最终归宿呢?
理音的小说《桥洞人家》同样关注入城的农民工在城里谋生的经历和他们的生活际遇。二胖如毛仓一样在农村是一把劳动好手,为了生计进入了城市,发现“这城里也不是遍地黄金等人捡,有些城里人活得比乡下人还艰苦。要想过得好,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最后投身到了拾荒一族。因为生活的窘迫,二胖一家住进了护城河桥下的桥洞里,过着一种贫贱而安宁的生活。可以说,二胖一家人尽管进入了城市,但是没能融入城市,仍然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艰辛地努力拼搏。但是二胖没有像毛仓一样看不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平静地接受这一切,默默地享受着这份寒酸的幸福。
但是理音的这种描绘多少掺杂着作者超越世俗的理想化表述,是对农民工苦难生活的诗化和美化。进城后的农民工与城市的方方面面进行着碰撞,也置身于城市各种利益的纠葛中,不可能像二胖夫妻那样置身事外。王凤国的《黑夜里的歌唱》就是将艺术视角探寻到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当下描写底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小说实在是太多了,让人应接不暇,然而这部小说却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农民工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孩子也遭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公平待遇,忍受各种流言蜚语。为了维护孩子幼小的心灵不受伤害,父亲绞尽脑汁,在那黑夜的霓虹灯下为儿子创造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孩子的歌声如一阵清风吹进了人们的耳中、心中,多少带着点心酸与无奈。
农民工进城尽管经受了各种屈辱、各种艰辛,但是他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家安在城里,成为城里人,所以买房成了农民工奋斗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城里有了房子,就能将家安在城市,成为城里人。米原的小说《家在城市》叙写了经过十年努力后在城里买了房子的阿山和阿芳两口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诉求。经过辛辛苦苦地打拼,阿山和阿芳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城里新房,才开始有了其他的愿望和诉求,准备将父亲接过来孝敬,准备要小孩,准备开始全新的城市生活。成为城市人的阿芳突然间也散发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缘于乡村女人毫无心机的聪敏、温顺与热情”很快就吸引了超市老板的爱情。尽管这段爱情在笔者看来,作者多少写得有些牵强,但是阿山的残疾使得阿芳有了一种情感抉择的机遇。作者有效地利用这一机遇,佐以堂兄堂嫂的婚姻危机,成功把捏到农民工面临利益、欲望、爱情、道德等多重关系扭结下的复杂情感和人性光辉。
农村人进城了,成了城里人,那么,故乡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是精神家园的寄托,还是痛苦生活的回忆?《鸽子》和《我可以叫你幸福吗》都是书写了已经成为城里人的主人公回家过年的故事,只不过《鸽子》中的邓家乐最终没能回乡,只能借助一个鸽子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深情。同时《鸽子》借助“鸽子”来书写城市与乡村矛盾下的婚姻危机。鸽子在这里其实是作者故乡的一个精神象征,看到在自家阳台上筑巢的鸽子,便会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曾经饲养过的那只叫做“天使”的鸽子。“天使”带着伤痛也要拼命往家的方向飞,而他却被深深地禁锢在城市的牢笼中,迷失了家的方向。而这城市与乡村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暴露了他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城市人的妻子永远无法理解他的故乡情怀,他虽深爱着她,也不得不感叹他们之间存在的遥远距离。现实的挣扎和争吵只会让他身心俱疲,只有在回忆里才能感受到属于他的温暖归宿。
许侃的《我可以叫你幸福吗》表面上这部小说是探讨幸福的问题,叙述了韦幸福衣锦还乡的幸福。但当他看到骡哥开着公司,开着汽车,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一半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儿,就认为骡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想到一盒伟哥的滑落暴露出了这种幸福的伪装。从深层来看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回乡的故事,提了副科、买了车的韦幸福想“衣锦还乡”地回家过年。这是多少农村人出走发达后的愿望。但是,由于城乡观念和城乡地位的差异,城市一方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城市一方的阻隔,回乡成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这在《鸽子》中我们已经领略。即使是小说中的“衣锦还乡”也只能在附加条件的基础上才得到实现。小说在回乡后仍然延续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从亲人见面就开始出现,但是作者却在这种冲突初现端倪后戛然而止,而拐到了和骡哥探讨幸福的主题上来,影响到了小说主题的深刻凸显。
另外,2011年的《延安文学》刊发的小说作品中还有一些尽管关注的不是“城市化进程”这一文学主题,但就其艺术性、思想性和时代性而言,毫不逊色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品,有些甚至比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更为优秀。这些作品中有左雯姬的《次危机》、徐岩的《你看见什么了》、霍君的《我们的非幸福生活》、范怀智的《石榴的街镇》,还有我们之前评论过的惠雁的《唯有香如故》、侯波的《婚内婚外》以及牧北的《变声期》,只是由于篇幅和主题限制,就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魏建国 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