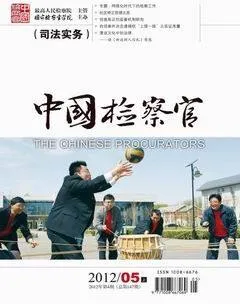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证据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任务具有“同质性”,都必须围绕证据开展诉讼活动,履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职责。尽管如此,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却经常由于取证有“瑕疵”而造成检察机关对有些案件无法提起公诉。为此,我们以2006年—2010年期间,提请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委会上会讨论的265起案件中以存疑不起诉和法定不起诉的案件作为样本,来实证分析取证“瑕疵”情况。我们选择存疑不起诉和法定不起诉案件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案件既能较全面的反映出侦查人员取证“瑕疵”的实况,[1]也能反映出检察机关监督侦查取证的空间与缝隙。在这5年中,共有89起案件以法定不诉或存疑不诉提请检委会讨论,其中,34件是法定不诉,55件是存疑不诉。
这89起案件共涉及32个罪名,其中以常见的故意伤害、盗窃、抢劫、强奸、诈骗、非法经营等罪名的案件51件,占据提请案件的57.3%。绝大部分是由于案件事实难以查明,而非法律适用问题提请检委会讨论的。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研究,其中,共有19起案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提起公诉,其中,包括5起承办人员认为属于法定不诉的案件。另外的70起案件作了存疑或法定不诉处理。通过对这些存疑案件和法定不诉案件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有70%左右的案件都实际存在或隐含取证“瑕疵”的情况。
二、样态分析:侦查取证中“瑕疵”情形
在以上89起经过检委会讨论的案件中,出现取证“瑕疵”的形态各异,既有证据收集方法上的瑕疵,也有证据内容的瑕疵;不仅包括实体上的“瑕疵”,也有程序上的“瑕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情形:(一)取证中忽视不同种类证据内容的相互印证。在正常情况下,案件事实并非仅靠一种证据就能证明,而是需要多种证据相互印证才能使案件事实达到“结论唯一”。然而,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经常会无序杂乱,证据内容相互不能补强甚至冲突,造成对案件的发生过程无法证明。(二)取证程序不合法而导致证据无效。取证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收集固定证据时轻视程序的合法性,尤其是关键证据因程序违法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影响案件的审理。(三)取证时效不强而造成有些关键证据的遗失。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之后应当及时赶赴现场,并全面客观地搜集证据。[2]根据统计,在不少案件中,侦查人员由于延迟取证造成关键证据毁损灭失后之后又无法补救,只能做存疑不诉处理。(四)取证不全面而造成关键事实难以认定。在正常情况下,侦查人员对每个案件都应当尽可能的按照刑诉法列举的八类证据收集取证,对遗漏的证据予以补强,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取证不全面主要表现为过于重视口供,对潜藏的物证、书证等其它证据发掘的力度不够。[3]由于口供具有主观性、不稳定性等弱点,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若无其他证据佐证,很容易使案件陷入僵局。除此以外,由于有些讯问或记录粗糙肤浅,有时甚至曲解误记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犯罪嫌疑人在当时阅读讯问笔录的时候没有提出疑问,但是在事后的诉讼中提出来,这就使得供述的前后不一致。(五)对特殊物品的取证缺乏规范指导。基层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类型多属于高发、常见的普通刑事案件,由此,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中很容易形成思维惯性,容易忽视个案特点,造成有些特殊证据灭失。(六)取证过分依赖鉴定意见。虽然立法上已经规定鉴定意见要经过审查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要求,但是,公安机关办案情况无不体现了对鉴定意见的过分依赖,伤害够不够轻伤、涉案财产是否达到定罪数额等都完全以鉴定意见为准,即无鉴定意见就无法立案或定罪,这已经成为日常办案中的一大怪圈,已经影响到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判断。
为此,我们分别以B代表取证忽视不同种类证据内容的相互印证;C代表取证程序不合法导致证据无效;D代表取证时效不强造成有些关键证据遗失;E代表取证不全面造成有些事实难以认定;F代表特殊物品取证缺乏规范指导;G代表取证过分依赖鉴定意见。对这89起案件中造成存疑或法定不诉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4]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B类和E类占据了存疑和法定不诉案件的70%。在B种情况中,证据内容不能相互印证,绝大部分在于很多言词证据不统一,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相互冲突,也有些是言词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物证的冲突。在E种情况中,经常出现侦查人员没有提取应该取的证据,遗漏对证人的询问,涉案物品的扣押等情况。除此以外,在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中,电子证据很容易被犯罪嫌疑人快速处理掉,公安机关很多时候仍以笔录的单一方式进行固定,甚少运用同步录音、录像、拍照等手段进行辅助性固定,增加了认定案件事实的难度。
三、问题剖析:检察机关监督侦查取证的难题
(一)监督取证的意识不足
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5]从目前检察机关审理案件情况看,检察人员主要根据案卷证据判断案件是否达到逮捕标准、起诉标准或抗诉标准,这种思维模式仍是保证案件进入诉讼通道。虽然这种审查制度自身隐含有监督的“因子”,但是承办人员主观上却缺乏监督意识。这种办案模式主要通过对公安机关已经获取的证据来判断案件的定性与情节,由于不介入侦查过程,检察机关更是缺乏对取证过程监督的意识。实践证明,虽然不少存疑不起诉和法定不起诉的案件与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密切相关,但是也与检察人员取证监督意识淡漠密切相关。有的侦查人员还错误地认为检察机关取证监督是“找茬儿”、“挑刺”,不仅不配合甚至予以抵制,导致有的检察人员对侦查机关取证监督存在畏难情绪,甚至不愿实施法律监督。
(二)侦查权缺乏有效制约
警察职能对于任何一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