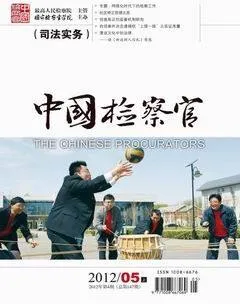论利用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法律适用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赌博活动也逐渐深入到互联网领域。利用互联网建立赌博网站,接受参赌人员投注,成为赌博网络庄家吸取巨额赌资,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受众人群的广泛性以及电子商务的便捷性等特点,使得赌博网站在近些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例如:太阳城网、金沙网、皇冠网、宝马网等大型赌博网站在我国境内拥有众多参赌会员。以太阳城网站为例,仅在北京地区,自建立后短短数月内,就聚集参赌会员3000余人。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2005年5月颁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行为明确规定为“开设赌场”。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行为从赌博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开设赌场罪。2010年8月,两高又会同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以及网络赌资计算方式等问题。这些法律及司法解释为办理在网络赌博案件提供依据和指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在办理该类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在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过程中,尚存在诸多争议。现以笔者2010-2011年度指导和参与办理的北京地区网络赌博犯罪案件为基础,对当前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关法律问题存在的争议进行分析与反思。
一、“赌博网站代理”应如何理解
(一)法律拟制下的“作为赌博网站代理”
2005年与2010年两个关于网络赌博案件司法解释中均规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行为,属于开设赌场罪。特别是在2010年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赌博网站的代理。”这是对开设赌场行为的法律拟制。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国内互联网管理制度森严,境内基本没有建立赌博网站的空间。因此在境内较为活跃的赌博网站几乎均为境外接入网站。这些境外赌博网站为了吸纳我国境内赌资,必须通过网络赌博代理人进行。也就是说,在我国境内从事网络赌博网站运作的人员几乎均系境外网站代理。为了有效打击这类犯罪,故法律将这种代理行为直接规定为开设赌场罪。
(二)形式上的赌博网站代理与实质上的赌博网站代理
司法解释将网络赌博代理接受投注的行为规定为开设赌场罪。这一规定看似并无争议,但是我们在办理网络赌博犯罪的过程中,却发现有两种特殊的“网络赌博代理”情形:
第一种情形:有的行为人为了方便自己“上分”[1]方便,使用代理账号仅接受自己投注的情形。也就是说,行为人使用了代理账号,但接受的仅仅是自己的投注。第二种情形:有的行为人不掌握代理账号,仅仅使用会员账号,但是其利用会员账号聚集多人在其家中参与网络赌博。即:多人使用同一个会员账号投注。
在认定这两种情形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司法实务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大致分为“形式符合说”与“实质符合说”两派。“形式符合说”主张网络赌博代理的认定应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即:拥有赌博网站代理账号。至于其是否从事代理行为等问题则不必考虑。而“实质符合说”则强调网络赌博代理身份的认定,不能僵化地局限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不能仅以是否掌握代理账号为唯一的判断依据,应当对其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1.赌博网站代理的“形式符合说”。对于第一种情形,“形式符合说”认为依据上述两个解释,只要行为人使用了代理账号(代理账号下能开出下级账号)参与赌博就构成开设赌场罪。因为根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要求主客观相统一。而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自己使用代理账号,在客观行为上又实施了接受投注的行为,符合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犯罪构成,并且做到了“主客观相统一”。
对于第二种情形,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行为人不掌握代理账号,不符合司法解释中有关“赌博网站代理”身份的规定。故对该行为不应认定为“开设赌场”。如果该行为符合“聚众赌博”的犯罪构成,应以赌博罪定罪处罚。
2.赌博网站代理的“实质符合说”。我们认为,“形式符合说”的观点忽视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也就是说,只要法益未受侵害或无受侵害之虞,则不存在犯罪。具体到赌博网站代理身份的认定过程中,赌博网站所提供的身份认定固然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但在司法认定中不应机械囿于赌博网站给出的身份名称,而应该考察其所实施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赌博网站代理、接受投注的本质特征,即实现了网络赌博中重要的信息和资金的流转。
对于第一种情形,虽然从代理的权限、接受投注的事实等形式要件考察,这种行为完全符合2010年解释的规定,但是我们认为,对代理的认定应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角度考察。就实质角度观察,该行为与单纯通过网络参赌账号投注的参赌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自己代理自己,也就是说仅仅是利用代理账号实现自己参赌的目的。虽然2010年解释中规定“赌博网站的会员账号数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如果查实一个账号多人使用或者多个账号一人使用的,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人数计算参赌人数”。但这种参赌人数的计算方法,也是以构成开设赌场的行为为前提的,如果尚不能认定是开设赌场的行为,则不应简单按照上述要求认定参赌人数。
由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没有实现赌博网站与参赌会员之间的有关信息、赌资等内容的交流,其行为仅仅是自己参与赌博的特殊表现方式。因此,这种开出代理账号单纯供自己赌博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开设赌场”。
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其中形式上并没有赌博网站给出的“代理”身份,即使用代理账号,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起到了赌博网站与参赌会员间的沟通作用。由此可以看到,该行为与使用赌博代理账号发展参赌会员的行为在实质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高度相似性”而未使用“同一性”的表述是由于使用赌博代理账号是在网络中发展会员,而使用仅能投注的会员账号,需要在现实中发展会员。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广域性及迅捷性使得使用在网络中发展会员的危害程度要高于现实中发展会员的行为。换言之,二者在法益侵害的程度上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所带来的问题是,是否应将这种使用会员账号聚集多人参与网络赌博的行为评价为“作为赌博网站代理接受投注”。我们认为,应当根据法益受侵害程度来区分这一行为:
首先,对于利用会员账号长期聚集众多参赌人员进行赌博的行为,应直接认定为开设赌场,不再援引“作为赌博网站代理接受投注”的表述。因为其已经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小赌场,此时会员账号不过是一种实现其赌场经营的工具。其次,对于利用会员账号在一定时间聚集众多参赌人员进行赌博的,可以认定为“聚众赌博”,以赌博罪处罚。因为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虽建立起了赌博网站与会员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其行为模式决定了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有限,故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责任将造成罪刑不均衡。最后,对于利用会员账号仅提供亲朋偶尔参与网络赌博的行为,即使其符合聚众赌博的行为特点,但由于缺乏犯罪故意,即缺乏非难可能性,也不能用刑法处罚。
(三)“网络赌博代理”的认定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
我们认为“形式符合说”与“实质符合说”这两种观点的碰撞实际上是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冲突,即:传统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与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理论之间的冲突。在传统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中,四个犯罪构成要件是互为前提、互为依托的闭合式结构。这种理论对犯罪是“主观-客观”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很容易出现上述忽视刑法法益保护功能的情形。而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理论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者呈相互递进式的开放结构。在这一体系下,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依次判断,而非如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对四要件同时判断。在这一判断过程中,首先判断行为是符合罪状表述,再判断法益是否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最后判断该行为是否有非难可能(即是否有责)。这种理论对犯罪是从“违法到有责”的认识过程。其优点在于可以清晰的分辨犯罪的结构特征,易于把握罪与非罪。以认定网络赌博代理行为为例:虽然该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罪状表述,但是由于其在实质上并未侵害法益,故缺乏违法性要件,因此该行为不能评价为犯罪,进而也就不用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出于何种故意等责任要素。
二、在网上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标准设定过低
2010年的解释中规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之一。但是通过办理相关案件我们发现,这一法定刑升格的标准设定明显偏低,导致打击面过大,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
(一)新旧标准差距过大
认定网络赌博“情节严重”的新标准与先前判例中所掌握的“赌资累计达上千万或上亿元”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差距过大,使得量刑档次缺乏有效衔接。
举例而言:2009年2月16日《法制日报》刊登《上海网络赌博第一案一审宣判20名被告人犯开设赌场罪获刑》。上海普陀区法院认定作为赌博网站代理的犯罪团伙接受投注金额达6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主犯钱葆春最终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0万元。再如:2009年7月3日杭州网刊登《萧山亿元跨国网络赌博案宣判 开设赌场罪成立》,萧山法院认定作为赌博网站代理的犯罪团伙接受投注金额达1.25亿元人民币,其中5名被告人均成立开设赌场罪,最高量刑是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70万。
此外,由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可溯及至刑法规定之时,而开设赌场罪的赌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虽然赌资数额不是入罪标准,但在该解释下却是法定刑升格标准。将这一标准溯及至行为之时,明显对被告人不公。举例而言:行为人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在网络上开设赌场接受投注30万,后其被抓获。依照旧标准其仅能判处数月至1年不等的刑罚。而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新司法解释出台,则要承担3年以上的刑罚。可见由于量刑标准设定的不当,使得司法解释在溯及既往的过程中严重侵犯了公民对刑法的可预期性,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二)赌资计算依据不当
由于该解释规定:“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将从网络赌博系统中提取的网络投注记录作为认定参赌金额的依据。然而,在网络赌场内投注30万元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远远低于在现实赌场中投注30万元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将30万元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将导致罪刑不相适应。这是因为,网络赌博中的赌资与现实赌场中的赌资并非同一概念。网络赌博与传统赌博赌资计算的方法不同。非网络的赌博是同一时间在同一空间,赌资数额是以起获的为准,但事实上该总量赌资可能在被抓获前进行过反复的下注,可从取证的可行性上难以做到累计下注金额的统计。但网络赌博恰相反,由于赌博网站的详细记录,可以清晰的显示每次接受投注的金额,进而累计。具体而言:网络赌博中,参赌人员进行投注所使用的是虚拟的“点数”,这些“点数”虽然先要进行购买,但是在赌博过程中却不会即时交割,而一般是以一个星期为周期进行整体交割。如果参赌人员在赌博过程中赢了相应的“点数”,就可以继续投注,由此网络赌博系统就会重复计算其投注,最终使得累计接受投注的数额比其实际花钱参与的数额要高出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举例而言,参赌人员用1000元购买1000“点数”,然后再将这1000点投注,如果其赢,则网络赌博系统将记载其投注1000点,并赢得1000点,这样其赌博点数累积为2000点。如果其再用这2000点投注,则系统就会记载其累计投注3000点。不难看出,仅仅是两次投注行为,就可以使累计投注数额成倍增长。由此可见,网络赌博中的投注与现实赌博中的投注并不一致。这样就可能造成,完全相同的赌博过程,但在网络上进行和以非网络方式进行,涉赌金额会有非常巨大的差距。
三、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在2010年解释中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认定网络赌博“情节严重”情形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和认定参赌金额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就认定参赌金额认定而言,在2010解释中虽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对于其银行账目中的往来款项常常以生意往来进行辩解,加之网络赌博实际资金交割一般以一周为结算期,因此在嫌疑人不认罪的情形下,难以认定其银行账目中往来款项系赌资。
注释:
[1]在赌博网站上为使用者的参赌账号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