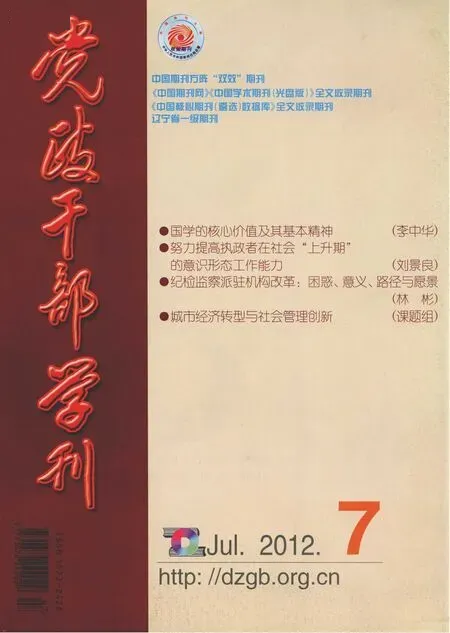再论黑格尔的真理观
李基礼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再论黑格尔的真理观
李基礼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黑格尔真理观从超越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而直面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问题本身,通过世界理性化的方式建构起一种本体论的真理观,从而深刻地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问题。这种真理观从根本上发端于黑格尔深切的历史意识,从而引发出真理本质就是历史理性的这一深刻命题,由此实现了近代哲学从祛魅到化魅的超越。
黑格尔;真理观;历史理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真理观。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解读:有学者指出它属于传统“符合论”真理观,[1]有学者认为是一种“融贯论”真理观,[2]还有学者认为既不是“符合论”真理观,也不是“融贯论”真理观,而是一种“整体论”真理观[3]。从已有解读来看,绝大多数是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真理观诠释的一种继承与延续,而这种诠释本质上是知识论的,没有跳出笛卡尔肇始的主客二元论的窠臼,这种奠定于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真理观必然是直观的、静态的。而综观黑格尔哲学,旨在超越二元论,批判无历史的真理观。
一、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
任何哲学观点,如果不被纳入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域中进行思考,其结果往往只是关注者自身思想的一种镜象。正如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是我们不了解引起黑格尔关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基本问题和渴望——它们也是其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渴望,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地了解黑格尔在将来的作为。”[4]对黑格尔问题域的把握,我们通常从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确定,“以彻底的唯心论的态度,把先验唯心论发展为绝对唯心论”。[5]这一学理展现的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自己也说:“我们在这里应当考察近代哲学的具体形式,即自为思维的出现。……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6]根据黑格尔后来的论述以及黑格尔研究专家查尔斯·泰勒的指认[7],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也包含在“一切哲学”之中。
如果抽象地理解黑格尔的这一问题域,很难不把黑格尔的真理观归入“符合论”或“融贯论”真理观,因为这些真理观的两极就是思维与存在。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笛卡尔之后就转化为两方面: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自然的人与作为道德的人的关系问题,后者又进一步转化为人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康德从人的理性的自我分裂着手,把自然的必然性归为理论理性,把人的自由归为实践理性。这样,人的欲望、情感等受理论理性支配,表现为一种自然必然性;人的意志则归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确保了自由,也就确保了道德世界的合法性。从这一逻辑出发,康德不仅把作为整体的人一分为二,也把世界分为物自体与现象,把人与世界的分裂推向了极致。这种巨大的分裂让当时流行于德国的表现主义者强烈不满,他们要求统一、自由,要求人与自然的融合。
实现从分裂到统一,费希特哲学构成了极为重要的一环。他不满康德自我意识的巨大分裂,把康德哲学中作为最高原则的自由意志推向极致,取消了物自体与现象对立。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唯一原则,通过自我的意志活动设定非我,设定对象化的自然界,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对费希特构成了巨大挑战。因为自我的绝对自由必须不断征服在现实中的相对自由,而对这一永无休止的过程,自我只能疲于不断的奋斗。谢林吸收了表现主义肯定世界存在某种更高的统一的观点,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但这种统一不是通过自我意识——理性而是通过艺术或宗教的神秘启示完成的,因而启蒙运动呼唤的理性精神到谢林这里失落了。
如何通过理性精神来实现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的一致的重担落到了黑格尔的肩上。他承担起表现主义坚持统一、融合世界的历史使命,又秉承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传统,力图通过理性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一统一性问题。黑格尔把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分裂、自我运动、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种统一是通过概念完成的,是一个逻辑化的过程,因而也就把理性保存在统一之中。
因此,真理在黑格尔这里并非指其他,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及其统一就是绝对精神本身的“现象”或者“显像”。黑格尔之前的哲学都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两者的对立,所以他们努力去寻找两者的同一,而黑格尔却是以积极的方式理解和把握这种对立,认为它是绝对精神的必经阶段,因而真理不是要求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而是对立本身就是真理,或者说就是真理的展现。黑格尔的真理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理观。
二、黑格尔的真理观
黑格尔的真理观之所以是更高层次的真理观,在于他关注的不是在分裂的两个世界——主体与对象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的知识论境域,而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生成过程。如果说传统的真理观是认识论的,那么黑格尔的真理观则是本体论的。只有立足于本体论,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真理观及其对真理的表述:“真理之作为科学的体系”、“真理是全体”、真理不是“对绝对的感觉与直观”等。
“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8]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全体,是结果,是科学体系?可以说都是,又都不是。说都是,因为它们都是对真理的一种描述;说都不是,因为任何描述无法真正捕捉到真理本身。但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把握,仍然只能在描述中展现真理的生成过程。
要把握黑格尔的真理,首先要把握其哲学考察的对象。这一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宇宙(黑格尔称之为 “绝对精神”),但它不是静态的而是生成着的宇宙。黑格尔以植物的生命过程为喻,[9]表明了他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整体性的,不断运动、生成、超越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在于其“流动性”,其流动性则在于“自我否定”。这种生成着的宇宙如何把握?正如他所言,宇宙是一种运动的生命,但这只表达了宇宙的状态,并未揭示宇宙的本质。那么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是黑格尔与当时德国浪漫派分道扬镳的关键,也是超越谢林的真谛。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精神,是一个理性化、逻辑化的宇宙。因而真理不是“对绝对的感觉与直观”。
由此,黑格尔关于真理的表述就可以理解了。为何“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因为真理是理性辩证发展的过程,是概念辩证法,而科学(这里是指哲学)正是通过概念的推理得以实现的学问。而概念辩证发展的过程就是宇宙本身演化的过程,宇宙就是一个逻辑化、理性化的生命。因此,真理不是外在于宇宙、对宇宙做镜面式反应的真理,真理即宇宙,真理即绝对精神,而科学体系即绝对精神的生生不息。同样,“绝对即主体”表达的同样是真理本身。在这里“绝对”(或者称实体)并不是别的,而是理性本身。“‘理性’是宇宙的实体”,“由于‘理性’与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10];而主体是指自己是自己运动的根据,而理性本身就具备自我运动能力,因而理性精神实现了主客的一致。由此,黑格尔超越了传统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也保留了近代哲学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义传统。
三、作为历史理性的真理
黑格尔是拒斥直观的,他认为通常意义上作为标准科学的数学不是真理。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数学知识是沿着同一性的路线进行的,没有达到本质的差别,“因而到达不了对立面向对立面的过渡,到达不了质的、内在的运动,到达不了自身运动”;二是数学“并不把时间作为时间而与空间对置起来”,[11]尽管数学也研究时间,但数学的研究是把时间空间化了。而黑格尔所要阐发的哲学真理不是一种知性真理,而是概念真理。“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12]这种真理是一种概念辩证法,是历史的本质。
这一立场起初就蕴含在黑格尔问题域中。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然与自由如何统一,而诉诸方案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通过艰难劳作不断地在自我分裂、自我斗争中前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绝对精神成为了“世界精神”,而历史则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那么世界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自由:“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 ”[13]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那么自由如何实现?黑格尔说:“人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惟一的源泉。”[14]自由是内在的,而实现自由的手段是外在的。康德无法统一两者,他最终把需要、热情等归入现象界,而把自由配给了本体界,所以现实的人对自由的追求只能通过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保证成为到彼岸世界的奢求。而黑格尔却指出:“我们所谓原则,最后的目的、使命,或者‘精神’的本性和概念”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伏性,但是还没有从它的内在达到 ‘生存’”,如果要产生确定性的,变成为现实,那就要加上人的意志,也就是“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15]康德眼中抽象的对立,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世界精神得以发展的必然环节,正是这种对立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黑格尔说:“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这两者具体的中和就是国家中的‘道德自由’,我们已经把‘自由的观念’当做是‘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16]
这种为一己私利、有目的的活动是否会导致人类历史的无序状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欲望、兴趣和活动,只是“世界精神”为完成自身目的的手段。是否会因“世界精神”的目的(自由)而妨碍个人的自由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自由与必然是内在地统一的。因为在“世界历史”本身的进程尚未完成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此前的人类还处于史前史时,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无法明白“世界历史”本身的进程,世界历史正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意志)为自己开道,“普遍的原则蕴蓄在它们个别的目的之中,并且由它们来实现它自己”[17],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理,“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显然也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只有在“世界精神”真正展开的过程中,真正的哲学才有可能。“哲学的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 (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18]
四、祛魅到化魅
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笛卡尔肇始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启了把世界理性化、逻辑化的过程。笛卡尔通过分析的方法、怀疑的精神,以“我思故我在”为逻辑基点,建立起了以“思想”为存在属性的精神实体和以“广延”为存在属性的物质实体。这种划分经斯宾诺莎用样式与属性两个概念把世界分为无数独立的思想与广延的存在者,单个事物通过外在关系保持联系。这种哲学观与牛顿力学体系、西方经济学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牛顿力学体系中,宇宙是由单个事物——天体构成,它们通过力这一外在关系发生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组成,他们通过价格这一外在关系发生作用。上述哲学观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休谟对自然科学基础性原理——因果关系的怀疑危及到原本试图为科学奠基的哲学本身;为自身利益追逐的理性经济人把人类的道德与自由推向了彼岸世界。
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根源在于,以知性思维主导的近代哲学在对世界进行祛魅的过程中,把人与世界深层的内在关系祛除了。从知性思维出发,这种内在关系成了“先验幻象”。在主客体的抽象对立中,思维着的主体对外在客体的把握成了问题。如果人们囿于原初的哲学基地,将难以跳出自身划定的牢笼。只有进行思维革命,跳出知性思维的局限,诉诸辩证思维,才能真正把握人与世界的本真关系。黑格尔真理观就是立足于思维超越,把原本在理性化过程中被祛去的“迷魅”唤醒。但黑格尔所走的不是谢林的路,即试图通过直观或启示等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本质,而是通过理性精神本身这种人类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成果去化解知性思维无法把握的“迷魅”,这正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
但黑格尔用理性把握生命的整体性时,这种用大写理性吞噬万物的方式也预示着近代哲学的终结。尽管他试图通过辩证法保存个体的人,但是活生生的生命本身还是成了理性谋划自身的手段和工具,由此走向了启蒙运动的反面。同时,用理性来规制生命本身也有违现代精神。因此,现代哲学大多以反黑格尔的理性为逻辑起点开展自己的哲学研究,如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对黑格尔大写理性的反叛,狄尔泰从反对对人的肢解入手,强调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体,对知、情、意做出区分只是为了便于描述而已。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必然的,但正如郑昕先生在《康德学述》“弁言”中所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9]其实,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亦是如此。
[1]李青.黑格尔真理观刍议 [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1).
[2]王荣祥.黑格尔的真理观[J].理论界,2009,(2).
[3]冉光芬.黑格尔的“真理观”[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4][7]查尔斯·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3,4.
[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5.
[6]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
[8][9][11][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2,4,29,34.
[10][13][14][15][16][17][18]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8,16,18,20,21,23,54.
[19]郑昕.康德学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
责任编辑 姚黎君
B504
A
1672-2426(2012)07-0010-03
李基礼(1979-),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