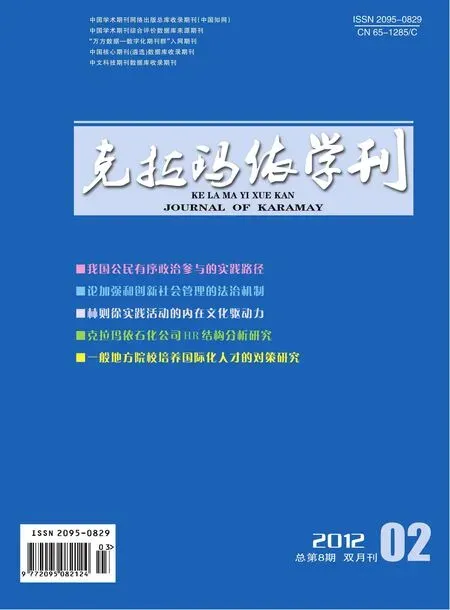以“荒谬”反击荒谬
——浅析加缪的《局外人》
唐海韵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人究竟为什么而活?这是个千百年来不断拷问人类灵魂的问题。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认为:只有一个问题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便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选择生活),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即人可以在否定生理自杀和哲学自杀(寄希望于上帝)后,依然能够任性而有道德地活着。在这一思想根基上,《局外人》诞生了。
《局外人》主要通过主人公莫尔索的感受来呈现故事情节,以他的内心世界来影射世界的荒诞: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小说所写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给人一种不连贯的荒谬感。莫尔索的言行举止更是超越了常人的习惯定式,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当我们悬搁了固有的道德判断来重新审视这个独特的形象,就会恍然大悟,莫尔索实际上是以“看似荒谬,实则不然”的举措来猛烈反击这个世界的荒谬。
一、《局外人》的“荒谬”体现
(一)《局外人》塑造的“荒谬”的人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1]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
1.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亲情、友情、爱情这些被世人奉为“圣物”的东西均被莫尔索视为虚无,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回馈所有的情感索求。
2.工作生涯中的局外人
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
“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
3.死神面前的局外人
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4.彼岸世界的局外人
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萨特评论道:“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二)《局外人》体现的“荒谬”的世界
文艺复兴发现了大写的人,即人的智慧、人的伟大、人的高超,而叔本华、萨特等人的哲学则着力于揭示小写的人,即人的卑微、人的怯懦和面对世界荒谬性无能为力的局限。
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的确需要一套规则,但这些法规、道德往往会异化为人类的枷锁和掩饰虚伪的工具。
莫尔索在料理妈妈的丧事时,有妈妈的一些昔日的好友前来守灵。有一个妇女“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然后又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有几个老头子“在咂自己的腮帮子……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这里的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这些说是要为逝者默哀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忧伤,却碍于面子,硬逼着自己佯装痛心的样子,努力演戏。当老板表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任职时,他坦率拒绝,但老板却不因他的真诚而欣慰,反而颇为恼火。
就像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一样,人类总是喜欢不断给自己加定义,不断将自己包裹,使自己被法律、道德戒条所束缚而忘记追求本真的东西,结果使自己身心俱疲。
莫尔索锒铛入狱到接受审判的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世界的荒谬性。本来,莫尔索是过失杀人,并且由于他杀的是阿尔及尔的阿拉伯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阿尔及尔还是法国殖民地),很有可能获得法律宽恕,罪不至死。但是,他最终被判死刑,原因就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得十分漠然。
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莫尔索认为:“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抛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当事人的陈述可有可无,只剩下求胜心切的律师和认定莫尔索罪大恶极的法官在争论不休。律师为了胜诉而要不肯说谎的莫尔索保持沉默,强行给他加一些评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喜爱,对他人的痛苦有同情心......”而法官则拼命网罗莫尔索的罪行,说他是怀着一个杀人犯的心理埋葬了母亲,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应麻木不仁,并且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将他在一个广场上斩首示众。
面对母亲死亡的冷漠表现和无意错杀阿拉伯人本是毫无干系的两件事,却被法官生拉硬扯在一处,狡辩说:“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还要代表法兰西人民来执行判决。这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而逼迫卢俊义上梁山的宋江之流一样冷酷荒谬,看似维护正义,实则祸乱法律。
二、《局外人》的“荒谬”实质:以“荒谬”反击荒谬
(一)并非“荒谬”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被以卫道士自居者视作放浪形骸、不学无术的“混世魔王”。似乎对儒释道三家都颇为不屑的他,其实才是真正领略三家精髓的智慧之人。他嘲弄儒家的“文死谏,武死战”,却躬行孝悌之道;他反对道家炼丹成仙的虚妄,却有老庄超脱飘然的情怀;他厌恶烧香拜佛的繁琐仪式,却有着博爱仁慈的胸襟。他踏踏实实地践行着三家的最高理念,痴迷地追求本真生命,却给人一种离经叛道、不可救药的印象。
同样,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评价说,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莫尔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只不过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样过于虚幻;也不认同禅宗的生命“如露如电”,从而寻求涅寂静;更没有鲁滨逊的“经济人意识”,唯利是图。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莫尔索十分关注生理欲望,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在处理母亲丧事时,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饿”、“热”,还大胆地在母亲的遗体前畅快抽烟,回家后便急于和女友玛丽发生肉体关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也不忘记欣赏玛丽的身体和装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紧张,想要逃避,但这也是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见,莫尔索基本摆脱了世俗镣铐。人们绞尽脑汁设置的礼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唯一真实的便是明媚的阳光、美丽的大海以及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种种需求。并且,他也懂得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没有真正侵害谁的利益(射杀阿拉伯人也是由于防卫过当),完全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这一规矩。
阿尔贝·加缪认为,说谎,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莫尔索则与他的表面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书中的沙拉马诺老头每日都要咒骂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叹“我怎么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妇对自己不忠,想要狠狠报复,可还觉得心底对她颇为留恋。这两组隐喻巧妙地暗示了莫尔索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语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交,他也没有所谓礼貌上的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做不做都可以”;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
在法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直言不讳;检察官说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甫为他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
对莫尔索来说,所谓道德,就是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动,就是要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忠实地表现这种感情,拒绝作假,拒绝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现世的、眼前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先验价值,不是任何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会道德,在莫尔索看来,就是要服从先验法则,就是要否定同社会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摆布。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他难道不比我们所有的人更加真实、正常吗?说他“荒谬”,不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很荒谬而不自知吗?
尚比尼说,基督徒由原罪的感情出发,不去追求与世界的一体化,而是回避世界,走向上帝;反之,莫尔索却在与外在世界的一体化状态中寻求欢乐,所以,莫尔索是以他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去创造出伊壁鸠鲁文明的救世力量的地中海英雄。
(二)不准“荒谬”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既然人最终要死且生活苦难重重,那我们又为什么要活呢?著名学者刘再复认为,短暂的快乐的瞬间能支撑我们沉重的人生。然而莫尔索追求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可是社会通过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对莫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恶意识、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正如《李尔王》中那个天真纯洁、不愿屈从于浮华形式而最终惨淡收场的考狄利娅一样,世界要以莫尔索生命的消殒来再次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谬的世界是强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个体生命面前,它似乎无往而不胜。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莫尔索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人格独立性逐步泯灭的社会里,他能够没有悔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是对世界荒谬性的有力反击,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世界的荒谬,也认识了自己的荒谬。
美国当代学者大·盖洛韦认为《局外人》是通过荒诞的主人公来表达执着于意图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谬主题。它实际上是一则寓言:每个人都走在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必然毁灭于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创建的荒谬世界。
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1]袁澍娟,徐崇温.卡缪的荒谬哲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