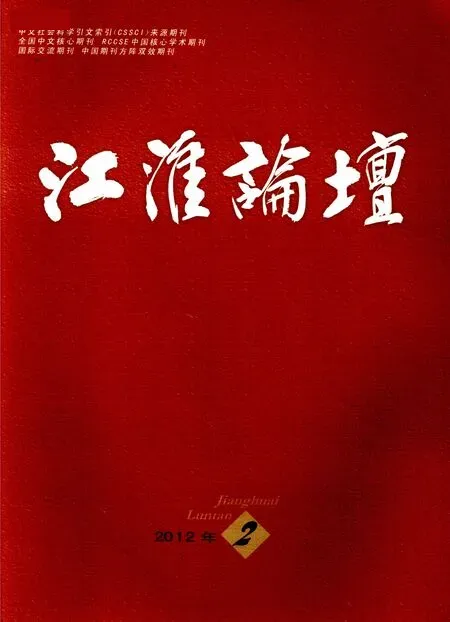试论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杨曙光
(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试论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杨曙光
(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证据材料,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对“毒树之果”和以秘密手段获取证据不应一概加以否定,而应具体分析与区别。另外,违反程序的证据、超期限举证的证据和域外证据等其他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也应加以排除而不予采信。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毒树之果;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规则一直是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尤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研究文章颇多,但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和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在行政诉讼(如工伤认定之诉)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的种种问题更不断出现。笔者就该领域的几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望各位同行指教。
一、非法证据的含义
何谓非法证据,我国法学界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笔者在涉猎资料的基础上共归纳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调查收集的证据。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所谓非法手段包括违反法定程序采取的手段,也包括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所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非法既包括程序违法也包括实体违法。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有关国家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1]第四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的非法除了包括程序违法、实体违法之外,还包括以已经取得的非法证据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2]
前三种观点在归纳非法证据的含义时均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因为在实践中获取证据的主体不仅包括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等执法部门,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主体,如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律师、第三人等。第四种观点则重点强调非法证据不仅包括“毒树”,也包括“毒果”。笔者认为,概括的讲,非法证据是指符合关联性和真实性而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它包括四种非法情形:第一,证据内容不合法,例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第二,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第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例如,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第四,收集、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例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质是由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与例外规则构成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3]严格说来,“证据规则”是一个外来词,它“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具体说就是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与准则,也可以概括为规范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4]在行政诉讼中,设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个人权利,损害正当程序。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效力问题的探讨比较少,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方面,不少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在我国应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笔者总结了以下五种理论,以资借鉴。
1.真实肯定说。该学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在证明案件真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5]
2.区别对待说。该观点认为应该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若作为证据就等于承认刑讯逼供、威胁取证、诱骗取证等活动,从而直接背离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因而应将其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采信。[6]
3.线索转化说。此说认为应以补证方式即重新而合法地取证,使非法证据合法化,或以非法证据为“证据线索”,靠它获得定案依据。[7]
4.排除加例外说。该说认为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这些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8]
5.全盘否定说。该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严禁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自然违反法律规定获得的证据就失去证据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9]
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全盘否定说”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工伤认定领域,劳动保障部门收集的认定劳动者构成工伤的证据虽然存在瑕疵,但基于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主义,不能轻易否定此类保护劳动者的证据;又如,普通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打击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寄托着较高的期望,而对制假贩假等违法行为则表现出深深的憎恶和恐惧。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全盘否定说”,不可能被大多数公民所理解与接受。另外,我国目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执法人员的水平与素质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严格彻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离我国的国情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真实肯定说”更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该学说不利于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也不符合世界法治发展的潮流。“区别对待说”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取向,“线索转化说”同样也忽视了程序本身的重要性,如果采用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会加深我们长期以来的制度思维缺陷,强化人们传统的将程序看作实现实体的载体而忽视其本身价值的观念。
笔者赞同在我国采用“排除加例外说”。对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我国也正在适应这一潮流,开始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非法证据的取得是以牺牲有关人员的人权为代价的,是与保护人权这一世界潮流相悖的,刑讯逼供,诱供以及以其他非法方式取证一直是我国司法界屡禁不止的顽症,矫枉难免要过正,所以对非法证据在原则上应予以排除。[10]而且这也是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树立司法公正权威、抑制非法取证行为、保护有关人员的权利及保证案件真实的需要。但不分皂白的绝对排除又是脱离实际的,执法人员出于故意、过失或者无主观过错地违反了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都一概被排除,真正严重违法的人将在大量确凿可信的证据面前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诚然其人权得到了最大的保护,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也得到了加强,但却违背了制止违法、保护社会秩序这一基本社会需求。而且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法律文化相差太大,难以为广大公民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还要有一些例外的限制,以期达到保护人权和制止违法这两个目标,而不会对某一目标的片面追求造成对另一目标的极端破坏。
三、“毒树之果”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属于典型的非法证据。⑴利诱是指当事人对有关人员采取利益引诱的方法获得的证据,例如“警察圈套(entrapment)”(2);欺诈是指当事人故意伪造虚假信息或歪曲、掩盖事实,致使有关人员产生错误判断,做出错误行为;胁迫是指当事人以对有关人员造成一定危害相恐吓、或强制他人处于恐怖状态、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出的行为;暴力是指采取激烈的强硬手段迫使有关人员就范的行为。在学理上依据“毒树之果(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论(3)可以把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划分为“毒树”和“毒果”。
在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中,“毒树”证据毫无疑问是应该排除的证据,但“毒果”证据是否也应该一律不予采信而加以排除,如何判断“毒果”的证据效力则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司法实践部门主张,对于“毒树之果”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未说明如何判断与区分。[11]有学者认为:“至于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理论,不能在行政程序(或诉讼)中适用。因为行政程序的问题与人权保障毕竟没有刑事诉讼严重,而行政诉讼必须讲究效率,所以以违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发现并收集了其他证据时,后发现并收集的证据应该有证据能力。”[12]也有学者提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非法证据中的“非法”是以调查取证措施本身违法为前提的。如果调查取证措施本身并不违法,相应的证据也就不构成“非法”。行政执法人员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取合法措施调查收集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违法性,应属于合法证据。[13]另外有学者主张可将行政机关非法取证的行为按主观恶性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构成犯罪的违法取证行为,第二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取证行为,第三是轻微违法的取证行为,前两种情形应界定为非法证据。[14]
对行政诉讼领域中“毒果”的证据效力的判断,要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行综合分析,同时也应充分考虑行政效率问题。笔者认为,可将“毒果”证据的效力认定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行政相对人的重大违法行为,如处以拘留、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执法部门在调查时取得的“毒果”证据应认定为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例如,工商机关做出吊销营业执照处罚时,采用胁迫手段取得证据线索,然后通过该线索取得相对人走私物资的证据。在此时,因为对于重大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往往给予较重的处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重大权益,所以,基于自然公正(Nature Justice)原则,在追求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之间,我们应选择程序正义,这也使得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过程中取得平衡。法院对行政机关据此“毒果”证据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并以此作为证明行政机关严重程序违法的证据。例如,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了被告人的口供,然后根据口供的内容发现了相关的物证——赃物,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毒果”的定案效力,就有违公正之基本理念。
第二,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轻微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取得的“毒果”证据应认定为合法证据而予以采信。例如,在交警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的简易处罚中,交警在未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主动做出供述,交警根据供述的内容再获得有关证据,这时,获取的证据不宜排除。事实上,美国确立“毒树之果”原则后,又设置了若干例外,这些例外包括“独立来源”的例外、“最终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15]现代行政要求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的同时,要兼顾效率原则,达到简略、迅速和经济的目的,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为了避免事倍功半和时过境迁,及时查处重大违法行为,通过认定“毒果”证据为合法证据,达成促进行政效率提高的目的。行政诉讼毕竟是为了解决行政纠纷,对纠纷的解决也要考虑到司法效率和行政效率问题。如果忽略效率原则,有可能会导致审判中可以利用的证据大大减少,拖延案件审理期限,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另外,就目前行政执法水平及司法审判现状来看,排除一切违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是不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第三,非执法部门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毒果”证据应认定为合法证据而予以采信。行政机关掌握巨大的权力,权力的行使必须公平而且有效率。[16]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行政权的确定力、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势实力形成显著差异,两者在法律地位上明显不平等,而自然公正原则要求行政诉讼法应该为相对人在行政主体实施行为过程中争取主动、避错远罚服务,为抗争行政机关可能做出的恃强凌弱行为提供法律武器。例如,在工伤认定之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自行收集提供的支持工伤结论的“毒果”证据。通过认定相对人提供的“毒果”证据为合法证据,可以缩小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不对等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双方在权利和义务分配方面的不对等得以恢复均衡。
四、以秘密手段获取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以秘密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属于非法证据,其中秘密调查手段包括偷拍、偷录、窃听等方法。但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在采用正常方法难以取证的情况下,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秘密取证也是合法的。事实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亦规定了“秘密取证”的明示或默示的条文,例如,《产品质量法(修正)》第18条第1款规定,质监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对当事人涉嫌从事违反本法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笔者认为,现场检查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拍摄、录音等方式,该条款默示授权质监部门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依照法定职权可以采取拍摄、录音或者窃听等手段。所以,执法人员在做出处罚或许可等行政行为时进行秘密录音、录像所收集的视听资料不应认定为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
另外,行政相对人或与案件无关的公民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采取偷录、偷拍等手段取得的执法行为活动的视听资料,亦不构成违法。理由如下: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是公开进行的,行政相对人或与案件无关的公民在未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拍摄、录制等方式获取的证据,不存在侵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妨碍行政机关活动的问题,所以不构成违法;二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相对人,处于被管理的弱势地位,其获得证据较为困难,特别是获得行政执法违法的证据更加困难,如果将这种证据定位为违法,显然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例如,请求工伤认定的劳动者,无论在财力、精力、知识和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第三,只要经审查这类证据是真实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审判成本和查清案件事实的行政诉讼价值标准也要求采信此类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1995年3月6日)的批复中认为:“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方式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实际上是对诉讼中采取秘密方式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的否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规定第70条第2项同时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品。”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对采取偷拍、偷录等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上,给予了一定的宽容。《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第58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57条第2项规定:“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旧的《批复》与新的《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相矛盾的情况下,应适用新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以秘密调查手段取得的证据并不当然属于应该排除的非法证据,还必须同时具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条件,才构成非法证据。例如,行政机关在没有行政法律规范的特别授权或者没有履行内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窃听他人电话,偷录他人私生活等获得的影音资料证据,该证据已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予以排除。
除“毒树之果”证据和以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外,依据《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的规定,应该予以认定和排除的证据包括其他几种类型:第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第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第三,域外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第四,在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五,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第六,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第七,其他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情况非常复杂,《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不可能穷尽列出。因此,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规定了“口袋”条款(其他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以避免遇有特殊情况无法可依的情况。
注释:
(1)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采用违法手段和方法获得的证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笔者分别予以阐述,“毒树之果”是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
(2)“警察圈套”(entrapment)是最常见的利诱手段,该问题已由几位学者作过具体论述,本文不再重复,具体内容可参阅,廖万里:《略论美国刑法中的警察圈套及其借鉴意义》,《法学家》2001年第3期。何家弘、龙宗智:《诱惑侦查与侦查圈套》,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3)“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 (Sliverthorne LumberCo. Vs.U.S.A)(1920)判例确立的一项美国宪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1]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J].中国法学,1993(3):89—94.
[2]商文艳.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1(3):80—86.
[3]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3.
[4]何家弘.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之构想[J].法学家,2001(6):56—63.
[5]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J].法学研究,1988(4):18—23.
[6]徐益初.论口供的审查和判断[J].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3):7—12.
[7]刘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23—26.
[8]徐鹤南.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排除[J].政法论坛,1996(3):39—44.
[9]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证据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231.
[10]余川、程辉、葛娟娟.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法律科学,2001,(3):108—113.
[11]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25.
[12]朱新力.论行政诉讼中的事实问题及其审查[J].中国法学,1999(4):76—83.
[13]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93.
[14]金诚.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J].行政法学研究,2002(4):65—69.
[15]汪海燕.论美国毒树之果原则——兼论对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启示[J].比较法研究,2002(1):70—76.
[1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1.
(责任编辑 吴兴国)
D925.3
A
1001-862X(2012)02-0139-005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FX044),本文同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9YJC820101)和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烟台大学应用法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杨曙光(1975-),男,山东寿光人,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和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