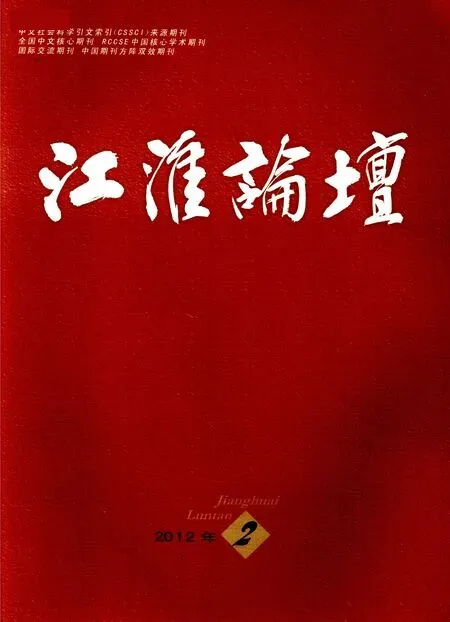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张瑞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山东青岛 266555)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张瑞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山东青岛 266555)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二分”;“圆融”;宋明理学;方法论
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以五月遗腹,念其父秦台公,别号念台;晚年更号克念子,以励其学;后讲学于浙江省山阴县城北蕺山,自称蕺山长,后世学者尊其为蕺山夫子。据蕺山子刘汋(1613-1664,字伯绳)所撰《蕺山刘子年谱》记载,蕺山 67岁曾撰《存疑杂著》,将先儒二分对待的诸哲学理念作统合阐释,“举凡先儒分析支离之说,先生皆统而一之”,并有如是断言:“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先儒意见:“心”与“性”对,“性”与“情”对,“心”统“性”与“情”,分“人欲”为“人心”、“天理”为“道心”,分“性”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分“未发”为“静”、“已发”为“动”。 而在蕺山这里:“性者心之性也”、“情者性之情也”、“心之性情”、“心只有人心。人心,人之心也”、“道心者,心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为心也”、“性只有气质之性”、“义理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存发只是一机”、“动静只是一理”。[1]147-148《蕺山刘子年谱》评论蕺山的这段文字,虽有失实之处,(1)却道出了蕺山学的特点,并为学者所推崇。如劳思光先生说,蕺山“合‘道与器’、‘理与气’、‘道心与人心’等等对别概念而为一之特殊观点”是“刘氏说中之最大特色”,[2]429故以“合一观”名之。牟宗三先生曾对刘汋的这种说法表示批评,认为它“无实义,乃故作惊人之笔之险语”,“即使可以这样一之,又何碍于分别说耶?若胶着于此而讲其学之性格,必迷失旨归而至于面目全非”[3]321,但亦承认蕺山对先儒诸哲学理念“一之”之实。实际上,蕺山对宋明儒诸哲学理念的统合方法,可视为他哲学思辨方法的展示,本文称之为“一体圆融”思维。这一思维方法是对先儒“二分”思维的超越,是宋明理学方法论的新走向。
一、宋明理学诸家的“二分”思维
宋明理学家对先秦以来的诸哲学理念,如心性情、动与静、尊德性与道问学、已发与未发、中与和等等,在参考、借鉴释道相关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加以诠释,理论深度不可谓不深,但思辨逻辑依然停留在概念间的 “二分”、“对待”基础之上。
比如张载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孟子主张“性善”,告子主张“生之为性”,佛教主张“佛性”。张载则认为此三种对性的认识皆有偏执,从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他在《诚明》篇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4]23人在形成过程中,禀受阴阳二气,人的身体条件、形体各有不同,从而造成人的“气质之性”之差别,是兼有善恶。“天地之性”则是“太虚”本性,纯一至善。具体而言,所谓“气质之性”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人生来俱有的属性,“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4]22,此“攻取之性”即“气质之性”;其二,人与物所共有与个有之性,“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 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4]281草木与人皆为“物”,皆有“气质”,只是“气质”有“清浊”,“清气”为人,“浊气”为物;其三,“气质”可变,“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4]321,变化气质便是迁善改过,克去“气质”中恶的成分,而达致“天地之性”。所谓“天地之性”,则是较“气质之性”高一层次的“太虚”本性,为“圣人之性”,其本质表现:其一,“天地之性”是永恒的,“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4]7;其二,“天地之性”是善的,“性未成则善恶混,故舋舋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4]23;其三,“天地之性”是“和”与“乐”,“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4]24。 在张载看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既相分别,又相融合,“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4]21。 说“一源”,表示二者皆来源于“太虚之气”,一于“气”。张载“性二元论”不仅说明了一般人与“圣贤”之间的不同,亦说明了人可以通过变化气质而“知礼成性”,反本为“圣”。[5]224-228张载对人性论的分析较前辈更为完善、合理,但其性论的“二分法”已然人为预设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落入双方、人物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之中。
至于解“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天理”与“人欲”、“涵养”与“省察”、“知”与“行”、“心”与“性”、“性”与“情”、“理”与“气”等等,周、程、张、朱、陆等宋明大儒皆未能脱离“二分对待”思维。张立文先生说:“(朱熹)在理论上陷入了‘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格物’与‘穷理’、‘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二分和对待之中。曾与朱熹‘道学’相抗衡的陆九渊,尽管觉察到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这个矛盾,但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沿用程、朱观点,即使在论述‘心’与‘理’的关系中,有把‘心’与‘理’并列的价值取向,说明他还处在一种未圆融之中。”[5]484那么,王阳明是否就实现了“心”与“理”、“心”与“物”的圆融呢?从前者讲,阳明的确是“消解”了朱子以来的“心”与“理”的二分,其“心即理”论断将“心”与“理”圆融。但是,阳明“心外无物”的论断,却未将“心”与“物”圆融,终究亦是设定了自我 “心”之外的 “非我”——“物”——作为自我“心”的对待面,这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是“二元对待”结构。
那么,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否打破了“二元对待”思维呢?客观地说,“知行合一”论已经有打破二元思维的倾向。比如,“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6]4-5;“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6]43真知即是行,行便是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与“行”圆融一体。但是,阳明之“知”是“心”之“知”,“检验是非之‘知’的标准,不是孔子和朱熹的言论,而是心体”[5]513。将“知”归根于“心”之“知”,一方面可以反对权威崇拜、反对教条,解放思想,但另一方面却是无限张扬“个体”,是从“权威”、“束缚”倒向“纯粹自由”、“绝对自由”,是由一个“本体”到另一个“本体”的转换,而不是对“本体”之惟一性、绝对性的打破。所以,阳明在思维方法上有新观念的提出,却又囿于自己的“良知”框架,终究亦是在打破权威时走向“自我的绝对化”。
单纯从思辨方法上讲,我们须重视朱熹的“一分为二”法。朱熹之方法建基于邵雍“一分为二”命题和二程“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并吸收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维。朱熹学生甘节记载:“问:‘先生以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又细分将去。程子曰:“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敦颐)亦止分到五行住,若要细分,则如《易》样分。 ’”[7]105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 程颐只分到“四”,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只是分到“五”,而朱熹则把它无限延续下去,在解释《周易·系辞传》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便指出:“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二尔。 ”[7]1651关于“分”的内容,《朱子语类》这样记载:“问:‘去岁闻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体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慈、孝是用。’”[7]102“体”便是本质,“用”即是表象,“二”在性质上与“一”是不同的。那么“一”为何?朱子说:“‘一’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用处不同。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 ”[7]2511即是说,“一”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对待的“两端”,它们各有用处,却又不可分割。一端须以另一端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相对待双方存在于统一体中。对待双方终究要落于“一”,统一到“理”。所谓“二”,朱熹说:“东之与西,上之与下,以至于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也。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故程先生尝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7]1324万事万物间自然有差别,有差别便有事物间的联系。这从理解事物存在本质而言,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朱子之论是为其“理”本体论服务的。[5]48-49
尽管说朱熹的“一分为二”方法在阐释“气”与“物”的进程中效果不错,能够清楚梳理二者关系,但毕竟是为其“理一”之本体服务。“一分为二”理论看到了事物间的差异,将张载“一物两体”之“两”的认识发挥到极致。之后,方以智则提出“合二为一”说,注重阐释相异事物间的通合性。他在《三征》篇中指出:“曰有,曰无,两端是也。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器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事物之间有对待的“两端”,两端自然要“交”,从而“合二而一”[8]39-40。看到差别的事物之间有联系、交往,就其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而成为一个“关系体”言,固然真实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但是,方以智非要探寻出一个终极的“一”,将差异的、联系的事物之本质归位于“几”、“真天”、“真阳”,如在《三征》篇说:“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征矣。”[8]57在《反因》篇说:“有天地对待之天,有不可对待之天;有阴阳对待之阳,有不落阴阳之阳;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故曰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真一统万一,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8]94他依然坚持“无对待”的形上学本体,显然还是未能跳出“一元”实性本体论窠臼。
认识到事物之间有差异,固然是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深化;将差异的事物“合二为一”,实现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明确化,亦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若非要为差异的事物寻求一个终极的“一”,则必然走向极端。综合来看“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之说,在承认它们的积极性的同时,亦应看到它们的理论偏颇:要么偏向“一分为二”的易简化分析,崇尚“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为制造“非此即彼”的取舍推理和“两败俱伤”的价值冲突;要么偏向“合二而一”的简单化综合,崇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一,人为设计“亦此亦彼”的二元混淆和“无可无不可”的随意掺和;要么否定之否定,斗争与同一阶段性极化,分析与综合周期性震荡。[9]51
二、刘宗周的“圆融”思维
刘蕺山在处理先儒所涉及到的哲学理念时,采取的是与“对待”、“二分”思维不同的另外一种思维,可称为“一体圆融”思维。这一思维可通过“即~即~”来表达。要充分体会哲学理念间的“即~即~”圆融关系,必须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即~”与“即~”二者相对独立,各有蕴涵与意义;第二,“即~”与“即~”二者不可割裂开来,应该在相对相生的存有状态下互相理解;第三,前者“即~”为根基,但由后者“即~”来体认、反思,二者不离不弃,和合一体。有学者曾以“辩证的思路”来说明蕺山阐论哲学概念的特征:思想家们并不以一套人为设计的、分解的存有论层序之理论架构,来区分、来框套,以及来解释天地万物及人类的生命、社会、历史与文化等,而是直接就整个实存的宇宙人生之大化流行来说本体,并认为本体之中含有相反而又相成、相灭而又相生,同时互为隐显,浑然相融的两股势能或动力,如阴与阳、翕与辟或静与动等,而由于它们彼此不断地相互起作用,不断地一阴一阳、一翕一辟或一静一动等,因而带动了整个实存的宇宙人生之生生不息和永续发展。[10]49但是,“辩证的思路”并未能就刘宗周处理哲学概念间关系的具体步骤、逻辑理路有清晰说明。
蕺山早在1613年《与以建二》书信中便主张哲学理念间的融合通贯。他说:“道形而上者,虽上而不离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学而上达。下学非只在洒扫应对小节,凡未离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处在方寸隐微中。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形上形下之说也。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惧之功焉。”[11]299李明辉先生在诠释这句话中的“即”之涵义时,指出:“这个‘即’字既非表示逻辑意义的A=A,亦不可理解为象山、阳明就心之自我立法而言‘心即理’之‘即’,更不同于天台宗以非分解的、诡谲的方式说‘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无明即法性’之‘即’。这个‘即’字当是意谓‘虽形下者,而形上者即在其中’或‘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之义。”[12]正由于形上寓于形下、形下内蕴形上,那么,为学之“应然之则”便是立定下学而实现上达,在形下工夫中彰显天命之性。这样的观点在《虞书》便是“精一”,在孔门便是“克己”,在《易》便是“洗心”,在《大学》、《中庸》便是“慎独”,在周子便是“一”,在朱子便是“主敬”,在阳明便是“致良知”,本质一同。归根结底,形下之处世应物与形上之性天道体“无显微,无精粗,无内外,无动静,无大小,无之非下学,则无之非上达”,凡是将形上与形下分割、下学与上达对立的观点都不合蕺山之意。故而,在蕺山哲学思辨逻辑中,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便构成了 “即形下即形上”、“即器即道”的关系。
统合来看,蕺山以“一体圆融”思维来阐释的哲学理念主要表现为 “即形下即形上”、“即气即理”、“即器即道”、“即心即理”、“即心即性”、“即性即独”、“即性即情”、“即存养即省察”、“即隐微即显发”、“即知即行”、“即本体即工夫”、“即心即易”、“即太极即阴阳”等对偶范畴。我们可进一步以蕺山论“隐微”与“显发”关系来说明他“一体圆融”思维的特点。
在蕺山看来,言“隐微”,自然有“显发”之时;言“显发”,必然有“隐微”之存。蕺山1643年《学言》曰:“《中庸》之道,从闇入门,而托体于微,操功于敬,一步步推入,至于上天之载,而乃能合天下以在宥。愈微,亦愈显;即微即显,亦无微无显;亦无有无无,仍举而归之曰‘微’。呜呼!微乎!至矣哉。”[13]463无微不显,无显不微,即微即显。无论是情,还是容貌辞气、言谈举止、五伦百行,皆有其内心之隐微之理则,各种过错之显发,亦从内里之妄念开显出来。正如《人谱·证人要旨》所言:“独体本无动静,而动念其端倪也。动而生阳,七情著焉”[13]6;“慎独之学,既于动念上卜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诚于中者形于外,容貌辞气之间有为之符者矣”[13]7;“故学者工夫,自慎独以来,根心生色,畅于四肢,自当发于事业,而其大者,先授之五伦。”[13]8人们审视围绕自身而展开的各种行为言论,其发源之地正是人之“内心”,万事万物皆渊导于根深凝集之隐微自心。因此,从隐微处下手用工夫,便会得力。《人谱·改过说一》有如此之论:“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则时时知过,时时改过。俄而授之隐过矣,当念过便从当念改;又授之显过矣,当身过便从当身改;又授之大过矣,当境过当境改;又授之丛过矣,随事过随事改。改之则复于无过,可喜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虽然,且得无改乎?凡此皆却妄还真之路,而工夫吃紧,总在微处得力云。”[13]17由此可说,微处用力便可防微杜渐,而隐微与显发之关系亦可从中明晰,即“即隐微即显发”,隐微是显发之源起,显发是隐微之彰明。从根本来说,隐微之地当是“本心”诚明处,其显发之所自然合德符节、循规守矩,莫不各有其必然之理、当然之则。人所犯之过,亦是因个体之“心”的隐微之地妄念有生而起,改过之进路自然于此端始,方可药到病除。
正因为“隐微”与“显发”间有如此关系,蕺山在阐释“体用”关系时亦遵循如此之理。他在1642年《答叶润山三》书信中说:“所示‘体用一原’之说,乃先儒卓见道体而后有是言。只今以读书为一项事,做官为一项事,岂得成体用?更复何一何原?须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无用非体,无体非用。盖自其可见者而言,则谓之用;自其不可见者而言,则谓之体:非截然有两事也。日用之间,持而循之,便是下学;反身之地,嘿而成之,即是悟机。此所谓即学即达,非别有一不可思议之境界也。……惟其无微非显,是以无体非用;惟其显微无间,是以体用一原。”[11]370-371按照蕺山之意,体与用并非二分,“自其可见者而言,则谓之用;自其不可见者而言,则谓之体”,“体”者隐微之理,“用”者显发之见,日用之间虽不见“体”却不离“体”,反身之地虽无显发但必有其“用”。隐微之地不可见,但有体隐;显发之地有其见,故有用显。“即隐微即显发”,显微无间,故而“体用一原”。
正是运用这个思维方式,刘宗周将先儒“二分”的诸哲学理念统合圆融;也正是运用了这一思维,蕺山才提出了冠之以各种概念的“盈天地间皆~”的哲学论断。如《学言》:“盈天地间皆道也,学者须是择乎中庸”[13]365;“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13]407;“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13]418;“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13]479-480;“盈天地间皆理也”[13]480;“盈天地间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13]482;“盈天地间,皆物也”[13]279;“盈天地间,皆仁也,则尽人仁也”[13]329;“盈天地间,皆易也;盈天地间之易,皆人也。”[13]122等等。乍看来,蕺山言语之中似充满矛盾,属于为学 “无主”之论,曾遭到学者批评。(2)实际上,蕺山这些言论是要通过“一体圆融”思维来开显他别具特色的“本体论”。
蕺山1637年《学言》说:“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有气斯有数,有数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后起也。而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气乎?”[13]407显然,蕺山不认为“理生气”、“理在气先”,而主张“有气斯有理”、“有气斯有道”,“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13]410。同时,蕺山还认为:“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一也。人未尝假贷于天,犹之物未尝假贷于人,此物未尝假贷于彼物,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物物各具一太极。’自太极之统体而言,苍苍之天亦物也。自太极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各有一天也。 ”[13]408也就是说,事事物物作为存在者,都有其道理、必然之理、当然之则,就它们有“理”言,作为“气”而存在者的“物”本质上就是“理”的化身。这样,气与理、道间便形成“即气即理”、“即气即道”的关系,气与理圆融通贯。 换言之,“理”与“气”、“道”与“器”并无“生成”关系,而是“含蕴”、“圆融”、“共生”、“共存”的关系。 “理”必然内蕴于“气”、“道”必然内蕴于“器”,反之,“气”自然与“理”同在,“理即是气之理”;“器”自然与“道”同在,“有气斯有道”。 “理”与“气”、“道”与“器”彰显出“共生”、“共存”特性。 蕺山言“盈天地间皆~”之“~”,并非是以“~”为“宇宙生成”的“本根”,而是将“~”所表达的“所以然之道”、“所当然之理”与万事万物相通贯圆融,凸显“理念”与“存有”、“形上”与“形下”的“共生”、“共存”属性。正是如此“共生”、“共存”属性,蕺山以之为“本体”,谓之“太极”,“太极之统体而言,苍苍之天亦物也。自太极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各有一天也”。
在蕺山哲学逻辑结构中,“太极”之本质为“生生”。他1634年所撰《圣学宗要》论濂溪《太极图说》指出:“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阳生阴,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而合之只是一个生意,此造化之蕴也。”[13]230-231蕺山《周易古文钞》释《易·系辞下》“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时,指出:“于是圣人分明指示道体,曰‘易有太极’,盖曰道无道,即乾坤之生生而不息者是,是以乾坤列而四象与八卦相蕴而生。此易道之所以为至也。强名之曰‘太极’,而实非另有一物立于两仪、四象之前也。 ”[14]234-235蕺山认为“太极”之本质意蕴乃是“生生”。“生生”并不是指生成的某个结果,而是事物、要素之间共生、互蕴的共存关系,以及由这样的关系制约所达致的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在此“生生”之意下,物与物之间是互相体现、互相显像的。“太极”生生,从而“动”便体现为“阳”,“静”便体现为“阴”;“阳”之根为“阴”,“阴”之根为“阳”,阴阳互为其根,阴阳动静互蕴,故而“动”与“静”生生不息,有“动”自然有“静”,有“静”定会开显出“动”。或许正是从此意义上,黄宗羲以“太极为万物之总名”为蕺山“发先儒之所未发之论”的四方面之一。(3)
总之,刘宗周出入宋明儒学诸家,转变先儒阐论哲学理念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新创 “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儒学“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注释:
(1)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分始于张载。张载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宋]张载.张载集·正蒙·大心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8:24.)即此可说,“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非从王阳明始有。“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亦始于张载。自朱子门人以后,“天地之性”亦称为“义理之性”,而非程子始有此分。(参见:李明辉.刘蕺山对朱子理气论的批判[J].汉学研究,2001(2):23.)
(2)如侯外庐先生说:“刘宗周的理学思想是一个充满自相矛盾的体系。”(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 (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09.)于化民先生指出:“刘宗周的本体论思想是令人眩惑的,因为他的著作中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观点并出。”(转引自: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169.)郑宗义先生亦有论:“(蕺山)这样混淆了圆融说与分别说的不同层次,遂可以说出一些极为不称理之言。……明显于此窒碍不通。”(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60.)
(3)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指出,蕺山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其大端有四:“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清]黄宗羲.子刘子行状[Z]//刘宗周全集(第6册):39-40.)
[1][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六册)[M].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宋]朱熹.朱子语类[M].[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清]方以智.东西均注释[M].庞朴,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9]张立文.和合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陈立驤.宋明儒学新论[M].高雄復文图书出版社,2005.
[11][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三册)[M].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12]李明辉.刘蕺山对朱子理气论的批判[J].汉学研究,2001,(2):1-37.
[13][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M].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14][明]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一册)[M].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吴 勇)
B248
A
1001-862X(2012)02-0086-0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蕺山后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11YJCZH23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张瑞涛(1977-),山东肥城人,副教授,博士,当代中国哲学名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