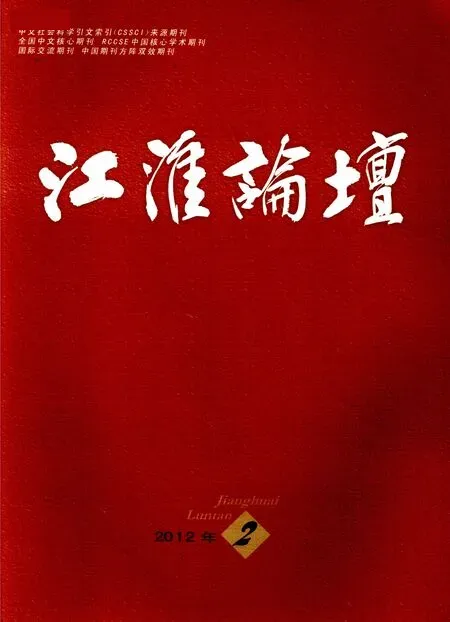现代人文化和谐发展:生态批评的理性审视
李金泽
(亳州师专中文系,安徽亳州 236800)
现代人文化和谐发展:生态批评的理性审视
李金泽
(亳州师专中文系,安徽亳州 236800)
“生态批评”在探索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引入生态主义理论,提倡自然界生命整体主义,主张尊重生命,以此建立生命平等的和谐生态理论,开始了文学艺术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在当代生态批评实践中,对长期占据人类文化思想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予深刻的反思,既有极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理性地审视当代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中,如何辩证地看待人类中心主义?需要在尊重生命平等、生态和谐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人文化的精神观照,理性地建设符合现代人文思想的和谐生态。
生态批评;人文化关怀;和谐发展;理性建构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旨在探索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1]我国较早研究生态批评的学者王诺说:“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思想的合理性,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
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生态整体主义,也称生态主义。当前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美学研究者大都从生态主义出发,建立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和谐生态哲学观。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人提出生态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人文主义的终结,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物种频频消失的现实,提出反人文主义的质问:“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问:这是人文主义的必由之道吗?”[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态主义,以此反对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就把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起来,引入生态整体论,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人主张生态批评不能离开人文关怀,要在生态批评中引入人文关怀。那么,如何正确理解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绝对对立,在反对惟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的人文性话语,坚守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的生态主义理论。在生态批评视域中,融入现代人文关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审视当前的生态建设,进而建立理性的生态批评理论,将会对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尊重生命的和谐:生态主义的积极意义
王诺说:“20世纪的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2]建立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主义否定人类是世界的标尺,主张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体,尊重万物存在的权力。
以生命平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生态主义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对长期占据人类思维中心地位的人文主义予以质问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义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标尺,对自然万物有主宰的作用。在这一传统思想支配下,人类文明发展进入现代化高度。但同时,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毁灭的现实,让人类自身产生了行将毁灭的恐惧。生态主义认为,这一后果的产生,人文主义应负主要责任。在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生态主义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立生命整体论,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来追求。整体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维度。
生态主义首要的主张是“自然为本”,回归自然。在生态主义看来,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生态主义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无度地劫掠、挥霍大自然的资源,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直接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己。呵护自然,呵护生命,是人类必须选择的新的生存价值和文明取向。
因此,生态主义极力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论。在生态主义看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失去理性的狂躁中,向自然界索取无限的物质利益,并且以破坏或毁灭自然的方式索取,以此满足人类自身的现实发展欲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了人类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成就显赫,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类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物质文明的突进与道德良知的低落形成鲜明的对比,暴露出的是人类发展与建设的狭隘群体利益观、消费享受价值观,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严重摧残。环境恶化、部分物种相继灭绝、能源越来越紧张、生命健康伤害事件此起彼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任务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人类的文明建设与发展进行反思,找出我们文化思想内在的自私、狭隘与欲望无边,进而建立新的发展观和生存观念。在这种反思基础上,生态主义提出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带来生态批评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
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这是生态主义的先进性。在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似乎对立的思想中,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概念——环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系统,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都在为人类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可能。而生态主义则对环境主义提出批评,认为环境主义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生态主义提出“生命圈平等主义”观点,主张在生命圈内一切生命都同样拥有生活、繁荣的权力,并在更大的空间中实现自身的整体发展,在这个整体生命圈内,人类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其他生命形式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这一观点就是自然界整体观,在理想化的建设想象中给自然界的发展描画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理想蓝图。生态主义从根本上质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生态主义理论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借以警示人类:在实现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和谐的生命圈。这成为生态主义的进步性与合理性的理论支撑。
生态主义影响着文学作出新的“思想转向”,对传统文学中的“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和“惟发展观”等都作出了现实性的诘问和批判。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从传统的高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转向对自然界是一个大生命圈的观念的认同,以此探寻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新的文化思想内涵。因此,生态批评带来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思想革命,对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思维方式的变革都将产生新的启示,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文学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生态批评中,是否绝对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视野下,人文主义对和谐生态的建设还有没有现实关怀价值?
二、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的非理性想象
要辩证地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有其历史性的缺陷,也有其对现实和未来世界建设的合理性。反人类中心主义只是生态批评的一种非理性想象。
生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沿用了这一理论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环境对人类的服务价值相反,生态主义否定环境为人类服务的价值性质,强调人与自然界里其他生物共生共存,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成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化。这就否定了人类的“中心”地位。
生态批评不仅否定人类中心地位,而且指责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性。生态批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反思,以期建立新的文化思想。王诺说:“生态批评起始于思想文化批判,也扬名于思想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对促使人们认清人类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在当下的生态批评实践中,多数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反自然”的,是重发展而轻生命的。于是,在生态批评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性”加以批判。很多生态批评的文章对传统文化中的“反自然”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传统文化具有‘反自然’的性质,不仅不承认自然价值,而且常常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4]“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生态主义首先与对西方传统文化整体上的哲学反思有关。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哲学的影响很大。”[5]生态批评的任务就被限定在以文学的形式来反思人类文明现象中的非自然性,也就是非生态性,叙述经济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审美现代性背景下的生态灾难和人类自身的困惑,从而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合理性。通过反思与重构,文学领域出现了生态小说、生态报告文学、生态散文等文学形式。一些评论家也撰写大量的生态批评论文,对生态批评进行理论系统建构、解释。而这些反思与建构,大多都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对立视角来思考的。
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真的就没有合理性吗?人类如果不成为世界(包括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中心,那么世界就会进入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无中心,特别是没有精神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一个多元化的生命世界,这是一种返回自然本真状态的无序元态,人类在世界中不再成为引领万物的灵魂,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维系依靠种类之间的自然化调节,人类在世界中的智慧调节缩小到人类种族自身利益结构的调节。而且,无中心,实际上就是多个中心,多种物种争相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宰,那将带来自然界更加混乱。二是另一种物种进入自然界的中心,这种物种必须具有在精神上引领万物的价值意义。事实上,现在还没有某一个物种能够代替人类实现这种价值意义。人类的智慧决定了人类可能成为自然世界的灵魂,发挥着引领自然万物和谐生存与延续的积极作用。
生态主义是建立在反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生态主义在道德伦理层面建立生命平等的整体利益观,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基本权利分享;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更多的是在世界精神层面建立人文关怀的责任价值观,强调的是宇宙的精神价值引领,两者并不绝对对立。造成自然界生态结构失衡的根源并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于人类价值实践的非理性,人类在自身价值观念的调整上失去了理性,过度的追求狭隘利益的最大化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而且,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是不同地域、国家之间的社会制度、法律严重分裂,各自在利益的争夺与责任承担上严重脱离人类设定的共同的精神价值。在这种缺乏价值关怀的自然界秩序中,过于激进的生态主义将会带来社会公正性的偏离。
实际上,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在于:人类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追求降低到物质利益的占有与享受上,不要把自己的欲望极限化,不要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扭曲万物生命的存在形式。为什么现在的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把自身利益的实现建立在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上,人性中的私欲扩大化、极限化带来了自然界的生命失衡,扭曲了万物的自由生存与发展。在自然界的发展演进中,人类整体的智慧、人类的实践经验,都决定着人类在自然界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依然存在,人类在生态平衡中积极调节的价值作用依然存在。
人类的智慧可以支持自身成为自然界的中心,引领自然界的精神价值发展。但是人类在成为中心的同时,不要忘记这一中心是建立在自然界内部的,而不是自然界外部;中心的一切支撑条件都存在于自然界内部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生存结构平衡有利于中心地位的保持,反之,则会带来中心地位的动摇。在文化思想重建中,应该强化的是,人类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进化。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人类就必然与自然界的非人类物种、物质相关联,就要保证它们的生命更好地存在与发展,建立和谐稳定的生态结构。人类的责任在于在坚守自然界生命圈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下,寻找适合于自身更好发展的道路,这种道路既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消极避退,也不是经济利益至上、消费享乐主义式的畸形盲动;而是尊重生态发展的自然规律,尊重生命,和谐发展,保持持续发展的潜力,树立动态发展、持续发展的思想,建立大人类思想的发展理念,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放在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长远利益背景下去思考与筹划,避免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发展,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人类自身的和谐,这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关怀。事实上,“在人类对危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类的主体性开始走向了成熟,进而提出了理性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还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但它内在包含着尊重自然的逻辑要求,认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共同发展。 ”[6]
三、现代人文化和谐发展:生态批评的理想建构
现代人文化和谐发展是一种理性化的生态观念,其根本思想就是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融入人类主体性的积极的人文关怀,在和谐生态建设中人类仍然发挥着积极主导作用,建设现代人文化的和谐生态。这是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结合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是生态批评的理性思维方式。
人文化和谐生态带给人类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生态,这种理想化的审美生态的实现离不开人类的自觉。在生态文学中,人文化的和谐生态自觉表现为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反思人类自身在自然生态建设中的狭隘性,借以启发人类思考自身发展与自然生态失衡的现实,反省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二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人文关怀,从和谐生态的角度,运用现代美学的目光,理性探索人类在和谐生态建设道路上的经验和想象,勾画具有现代人文关怀价值的和谐生态的理想蓝图。
和谐生态要求人类对自身的文明史给以理性的审视,而不能一概而论其善恶对错。关于对生态灾难的批评,很多生态文学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科技的发展与和谐生态的关系,一些生态文学主观地认为,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工业化进步,同时带来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困境,想象人类回归到非科技化的自然生存境界和自然化的发展方式中去。不管是西方的《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还是中国的 《狼图腾》、《伐木者,醒来》,都有这样的思想。
事实上,科学技术并没有罪恶,罪恶仍然在于人性自身。和谐生态的建设仍然离不开以人的智慧为主要因素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科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科技的发展必然促进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程度的加深,认知广度的扩大,推动人类更加科学地认识世界;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会促进人类自身精神文明的变革与提升。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没有先进的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生态失衡的原因之一是科技成果使用者自身的生态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错位,盲目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对自然界资源的最大保护。科技本身是要发展的,借助科技发展社会的宇宙观也要发展,要随顺自然规律适时调整人类自身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当下急需调整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思路,摒弃惟发展主义理念,弱化人类的贪欲,强化生命平等意识。这就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都树立和谐生态的理念,在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中积极发挥人的智慧,建设具有现代人文化关怀的和谐生态。
生态批评尤其要担当起这一历史责任。生态批评的理想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题之一。但是,在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中,还存在着生态意识不强、观点分歧较多的现象。文学作品尽管已经涉及生态主题,但是,文学家对生态的理念建构还缺乏相关的经济学、人类学的知识支撑;另一方面,一些生态文学重生态概念的解释,走入重“生态”轻“文学”的误区,恰恰暴露了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人文化关怀不够。生态文学最应该做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不可把生态学与文学拼凑起来。事实上,“真正把生态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从人类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去把握文学的生命意蕴和人学内涵,似乎不是很多。 ”[7]
综观生态文学创作的现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批评中,必须坚守现代人文化的和谐生态思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深化认识:
一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尊重自然万物共同体的生存权力。生态批评主张人与自然界的一切非人类物质都是生命体的存在形式,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都认为,在自然界这个大生命共同体内,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同样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人类不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违背自然规律去扭曲、伤害、扼杀其他生命体。尽管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和发展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发展,但是,人类不可否定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权力,只能减少对自然界物质的索取,拒绝人类自身的盲目发展,或者改善自身发展的方式与途径,维护自然界的最大保护。需要明确的是,不仅仅是人类,任何一种生命体都不能过度膨胀以至于挤压其他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否则,自然界仍然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发展困境,甚至走向灭亡。生态批评的目的是反思人类自身发展中存在着的错误的文化思想观念,反思人类欲望的膨胀带来了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的事实,进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凸显人对自然生态的关怀与悲悯。生态批评既不能盲目地宣扬反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能在生态文学创作或批评实践中,无意之中揉进人类独尊的旧观念。必须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现代人文化的和谐生态观念,这样才能在反思与探索中寻找到新的出路。一些论者在生态批评中仓惶地宣扬回归到先民的社会时代,走入历史倒退的胡同,明显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极端否定。相反,另一些论者仍然在宣扬人类中心主义具有绝对合理性,这也是不符合现代人文化和谐生态建设思想的。
二是尊重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生态和谐理念视域中,人类的发展总会带有自私性,人类不会为了其他生命体的发展而毁灭人类总体的生存与基本发展。生态批评仍然不能否定把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实现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视点,而是要打破地域、民族限制,更好地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大利益观。在自然界中,人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过去、现在,也有未来,现在的发展不能回归到纯自然发展的原始状态,也不能为了现在的发展而断绝未来发展之路。在文学创作中也要树立人类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彰显人性中善良、宽容的生命悯恤,文学在艺术化的叙事中,启发人类自身怎样找到适合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理想,设计我们美好的未来家园。
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不能停留在灾难叙事和仇恨的宣泄上,而是要转向建设和谐生态的理性思考。和谐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不可停留的,而是更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去发展。这在人类美好生活理想的建构中提出了一个思考:什么才是人类的理想生活和社会。实际上,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诗意栖居,这是人类一直未变的理想追求。诗意栖居要靠两个条件来支撑:一是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生存环境和谐;二是人类自身理性的价值调节。中国历代文人,都不乏在文学中描画这一理想的例子。陶渊明《归园田居》描绘的就是一种诗意生活,王维的山水诗同样充溢着回归自然、享受天籁美妙的士人理想,庄子的文章更是构思着自然、和谐的人生画图。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是,文人们的田园式生活都有一个根,就是农村生活,他们把农村生活作为田园生活的样板来进行诗意勾画。那么,士人们的农村生活真的就是一种天上人间吗?事实上,古代文人诗中淳朴自然的农村生活对立的是险恶奸诈的官场,不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生态意义上的诗意栖居。工业化带来了城市与农村都无法逃脱的生态失衡,而且农村比城市更加严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双重落后,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思想困惑。消除这一困惑,还是必须树立发展的思想,不发展,理想就难以实现。与农村生活相对应,城市建设明显先进于农村,最能体现现代化的特征。但是,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同时最能显示出人类发展的不科学、不和谐。城市生活的孤岛性,人际关系的隔膜化,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精神焦虑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理想还是要回归现实,在和谐生态建构中,人的因素依然很重要,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依然是和谐生态的一个主题。近年来的一些生态文学在关注人类自身健康生存、和谐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李青松的报告文学《茶油时代》从人类健康食用油料的角度为现实生活提出了新的启发与智慧。何建明的《中国式风流——右玉纪事》叙述了山西省右玉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位县委书记持之以恒地植树造林、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动人事迹,其中高扬的是人在自然生态建设中的智慧和勇气。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是一部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急与种种困境的生态散文,既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也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在万物人格化的艺术表达中,融入人道主义思考。
在和谐生态建设的催生下,现代人文化关怀的和谐生态必将成为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向度。
[1]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
[2]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
[3]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J].文艺研究,2002,(5).
[4]余谋昌.生态哲学与可持续发展[M]//党圣元.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1.
[5]党圣元,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M]//党圣元.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6]吴博.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7]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J].理论与创作,2006,(1).
(责任编辑 岳毅平)
I206.7
A
1001-862X(2012)02-0178-006
李金泽(1968-),男,汉族,安徽蒙城县人,亳州师专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