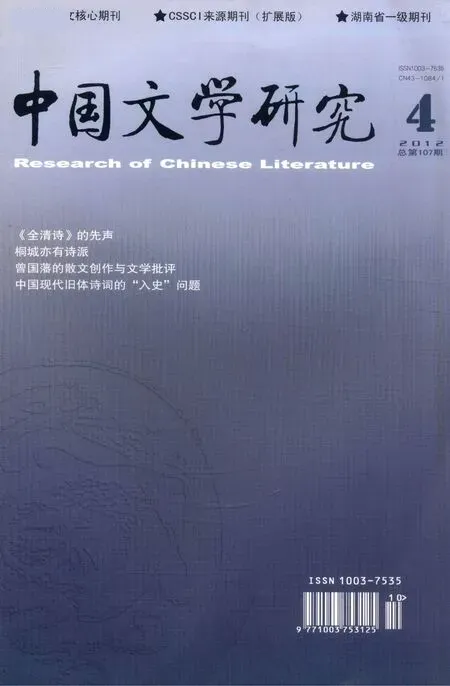《全清诗》的先声
朱则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系统、完整编纂为分体断代的全集,这是学术发展的一种标志,也是无数学人的一项追求。以诗歌而论,清朝康熙皇帝敕编的《全唐诗》,就是一个范例。时至今日,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到《全明诗》,或已成书,或已立项,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已经配套成龙。唯独古代最后的《全清诗》,始终未能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关于编纂《全清诗》的动议,却早在此前百年左右就一再有人反复提出过。现在根据所见资料,将有关情况分组考述于次。
一、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胡玉缙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出版机构之一,创办于清末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数年之后,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张元济先生投身该馆,继而在馆内建立编译所并长期主持各项事务。该馆自办《东方杂志》月刊(后曾改为半月刊),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二十五日(公历1908年11月18日)发行的第五卷第10号(期),刊登有这样一篇《征求诗文集启》(原无页码):
本朝开国已二百余年,文风之盛,远轶前代。本馆拟仿《全唐文》、《全唐诗》之例,纂辑国朝诗、文。惟是见闻有限,加以近人专集刻本无多,访求不易,用特敬告海内著作家、藏书家,如有前人及生存人之诗文,无论刻本、稿本,祈挂号寄交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收到后,按月将目录登载《东方杂志》,以志谢忱。如系不易购求之刻本,乞示明价目,本馆或备价寄奉,或从速钞录,仍将原书挂号寄还。其未刻之稿本,无论全集、零篇,亦希寄示;如无副本,钞录后仍即挂号寄还,想亦大雅君子之所许也。再,寄书时,能将著者生平大略见示,尤为厚幸。商务印书馆谨启。
其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历1908年12月18日)发行的第五卷第11号,同样有类似启事,标题改为《商务印书馆征求国朝诗文集启》,正文仅删去“访求不易”、三处“挂号”以及“想亦大雅君子之所许也”,并在最末添上:“兹将第一次所收书籍表列如下,其次序依收书先后为准。”又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09年1月16日)发行的第五卷第12号,次年宣统元年己酉闰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09年4月15日)、三月二十五日(5月14日)、六月二十五日(8月10日)发行的第六卷第3号、第4号、第7号,启事所涉书单依次改为“第二次”至“第五次”,其他内容基本相同,唯第六卷第3号的标题脱漏“国朝”二字。
以上凡六篇启事,都是以“补白”插页的形式出现,一般置于杂志卷首,只有第五卷第11号置于卷中。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今某些收藏单位的《东方杂志》旧刊合订本或其影印本,往往遗漏不收,翻检不到。笔者也是刚刚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古籍·民国专栏·民国期刊”内的影像扫描本,得以完整读到各篇的原文。并且从内容来看,此六篇刚好配套。至于后面各期是否还有,则未尽查检,姑置不论。
上述启事根本的动机,都在于“纂辑国朝诗、文”,而又是“拟仿《全唐文》、《全唐诗》之例”,这就等于说编纂《全清文》、《全清诗》。配合这个动机,商务印书馆做了一系列“征求国朝诗文集”的工作,并且确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是启事刊登之时,本身还处在“国朝”,清王朝尚未灭亡,也不能预料。因此,这里所谓“全清”的“全”字,即使从时段上来看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与今天所说《全清诗》的概念并不完全相等。
启事刊登之后,不但社会上有人响应寄书,而且学术界也有人出谋献策。著名文献学家胡玉缙所撰《许廎学林》,卷二十有一篇《与张菊生元济论纂辑全清诗文书》;兹以“诗”为中心,将其前后相关者抄录于次:
前见贵馆《征求诗文集启》,欲仿《全唐诗》、《文》之例,纂辑全清诗、文。窃叹如此盛举,非贵馆财力不能办。但二者浩如烟海,几有“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之概。嗣见第一次所收书籍表,尤为庞杂。固由寄者不明贵馆之意,业已寄到,则不得不收耳。最后有“非为清人刻专集”之广告,而贵馆之宗旨,于是晓然于海内。以臆见论之,当时纂辑《全唐诗》、《文》,亦各有蓝本。此次文当以《皇清文颖》……为蓝本,诗当以《国朝练音集》(王辅铭编)、《皇清诗选》(孙鋐编)、《国雅集》(陈允衡编)、《感旧集》(王士祯编)、《湖海诗传》(王昶编。其王士禛《十子诗选》、吴伟业《太仓十子》、宋荦《江左十五子》、阮元《两浙輶轩录》等,亦当及之)为蓝本,再益以其他各集,并诸人之所未及见者,如此则似较扼要,而亦易于蒇功。惟二十世纪时代与十九世纪不同,其中亦须斟酌,当以不悖于科学者为断。如陆燿以雷为气之所为,必当甄录;刘大櫆以雷亦虫之一类,必当删汰。……诗本陶写性情,然更汗牛充栋,似亦宜以征实者为归。但此类不多,当视文为从宽耳。其体例,当以一人归一人,以其人之先后为次;另编目录,则以类相从,各题下注明某人;再仿《两浙輶轩录》之例,别以其人之姓,依韵编次,各注卷数于下。如是则体例颇雅,而人必以为便,当可风行矣。偶有所见,聊贡于右,惟台从裁之。〔1〕(P483-484)
这里提到的“最后有‘非为清人刻专集’之广告”,不知载于何处。但从“嗣见第一次所收书籍表”云云与称“国朝诗、文”为“全清诗、文”综合推测,此函大约写于清朝灭亡后不久。只是据所谓“扼要”、“斟酌”、“删汰”,以及“诗……亦宜以征实者为归”而又“当视文为从宽”之类的提法,可以想见胡玉缙这里理解的“纂辑全清诗、文”,实际上乃是编纂有清一代诗、文的选本,而并非今天所说的编纂《全清诗》、《全清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最新出版的《张元济全集》,前三卷(册)均为“书信”,但其中未见有答复胡玉缙者。因此,张元济(菊生其字)先生的原意或者说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是否果真如胡玉缙所理解,这一点还不能确断。但不管怎么说,“全清诗”的这个名称,至少已经在模糊使用。
附带关于胡玉缙此函作为“蓝本”列举的五种清诗总集,第一种《国朝练音集》实际上是关于江苏嘉定一县(今上海嘉定区)的地方类诗歌总集(嘉定又称“练川”),而这里似乎把它误解作了全国类诗歌总集。
二、胡怀琛、高旭、王葆桢
民国初,南社创始人之一高旭,曾拟编纂《变雅楼三十年诗征》。该书最终似乎没有编成,但由之引起的讨论以及预写的序言之类却很多。其中社友胡怀琛有一篇所谓《再复高剑公书》,部分内容像是涉及《全清诗》:
……尊辑范围限于三十年,自是一体裁;顾弟别有一见,谓从来一代诗文,类有集为大成者。以诗而论,唐有《全唐诗》,宋有《宋诗纪事》、《续宋诗纪事》,金有《中州集》,元有《元诗纪事》(近人陈衍辑),明有《列朝诗集》、《明诗综》;即如五季匆匆代谢,李雨村犹惜其文献无存,为集《全五代诗》五十卷。有清一代,此书尚付缺如,吾固知后必有为之者,今尚未见也,公有意乎?又尝论清时选本之巨者,乾隆以前推沈氏《别裁集》,清之末叶推孙氏《诗史》。顾一则止于乾隆,一则起于道光;自乾隆之末,历嘉庆以迄道光之初,其间尚有数十年,合两书尚不得为完璧。《别裁集》成于清之盛时,明遗民诗以触忌不收者极多;《诗史》所收,公卿多,布衣少,是两集之缺陷也。此外如渔洋《感旧集》,限于朋旧;简斋《同人集》,更不足言矣。合观上说,益知此举不可少。着手之法,无妨以上举各集为蓝本,更博采旁搜以补之。得一郡一邑“诗征”、“诗存”等,不啻得专集百数十种。若专集之多,收不胜收,尽耳目之力可耳。大抵晚近专集,佳者甚少,然一集之中,终必有一二首可收者,不得轻弃之也。昨剑华来访,亦与谈及此。尊意若何,尚祈教之。
此函原载民国三年(1914)七月出版的《南社》杂志第十集①,主要是建议高旭(剑公其号)将编纂对象的时间范围扩大到整个清代。不过,这里所列举的“从来一代诗文……集为大成者”,只有《全唐诗》、《全五代诗》这两种属于《全清诗》的同类著作,其他都属于选本的性质。又其下文“蓝本”云云,与前述胡玉缙该函相类似;所举四种清诗总集——沈德潜辑《国朝诗别裁集》、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以及王士祯(禛)辑《感旧集》、袁枚辑《续同人集》,同样也都明确是“选本”②。而其具体的“着手之法”,一方面说“博采旁搜”,另一方面对于“专集”亦即单家别集,却仅仅是“尽耳目之力”搜集,并择取内部“可收者”而已。因此,胡怀琛这里的意思,与今天所说的编纂《全清诗》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至于函末附带提及的“剑华”,指“南社四剑”中的俞锷(剑华其字),他有没有发表意见不得而知。
然而,高旭在《答胡寄尘书》中,却反复使用了“全清诗”的名称:
诵手书,甚佩。中解“以人存诗”二说,其识尤超。……弟原亦有此意,可谓所见略同。至所辑限于三十年者,乃依据孟子“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大都为所见者也。公进以《全清诗》之宏议,伟则伟矣,奈收拾颇不易何?况收拾即易易,而非我侪所思存者乎?盖满清一代,所谓学士文人,大半依附末光,戕贼性灵,拜扬虏廷,恬不知羞;虽有雄文,已无当于大雅。惟三十年来,则千奇万变,为汉、唐后未有之局。……故诗选之作,以三十年为断,……又何必《全清诗》之始为完备哉!古人选诗有二:一则取一代之诗,撷精华,综宏博,……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所载之诗,与国史相为表里者是也;一则交游之所赠、性情之所嗜,偶有会心,辄操管而录之……
此函原载民国四年(1915)五月出版的《南社》第十四集③;现今也可见郭长海、金菊贞两位先生合编的《高旭集》卷二十二〔2〕(P538-539),属于下编《天梅遗集补编》,唯文字多有错误。从所谓“诗选之作”、“古人选诗”云云,以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本身的性质,可以确切知道这里的两处《全清诗》都是指有清一代的诗歌选本,而并非今天所说的《全清诗》。
胡怀琛后来又写有一篇《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正文如下:
高剑公尝辑《三十年诗征》,其友人胡怀琛闻之,寓书以辑《全清诗》相勉。剑公复书,有曰:“世事之变,以近三十年来为最亟。故诗之奇,莫奇于此;诗之正,亦莫正于此。读三十年诗者,可以观学术之蝉蜕、政治之变迁,不特诗也。”此言甚当,吾于是乃知剑公之用心矣。黄岩王葆桢,亦剑公旧友也;昨岁与余遇于沪上,颇有意于《全清诗》事。又闻同社景耀月,欲作《清诗存》,其意盖与余略同。今剑公《诗征》既成,若更为此,或亦为今日应有事。吾闻“合力,事则易成”。今同志有人,公抑愿彼此相助,以成巨帙乎?公命予为《诗征》序,再以此意进之,即书于卷端云。
此序原载民国五年(1916)四月出版的《南社》第十六集④,末署写作时间为“民国四年(1915)春”。其开头所谓“寓书以辑《全清诗》相勉”,明显接受了高旭复函所用的“全清诗”名称,而内涵自然也与高旭所说相同。
此外,胡怀琛此序还提到另一社友王葆桢“颇有意于《全清诗》事”,这应该也是指编纂有清一代的诗歌选本而非今天所说的《全清诗》。至于景耀月“欲作《清诗存》”,则从书名即可确知其属于选本一类。而“其意盖与余略同”,可以进一步证明胡怀琛等人所说的《全清诗》都是选本。
三、邹永修、纪钜维、徐世昌
邹永修《烟海楼文集》卷五,有一篇《与纪悔轩世丈论编全清诗书》,中间具体论述如下:
乃者,大总统徐公搜采诸家别集,为《全清诗》,开馆编排,聘世丈为主纂。逖闻欢忭,无可言宣。徐总统稽古右文,保存风教。輶轩逸典,再见于今。甚盛,甚盛!夫诗,与史相表里也。萃一代之诗,可以观一代之政。此其为业,岂仅与富四海、首庶物较短长哉?世丈耆宿灵光,风骚泰斗;覈量文质,精讨锱铢;发前哲之幽光,显逸才于来世;搜岩剔穴,侧陋俱扬。则赤水不至有遗漏之珠,而丹山不患无朋从之凤。网罗如此,勤渠如此,其功其德,宏博何如!惟编录条章,无因窥测,其照康熙时之《全唐》、《全金》乎?抑仿吴之振之录宋、顾嗣立之选元、朱彝尊之综明也?两者料量,缥缃俱富,知不止归愚《别裁》、兰泉《湖海》也已。粤稽逊清诸老,若吴(梅村)若王(渔洋),若朱(竹垞)若查(初白),若施(愚山)若宋(绵津),若冯(定远)若毛(西河),若厉(樊榭)若黄(两当),若欧阳(涧东)若王(湘绮),一代作者,与古同符;即弗表扬,已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盖久已家有其书,脍炙人口。所恨者,布衣韦带之伦,名不出于里闾,籍不登于仕版,竭毕生心血,短咏长吟,大而国典朝章,细而劳人思妇,形诸歌曲,伤心感人,而无人阐彰,遂埋没于荒烟蔓草之中,不知凡几,虽曰命也,谁之过欤?徐总统创为是举,蓝田之玉,从此生烟;廿二省风谣、三百年篇什,传诸千古,毗[媲]美列朝。永修为徐公与世丈贺者犹浅,为近世骚人不得志于时者幸实深焉。⑤
按邹永修为湖南新化人,清末曾经留学日本,后来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此函提到的“大总统徐公”,指的是徐世昌。
徐世昌于民国七年(1918)十月至十一年(1922)六月期间任总统。就任次年,在总统府内创设“晚晴簃诗社”,又称“晚晴簃选诗社”,延聘名流,行文征诗,从事选录清代诗歌的工作。黄山民《徐世昌之秘密》第十八章《徐世昌之晚晴簃》,说当初曾有人这样“进言”:
兹值开国之初,尧舜在位,宜将全清诗诠选合刊,以成一代巨制。如前清钦定《全唐诗》,向称一朝盛典。今既有“晚晴簃”之设,名公巨卿、硕彦鸿儒咸萃于此,苟能建此鸿业,不仅足为诗学前途无穷之利,而“晚晴簃”之盛名亦昭垂千古矣。〔3〕(P23)
这段话关于“全清诗”,虽然举《全唐诗》为例,但明确说是“诠选”,因此属于选本的性质。《徐世昌之秘密》一书,据其卷首序言署款及出版时间,写于徐世昌下野当月,并且对徐世昌持讽刺的态度。其下文以为徐世昌并非真正有心编纂,“此项之建议,遂消灭于无形”,“‘晚晴簃’之……寿命,亦随徐世昌之总统而告终”〔3〕(P23),这个判断与后来的实际并不相符。
徐世昌在下野之后,更加集中精力“诠选”清诗,终于在民国十八年(1929)由其退耕堂刻印成书。该集原名《清诗汇》,后来考虑到作者多有入民国之人,因此即更名为《晚晴簃诗汇》。全书凡二百卷,入选作家多达六千一百六十八人,是目前单种规模最大的一部清诗总集。当然,它的性质,仍然属于选本,而并非《全清诗》。
现在再回头来看上引邹永修该函,它显然写于徐世昌在任期间,并且对徐世昌的编纂宗旨还不了解。但也恰恰因为如此,所以邹永修做出了两种猜测:一种是像吴之振等人合辑《宋诗钞》、顾嗣立辑《元诗选》、朱彝尊辑《明诗综》那样的大型清诗选本,即后来果真如此的《晚晴簃诗汇》;另一种则是像康熙皇帝敕编《全唐诗》和《全金诗》那样的有清一代诗歌全集,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的《全清诗》。
邹永修该函所致的对象纪钜维(悔轩其号),河北献县人,系纪昀五世孙。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拔贡,曾官霸州训导、内阁中书。后长期游于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又历主各地书院。宣统三年(1911)“辛亥北归,伏居里閈”。民国九年(1920)“庚申八月避盗,卒于天津旅次,年七十有三”。⑥其现存著作,只有后人搜集编印的《泊居剩稿》、《续编》各一卷,所收作品都很少。《泊居剩稿》初编,经翻检未见有致邹永修的复函;《续编》虽未寓目,但猜想情况很可能也是如此。所以,纪钜维是否参与过《全清诗》的讨论,这一点目前还无法确定。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影印《诗歌总集丛刊·清诗卷》本《晚晴簃诗汇》卷首,有一篇当事人闵尔昌所写的《记晚晴簃诗汇》〔4〕(P1-2),其中列有“晚晴簃诗社”当初延聘的名流名单;该名单除去因“以后不复至、不常至”而“不备举”的“数君”不详之外,未见有纪钜维其人。结合纪钜维晚年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在谢世前夕是否果真曾被聘为“主纂”,甚至是否参加过“晚晴簃诗社”,这也都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总之,邹永修致函纪钜维讨论《全清诗》,从纪钜维的角度来看,也许仅仅是缘于某种传闻。不过尽管如此,毕竟该函是明确写给纪钜维的,所以我们还是把他也算在里面。
附带关于邹永修该函的实际动机,乃在于末尾所说的“汇集寒门遗稿”为《邹氏一家言》,寄请纪钜维予以采择。但该处提到的湖南新化邹氏作家凡十二人,《晚晴簃诗汇》仅入选其中邹汉勋(字叔绩)、邹湘倜(字资山)二人,分别见于卷一百五十三〔5〕(P6679)、卷一百四十四〔6〕(P6307)。由此看来,该函事实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里的原因,撇开选录原则不论,一个是可能该函确实没有到达纪钜维的手里,再一个就是纪钜维确实没有参与《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工作。
上述商务印书馆等三组机构和个人,每组都提到了《全清诗》。虽然根据目前的考察,他们所说的《全清诗》基本上不是我们今天的概念,但至少这个名称已经被多次提出,并且颇有与《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以及《全唐文》等分体断代作品全集特别是诗歌全集相提并论甚至完全等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他们视为《全清诗》的先声,应当是不以为过的。
在上述三组机构和个人之外,截止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是否还有其他机构或个人也曾有过类似关于《全清诗》的提法,目前还不得而知。至如抗日战争前后张翰仪辑《湘雅摭残》卷十四吴士萱小传,称其“于近代二百余年诗人之有专集者尤刻意搜求,撷精取华,手录不辍”,编为《全清诗录》云云〔7〕(P643),则因书名带一“录”字,明显与《全清诗》无涉。
此后率先正式提出编纂《全清诗》的建议的,是已故郭绍虞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复刊号的《从悼念到建议》一文⑦。本师钱仲联先生写于1991年的《自传》,也说晚年“曾有编纂《全清诗》的愿望,限于种种条件,要想从事,力不从心”⑧。两年之后,以多位钱门弟子为主要组织者,若干单位联合成立了《全清诗》编纂筹备委员会,并聘请仲联师担任首席顾问。只是为外部条件所限,一直未能正式开编。现在学术大环境和相关资料的积累,都远胜从前,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在这个时候回溯《全清诗》的先声,未尝不具有一种激励的意义。
本文大致写成于2012年元旦前后,上距清朝灭亡刚好一百周年。
〔注释〕
①见《南社》第十集“南社文录”,第26a-27a页。作者原被误作陈世宜,可参见门下夏勇同学博士学位论文《清诗总集研究(通论)》第一章《清诗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流变》第二节《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第四部分《清代之后》有关注释,浙江大学2011年3月,第63页。又关于此函及下文所述高旭复函,该处正文也曾大致论及。
②原函关于“清时选本”的具体论述,以及上文关于《全五代诗》卷数的提法等,多有不准确之处。
③见《南社》第十四集“南社文录”,第34b-35a页。胡怀琛字寄尘。
④见《南社》第十六集“南社文录”,第15a-b页。
⑤见《民国文集丛刊》第一编第140册,第192-194页。此函承湖南新化文史爱好者曾俊甫先生提供线索并录入文字,特此致谢。
⑥参见纪钜维《泊居剩稿》卷首所附《传略》,民国十四年(1925)排印本,第1a-b页。
⑦详见《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第156页。
⑧见《钱仲联自传》,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5页。另曹正文先生《珍藏的签名本》内《情系清诗六十年——记钱仲联》一文,曾提到八十年代末访问钱老时,“他正带领学生编一套规模宏大的《全清诗》”,“他说,他早在1930年就想编清诗全集”。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9页。不过,此处至少前者所指实际为《清诗纪事》。
〔1〕胡玉缙.许廎学林〔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2〕高旭.高旭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山民.徐世昌之秘密〔M〕.民国十一年(1922)新学印书局排印本.
〔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上册)〔Z〕.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5〕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8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0.
〔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0.
〔7〕张翰仪.湘雅摭残〔Z〕.长沙:岳麓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