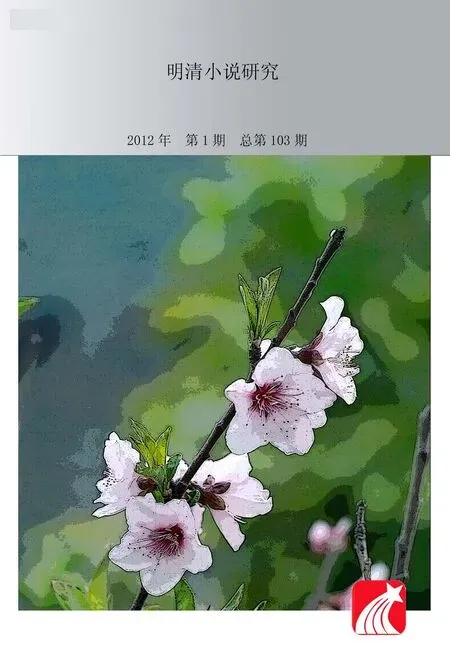祭赛·斗法·精变
——古代小说所反映之宗教神异民俗文化的斑斑点点
· ·
在中国古代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宗教”总是要和“神异”挂上钩的,否则,就不能显示宗教的力量。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其他宗教教派,其中法术道行高超者,总会留下一些神异的传说故事。同时,这些宗教领域的“大腕”之所以能美名流传千古,又多半是由于他们战胜了同样法术道行很高的反面神异人物的结果,民间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对于普普通通的“凡人”而言,那些邪恶的“魔”,却仍然是神通广大而且不可战胜的。于是,人民群众就特别需要某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英雄人物来战胜那些“邪魔”,还人民一份安全。
在上述这些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故事中,有些问题,如祭赛、斗法、精变等,尤为广大民众津津乐道。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传说故事又自然而然为小说作者所摄取,写入自己的作品中间。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个特定的角度——古代小说所反映之宗教神异民俗文化。
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祭赛
何谓“祭赛”?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就是“祭祀酬神”。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作品中,对这种宗教民俗活动多有描写。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戏曲方面的例证:
元·无名氏《来生债》第一折:“先生,还有一等无端的小人,到那腊月三十日晚夕,将那香灯花果祭赛,道是钱呵,你到俺家里来波!”①
元·李寿卿《伍员吹箫》第三折:“我这丹阳县中有个牛王庙儿,秋收之后,这一村疃人家轮流着祭赛这牛王社。”②
元·无名氏《盆儿鬼》第二折:“(净云)你说是甚么神道?等我好香灯花果祭赛你波。(正末云)我就是你家瓦窑神。”③
明·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自家钦差识宝使臣苗舜宾便是。三年任满,例当祭赛多宝菩萨。”④第三十一出:“【红绣鞋】〔众〕吉日祭赛城隍,城隍。归神谢土安康,安康。祭旗纛,犒军装。阵头儿,谁抵当?箭眼里,好遮藏。”⑤
清·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老夫住在燕子矶边,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路过此间。”⑥
以上祭赛活动所酬谢之神灵,有钱神、牛王、瓦窑神、多宝菩萨、城隍、福德星君,可谓形形色色;而祭赛者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求发财的,有求丰收的,有求包庇的,有求得宝的,有求安康的,亦可谓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却是所有祭赛活动所共有的,人们巴结神灵,希望自己得到好处。因此,从根本上讲,祭赛就是一项民众希望得到护佑而讨好神灵的“公益事业”。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些邪神精怪却利用了老百姓的这种宗教文化心理,借着自己的妖法,强制性地要百姓“祭赛”自己,而且,祭品是极其不人道的“活人”,多半是童男童女。
较之古典戏曲而言,在古代小说中,写得更多的却是这种被扭曲的“祭赛”。某些邪神精怪要以童男童女为祭品,否则就要危害一方,善良无助的百姓为此不知贡献了多少亲生骨肉。当然,最后还是正义战胜邪恶,总有“神”或“非神”的英雄为民解难,消灭邪魔精怪,拯救弱小善良。
谈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祭赛”情节,一般读者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西游记》第四十七回所描写的发生在通天河边的故事。原来通天河上有一个“灵感大王”,虽能“年年庄上施甘雨,岁岁村中落庆云”,但却“一年一次祭赛,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猪羊牲醴供献他,他一顿吃了”⑦。这一年该陈家庄的童男童女献祭,幸亏碰上唐僧师徒,悟空变做童男,八戒变做童女,救了两个小孩性命,这就是典型的宗教文化中的正义力量战胜非正义力量的事例。
然而,《西游记》的作者绝非小说作品中祭赛故事的发明者,早在六朝志怪《搜神记·李寄》中,就有关于祭赛的描写:“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⑧最后,这个罪恶的蛇精终被少年女英雄李寄消灭。
《搜神记》中的故事较之《西游记》所写,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李寄是奋勇自救,陈家姐弟则是圣僧所救。其二,巨蛇是土生土长的妖精,吃人本属正常;而金鱼精则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⑨。就第一点而言,《西游记》显然不如《搜神记》,因为陈家的童男童女在故事中不过摆设而已,而李寄却显得光彩照人。但就第二点而言,则《搜神记》不如《西游记》,因为金鱼精凭着从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里学来的手段,却去残害童男童女。这就具有讽刺意味了。
自从《西游记》描写了精彩异常的“金木垂慈救小童”的故事以后,中国古代小说写到这种祭赛情节的作品就绵延不绝了。请看数例:
此处有一乌龙大王,连年要办童男童女祭赛,方得村中一年无事,若无童男童女祭赛,一年不得平安,自然起瘟出瘴。(《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第八回)⑩
这神仙叫做神火至尊,离此半里路,有个庙宇,是他的香火,年年到了四月十五日,小人们备办猪羊,扛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儿,到庙中去献他,等他吃了,然后下秧种田,那年收成,定有二十分,就是小人们也都健旺,没有疾病。若一年不去献他,或无活人,不是田荒,就是人死,家家弄得七零八落,小人不能生活了。(《后三国石珠演义》第六回)
我们这庄上,三年前来了个青头大王,甚是厉害。一到庄上,连鸡犬牛羊都抓了去,又会飞砂走石,驾雾腾云,了当不得。我们没奈何,请了本处的道士,前来没坛打蘸,讨个阔面。每年春秋二季祭他。尔时节,童男童女整猪整羊前去,俱祭到晚,一庄人家.各人都关了门,清清净净的。倘有一些儿不好,不是行瘟,便是来抓人。(《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第三十二回)
铁马溪出一妖怪,常吃行人,而今官马大道由山左转去,溪无人行。妖肆淫威,即于沿村攫人而食,合村人等焚香溪岸,计以每月供二孩子。今日轮流是老,彼子已没,只此一孙,供妖食之,则宗嗣绝矣。故妇不舍,叟亦伤神,欲弗从同,又议出合村,难以傲众。(《绣云阁》第三十六回)
以上这些妖精,都要童男童女作为祭物,然后吃掉。有的一年吃一对,有的春秋两祭都要吃,有的甚至一个月就要吃掉两个孩子。如若不祭赛童男童女,妖精们无一例外地就要兴风作浪,危害一方。碰到这样的妖精,老百姓真正是苦不堪言。幸而,每一个故事中总会有一个正面的神灵或英雄人物来扫除妖孽,为民除害。这样的故事,所反映的其实是封建时代的一般民众对于来自大自然的种种危害——如瘟疫、干旱、水灾、风暴等等的恐惧感和无可奈何的心理,同时,也反映了广大读者急需强有力的英雄救民于水火的愿望。然而,我们不可忽视其间的“人为”因素。因为几乎所有的妖精都是幻化成“人”的形态来欺压善良的。而且,他们手段之卑劣、心性之歹毒、气量之狭小完全像那些街头巷尾的黑道小混混,像那些称霸一方的地头蛇。总之,这些要吃童男童女的妖精形象,其实正是“天灾”“人祸”相加的结果,是天灾人祸在普通民众心头痛苦记忆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
以上所言,乃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祭赛”的一般故事,但也有些故事具有特别的意味。例如清初小说《飞龙全传》中有一位市井无赖郑恩,此人还是一个饕餮大王。有一次,他混吃了别人一顿食物,被掌柜的骂作“黑吃大王”,并说“你遇着我们白吃大王,他有本事生嚼你这位黑吃大王”。这一下可把这位莽汉惹火了,于是,出现了以下这段对话:
郑恩听说,立住了脚问道:“乐子问你,那个白吃大王如今现在那里?待乐子与他会会。”掌柜的道:“你黑吃了东西,心满意足,只管走路,莫要管这闲帐。”郑恩道:“咱偏要问你,你若不说,乐子又要打哩。”掌柜的慌忙答道:“我们这位白吃大王,要吃的是童男童女,不象你这黑吃大王,只会吃些酒肉。所以劝你保全了性命,走你的路罢,休要在此惹祸生非,致有后悔。”郑恩听罢,心下想道:“这大王要吃童男童女,决定是个妖精,咱何不替这一方除了大害?”(第十四回)
在这里,作者通过“黑吃大王”“白吃大王”的调侃,表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毒攻毒。结果,“黑吃大王”郑恩果然帮助地方小民铲除了妖精“白吃大王”,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实正是一种以毒攻毒、以暴抗暴的民众心理情结的发泄。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在郑恩这位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生动形象身上,英雄的、正义的、善良的一面毕竟是其主旋律,而那种扰民的、无赖的、丑恶的一面不过是其性格的变奏曲而已。
《飞龙全传》以外,还有“祭赛”故事的另一种变体。如《反唐演义全传》中的薛蛟、薛葵所降服的吃童男童女的妖精,却不是动物或者植物修炼成精,而是另一种怪异:“这村东有座花豹山,山上有座四神祠,内有四位神道,一名白龙大王,一名大头大王,一名银灵将军,一名乌显将军,十分灵验。年年本月十三日,用童男二个、童女二个前去祭他,他若吃了,这村中一年平安,田禾丰收;如不去祭他,便家家生病,田禾不收,所以年年去祭他。”那么,这些精怪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在薛家兄弟消灭了他们之后,妖精们“都现了原形,伏于地上”(第六十三回)。变成了薛家兄弟的武器和坐骑。这样一种故事范型,已经与本文第三个专题——“精变”发生情节意象的交叉了,我们只好在后面再详加论述。
二、斗法
宗教传说中的高手,都是有“法术”的,如果两个以上的有法术的“佛”或“道”遇到一起并发生矛盾,就会斗法。当然,更多的时候则是仙佛中正邪两派之间的斗法。
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斗法的片断极多,有的也非常精彩。但是,我们在研究斗法之前,还得先来见识一下得道之人的高超法术。且看一例:
又是一日,偶与乖崖对食,陈抟失口嗽了一声,喷出一口饭来,登时变作数百个大蜂,向外飞去。陈抟饮了一口茶,将口张开,那些飞去的大蜂,依旧飞到口中,陈抟嚼之,仍旧是饭。(《二刻醒世恒言》第九回)
陈抟老祖的这些法术在凡夫俗子看来,当然是神乎其技的。但是,若与齐天大圣孙悟空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孙大圣的本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筋斗云、绝食法、隐身术、分身术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如行山阴道中。
然而,孙大圣的许多法术都是渊源有自的。例如他的上述本领都是源自唐代话本《叶净能诗》中对叶净能的描写:“一旦意欲游行,心士只在须臾。日行三万五万里,若不餐,动经三十五十日;要餐,顿可食六七十料不足。或即隐身没影,即便化作一百个人。”
孙大圣还有一样法术,就是对着某物或某人吹一口仙气,就能随心所欲地将其变成另外一样东西或另外一个人。一次,在车迟国,当鹿力大仙剖腹剜心与孙悟空赌法力时,“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着一只饿鹰,展开翅爪,嗖的把他五脏心肝,尽情抓去,不知飞向何方受用”(《西游记》第四十六回)。
有时候,神仙们不用吹仙气,而采取用水“噀”的方法,效果也是一样的。而这种“噀”法早在唐人小说中就屡见不鲜了。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茅安道》篇中写道士茅安道为救二徒,施展法术,“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噀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
这段故事后来又被明代拟话本作家周清源在其《西湖二集·韩晋公人奁两赠》一篇中翻译改写成了地道的白话小说片断:“茅安道就走到韩公案前,把砚池中水一齐吸了,向二子一喷,二子便登时脱了枷锁变成两个大老鼠在阶前东西乱跑。茅安道把身子一耸,变成一只大饿老鹰,每一只爪抓了一个老鼠,飞入云中而去,竟不知去向。”
其实,不仅老道精于此道,就连猴精也会“噀”法,不过此猴精不是《西游记》中的孙大圣,而是他的原型老祖“猴行者”而已。在宋元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中就有这样的描写:“猴行者一去数里借问,见有一人家,鱼舟系树,门挂蓑衣。然小行者被他作法,变作一个驴儿,吊在厅前。驴儿见猴行者来,非常叫啖。猴行者便问主人:‘我小行者买菜从何去也?’主人曰:‘今早有小行者到此,被我变作驴儿,见在此中。’猴行者当下怒发,却将主人家新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主人曰:‘我新妇何处去也?’猴行者曰:‘驴子口边青草一束,便是你家新妇。’主人曰:‘然你也会邪法?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今告师兄,放还我家新妇。’猴行者曰:‘你且放还我小行者。’主人噀水一口,驴子便成行者。猴行者噀水一口,青草化成新妇。”
当然,这段故事中猴行者的“噀”,已经不是单纯的卖弄法术了,因为有了玩弄法术的对立面,于是,就演变成为“斗法”了。
古时候,各种宗教流派为了显示自身的不同凡响,往往自我吹嘘,甚至吹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而普通民众在接受了这种各派别的自吹自擂以后,往往又会添枝加叶,进一步宣扬各宗教派别通天彻地、呼风唤雨的本领。而将这些内容写进小说作品之后,就成为僧道仙妖斗法的精彩片断。
僧道仙妖们斗法的方式是五彩缤纷而又复杂多变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噀”法以外,还有变化后钻入对方肚内而有效打击敌人的方法。《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惯用此法,如第五十九回对付铁扇公主、第六十六回对付黄眉大王、第六十七回对付长蛇精、第七十五回对付青狮精、第八十二回对付老鼠精等等,都是运用的这种出奇制胜的办法。然而,若认为这种特殊的斗法方式乃是《西游记》作者的首创,那可又大错特错了。早在宋元说经话本中就出现了对这种法术的描写:“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白虎精闻语,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如此描写,不仅使这些神话故事兴味盎然、妙趣横生,而且,还平添了几分童话趣味。因为,少年儿童最喜欢这种“捉迷藏”式的法术游戏。
还有一种斗法方式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的“变”。这种法术游戏最开始是在魏晋小说中出现的。署名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樊夫人》一篇中,写樊夫人与其丈夫刘纲斗法戏耍,甚为有趣:“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之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其鱼。”
后来,明清小说中的某些作品又将这种游戏发展为比赛变金银。如《七真祖师列仙传》下卷写马丹阳与其夫人孙不二斗法:“夫人遂将门外拳石拿了几块,付与丹阳。丹阳接住,将石拳了一拳,伸手递与夫人,说道:‘这就是银子。换些钱钞,家中使用。’夫人接在手内,呵呵大笑:‘将石子拳成银子,有甚出奇?你好比井里打水江边卖,孔子面前讲《孝经》。’夫人也将石子拳了一拳,变了金子,将手一伸,道:‘你看这是甚么?’丹阳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大吃一惊,才知夫人的道行比自己强多了。”
至于《西游记》中这种变化比赛的描写就更精彩了。尤其是“小圣施威降大圣”一节,堪称最令人眼花缭乱:
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搜的一翅飞起去,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撺出水中,一变,变作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嗛他不着,他见水响中,见一条蛇撺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贱——花鸨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不拘鸾、凤、鹰、鸦都与交群,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踵。(第六回)
大圣变作麻雀,二郎就变作饿鹰儿;大圣变作大鹚老,二郎又变成大海鹤;大圣变作鱼儿,二郎即变作鱼鹰儿;大圣变作小蛇,二郎又变作灰鹤……。如此这般的变化比赛,既充满童心童趣,又体现了一物降一物的哲理,可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具有极佳的审美效果。幼稚的孩童在从中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扩大了认识自然的知识面。即便是知识渊博的成年人,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大千世界的亿万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所蕴含的往复循环、相生相克的深刻哲理。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僧道仙妖在斗法时展现的诸多本领,更为有趣的是,还有在众多正邪两派人物之间展开的团体斗法。《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对这种“强中更有强中手”的集体斗法多有描写,此不赘举。这里请读者看一段三、四流小说中的综合斗法描写:
只见红日当空,左跷略施些小本领,拿张红纸起来,吹一口气,默念了真言,一放便变成了华盖挂在空中,遮住了太阳。张鸾呵呵冷笑,也取了一张红纸,吹上一口气,喃喃的念几句,望空一放,立刻微微的一道清风,也变成一个华盖,挂在空中。各把太阳遮住了。众人喝采。左跷便取出七把集云刀来,望着当空一总撩去,但见霞光闪闪,直冲斗牛。那刀在空中旋了几遭,便变成七只翡翠鸟,反转身来,多是翠翎毛,一齐飞来,要啄张鸾。吓得那宗看客心里多跳起来了。幸亏张鸾法力也好,笑嘻嘻取出一只玉连环来,也望空中撩起,但见云端里有千条瑞气。众人多道:“好看,连我眼睛多张勿开了。”但见周围瑞气逼拢来,七只翠鸟飞不起了,依旧变了七把集云刀。左跷见了胆寒,即忙收拾了集云刀。那知道这玉连环便要来打左跷了。此刻左跷着了急,即忙就摇手大喊道:“来不得。”圣姑姑在旁边忙取天书当空抛去,把这连环收了去。张鸾一见,胆碎魂消,说道:“啊唷唷,什么东西破吾的法么!喏喏喏,法宝又来了!”登时撩起一把金绞剪来,快利如锋,形像剪刀。此刻左跷难以抵挡,幸得圣姑姑又是一卷天书抛起来,也被他收了去。张鸾一见,怒气冲霄。在左跷,只得先下手为强,喝声:“松云,喏,俺家的法宝来了。”手取一个白玉瓶,那瓶中放出来的像朱砂一般红光闪闪,对着张鸾绕过去。张鸾一见,笑嘻嘻道:“此法有何希奇!”便撩起一粒定妖珠,分出五色彩光,在空中括拉拉的响如霹雳交加,登时把红光冲散。吓得那宗看客肉也麻了:“啊唷唷,勿好了,这一记打下来,必要打做肉酱的了。”圣姑姑又将天书抛起,登时收了那定妖珠。左跷抢先撩起一个惊天弹。此刻张道就要输了,法宝已完,无法可破。幸亏得蛋僧在旁,也抛起天书,那惊天弹全无用场。左跷便呆了。此时左跷发起急来,放声大叫:“张泼道,你的本领平常,法术有限,可还有什么东西么?”张道也放声大叫:“左跷儿,你可还有什么东西么?”左跷道:“俺的法宝多得很!”但见一座黄金宝塔一丢,万道毫光,直射斗牛,把张道头上打来,霹雳交加,其声甚响。此刻张道情急万分,只想拔脚逃走,喊一声:“左跷儿果然利害也。”旁边蛋子头和尚说:“休得慌张,有俺家在此。”忙把天书祭起,将那座黄金宝塔打落尘埃。旁边陈抟走近,那首鬼谷仙师走来,各将法宝收去。(《金台全传》第十三回)
这种斗法方式叫做“祭宝”,是灵物崇拜和神仙崇拜双重文化心理的在广大小说作者和读者心中叠印的结果。当然,这种描写如果在一篇小说作品之中出现得太多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只见宝贝不见人”的不良创作倾向。《西游记》中本有这种弊病,《封神演义》廓而大之,成为一个严重的艺术缺陷。至于《说唐三传》《五虎平西》等末流小说中反反复复进行的这种“祭宝”“斗宝”描写,则最终成为某些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一个致命伤了。
三、精变
此所谓“精变”,并非妖精变成别的什么,而是特指妖精变军备。所谓“军备”,对于上阵打仗的军人而言,所指当然就是兵器、马匹之类。
在冷兵器时代,那些著名的将领上阵时究竟用何种兵器、骑什么样的马匹,其实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普通百姓和下层文人却不管这些,他们往往按照某位英雄的基本性格、业绩以及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约定俗成地给古代名将配备兵器、马匹。到了古代小说中,这些兵器马匹甚至被传奇化、神异化,成为某些英雄人物性格的延伸和补充,有些甚至成为英雄人物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和赤兔马,张翼德的丈八点钢矛和乌骓马,鲁智深的禅杖,李逵的板斧,岳云等少年英雄的“八大锤”等等。更有甚者,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马匹来源更是特别,居然是妖精变化而成,而且,每一次“精变”过程都被描摹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片断。
例如民族英雄岳飞,他的兵器在古代小说作者笔下就有一个神奇的“精变”过程:
只见半山中果有一缕流泉,旁边一块大石上边,镌着“沥泉奇品”四个大字,却是苏东坡的笔迹。那泉上一个石洞,洞中却伸出一个斗大的蛇头,眼光四射,口中流出涎来,点点滴滴,滴在水内。岳飞想道:“这个孽畜,口内之物,有何好处?滴在水中,如何用得?待我打死他。”便放下茶碗,捧起一块大石头,觑得亲切,望那蛇头上打去。不打时犹可,这一打,不偏不歪,恰恰打在蛇头上。只听得呼的一声响,一霎时,星雾迷漫,那蛇铜铃一般的眼露出金光,张开血盆般大口,望着岳飞扑面撞来。岳飞连忙把身子一侧,让过蛇头,趁着势将蛇尾一拖。一声响亮,定睛再看时,手中拿的那里是蛇尾,却是一条丈八长的蘸金枪,枪杆上有“沥泉神矛“四个字。回头看那泉水已干涸了,并无一滴。(《说岳全传》第四回)
原来岳飞的长矛乃是“长虫”所变,这真正称得上是匪夷所思的描写。“岳家将”的兵器既然如此“先锋”,“薛家将”兵器的来历当然也不甘“滞后”,同样极富神奇色彩。本文第一节曾经提到薛家第四代小爵主薛蛟、薛葵兄弟二人在帮助别人捉拿要吃童男童女的四个妖怪过后,没有料到妖精突然变成了两套兵器和坐骑:
四个妖怪一见二人,认得是主人,都现了原形,伏于地上。薛蛟左手捉住白龙大王,右手按定银灵将军,薛葵左手拿定大头大王,右手扯住乌显将军,一齐举脚乱踢,踢了一会,端然不动。二人定睛一看,薛蛟左手捉的白龙大王却是一条滚银枪,右手按的却是一匹白银獬豸,薛葵左手拿的大头大王却是两柄乌金锤,右手扯的却是一匹黑麒麟。(《反唐演义全传》第六十三回)
其实,这种妖精变兵备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谓不胜枚举,许多小说作者在塑造自己心爱的将领或武士的时候,总是愿意赋予其“精变”的兵器和马匹。我们不妨再看另一位勇救小儿女而得到宝马的侠义公子:
话说那怪被公子追赶,即丢下双锤,回头一口来咬公子。公子一闪,飞起右脚,拦头一腿,打个正着。那怪大叫一声,就地一滚,现出了原身,乃是一匹青马。鞍辔俱全,搭蹬上挂了两柄金锤,浑身淌汗,后蹄上伤了一剑,剑痕独湿。公子一看,道:“原来是你这畜生作怪,害人家儿女儿罢,本当杀了你,代我的马抵命。怎奈我没有坐骑不好行走,就将你抵他便了。”(《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第三十三回)
更为有趣的是,能得到妖精变成军备的绝非仅止于七尺男儿,有些巾帼英雄也绝不让须眉男子。有一位忠臣的女儿唐金花逃难途中就有这种奇遇,且看她事后对其兄长所追叙的神奇故事:
到了三更时候,我甫交睫,即见一神将叫我起来,带到正面神前跪下,上座的神说道:我是五显华光大帝,可怜尔唐家受害,特欲传给武艺过你。俾得日后为国家出力,并替你唐家报仇。紧记。又命神将舞剑一通,旋说道:吾有三块金砖藏在石岩里,取了带往傍身。点化毕,神将带回,睡下。忽然擦醒,原是一梦,方对家嫂说个明白。刚有一阵神风,吹开庙门,望去,见一白衣鬼,你妹一拳打去,那鬼变了一剑。又到三个矮鬼,涌涌肿肿,到来被我一脚踢去,一踢成了一砖。未几天明,方悟神人所赐。(《绣戈袍全传》第二十五回)
在这个故事中,赐给唐金花宝剑、金砖的神道大有来历,乃是上界“五显华光大帝”。明代小说《南游记》(亦即本文第一节所引之全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者),就是专门写他的故事的。这位华光天王除了是“人”而不是“猴”而外,其他方面都酷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尤其是华光天王打起仗来,经常使用的独门兵器就是“金砖”,而“金砖”的威力也绝不亚于孙行者的金箍棒。由这样一位传奇色彩极浓的英雄人物,将“精变”的武器——宝剑金砖传给唐金花,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对忠烈满门的唐氏家族的无比崇敬和真心热爱。
不仅驰骋疆场的将军们往往拥有这种“精变”的兵器,就是那些行走江湖的侠客们有时也常常碰到这样的好运气。《施公案》中诸如此类的描写就有好几次:
妖怪只管把双手来抓他的上身,不防公然顺手将身往下一蹲着,向左边扭转身来,双手把妖怪两足捏住,大喝一声,跳起身来,把妖怪倒提在手。妖怪被他提空了,用不出气力来,只是两手乱舞,没法子了。李公然便将妖怪顺着势,照准太湖石峰上,用尽平生之力,呯的掼去,只听当啷一声,把个妖怪掼的不见了,倒把那李爷吓了一跳。计全同李七也是一怔,说:“妖怪那里去了?”公然见妖怪没了,自巴手内还捏着一件东西哪,提起来一看,却变了一柄耀目争光的宝剑。……正要下楼,公然抬头一看,忽见上面挂了一个剑鞘,连忙摘将下来,把剑插入鞘内,恰是原配。计全接过来,就亮光之下细看,见是缕金嵌宝,十分精工,雕刻龙凤花纹,中间用珍珠嵌成“青虹”二字。计全看罢,说:“怪不得了,原来是魏武帝的青虹宝剑,乃价值连城之物。”(第二百零九回)
那妖精见了人杰追得切近,复返身将前爪一扬,猛然扑到。人杰手急眼快,将身一偏,那妖怪扑个空。人杰趁势一刀砍去,只听那妖又吼了一声,在地乱滚。人杰赶上一步,一磕膝将妖怪按住,正要举刀复砍,忽然二目昏迷,不能下手。约有半刻,才清明些,睁开二目,只见妖怪已毫无影响,再一细看,自己膝下却磕着两柄铜锤,颜色斑斓,实在可爱。心中暗思:“怎么那怪物忽然变作铜锤呢?且莫管他。”说着拿起舞了一回,甚是称手。此时天已大亮,拿着铜锤,仔细一看,见上面还刻着字,写道:“山东贺人杰用,凭此建功立业。”人杰好不欢喜。(第三百十九回)
上文说李公然所得之“精变”兵器,乃曹操的“青虹宝剑”,这其实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化”过来的。该书卷之九《长阪坡赵云救主》一节有云:“原来曹操有剑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倚天剑自佩之,青剑教夏侯恩佩之。倚天剑镇威,青剑杀人。夏侯恩以为无敌之处,乃撇了曹操只顾引人抢夺掳掠。正撞子龙,一枪刺于马下,就夺那口剑,视看靶上有金嵌‘青’二字,方知是宝剑也。”
至于贺人杰的“铜锤”,虽然没有什么“祖宗”可以沾光,但却“现实”得可以。君不见,作者故意弄一特写镜头:“山东贺人杰用,凭此建功立业。”以此表示这“精变”宝器的来历不凡和威力无比。
《施公案》中的施公,乃清初大将军施琅次子施世纶,史载:“施世纶,字文贤,汉军镶黄旗人。琅仲子。”(《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八)然而,除了施公而外,该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多半为小说作者根据民间传说而创造。上文提及的李公然、贺人杰都是书中虚构出来的江湖豪侠,后归施公麾下,地位都比黄天霸略低。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或侠义公案小说的“英雄谱”中,他们二位都算不得“大腕”,二三流人物而已。但是,作者为了突出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色彩,在写他们与妖精搏斗、妖精变武器的同时,更突出了这武器的传奇性。不仅李公然、贺人杰的故事如此,就是上面提到的所有“精变”军备的故事,都有这一层意义。
进而言之,“祭赛”、“斗法”、“精变”这三种故事之间又是有着一定的内在文化联系的。它们同属于宗教、神话中最具世俗色彩的那一部分,从中,亦可透视出普通民众对宗教、神话的一种最低级也最实用的理解。而小说,尤其是话本或章回类的通俗小说,则毫无疑问是这种最低级、最实用的宗教、神话理解的最佳载体。
或许,对于高层次的文人学士而言,这种最低级、最实用的宗教、神话理解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但是,且慢!我们所有高级的、形而上的、理论化的宗教、神话理解,无一不从这里发轫。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又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又有趣的话题,但终归有些漫长。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只好另起炉灶,再寻找机会向方家学者讨教了。
注:
①②③ [明]臧晋叔编《元曲选》(全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98、656、1397页。
④⑤ [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9、155页。
⑥ [清]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5页。
⑧ [晋]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9-290页。
⑩ [明]余象斗等《四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