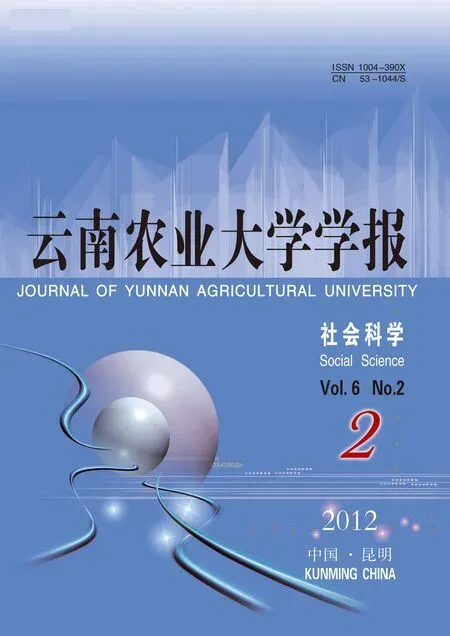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
王映平,王晓羚,杨剑全
(西南林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4)
典型人物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典型环境描写则是典型人物塑造的基本前提。因为一定的人物性格总是由一定的环境因素决定的,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抑或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无一能够例外。
当然,在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中,环境描写的强度和技法不尽相同。鲁迅说过:“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上却多有背景),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绝不疏导一大篇。”[1]有鉴于此,有人认为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是不充分和不典型的,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因为衡量小说环境描写的充分和典型与否,不仅与作品的体量密不可分,而且涉及诸多相关要素,不宜仅用着墨多少来加以评判。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样典型了。”[2]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原则和衡量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呈现的环境和人物是否具有真实性与典型性,以及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匹配度与互补度。鲁迅小说一以贯之的重大特点和亮点之一,正是在于作者十分注重写好人物活动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域特色。
一、鲁迅小说社会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社会环境是特定历史阶段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文学作品人物活动相对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在作品中犹如地心的吸引力,虽未直接见示,但却无处不在。它决定着人物的性格,支配着人物的行动,主宰着人物的命运。鲁迅小说的过人之处和特殊贡献,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以疗救国民和改造社会为己任,毫不掩饰和忌讳地写出了“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社会的不幸”、中层社会——“革命者的悲哀”,并且达到了力透纸背和入木三分的艺术境地与语言维度。
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努力创作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气派的优秀作品,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孜孜以求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境界,鲁迅也不例外。由于个人身世、境遇、学养、胆识、性格、气质、思想、观念等原因,鲁迅一贯主张文学创作“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民族使命,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大弊端,在于不敢正视现实,对于现实的缺陷,总要设法加以弥补,用“瞒和骗”造出奇异的逃路来,于是也就成为“瞒和骗”的文学。这同他赞赏《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颂扬《儒林外史》能够“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等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主张“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起人生并写出它的血和肉来。”因此,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带着无比强烈的爱与憎、好与恶、哀与怒,描绘了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灰暗冷酷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画面。
比如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所描绘的画面:“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3]反封建的狂人,因为敢于蔑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历史——“陈年流水簿子”、敢于挑战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敢于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本质,竟然遭到了以古久先生、赵贵翁、大哥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打击,以及众多“看客”的讥讽与嘲弄,被封建统治阶级像鸡鸭一样地关了起来,剥夺了起码的人身自由,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狂人没有动摇、没有妥协、没有屈服,始终坚持挣扎、反抗、斗争,直至被迫害致狂仍不肯罢休,从而昭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进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召唤人们为彻底改造旧中国而进行无畏抗争和殊死战斗。鲁迅小说这种高度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融入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从未有过的抗暴精神与革命特征。
对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不应当满足作品的生活真实和客观真实,而应当追求作品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即通过真实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写出由这种关系决定和演化而来的典型环境,使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同这种环境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从生活真实和客观真实,升华到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从而大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因此,只有真实地反映主人翁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更真切地再现社会环境,更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格。鲁迅小说所绘制的所处时代的黑暗冷酷的社会面相,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酷无情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是冷酷无情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强权政治、专制统治、宗法秩序基础之上的,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吃人”与“被人吃”的关系。
比如在《药》中,鲁迅不仅描写了革命者与统治者及其帮凶的关系,即夏瑜与夏三爷、红眼睛阿义、刽子手康大叔等人的相互关系,而且描写了革命者与旁观者的关系,即夏瑜与华老栓一家及众多看客的相互关系。憨厚朴实的华老栓由于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蛊惑和毒害,居然和盘托出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到刑场为儿子购买治疗绝症的“人血馒头”,而那被杀害的对象,正是舍生忘死试图挽救他们苦难命运的革命战士,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和损人害己的悲惨结局。夏瑜的革命理想和行动,甚至未能被自己的母亲所理解和认同,因而她在上坟祭奠儿子时,仍不免在“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总结了革命志士未能把自己的理想变成民众的意志而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指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缺陷,提出了在中国必须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命题,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成分和悲情色彩;又如在《祝福》中,造成祥林嫂家庭和个人悲剧的,除了四叔、婆婆、大伯、卫老婆子等人外,还有无数旁观、玩味、嘲讽、鄙弃她痛苦经历的茶客庸众。这些人本来也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但由于满脑子充斥着封建伦理教义和迷信思想,逐渐变得愚昧无知和庸俗无聊,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甚至成为“无主角的杀人团”的一员,要想挽救祥林嫂们的命运,惟有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从而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鲁迅小说这种对现实社会制度、秩序、痼疾持根本性、整体性、坚定性的否定、批判、讽刺,已触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根基,不仅提出了进行政治革命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进行思想革命的迫切性,适应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要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达到了当时所有现实主义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呐喊之后的彷徨,彷徨之后的求索,鲁迅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指引他冲破思想桎梏和认识迷局,使他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沉默中看到了爆发、从失败中看到了成功,一扫看不到民众力量和国家出路的哀伤与悲愤。作为一位极度清醒和异常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斗士,尽管他对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敌对势力的强大力量、官僚阶层的凶残本性、社会变革的坎坷道路、民族解放的艰困历程,依然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觉,但已没有任何思想迷雾和时局乱相,能够泯灭他内心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和理想之光。
他怀着崇敬的心情,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形式,创作了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一方面塑造了女娲、大禹、墨子、眉间尺、宴之敖等一批中华民族“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民族英雄、信心百倍地重塑民族性格、矢志不渝地弘扬民族精神、殚精竭虑地鼓舞民族斗志,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光明与希望。另一方面刻画了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典型形象,把他们为了追求让位的仁名,置国家存亡于不顾、阻止人民正义战争,一事不做、徒作大言和唯无是非主义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昏庸堕落,热忱讴歌正义的复仇行动,大力倡导韧性的战斗精神。与此同时,他已从另一部分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力量,在同期发表的若干著名杂文中,一再表明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再三声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并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这就是鲁迅小说前无古人的思想性、战斗性、情绪性、写实性、象征性和暗示性,也是鲁迅小说社会环境描写的独一无二的真实性与典型性。
二、鲁迅小说自然环境描写的简约性和原创性
自然环境虽然只是文学作品人物活动的相对狭窄的舞台和背景,但却是塑造典型环境和人物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什么矛盾冲突的发生和发展,还是何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总是在一定时空和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因此,适度而精妙的自然环境描写,不仅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心路历程,而且有助于反映人物的社会关系。
师承传统、取法异域、鼎新革故、删繁就简是鲁迅小说景物描写的最大特点。鲁迅小说的景物描写既不像西方小说那样,用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有别我国旧戏里的人物出场,总是在几通锣鼓之后,才能出将入相。那样就把精彩纷呈和千差万别的人物及其活动给脸谱化与程序化了,非但不利于再现典型环境,反而有害于刻画典型人物。鲁迅小说的景物描写,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借鉴了外国现代文学的成功经验,同时吸收了其他门类的艺术养分,如绘画的白描、剪纸的凝练、戏剧的形象、诗歌的律动等等,并且加以兼收并蓄和推陈出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独门绝技,发挥了多重功能和作用。
比如在《离婚》中对慰老爷客厅的描写:“客厅里有许多东西,她不及细看;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缎子马褂发闪。”[5]客厅再大、里面东西再多也可一览无余,与其说是不及细看,到不如说是不敢细看和无心细看;既然出入客厅的都是披绸挂缎的贵客,那么客厅装饰的豪华和奢侈程度自不待言。这种景物描写以简胜繁,言简意赅,既省略了大量的细枝末节,又留下了充分的想象余地。
服务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是鲁迅小说景物描写的鲜明特点。在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中展开景物描写,使景物能够通过人物经历和感受自然流露出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陪衬和拖带,并使景物更好地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服务。这样看起来极少写景,但却充分发挥了景物的寓意和效能。
比如在《一件小事》中,鲁迅一共四次写风,从“大北风刮得正猛”、“北风小了”到“微风吹着”、“风全住了”,都是通过人物的感受和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而且每次不过极简短的几个字,没有任何铺张藻饰,但四次风的变化却契合和烘托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与情节发展变化,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烈,更深刻,更感人。在沿海的冬天出来拉车,车夫家庭生活的窘迫程度可谓不言而喻,而在“北风”小了的时候“跑得更快”,又把他冒着严寒多拉快跑的急迫心情表露无遗;既然如此,那么按常理老妇人被车把挂倒以后,他本应为担心生意和生计受到影响而焦虑,况且她跌倒的责任并不在他,她在本次事故中并未受伤,她对此并无任何怨尤,他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拉着客人一走了之;但他既没有焦躁更没有溜走,反而满怀关爱和歉疚之情,躬身扶起和耐心照顾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妇人,即使客人一再催促和抱怨,也全然不予理会,从而凸显了他乐善好施和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但正是这种风平浪静的环境和氛围,把他的高尚品格在“我”的灵魂深处激起的人性狂飙和感情巨澜,淋漓尽致地衬托和展现出来,给人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心灵冲击和精神震撼。
精美的“感觉顺序”是鲁迅小说景物描写的突出特点。鲁迅小说除了景物描写的逼真传神外,那精巧灵动的感觉顺序、缜密细腻的逻辑推演、简洁明快的白描手法,同样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带来了异常丰美的享受。
比如在《社戏》中的景物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蓬。”[3]
从远处看,最引人瞩目的肯定是开阔地带拔地而起并有光照的戏台,何况看戏又是此行的唯一目的,看戏主角还是戏迷和充满好奇心的翩翩少年;当目光从戏台逐渐向四周拓展时,由于暮色降临和光照局限,所见自然就与月色融为一体了;走到近处,首先关注和看到的当然是台上演员红红绿绿的流动身影,然后才会顾及近台河里还有一望无际的看戏人家的船蓬;既然看戏人家的船篷如此壮观,那么观众人数、表演激情、现场气氛等后续效应,虽然惜墨如金,但已跃然纸上。这稍纵即逝的感觉顺序,被作者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同时这种顺序还兼顾了光照因素和背景关系,使我们不得不惊叹作者观察自然景物的超群锐度和捕捉瞬间感觉的非凡功力。
浓重的抒情色彩是鲁迅小说景物描写的重要特点。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不可不依托客观事物的陪衬和点染,这便有了以景抒情和以事显情等艺术载体与创作技法。
比如在《伤逝》中,子君死后,涓生又回到以前同居过的会馆,眼前:“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5]但物是人非,触景伤情,其不胜今昔和恍若隔世之感,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会肝肠寸断以致难以自持,这是以景抒情的方式;又如在《祝福》中,祥林嫂被迫再嫁后,又遭丈夫突然病故和儿子被狼吃掉的巨大不幸,为宣泄内心无法排遣的悲痛和悔恨,逢人便讲儿子遇难的经过和惨状,反复叨念“我真傻,真的”,这是以事显情的方式;再如在《故乡》和《伤逝》中,鲁迅独辟蹊径地采用了诗歌一样的排比和反复句式描写景物,兼收一唱三叹和一举多得之功,并蓄寄物托情和抒怀明志之效,从而突出了某种生活境遇和人物情感,收到了情景交融和抒情传神的艺术效果。
强烈的气氛烘托是鲁迅小说景物描写的个性特点。 基于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和精心铺垫,有利于文学作品突出人物感情和深化思想内涵。鲁迅小说一向擅长借助色彩斑斓和奇谲变幻的自然景物,渲染环境气氛和抒发思想感情,彰显人物性格和提升作品张力。
比如在《药》中,为了烘托悲剧气氛和强化悲剧色彩,鲁迅独具匠心地安排夏瑜妈和华大妈在清明节扫墓时不期而遇,不仅剖析了两户贫苦人家唇亡齿寒的悲剧根源,而且揭示了她们休戚与共的命运转机。为了营造这种悲悯意境和悲剧氛围,鲁迅对坟地周围的自然景物作了细致入微和浓墨重彩的描绘,从坟地墓冢的等级排列、清明节的寒冷、杨柳的新芽、坟顶的红白花,到吹拂的微风、钢丝一样的枯草、铁铸一般的乌鸦及其挫身飞向辽远的苍穹,勾勒了悲凄的自然画卷和沉郁的人文景观,构成了浓重的抒情色彩和积极的象征意义,抒写了两户人家的深层悲剧和两位母亲的无限哀思。在令人窒息的绝境中,透出了微茫的曙光。
三、鲁迅小说环境描写的地方性和民族性
从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中,我们还强烈感受到醇酒般浓烈的江南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习俗、景物,无不浓染着浙东地区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鲁迅说过:“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6]也就是说,地方色彩越浓郁,非但不会限制文学作品的流布,反而还会像土特产一样,不胜而专,不胫而走。由此使我们不禁联想到《风波》中那江南水乡傍晚的灵秀剪影、《社戏》中那仙山楼阁般的空茫夜景、《故乡》中那海天一色的神异图画、《在酒楼上》那“赫赫的在雪中朗得如火”的明艳山茶、《孔乙己》中那光顾酒店客人约定俗成的陈腐规则、《祝福》中那奉献天地众圣歆享时的庄严礼仪,等等。因此,当我们仔细温习和品味鲁迅小说及其环境描写的时候,犹如在欣赏王维的山水诗、齐白石的水墨画、舒伯特的小夜曲,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雅艺术熏陶与清新审美享受。
果戈里说过:“真正的民族风格,不是在外衫的描述中,而是在人民的精神中。”这种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在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中得到尽情展示和尽兴挥洒,使其不仅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而且弥漫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社会气氛,同时浸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悲欢和生活情趣。比如在《孔乙己》这狭小的篇什中,鲁迅放手展现了鲁镇这个在晚清末年连结城市与乡村的江南集镇,着力描写了特定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倾情抒写了极富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的生活场景。那当街的酒店和柜台,下酒的盐煮笋和茴香豆,穿长衫和着短衣的热衷揭别人疮疤的庸众;穿长衫的雇主可踱进隔壁屋里,要了酒菜慢慢地坐着喝;着短衣的劳工只能靠着柜台站着喝;唯利是图的掌柜,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在酒里羼水;不谙世故的小伙计虽不讨掌柜欢心,但因为荐头情面大,所以仍然辞退不得;穷凶极恶的丁举人,对迫于生计入室窃取小件物品的孔乙己大打出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等等。孔乙己就是在这样凉薄的社会环境中,一步步落魄、沉沦、流卑和成为他人笑柄并饮恨离开人世的。在这里每个细节描写都是富于地方和个性色彩的,同时又无不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这就是鲁迅小说引领潮流的开放性、内敛性、时代性、阶级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也是鲁迅小说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的思想深切性与格式特别性。这种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是他精美艺术画廊中的瑰宝,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昂首步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林的秘诀。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在社会环境描写方面,通过典型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勇敢控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嚣张气焰、如实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真实再现了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特殊环境,从而深刻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曲折进程和发展趋势;在自然环境描写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摄取了“异域”的“良规利法”、吸收了其他艺术门类的有益养分,并且加以兼收并蓄和锐意创新,从而大大拓展了环境描写的艺术容量和技术含量。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简约性与充实性完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同时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彩、更多地打造光鲜环境和鲜活人物、更快地提高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准,创作出无愧于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精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1.
[3]鲁迅.呐喊[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4]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98.
[5]鲁迅.彷徨[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6]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