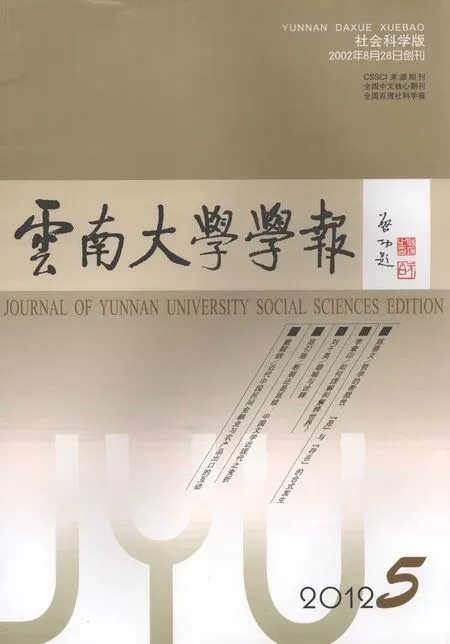公益诉讼界定的困境和出路
郑贤宇[集美大学,厦门 361021]
公益诉讼界定的困境和出路
郑贤宇
[集美大学,厦门 361021]
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公益属性;不确定性
作为近年来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公益诉讼的研究领域横跨诉讼法、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环境法等诸多学科。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学者们习惯于从个人的特定视角来界定公益诉讼,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尽管各起炉灶、互不干涉的研究方式使得对公益诉讼的研究百花齐放,但也因此导致了对公益诉讼界定的混乱。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了公益诉讼条款后,考虑到司法者在个案裁判时对该条款的适用,对公益诉讼进行准确界定已成为现实且急迫的需要。基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应当结合立法和司法、正向和反向等多种方法解释公共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准确界定公益诉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带来了诸如环境公害、消费者权益损害、就业歧视等社会问题。不断有热心于公益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甚至地方检察机关,以维护公益为名提起公益诉讼,在民间掀起公益诉讼的热潮,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公益诉讼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有成功的经验,而更多则是失败的教训。究其原因,法律无明文规定是导致公益诉讼不予受理或被驳回的最主要因素。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该草案如能顺利通过立法程序后生效,对公益诉讼的发展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公益诉讼入法仅仅是完善公益司法的第一步,对于司法者而言,准确界定公益诉讼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公益诉讼的界定,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如何解释公共利益?其二,如何判断诉讼的公益属性?
一、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
公共利益的概念在我国的使用较为混乱,在立法以及学术研究中,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概念有十余个,例如: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公共利益、政府利益、群体利益、集体利益、公众利益、大众利益等。相关概念如此频繁地出现让人感觉扑朔迷离无所适从,其根源在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发展的不断变迁,一种利益在某时某地可能是公共利益,然而当时空背景发生变化时,这种利益就有可能转变为私人利益。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利益的公共性质和私人性质常常掺杂在一起,从而使利益的公共部分难以确定,这也是实践中经常出现许多以私人利益冒充公共利益现象的原因之一。第二,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享有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主体(公众或大众),而何谓“公共主体”则是探讨公共利益的学者们最感困惑之处。例如,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公共利益在受益对象上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公共利益的受益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群体。[1]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让学术界陷入一个怪圈:尽管每个人都希望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在付出种种努力后,却没有任何一个定义能够说服所有人。于是,公共利益虚无主义产生了,有的学者跳出圈外,指出“公共利益”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比如,经济学界认为不同的价值偏好之间不可能形成公共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在关于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一定理的基本结论是:无数个人偏好不可能集结形成共同的偏好,因而凝结着共同偏好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存在。参见:肯尼思·约瑟夫:《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钱晓敏、孟岳良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页。法学界部分学者则认为,它是政府为了调和不同的利益而臆造出的一个概念。边沁所谓只有个人利益,没有“公共利益”的观点又从另外一个视角为“公共利益”敲响了丧钟——“公共利益”如不能通兑为个人利益,则“公共利益”便是虚幻的。[2]有的学者另辟蹊径,提出通过反向展开的方式不断逼近公共利益的核心。如刘连泰教授认为,“力图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只能是人类在公法领域的认识论狂想。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只能是无限逼近那个本真的‘公共利益’,这个逼近的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伪’去得越多,我们就越逼近真理。”[2]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政府自身的利益、商业利益、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三类形态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
二、公共利益的解释路径和标准
在法哲学的意义上,刘连泰教授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如果无法准确定义,不如用排除法步步逼近。甚至我们可以在此思路上进一步拓展,通过正向列举和反向列举两种方式,从两头不断压缩谬误的空间,尽管这样也许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至少降低了误读公共利益的可能。但仅仅如此,对于法律适用而言,其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法哲学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包罗万象,即便无法准确界定,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缺憾。然而,部门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由于起着指导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作用,如果不能对其准确界定,立法、执法和司法则无从谈起。“公共利益”一词是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之一。笔者以“公共利益”为关键词在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如下结果:明确使用了“公共利益”表述的法律115件,行政法规116件,法规性文件30件,司法解释126件,部门规章378件,部门性规范文件577件,地方性法规规章6756件,中外条约256件,外国法律法规28件,香港、澳门、台湾法律法规共335件。考虑到相关数据库对外国法律法规收集困难,我们可以认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共利益”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概念,即便排除其中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性文件和宣言式条款,其余大量规范性文件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一词理应得到有效界定。前述正反两向列举的方式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存在的缺陷说明,实体解释永远只能“接近”而非“达到”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因此,有必要将思路转向实体解释与程序解释相结合。所谓程序解释,是指把“公共利益是什么”的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虽然也有学者批评程序解释模式,认为这种将问题转化的思路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将这个问题的解决交给了另一个问题。[2]但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犹如博登海默笔下的正义,也具有普洛透斯般千变万化的面孔,在代议制民主的情境下,实体解释与程序解释相结合无疑是界定公共利益最合理的方式。
(一)公共利益的解释路径
现代民主国家的治理结构,以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行合一为代表。在成熟的三权分立的宪政理论中,立法权之优势在于代议制度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行政权之优势在于机构庞大、程序简捷所产生的高效率,而司法权之优势在于地位中立带来的公正以及对法律的熟知带来的专业性。就三权相互比较而言,己之优势则为彼之劣势。因此,在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同样需要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分工与合作。
代议机关作为民意之代表,因公共利益是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或抽象的集合,由代议机关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应是首选路径。当然,代议机关立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并不具有绝对的准确性,正如张千帆教授所言,为了确保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可信赖性,人们常常寄希望于民主制,希望每个人所持有的多种多样的意见,经过理性的讨论而逐渐集中,最终形成广泛的合意即人民的意思表示。而有些经过讨论形成的“人民的呼声”却并不具有可信赖性。[3]我们应当看到,尽管代议制民主并非完美无缺,然而,只要人类还存在个体差异(包括个人身体素质、智商、理念、占有资源等),除非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至善的且诸事皆可高效处理的“决策者”(甚至可以是一部电脑),否则,就现有的国家治理模式看,没有比代议制民主更完美的模式。在代议制民主下形成的代议机关,是所有个人与组织中最接近至善的那个“决策者”。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多数人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事物不一定就是“公共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数人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事物在一般情况下就应当被确认为“公共利益”。因此,尽管存在错误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排斥立法在界定公共利益时的优先地位。代议机关立法的另一缺陷在于很难具备周延性,因此不得不以抽象模糊的条款进行概括。以我国的《物权法》为例,在《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围绕公共利益的界定发生过许多争议,由梁慧星教授负责的《物权法》草案起草小组在其建议稿中曾主张对“公共利益”进行列举式规定,“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刘俊海教授认为,既然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很模糊,国民个体又往往缺乏对“公共利益”一词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往往导致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甚或开发商等利益集团滥用“公共利益”,堂而皇之地图谋并非公共利益的部门或企业私利,使权利人的利益受损。“公共利益”的立法定义不明确容易导致“公共利益”之滥用,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4]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我国的《物权法》中仍然应该维持《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抽象表述,不必采用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来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规定,这样做既不至于在法律上引起更多的纷争,也不会妨碍公共利益内涵本身的发展。[1]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该法最终采纳了概括式立法建议,对公共利益作了抽象界定,其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解释说,法律委员会经反复研究认为,在不同领域内和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况相当复杂。《物权法》作为民事法律,不宜也难以对各种公共利益作出统一规定。所以,法律委员会建议《物权法》对公共利益不作具体界定,而以由有关单行法律作规定为宜。[5]尽管梁慧星教授的草案建议采取了列举式立法,但因无法穷尽公共利益的外延内容,因此还是设置了兜底条款以弥补这一缺陷,这与《物权法》的概括式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法律规制不同的社会行为,僵化的立法模式无法应对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虽不能苛求所有法律在界定公共利益时都采取列举式立法,但至少在某些争议较大的法律中,可以采取正向和反向列举的立法模式,为执法者和司法者提供最大程度的明确指引。在此方面,不乏国外先进经验可供参考。如《日本土地征用法》(昭和二十六年公布,昭和五十三年最后修正)第3条列举了35大项共49种可以予以征用的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事业,其分类由道路设施至社会福利事业、宇宙开发事业等等,可称包罗万象,琳琅满目。[6](P472)韩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关于征收的列举式立法。[7](P66)即使无法通过立法穷尽所有情况,也应尽量采取列举式立法辅之以兜底条款的模式,而不宜采取纯粹的概括式立法。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立法机关无法在所有的实定法中以纯粹列举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因此,面对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立法机关把对公共利益概括性条款(包括兜底条款)的明细化工作交给了行政机关。为了能够及时做出决定,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我国的行政机关被授予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实务运行过程中的“公共利益”是由行政机关界定的。尽管各类法定的行政程序对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作出了一定限制,但行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因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配合的模式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决者,这样既能弥补立法的不周延,又能纠正行政的偏私。在英语语境中,司法等同于公正,其原因在于法官虽产生于议会,但其任职后却拥有相对独立于议会的权力,甚至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牵制议会。因此,司法机关成为中立的裁决者是由其天然属性决定的。虽然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法官对人大立法进行违宪审查,但通过审判或司法解释进行实质性“法官造法”,仍可以起到解释公共利益的作用。王利明教授认为,通过司法在个案中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是公共利益法律化的一条可行路径。因为公共利益经常是在发生争议之后由法官加以解释的,因而法律上对其不作界定并不会影响到法律的适用和操作,实际上,赋予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也能够充分体现公共利益的弹性特征,通过不同个案以逐步澄清公共利益之内涵。由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立法机关的概括式及列举式立法、行政机关明细化的执法,还是司法机关的居中裁判,都不具备单独界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只有分工合作、相辅相成的模式才是最合理的,这也是代议制民主的必然结果。
(二)公共利益的解释标准
如前所述,公共利益的界定需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相结合的方式,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作为决策者的公权力机关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时,不可能随心所欲,需遵循一定的普适的标准。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可通过以下两个标准判断。
1.公共利益原则上指向多数人的利益
所谓多数人的利益,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公共利益可以是多数人利益的简单叠加。比如化工厂排放污水,污染了某城市的水源地,全市居民的饮用水质量下降。每个市民都有自己特定的享用洁净饮用水的权利,而全市居民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足以构成公共利益。其二,公共利益可以是多数人利益的抽象叠加。比如城市的景观,对每个市民而言都是一种利益,但这种利益不存在份额上分割的可能,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利益为所有市民共享。当然,对司法者而言,最困难之处在于此“多数”究竟是多少?是一个以上还是若干个以上?笔者认为,所谓“多数”是指能够形成一个群体的人数。民事诉讼法中对群体性纠纷的解决设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司法解释中就将“多数”的标准界定为十人以上。此外,所谓的多数人不仅包括现实存在的多数人,还包括潜在的多数人。比如商业活动中大量存在的霸王条款,在某个时段使个别的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侵害,但如不制止侵害,受害人的范围可能会不断扩大,而这些潜在的受害人的利益,不论是简单叠加还是抽象叠加,都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
2.特定情况下个人的利益可以是公共利益
所谓特定情况,是指利益源于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情况。法学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8](P170)“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表述,几乎成了“从落后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特权社会到市民社会”的代名词,被称为梅因命题而频繁地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法学著述中。在早期学者的潜意识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既展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社会图景,又表达了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在契约自由观念的支配下,任何契约行为都是合法的、正当的。然而,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契约自由,孕育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洪流。因为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决定了在契约双方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强势一方可能迫使对方签订不平等的契约,可以歧视对方,剥夺对方的权利。动荡的政治局势,尖锐的社会矛盾,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等社会病症的出现,导致契约社会向身份社会的回归。回归福利国家、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法律主流,标志着西方社会在契约自由的背景下,有限度地走向了身份社会。从“契约到身份”是保障社会公正价值取向的实现途径,其中的“身份”,并不是“从身份到契约”中的“身份”的简单反复,而是一种“保护性身份”。回归身份社会,绝不是回到特权社会,而是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保护,从强调形式正义转向实现实质正义。所谓的弱势群体,可能是妇女、老人、儿童,也可能是消费者、贫困人口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在任何民主国家都被视为公共利益。要充分把握弱势群体这一概念,还必须明确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的范围。笔者认为,弱势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性弱势群体,主要指贫困人群;第二类是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第三类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弱势群体,比如消费者相对于商家,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相对于污染企业等。
三、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之判断
学者们对公益诉讼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起诉者的目的来界定公益诉讼,笔者称之为目的说。例如,有学者对公益诉讼的定义是:“由个人或组织、国家机关以维护国家的或集体的、社会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为目的,依据一定的法律向法院提起的一种诉讼。”[9](P4)还有部分学者没有明确提出“目的”二字,只是表述为“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的司法活动。”[10](P52)但从表述看,所谓“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应当是起诉者的自我判断,因此,也可以划归目的论一类。第二类是从诉讼程序适用的角度来界定公益诉讼,笔者称之为诉讼法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某些新类型的客观诉讼中,因为案件的特殊性产生一些诉讼法技术上的问题,需要立法对相关问题予以规定和明确,这种新型诉讼就是公益诉讼。”[11](P119)
对公益诉讼的界定无论是采用目的说还是采用诉讼法说,对学术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若论及某类诉讼的公益属性,并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时,目的说与诉讼法说都存在一定理论缺陷。目的是人的主观心态,只能从语言和行动中进行观察。因此,以目的说为依据所界定的公益诉讼,又可分为宣告式公益诉讼和行动式公益诉讼。前者是指起诉者明确提出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后者是指从起诉者的行为可以判断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当然,若将其延伸开来还可以出现第三种形态,即同时以语言和行动表明诉讼目的的公益诉讼类型。然而,因目的的主观性,在宣告式公益诉讼中,也许某些起诉者的实际行为表达与其诉讼宣告不符,显示出其私人利益的诉讼目的,这样,不论他的目的正当与否,其诉讼都谈不上具有公益属性。在行动式公益诉讼中,即便当事人的所有行为都指向公共利益,却可能因其对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实际表现为其维护的只是私人利益而已。因此,以人的主观目的来界定公益诉讼,可能产生原告将私益诉讼误认为或故意宣传为公益诉讼的情形。诉讼法说认为只有新型的需要采取特殊诉讼法技术的客观诉讼才是公益诉讼,这一观点排除了某些不需要改进立法或采取特殊诉讼法技术,只需要灵活运用现有制度的诉讼类型,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笔者认为,特定类型的诉讼是否具有公益属性,关键在于其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公共利益。例如,在具有波及性效果的诉讼中,即便原告宣称为自己的利益而起诉,其请求也具有个人权利保护的形态,但因其请求可能波及他人,司法者不得不考虑其他人之利益,此谓具有公益属性。比如针对机场噪音污染提起的不作为诉讼,即便仅有一个原告以自己的权利为请求基础提起诉讼,因其诉讼效果波及其他受到噪音侵害的民众,也可被视为公益诉讼。也就是说,只要司法者认为起诉者的请求会实质性地影响公共利益,就可以将该诉讼称之为具有公益属性的诉讼。
[1] 王利明.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J] .中国法学,2005,(6).
[2]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J] .文史哲,2006,(2).
[3]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法学,2005,(5).
[4]杨名.预防公共利益之滥用[J] .小康,2005,(12).
[5]欧阳晨雨.物权法草案:“公共利益”缘何不作界定?[J].政府法制,2006,(10).
[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7]曾祥华.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探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
[8][英]梅因.古代法[M] .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徐祥民,胡中华,梅宏等.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0]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11]林莉红.法社会学事业下的中国公益诉讼[J] .学习与探索,2008,(1).
■责任编辑/袁亚军
D923.2
A
1671-7511(2012)05-0098-05
2011-07-12
郑贤宇,男,法学博士,集美大学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