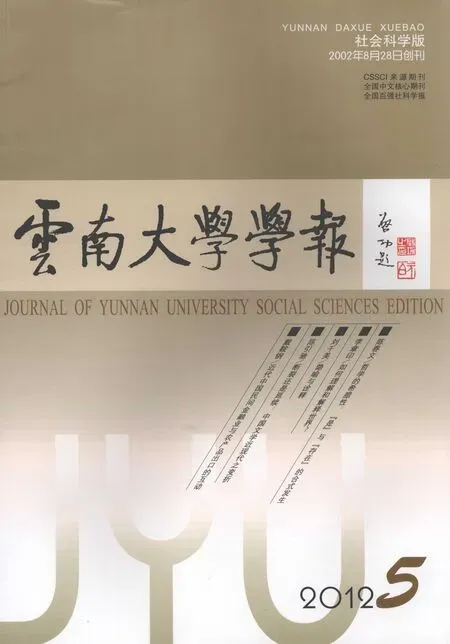“云起社”与17世纪福建乡绅的劝善活动
吴 震[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云起社”与17世纪福建乡绅的劝善活动
吴 震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颜茂猷;云起社;劝善;善人
本文利用日本所藏的海内孤本《云起集》这一珍贵文献,对几乎被当今学界所遗忘的17世纪初福建乡绅颜茂猷作一个案探讨。文章具体分析了他所发起的“云起社”及其五大分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会规会约等内容,指出颜茂猷努力在社会基层组织云起社来推动劝善活动,力图使个人的道德行善得以组织化、系统化,进而化为一场乡村社会运动,其目标不仅在于实现自我改善,更在于重建乡村秩序,而在颜茂猷看来,这两项工作不仅是个人应当自觉努力的方向,而且同时也是一项共同的社会事业。
晚明社会进入到17世纪初天启、崇祯的年代,由于国家机器出现了种种问题,明朝灭亡似乎已是命中注定。然而,在社会知识界,以士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仍然在思考着采用什么手段或方法可以使得社会不至于完全失序,笔者此前通过考察明末以降以《功过格》、《感应篇》等善书著述为主要载体的劝善运动的演变过程及其思想内涵,发现不少地方的晚明士绅正努力借助于善书文化或劝善活动来维系社会人心以及乡村秩序。[1]本文将要考察的以“云起社”这一民间社团为组织形式的17世纪福建乡绅的劝善活动,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和了解“后16世纪”*所谓“后16世纪”,是日本明清史专家岸本美绪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分析17、18世纪清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诸般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16世纪”产生的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性的普遍问题。[2]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用意仅指17、18世纪清朝中国的宗教文化问题乃是16世纪明朝中国该问题的延伸、衍变乃至转化。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之特质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
“云起社”的组织者是福建乡绅颜茂猷。颜茂猷(1578~1637)字壮其,又字光衷,号完璧居士,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进士出身,但其成为进士已是他去世前三年之事,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作为“乡绅”*关于“乡绅”一词的内涵,寺田隆信有这样的定义:“盖指拥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身份或资格的、居住在乡里的人。”[3](P6)此说基本可从。颜茂猷对“乡绅”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较士人百倍。”(《迪吉录》卷四《官鉴四》,《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子部第15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83页)不妨称其为乡绅乃国之希望的“乡绅论”。此论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然应注意的是,其将乡绅与士人对言,且从社会作用之角度将乡绅置于士人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在晚明时代已有一种观点认为,乡绅作为一种阶层已然具有超出士人之外的独立意义。度过的,他早年便以乡绅身份在家乡组织“云起社”来推动劝善运动,时间约在天启四年(1624),也就是其中举人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个组织既重视学问切磋,更强调行善实践,目的在于培养善人,它要求会员按照《功过格》实行迁善改过的道德实践,努力成为善人。
云起社是一个地方性的讲会组织,其活动范围大致不出漳州府。它的设立有两个目标,一是初级目标:改变地方风俗,兴起一乡善士;一是终极目标:由一乡之善人,推向全国全社会,以使天下人都成善人。用颜茂猷的话说,就是由“一乡之善”而“远至一国,远至天下”。*《云起集》第12册《云起会语·求四方会友疏》,东京:内阁文库藏明末刻本,第9页上。由此可说,颜茂猷的劝善思想既是一种道德学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他有一个基本设想:实现天下治平的终极理想须从个人的生活实际出发,落实在一人一乡的道德行为及社会风俗的改善事业当中。这既是组织“云起社”的缘由所在,同时也是“云起社”将要担当的使命。
关于“云起社”的人数及其成员身份,据称,有文献可查的该社成员共37名,大多为地方乡绅,其中进士出身者仅颜茂猷1人,举人出身者3名。[4](P237)然而,目前已无法查考清楚37名成员的身份,因为在一般的史书以及方志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关于云起社的活动情况、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颜茂猷在会中的讲学语录等,均见诸颜茂猷的著作《云起集》第12册《云起会语》。由该《云起会语》可见,云起社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结构,在总社之下,设有五个分会,分别是:树品会、经济会、修真会、善缘会、博雅会。颜茂猷似是总社社长,各分会另设有会长,由当地的地方名士来担任。
《云起会语》卷首有一篇简目,内分七个部分:一、树品会语录,二、经济会语,三、博雅会语录,四、善缘会语录,五、会日讲问录,六、诸君赞语,七、选订诸友课录(未行)。但这一简目与书中内容有些出入,其中缺了“真修会语录”。以下,我们就云起社的组织结构、思想宗旨及其各分会的活动内容等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使我们了解作为一介乡绅的颜茂猷是如何努力将劝善思想在社会基层加以推广,并力图将行善实践化为一场社会运动的。
上篇 云起社的组织结构
一、缘起
关于“云起社”活动的确切起讫年代,目前只能知其大概而难以确考。酒井忠夫指出,云起社大约创立于颜茂猷天启四年中举人之时,此说大致不错;他又说结束于崇祯七年中进士之前,*《(增补)中国善书の研究》,《酒井忠夫著作集》第1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99年版,第471页。这一说法有点含混。另据记载,《云起会语》刊刻于崇祯五年,*《栖北冗言·壬申》三月二十四日,载《祁彪佳文稿》,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记录了崇祯五年之前的云起社的主要活动,但由于颜茂猷及第进士后,直至逝世为止的那段生活(包括仕途生活),历史记载几乎一片空白,故难以断言云起社终结于崇祯七年之前。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它的辉煌时期只有三年,亦即天启四年至六年。
就《云起会语》来看,其中多次提到的纪年是丙寅(天启六年),*不过有一个例外,在某篇文章中,出现了丁卯(天启七年)纪年,这表明颜茂猷离乡赴京之后,云起社的活动仍然维持过一段时期。而颜茂猷在《重饬树品要言》中说道:“猷不才,自反多过,幸诸君不弃,交相励翼,近已二年,尚恐悠忽。今猷又有公交车之行,敬以此事推石丈老。”*《云起集》第12册《云起会语》,页码不清。这是说,云起社成立已有两年,而颜茂猷将有赴京之行,*按,当指颜茂猷以国子监监生身份赴京,参见《迪吉录》卷首顾锡畴《迪吉录序》。故将社中诸事委托“石丈老”(按,即陈朋石)主持。根据颜茂猷天启四年中举人,两年后赴京,则正好是上面提到的丁卯年。据此可说,云起社的主要活动时期应当是天启四年至六年之间,而《云起会语》记录的主要内容则是这一期间的活动情况。
现在,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云起社的组织情况。《云起会语》卷首有颜茂猷的一篇“引文”(中缺一页),其中对“云起社”之下分设五个分会的缘由作了大致的说明:“道固惟一,而禀习不同,志愿亦异。因略分为五会,以尽豪杰之襟期,以集遍地之精华,所乐实修实证,不贵浮名浮气。高明之士,勿鄙夷是幸!颜茂猷谨志。”*《云起会语》卷首,第1页下。这表明在“云起社”内部设立五个分会的设想源自人人“禀习不同,志愿亦异”的缘故。这个设想很切合实际。
那么,偏处南方一隅的福建乡绅颜茂猷何以如此热衷于讲会?颜茂猷在《求四方会友疏》中对于推动讲会的缘由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原文甚长,大意是说:兴起讲会能使远近四方、天南地北的“同志诸公”互相呼应,只要天下豪杰抱有“公共此心,公共此事”的宏愿,共同承担起“弥天之担”,那么哪怕是在“深山穷谷”,也能成就一番“度人度世”的事业。*《云起会语》,第9页上下。应当说,这是他成立云起社的最终目的,也是他成立各分会的宗旨之所在。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探讨云起社下设的五个分会的组织形式及其主要特征。根据《云起集》的记录,云起社的五个分会依次是:树品会、经济会、修真会、善缘会、博雅会。如果根据各会的会期设定来看,则其顺序应当是:树品会、修真会、经济会、博雅会、善缘会。以下介绍的顺序,依据《云起集》的安排。
二、树品会
该会的正式名称很长:“求坚志树品希圣希贤者为一会”,简称“树品会”,立意是“树立品格”,具体地说,就是成就儒家圣贤之“品格”。因此,“有半道半俗,以头面媚世者不齿”,*《云起会语·求坚志树品希圣希贤者为一会》,第 3页下。按,下引《云起会语》有关“五会”之引文,只注篇名,省去页码。“不齿”意谓不许入会。关于该会的成立宗旨,颜茂猷说道:
吾侪读孔孟书,识心性字,所学何事?阳尊其名,而阴叛其实,无异子之叛父,臣之叛君。且人生而得为男子,合下便有圣贤分量。舜何人也?为之则是。……盖所以优游忨愒、藏头躲耳者,亦只是物欲不能自割,制行不能自醇。恐惹物议,致废半途,所以姑示谦让。不知此泄泄忨愒处,正是有自便私图之心,虽行君子路上,终不得力。若敢旷然出脱,招同志人痛严刻责,立地便见俊伟。且有过相规,有善相翌,何愁纯白不到?……
窃不自揣,求吾漳中有旷然立志,欲以圣贤自期,以道义礼法自处,并以维持世风者,此为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殆当捧而拜之。奈若不相知,砥砺未由。乞先期于○○○○○*此处5空格,原文如此。是为填写人而特意设置的,下同。处报知,各书姓字于册,并及名号,某官某里某处居住,及某生庚,以便寻求记忆。定于○月○日会面○处,馔盒一个,谈论片时,并酌《会规》,交修不怠。愿同志者勿鄙猷为不足教,并勿以朋友一咲而止也。猷谨白。(有半道半俗,以头面媚世者不齿)*《求坚志树品希圣希贤者为一会》。按,原文以小一格字体刊印,似是入会条件,下同。
这里主要讲了成立“树品会”的原因。首先,颜茂猷强调指出:不仅是读孔孟书、识心性字的知识分子,并且只要是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人人都可成为尧舜而不甘愿成为一“乡人”而已;接着颜茂猷指出,今世之人大多以“乡人”自处,反而嘲笑那些立志成圣成贤的人,原因在于这些人担心求道之艰难险阻,故而一味追求优游玩乐;然在颜茂猷看来,求道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要按照“有过相规,有善相翌”的方法去做即可,换言之,规过劝善便是成就圣贤的法宝。要之,在“树品会”的说明当中,颜茂猷突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须以儒家圣贤作为人生的最高品格。这里的后半段文字很像是“入会表格”,要求将名号、籍贯、生辰、何时会面等信息详细填写清楚,以便日后“寻求记忆”,用今天的说法,便是一份“人事档案”。以下各分会的说明也都有此一段文字。
另据颜茂猷所定《会约》及《订会期》的规定,每会各立“会首”一名或数名,会期也互不重叠。“树品会”的会首是陈朋石(讳琦),*按,“云起社”主要成员的名讳,可参见《云起会语》卷末《诸君赞语》。文中,颜茂猷多以“字”或“号”相称。定于每月初二日开会,会员可以“随意招入,随意约束”,但须“以紧严立法为主”。*《云起会语·订会期》,第10页上。在“树品会”成立两年之后,颜茂猷将有“公交车之行”,临行之前,他召集了一次大会,将会中事务委托给陈朋石,希望该会日后能长久维持下去,他在《申饬树品要言》中要求会中诸友要立定志向、树立品格,并且“共相振刷,寻向上去”。而所谓“树品”,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从“孝弟伦理,以至衣冠言动”的日常行为做起,做到“按法而行,顺理而止”,便可实现“家庭肃穆,乡里顾化”这一家庭与社会都能向好的方面发生转化的双重效果,所以说是“至易至常”的,如果由此再推而广之,就能“达之天下”,使得全体国家和社会也能产生同样的积极效应。*《云起会语·申饬树品要言》,页码不清。
三、经济会
该会全称是“求实心经济炼达世务为一会”,简称“经济会”。关于该会的宗旨,颜茂猷说明道:
圣贤自合经济而一之,然世有拓落豪雄以诚正为迂谭,而其精锐才气,真足一瞬千里。……请得同志共会,如守令、监司以上官方,各有体要,共相讲求,以志其常。如河道、兵略、边夷、红夷、救荒、御乱等,各商方略,以志其变。如知人善任,棕核驾驭,化一方,易一俗等,共相扬榷,以志其小。如天下大积重,待挽之势,天下大吃紧,利害之原,各相维挽,以志其大。每期一事,各出所见,精者择而行之于册,可以致用,可以传世,不亦美乎!要当人人以万世太平为期,以各立愿力为标,聚相讲也,出相绳也。其有穷而干谒有司,达而阿附权贵者,必斥去之。谓其坏经济之本耳。
同志之志,乞先期于○○○○○处,书姓名及某官某里某生庚于册,定○月○日会面,○○处,谈论片时,酌立《会规》如前。猷谨白。(有放诞异志者,不齿)*《求实心经济炼达世务为一会》。
这里说“圣贤学问”即在“经济”之中,而所谓“经济”,按颜茂猷的理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河道、兵略、边夷、红夷、救荒、御乱等。这些问题不仅是晚明时代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几乎是历朝历代都无法避免的具体问题。
关于如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四点要求:“以志其常”、“以志其变”、“以志其小”、“以志其大”。首先,“以志其常”是指尽量要求“同志共会”,并邀请地方守令、监司与会,请他们来讲授自己的切身体会;其次,“以志其变”则是要求每次聚会,必就河道、兵略等各种经济问题中的“一事”展开具体讨论;再次,“以志其小”是指运用某种经济观点,来有效地治理某一个地方,以使一方得到教化而改善;第四,“以志其大”则是指对国家社会的“大积重”以及“大吃紧”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最后,作为会议记录,择其精彩之议论观点录入备案,以便“致用”和“传世”。更为重要的是,颜茂猷认为,经济问题也就是天下万世太平的问题,所以必须树立起“以万世太平为期”的宏大志愿。
据《订会期》的规定,经济会的会首是赵连云(讳宗成)、王近午,会期是每月十二日。颜茂猷还加上一句附言:“此会甚稀,尚当旁招,希留神共振。”*《云起会语·订会期》,第10页上。这说明“经济会”成员人数不多,大不如“树品会”和“修真会”。由此看来,从“河道”到“御乱”等各种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虽说是关乎天下万世之太平的大问题,然而,若从“术有专攻”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知识,光凭兴趣爱好而无切实研究,那么即便与会亦不会得到什么收获。可以想见,当时在颜茂猷的周围,擅长经济问题的专业人才是比较缺乏的。
另须说明的是,按“五会”的说明顺序,“经济会”在“树品会”之后“修真会”之前,然按照各会“要言”的安排顺序,则“修真会”在“经济会”之前,这一安排应有颜茂猷之苦心。他在《申饬经济会要言》中指出:“树品则必实能安身立命,修真则必实能超生出死,经济则必实有一条路头。”*《云起会语·申饬经济会要言》。可见,颜茂猷是有基本考虑的,他是以各会的重要程度来安排各会次序的。只是在现行的刻本中,“经济会”被放在了“修真会”之前。
在《申饬经济会要言》中,颜茂猷对“经济会”何以设立的目的及其对此会的热切期望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大致有三层意思。
首先,颜茂猷对“树品”、“修真”、“经济”三会作了一个比较,“树品”与“修真”的目标分别是为了实现“安身立命”和“超生出死”,相对而言,“经济会”只是向人指明了一条实路。根据他的自述“前日已分数事”,所谓“实有一条路头”,可以分别指:河道、兵略、边夷、红夷、救荒、御乱等。各会员可以按照自己所长,专攻其一。要之,宁可专一而成其“小用”,也不要贪图博滥,反而有害无益。
其次,颜茂猷强调“经济”之学是大有作为的,将来不仅可以为朝廷出力,甚至可以“斡运皇社、扶世翊运”,即便不能成为朝中重臣,而作为一位地方官,也能成为一名“良吏”。所以,他要求“社中兄弟”不妨扪心自问:学了“经济”以后,万一成为掌控朝政的大臣,退一步说即使只能成为地方官员,能不能成为“名臣”或“良臣”呢?抑或只能成为庸庸碌碌的“具臣”呢?可见,在颜茂猷的内心有一宏愿,他所倡导的“经济会”不仅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一般的有用人才,更是为了培养能直接为“朝家出力”的、掌控朝政、扭转乾坤的重臣。这一设想十分远大,而其可能性或许微乎其微,不过,在当时以科举选拔官僚的社会制度之下,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颜茂猷少时“事之如兄”而在崇祯年间进入内阁的林釬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最后,颜茂猷作了一番自我反省。他说两年来“经济会”的收效甚微,会中诸友“面目如故”,无甚长进,当然其过错“在猷”而不在诸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杂事繁多,不能用功,具体而言,这是因为颜茂猷一身“兼统”五会,所以精神多有不济所致。现在,颜茂猷已将“经济会”全权委托给赵连云等人,其他诸友“夹而辅之”,希望能有根本上的改观。*《云起会语·申饬经济会要言》。
上述这段自述反映出一条信息,颜茂猷分设五会会首,而他自己则扮演着“兼统”五会的领袖角色,换言之,五会在“云起社”之下统一运作,而颜茂猷自己俨然就是一位总领社务、运筹帷幄的“社长”。
四、修真会
该会全称是“求实意修真为一会”,它在五会中非常特殊,也颇具特色。按上引《申饬经济会要言》所述,该会的宗旨在于“超生出死”,这一目标关涉甚大,而且有一点宗教性的意味,也正由此,所以在五会中,该会人气最盛。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颜茂猷关于此会宗旨的说明:
宇宙间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而以弱丧忘归之性命,轮回于苦乐尘缘之间,一忙到底,万死不回,深可痛悯。间有有志之士,迫现此心,而悠悠忽忽,俗态侵人,于是事逐眼过老,向头来依然黑漫漫地,寄命于阎罗,不能自脱。所赖同学先醒提其已经之路,鞭其愿息之程,庶日新一日,损之又损,以有所就。……
请得同志之士,共讲此大根本,勤而修之,必期了事。乞先期于○○○○○处,书姓字某官某里某生庚于册,俟定○月○日,聚谈片响,酌定《会规》如前。猷谨白。(采战烧炼不齿)*《求实意修真为一会》。
如果说“树品会”的目标是要解决“安身立命”这一儒学问题,那么,“修真会”则是要解决“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生死问题。在颜茂猷的理解中,佛道两教更擅长谈论这一生死问题,所以,他在这里的使用语言已不免有几分佛老气息,诸如“轮回”、“苦乐”、“尘缘”、“阎罗”,等等。但在入会条件一栏中则明确表明:沉溺于道教的房中、黄金之术者应排斥在外,这显示出其与某些方外之术还是要求划清界线的。不过,与“树品会”或“经济会”相较,“修真会”的宗旨在于强调超脱轮回、尘缘、俗性、爱根等一切世俗妄缘,最后实现“超生出死”的目标。
据《申饬修真会要言》记载,该会非常有人气,会员人数达“数百人”,*《云起会语·申饬修真会要言》。与冷清的“经济会”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颜茂猷周围,生死问题以及修炼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在整个“五会”当中,“修真会”才是颜茂猷的金字招牌,因为颜茂猷早年就曾表示过,“玄修”问题无非就是“超生出死”之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对于颜茂猷的生命历程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根本性问题。而会员人数所以会有如此之多,或许是由于受到颜茂猷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的缘故。
据《订会期》的记载,该会“会首”为黄九变(讳士权)、陈裕阳(讳谦亨),会期是每月初七日,定在“树品会”之后“经济会”之前,因此,从重要性来看,它的位置应放在“经济会”之前。
在《申饬修真会要言》中,颜茂猷进一步向会员阐明了为何修真、如何修真等问题。首先,茂猷就什么是“修真”的问题作了回答:修真即是“性命大事”。亦即上述“超生出死”之大事,绝非是为了“博洽闻见”、“耳目声誉”。继而颜茂猷阐述了如何“修真”的问题,他要求做到“并心一路,辟捐万虑,以实求夫精气完足、形神俱妙而后已”。毫无疑问,无论是“并心一路,辟捐万虑”,还是“精气完足,形神俱妙”,都是带有技术性的专门术语,意指某种修身锻炼的技法。*《云起会语·申饬修真会要言》。用他自己的说法,也就是“玄修”方法,而上述所谓的“并心一路,辟捐万虑”,也应当与《守心十二法》开宗明义所披露的“心化无心,洞然太虚”之说以及“主一而实”的“守乾法”*《云起集》第11册《身世谱内编》,第9页下~10页上。在旨意上是基本相通的。因为“并心”、“捐虑”无非就是“心化无心”、“主一而实”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其意所指显然都是抛除杂念、化念归心的修炼方法。也正由此,“修真会”在整个云起社当中就显得别具一格。
五、善缘会
在云起社下的五会当中,该会是一颇具特色也非常重要的组织。关于“善缘会”的宗旨,颜茂猷在《求实兴善缘为一会》中说道:
善即道也,有见善而不见道者。盖道非上根不接,善则随缘可举。世界如彼其大也,困穷如彼其众也。独行善事,所与几何?但求人广度,善复成善,则救济无穷;其有独力不举,而众力可任者,则共肩之;其有独见不及,而众目可烛者,则共周之。期于畅满此善,接引同志,无一夫不获而后已,则善缘之所为结也。约每期相质证,行善事几条,度善人几个,立“功过簿”以自省克,庶辅仁之一助焉。
同志愿预会者,乞先期于○○○○○处,书名字里居,发其愿力,俟定○月○日会面,○○所求教。猷谨白(借缘诳众肥私者不齿)
“善即道也”,这是颜茂猷劝善思想的根本观点,这一点无庸赘述。一方面,颜茂猷将“善”与“道”并列,其目的在于将善事、善行乃至善人,提升到“道”的高度加以肯定,善不仅是人性的一种完美品格,它直接就是“道”之本身,从而“善”就具有了形上的、普遍的意义,所以说“世界如彼其大,困穷如彼其众”,都无不存在着“善缘”;另一方面,颜茂猷却强调世上“有见善而不见道者”,而且这一现象也很普遍,原因在于“见善”容易而“见道”难,颜茂猷之所以这样说,其用意在于强调“善”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通过行“善事”、做“善人”,便可通向“道”,而不是相反——悬空谈道却不做善事。关于这一点,颜茂猷在《申饬善缘会要言》中有更为清楚的表述,我们稍后再说。
在上述引文中,颜茂猷还谈到“独行善事”与“求人广度”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行善事固然须从个人的“独行”做起,但更为重要的目标则是“广度众生”,要以“畅满此善”为宏愿,做到“无一夫不获而后已”,意思是说,不使普天之下人人都成善人,决不罢手。这也就是“善缘之所为结也”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善缘会的实施方法是:“约每期相质证,行善事几条,度善人几个,立《功过簿》以自省克。”也就是采用记录“功过簿”的方式,来达到自我反省以及互相督促的目的。须注意的是,在五会当中,只有善缘会有这一具体规定,说明颜茂猷组织云起社与推动道德劝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下将要看到,颜茂猷在制定《会约》时,其实有更为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要求所有云起社成员都必须做“功过格”实践。也就是说,对于云起社而言,善缘会的“功过格”实践具有普遍意义,是其他各分会成员也必须身体力行的。
据《订会期》,“善缘以胡穆甫为会首,共董定念七日”,*《云起会语·订会期》,页10下。即每月二十七日定为“善缘会”的会期。这一会期的制定值得注意,这是五会中最晚的一个会期,顺便指出,“博雅会”的会期是在每月二十二日。事实上,颜茂猷之所以这样安排,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的考虑是,每个月的月底,以“功过簿”的最后统计作为对所有会员的考核,因此,“善缘会”必须置于最后。这说明“功过簿”的设立不仅是针对“善缘会”的成员,而且是其他各会会员也必须遵守的一条实践原则,换言之,“功过格”实践乃是“云起社”成员的共同行动纲领,“功过格”也就成了“云起社”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颜茂猷在《申饬善缘会要言》中就有关善缘会如何具体操作等问题有较详的说明,根据他的说明,善缘会几近于“救济会”或“慈善会”性质的组织,而他之所以设立“善缘会”,根本缘由在于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得不到任何庇护保佑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又由于信息传递往往受阻,使得有财力施赈者不能广泛施赈。所以,设立“善缘会”的一个目的就是令“有心有力”者广泛收集情报信息,共同捐资捐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庶可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措施的实行,有必要推举一位“廉直慈勤之士”来统领,其他成员也应积极配合,“共访疾苦”、“不惜宾士”,并且“广招出费”、“不惮拮据”,如此则可真正实现“救济”之目标,亦即善行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最后,颜茂猷强调,漳州府全体的生命实有赖于善缘会同仁的善行善事,而之所以组织“树品会”、“修真会”、“经济会”,正是要求大家从善行善事做起。*《云起会语·申饬善缘会要言》。
总之,善缘会与其他四会相比,看似是一个独立分会,其实它却是一个横跨性的组织,其他四会的成员也责无旁贷,有必要一同参与该会组织的行善实践。
六、博雅会
该会全称是“求博雅文词为一会”,又称“文词会”或“文艺会”。关于该会成立的缘由,颜茂猷说道:
文者载道之器,古来贯日月、薄云汉、历万劫而不朽者,独以文在耳。……抑请得邀同志数人,共骋古作,独造新裁,如凡经学、史学、诗学、字学,风流奥博,淹贯奇渺者,尽入词坛。相与捉云弄海,平分风月,品题史眼,吐玄凤之灵心,嘘赤文之瑞气,垂之宙宇,蜚英万劫,不亦康乎?……
愿预此会者,乞先期于○○○○○处,书名字里氏生庚于册,俟定○月○日会面,○○○所求教。猷谨白。(有恃才傲倪,撒拨无行者不齿)*《云起会语·求博雅文词为一会》。
不难发现,所谓“博雅会”类同于传统的以文会友的“文会”组织,以讲文学诗词为主。应当看到,虽然颜茂猷表示该会是在“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之下成立的,然而究其实质,该会无非是为了应对生员的科举考试而组织起来的。颜茂猷一方面站在儒家的立场,重申“四书五经”乃是“文章祖宗”,另一方面他也要求人们做学问应当博览群书,大凡经学、史学、诗学、字学,乃至其他杂家之类都应加以关注。这反映出追求博学正成为晚明读书的一种风气,也与颜茂猷个人主张学通五经的观点有关。
然而,该会的名称有些复杂,究竟应称“博雅会”,还是应称“文艺会”,这两个称呼在《订会期》一文中同时存在,据载:“文艺以黄九变为会首。此时制也,又经济所从出,而树品、善缘皆于是大其用,宜共励之。定十七日。”*《云起会语·订会期》,第10页上。其后又有一段关于“博雅会”的约定,其云:“博雅会以尹伯夏为会首,老宿登坛,旄旌耀采,而今谢世,良可哀悼。谨择○○○为会首,定每月念二日。”*《云起会语·订会期》,第10页上下。如此一来,“博雅”与“文艺”似是两会,然参照上引“求博雅文词为一会”,不应在“博雅”之外,另设“文艺”。在《云起会语》中,颜茂猷时常提到的是“五会”而没有“六会”之说。“博雅会”与“文艺会”名称不同,其实乃一。我推测,由于原“博雅会”会首尹伯夏突然过世,因此,另立会首时,名称改为“文艺会”亦未可知。
《云起会语》有两篇《要言》涉及该会,一是《申饬博雅会要言》,一是《申饬文艺会要言》,由其自述可见,颜茂猷原初并没有在五会中设立习“举子业”的计划,后来听从了黄九变的意见,始觉从事“世之所争趋”的“制义”亦不妨为“度世”之一助。因此,文艺会的管理实际上就全权委托给了黄九变。然而,“博雅会”与“文艺会”仍有微妙的区别,博雅会以经学、史学、诗学、字学为专攻方向,而文艺会侧重于“制义”。所谓“制义”即指应付科举考试的那套程文、时文之类的格式文章,是学习“举子业”的必读课程。故颜茂猷在此着重阐述“制义”并非不可取,若能善加引导,“上可以接性命,而下可以培经济为有用文章”。可见他不反对科举,相反极力主张社中诸君积极应试,若能使“公门异日采桃李,则吾社彬彬受物色焉”,其意很明显,应试中举乃“吾社”的一种荣耀声誉,人人应当努力,这也是颜茂猷衷心期盼的一件实事。
但最后他表示,还须“反本还原”,从“文艺”更上一层楼,则可与“博雅”、“修真”相通。再结合其中“此时制也,又经济所从出,而树品、善缘皆于是大其用,宜共励之”这一段话来看,则可说“文艺”、“博雅”其实是可以与“树品”、“修真”、“善缘”诸会打通为一的。*以上参见《云起会语·申饬文艺会要言》。换一种角度看,分则五会,合则一会;名为五会,实则一会。这应当就是颜茂猷在“云起社”名下设立“五会”的最初本意。
下篇 云起社的会约与会规
为约束“五会”成员的行动,以便推动“五会”顺利运作,颜茂猷制定了《会约》和《会规》。在《云起会语·会约》标题后,依次有四篇文字:《略拟会约》、《求四方会友疏》、《订会期》、《定会仪》。其中,《求四方会友疏》的内容不合《会约》体例,已在上面“缘起”部分作了介绍,《订会期》也已纳入上述各会的情况介绍之中,这里也就不必赘述。此外,颜茂猷制定的《会规》内容更为繁杂,具体规定了各会的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项。
以下将主要介绍《会约》与《会规》的内容,以便我们深入了解颜茂猷所设想的“云起社”到底具有哪些特质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作一“引言”,介绍一篇未被《云起会语》收入而见于《云起集·说铃次集》的文字,题作《书云起会规》,其中,颜茂猷讲述了设立“会规”的缘起,同时也可从中了解颜茂猷设立“会约”的初衷。
一、引言
颜茂猷有一篇《书云起会规》,严格说来,这篇文字不是《会规》本身,而是为《会规》或《会约》(文末称为《条约》)所作的一篇“引言”。以下略作分析。
首先,颜茂猷指出,“吾侪”在“云起社”汇聚一堂的目的是为了干一番“经世出世”的大事业。这四个字的组合有点独特,“经世”是指儒家“经世致用”之学,“出世”是指佛道“超生出死”之学。由此一语可见,颜茂猷有一种明显的三教融合意识,在他看来,儒家以“道德”经世,佛道以“修炼”出世,两者正可互补而不应互相排斥。然而从价值层面看,颜茂猷则认为儒家为“上”,佛道为“次”,这是他作为儒家士人的一个立场。接着,他分四个层面具体论述了“经世出世”的不同类型。其中,颜茂猷首先指出,作为“上者”应“以道德为事功”,这是就儒家而言,结合上述“五会”的情况来看,当是指“树品会”;与此相应,作为“其次”的方法,则应“修心炼性”,这是就佛道而言,就“五会”来看,当是指“修真会”。但从颜茂猷的叙述中显然可以看出,“道德事功”为“上”,“修心炼性”为“次”,他认为儒家的“经世”事业便可实现“横竖一世”的远大目标;其次则可通过“修心炼性”以便实现“住世一场”的目的。故从价值上来判断,儒家的“道德事功”可达到“顶天立地”的境地,而佛道的“修心炼性”仍未免“遗众独了”,须通过一番“穿尽刀山剑树”的功夫转化“方得成就”。由此可见,在颜茂猷的三教融合意识中,以儒为主的立场十分突出,他的主张是以儒来统摄佛道而不能相反。当然,若结合上述“修真会”的相关论述亦能看出,颜茂猷对于“超生出死”的佛道之学仍有所肯定,因为从“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这一问题的角度来看,不仅佛道的“超生出死”之学对此有相应的解答,而且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也不能回避这一根本问题。也正由此,颜茂猷强调作为“男子立身”,不出上述“经世出世”两种类型。
其次,颜茂猷阐述了另外两种学问类型,分别属于“文词会”及“博雅会”(两会实则一会)。其中所谓的“德业相规”,显是指“道德事功”与“科举事业”的互相结合,但其论述重点则放在“显亲扬名”这一世俗目的之上,指出通过“科举事业”可以达到光宗耀祖、成就功名的目的。毋庸讳言,对于当时社会的一般“学子”而言,这是他们从小习“举子业”之时就已设定的一个人生目标,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父母的“行孝”,这是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再次,颜茂猷要求人们“勤搜博览”以便为“掇取科第”作准备,这也是为了“无负父母生成之身、责望之意”,换言之,这是一种合乎“孝道”的行为。
要之,颜茂猷强调,为何“结社”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声气相属”的,所以应当互相勉励、共同提携。而为了最终的“成功”,故有必要“群居终日,豪杰聚首”,意谓应当过一种有组织的团体生活,而且还需要有一套组织措施以便互相“鞭策”。进而颜茂猷强调,人生在世应当树立远大志向,并不断刻苦努力,如果苟且偷生、碌碌无为,则是对“二老”之不孝,终为“吾党”所不齿。颜茂猷最后说道:出于上述考虑,因此“谨具《条约》事宜”以便大家“图之”为盼。*《云起集·说铃次集》,第36页下~37页上。以上论述充分表明,颜茂猷“结社”的用意在于将原本涣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
事实上,我们发现这篇“引言”的侧重点在于阐发设立“云起社”的总体设想:要人成就一番“经世出世”的大事业。这也是颜茂猷在这篇文字中所一再表明的他为何要结社创立“云起社”的一片苦心。同时也可看出,颜茂猷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一方面应以“道德事功”为至上目标;另一方面也不妨从其次做起,脚踏实地,奋起向上,“掇取科第”、“无负父母之意”,最终也必将“成功”。这也就是颜茂猷为何在“云起社”之下又分设“五会”的用意之一。
二、会约
《略拟会约》共由7条组成,依次是:
1.不论数会,俱以重行为主。平生有大过恶者,须自忏悔,方许入会。入会后,小过可以相规,倘复重大过恶,即指名革出。
2.入会者,俱以“功过格”十万善为准。各置《功过簿》,凭心报录。会日出之,以相儆察。惟树品圣贤,则考核尤详,居家孝友何如,接物敬信何如,须一一对勘。有闻会中朋友某事贻讥物议者,即以相规。
3.各会俱分数人为会首,或以地之相近,情之相孚,随自取之。凡公事及议论可以相达。某同会之精进,则会首预有荣焉。只此是功行。
4.各会首各置《度人簿》一册,人复寻人,随他手眼招致。每一月后,遍会大众。
5.各会俱择强(强)毅精进者为司纠,纠察怠惰量罚。
6.会以求道,贵贱贫富俱可一视参入。但有请托干谒及那借等项,则勿叩会中友,以免忮求怨尤之端。有难处者,可共商之。有自愿为出力者听之。厮养有志者,另一席可也。
7.大会后有私小会,可于各会首处议论。远家欲坐久者,不妨携米一筒,两不扰焉,可也。*以上均见《云起会语》,第7页下~9页上。
由第1条可知,所列7条“会约”是针对所有分会而言的,是各分会都须共同遵守的条约,亦即“俱以重行为主”。关于入会的条件则比较宽松,只强调一点:如平生有“大过恶”者,须经过“忏悔”才能准许入会。此外,如果入会后复有“重大过恶”,当立即开除。将此7条合观,则可发现入会不分“贵贱贫富”,只要在道德上没有重大过失,原则上是任何人都可加入的。可见,“云起社”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组织,而并非只是士人乡绅聚集在一起的会讲组织。由上述第3条亦可知,这个组织的分会还可根据“地之相近”来设立,不一定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这也说明颜茂猷有一个设想,尽量使“云起社”及其“五会”的活动可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来展开。当然就结论而言,他们的活动大抵不出漳州府的范围。
在《会约》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第2、第4条,这两条可谓是以“会约”形式来落实颜茂猷“功过格”实践的具体设想,换言之,颜茂猷创立“云起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通过“功过格”实践来凝聚四方朋友,以使大家“公共此心,公共此事”,否则,实现“度人”和“度世”便成了一句空话。
然颜茂猷以“功过格”十万善作为实践目标,而且要求各会成员严格遵守,对于“树品会”成员应“考核尤详”,要求更严,这一规定充分说明“云起社”的“重行为主”的宗旨体现出一种严格的道德主义。如上所述,根据他在《迪吉录》所附《功过格》的说明,若能一日行善十功,且坚持半月可“另加十功”这一计量方法来推算,顺利的话,一年可达“五六千功”,以此为准,“十万善”则需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此绝非易事。对于知府知县一级的官员而言,也许因为有“一千”至“三千”等数目庞大的“功格”设定,所以能较快地完成,比如袁了凡在及第进士之前,他要完成“三千善”,花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然而,当他成为进士当上知县以后,却仅以“减粮一节”便“可当万善”。[5](P13~14)可见,颜茂猷的“十万善”的设定也许适用于官僚士人,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不过也许可以推测,颜茂猷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看似高不可攀的目标,其目的在于要求社员一生不断地进行善行积累,以便将云起社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这条规定的具体实施情况,目前已无从考证,但可确认的是,“云起社”不同于一般的以讲学会友或思想切磋为主要目的的讲学团体,而是以劝善规过、与人同善为主要目的的讲会组织,由此可说,“以‘功过格’十万善为准”的规定正是“云起社”的特色所在。至于具体做法,颜茂猷规定每人须持一本《功过簿》,按自己的良心,忠实记录日常行为的功过。每当召开大会当天(大致一月一次),须向大家出示,以便互相检查,而且“司纠”者还要“一一对勘”,所以不得草率马虎。可见,《功过簿》乃是会员之间劝善规过的重要依据。以下,我们将在《会规》中还可看到,《功过簿》的誊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如果不忠实地记录,是会受到“先圣鉴责”的,如果拒不实行,则将被黜出“社外”。
除《功过簿》以外,颜茂猷还要求会员各立一本《度人簿》,每月大会须向全体成员公布,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关于这一条的说明文字很短,只是说“人复寻人,随他手眼招致”,意思无非是说,广招会员,多多益善。“度人”作为佛教用语,意指超度众生,然在颜茂猷的思想语汇中,“度人”也可用儒家的“立己达人”之说来加以印证,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故他在《迪吉录》卷6“公鉴二”就专门设立“度人门”,探讨了儒学历史上各种“救世度人”之典故所展现的思想意义。
事实上,在劝善运动中,作为思想口号的“善与人同”本身就已内含着“度人”这层涵义,颜茂猷为《迪吉录》八卷分别取名为“一心普度兆世太平”便可看出,“普度众生”本来就是颜茂猷劝善思想的要旨所在。在颜茂猷看来,不仅要自己成为“善人”,而且还要使他人乃至一乡之人都成为“善士”,推而广之,整个国家社会、普天之下,人人都成为善人,这应当是颜茂猷的劝善思想所追求的终极理想。现在,他把这一理想具体落实在“云起社”的《度人簿》的实践方式上,并以此作为社员的一项重要功德。应当说,《度人簿》构成了“云起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这一特质与《功过簿》一样,都体现出“云起社”是非同一般的讲学团体,而是以“重行为主”的追求道德之善的行动组织。
虽然在颜茂猷之前,已有袾宏禅师、云谷禅师、袁了凡等各种《功过格》范本出现,但在讲会团体中以《功过簿》、《度人簿》的形式来具体落实功过格实践,恐怕是颜茂猷的创见。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之一在于颜茂猷以为功过格实践不能仅局限于个人一己之行为上,而应是整个地方社会的“公共之事”,换言之,功过格实践既是家庭个人的一种道德实践,同时也是涉及公共道德的一种社会实践。按颜茂猷的设想,由个人而推向社会以及国家天下,便可实现儒家“治平”的宏伟理想,不仅如此,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亦可通过上述功过格的实践方法得到具体的落实。
总之,在有关“云起社”的一整套设计方案中,无论是“树品会”还是“修真会”或“经济会”,都须严格实行功过格实践,以功过格来统一社员的行动,并以此来提高社员的道德水准,树立起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品格,也就是颜茂猷所说的“圣贤品格”。可见,由“内圣”而及“外王”的工夫都有赖于“功过格”实践的实施与推广。更为重要的是,“外王”绝不等同于“经济”,而是在自身“树品”、“修真”的道德实践之基础上,以“救世度人”为其基本志向与目标。
三、会规
与《会约》相比,《会规》则对各分会的具体操作方法作出规定,其中包含《立分会簿》、《立愿力簿》、《立养志簿》、《各会立参稽簿》、《定会食》等内容,其中以《参稽簿》最为重要。以下依次作简单介绍,重点将介绍《参稽簿》。
在《立分会簿》中,颜茂猷说道:“大会以兴起人心,而精气难洽最重。小会随所招者,多属同气。即立会纠统之。中间鼓舞变化,自出机权,自满分量,则存乎其人。声气翕聚,后有愿入者,分会立《度人簿》,各收记。俟次会日,遍会大众。”*《云起会语》,第10页上。这一条对“大会”、“小会”及“分会”作了简单说明,强调各“分会”必须设立《度人簿》,以便统计入会人数。其中提到“会纠”,则可见上述《会约》第5条。
在《愿力簿》中,颜茂猷指出:“各人书所愿,如愿移某处风俗,当以何力成?……*原书以下缺一页。又或愿度多少人,以何力成之?又或愿为世界做何等事,以何力成之?如此等意俱可。”*《云起会语》,第10下~11页下。由于这里有缺页,故该条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从仅存的几点内容看,不难获知这条规定也很重要。这里所谓的“愿力”,与佛教所提倡的“发愿”、“立誓”等做法相当接近,在“功过格”运动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袁了凡在《立命篇》便再三提到“发愿”,且与“回向”相配合,最终须向“神灵”汇报“许愿”的结果,其中颇有宗教色彩。
颜茂猷自己也撰有不少“誓文”、“愿文”,如《十九大誓》、《二十一大愿》,*见《云起集·身世谱内编》。以此作为他一生的“所愿”。我猜想,《十九大誓》、《二十一大愿》便是颜茂猷为“云起社”所立《愿力簿》而撰写的范文。《愿力簿》应当就是入会者各自“立誓”、“发愿”的记录,这说明“云起社”要求入会者首先必须树立起宏大志愿。一般说来,所谓“立誓”、“发愿”既是发自内心的祈愿,同时也必然指向客观的第三者,希望自己的誓愿能得到上天神灵的眷顾,因而带有宗教祈向的性质,最后还须通过“回向”仪式,以求得到上天最终的印可,这是我们透过袁了凡《立命篇》已有所了解的情况。不过,与袁了凡不同的是,颜茂猷在其《大誓》、《大愿》中并没有规定须向“神灵”汇报等内容,他强调“立誓”、“发愿”应出自自律。这一点值得注意,这说明袁了凡受云谷禅师的影响,在其功过格实践中,非常重视宗教性的外向祈求,强调的是上天神灵在整个功过格实践中的监督、审查之作用。相对而言,颜茂猷虽也坚持认为神灵是果报系统得以成立的根本保证,但在他的《功过格》以及在《会规》(包括《会约》)的说明中,则几乎看不到对“神”的特别强调,颜茂猷更注重的是要求大家行为自律,故其所谓“发愿”不能含有任何为迎合他人的某种企图。应当说,与袁了凡相比,颜茂猷的功过格思想更体现出儒学化特色。
《立养志簿》的内容较为单薄,仅列举了四条涉及家庭伦理的注意事项,如“祖宗当办何事(成未)”*《云起会语》,第11页下。等,在此不论。接下来的《各会立参稽簿》非常重要,开首一句便是“会首及司纠者,以检察会中善恶勤惰”,*《云起会语》,第11页下。按,以下有缺页。下列《参稽簿》均见《云起会语》第11页下~第15页上,不再一一注明。足见《参稽簿》是“会首”及“司纠”用以检察社员日常行为的记录档案,是贯彻《会约》第5条的具体措施。其中设定了近20个问题,涉及面很广泛。首先由“司纠”向会友发问,然后会友各自据实“答应”。当然,这将近20个问题也只是举例而已,具体内容应当还不止这些。重要的是,《参稽簿》不仅具有横跨五会的普遍性,还具有适用于不同讲会组织的特殊性,故在此条之后,颜茂猷又设定了“修真”、“善缘”、“经济”、“文词”各会的“纠察”方法及内容,原文甚长,恕不具引。
要之,《参稽簿》规定了“修真会”、“善缘会”、“经济会”对其会员的纠察内容,根据各会的性质,其纠察之内容亦各有不同的针对性,我们很难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加以归纳,大致上其所涉及的内容遍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令人注目的是,除了对行为后果必须严格纠察之外,甚至要求社员们还要对日常心里所思所想亦即并未诉诸行为的心理活动状况的纠察内容作出回应,这反映出颜茂猷有一个重要的想法:仅仅注意行为上的过错是不够的,更应防范思想上犯错;行为过错人人易见,思想错误隐而不显,故更为可怕亦更应向大众坦白。例如,“有噩梦否”、“定心几日”等个人心理活动亦在纠察之列。至于“文词会”(即“博雅会”)所制定的纠察内容,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由上可见,各会成员都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针对各会成员的纠察内容也各有偏重,特别是在分会中设立的各种“善会”,这是在《云起会语》中首次出现的说法,应引起注意,这说明在“云起社”或“善缘会”内部,另有“因果会”、“放生会”、“救孩会”等小型善会组织,由于《云起集》没有对这些善会组织留下任何文字说明,故其活动之详情不得而知。我猜想,这些小型组织大概属于“善缘会”的分支机构,不过,正像“善缘会”具有横跨其他四会的特性一样,这些小型善会的活动也应当是云起社全体社员应当共同自觉参与的。当然,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亦在纠察范围之内。
至此可见,若要完成上述纠察活动,已经是不胜其烦了,然而,颜颜茂猷非常注重程序,他要把云起社完全放在程序化的操作过程中来加以掌控,所以,在进行了上述各分会的纠察程序之后,却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大会程序需要完成:
各项完,出《功过格簿》相证,长十人相订,次十人呈长十人,以次呈完。不誊者辞出社外,妄誊者先圣鉴责。
《参稽簿》出,共订之。
《愿力簿》、《养志簿》付司纠者,随所触,呼问之。
司纠纠平时之过愆怠惰,会时之戏谑狎、乱叱咤者,议罚。
能歌者歌诗,可。
作午,五会听从散处议论,或将所论登记之,复击鼓齐集,将五会得意妙义公扬搉毕,为旁观人若仆从人,以俗语说法竟。
这项规定显然与《会约》第2条是相呼应的。
所谓“各项完”,是指各分会的纠察活动暂告结束,接着便须各社员出示自己的《功过簿》,最后一项纠察程序就从检点社员日常的行为善恶开始。可见,功过格实践对于各社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义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云起社简直就像是功过格的实践团体,因为《功过簿》的记录具有超越五种分会之上的特殊性质,是每个社员不能“不誊”的,如果“不誊”,则将意味着自己脱离团队,尽管从程序上说,要求本人自动“辞出社外”。另外一种情况是在《功过簿》上“妄誊”,亦即说谎欺瞒,把坏事当做好事来记录,这种行为或许能瞒得过一时,但终将受到“先圣鉴责”,意谓是瞒不过“先圣”之“法眼”的。另外,《参稽簿》、《愿力簿》、《养志簿》则由各会“司纠”根据情况发问,若发现过错,则可商议处罚。五会结束后,应将会上“得意妙义”之议论“登记”在册,对于诸如仆从之类的旁观者则可“以俗语说法”,即可用通俗语言(大致是日常口语)另做一番开导。
在《会规》末尾,还有《定会食》一文以及一段无标题文字,规定了讲会时有关饮食、衣饰、举止等注意事项。令人注目的是那段无标题文字,该段文字以“智、仁、勇三会”为开场白,“定于四仲月望日,大会齐集”,我估计这是在“云起社”中的另一种大会形式,是所有社员都应参加的。其中规定与会者的注意事项,从服饰、饮食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婚娶”等事宜,规定一切必须“从简”,以纠“淫侈之风”、“浮夸”之风,并规定会中之友若有不是处,则可当面“议之”而绝不可“面是背非”。总体看来,设立“智、仁、勇三会”的目的是要表明“云起社”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能够自觉树立“立朝气节”的“士人”。颜茂猷直言不讳地告诫那些今后欲进入仕途的成员:“贱莫贱于无气骨”,若要入朝做官保住“气节”,就应在“居乡”时注意修养,首先不要让地方父母官对我们失望。*《云起会语》,第16页上下。由此可见,颜茂猷领导的“云起社”所要应对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培养地方精英,他清楚地意识到,做人要有“气骨”,为官讲究“气节”,都离不开日常的生活实践。
以上我们对云起社的“会规”及“会约”作了初步考察,从中可以看出,颜茂猷对于操作程序的设计非常详备,简直到了有点繁琐的地步,不过,颜茂猷的核心关怀显然在于培养善人以重整社会秩序、改变乡村民风。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坚强的观念支撑,在这一关键点上,颜茂猷并不讳言以“果报”思想作为行善实践的重要依据,他甚至把宣扬果报也作为一种实践手段。例如,他在《身世谱外编·行世机关》一文中,首先以程子之言“治道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为前提,设计了有关“治道”的各种方略,其中有一项内容叫做“一说果报”,他要求道:“平居亦令时时称说,遇近事近地有新闻报应者,则里甲大书露布,以达守令,而付讲长知悉,知必传,传必遍,天下沛然矣。”*《颜壮其集》第5册《身世谱外编》,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末刊本,第8页上。按,此本承蒙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复制相赠,谨致谢意!可以想见,颜茂猷非常明确地意识到,须将有关果报故事的新闻上达地方官员,又要传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这也是治理“天下”的良药妙方之一。
由上可见,“云起社”对内部成员的道德约束是极其严厉的,环视整个晚明时代的讲学活动及党社运动的历史过程,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像“云起社”那样有一套如此复杂严密的规章制度的组织或社团。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组织以“功过格”思想为主导来约束会员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度己度人,也是为国家培养今后能有“立朝气节”的人才。归结而言,颜茂猷所创立的“云起社”有几个重要特点:它以组织讲学为手段,以行善实践为功夫,以改变世风为目标,以成就人才为指向,其最终目标则是培养“善人”,由“一乡之善”推而广之,以及于“一国天下”人人为善。要之,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终极理想的实现,被颜茂猷纳入了区域社会中具体个人的行善实践过程。一言以蔽之,云起社无非就是将地方村落的行善活动加以组织化、规范化,纳入一种固有模式之中,以便将一盘散沙的村民“拧成一条绳子”。
若从整个晚明思想动向的背景中来看,我们或可说云起社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乃是晚明讲学运动、乡约运动乃至功过格运动的一种产物,但颜茂猷的设想又别具一格。他所组织的这个云起社,形式复杂多样,显然不是纯粹的学术团体,也与明代中叶以来的心学家所组织的讲学团体有异,他们很少有心学式的有关本体工夫等抽象问题的讨论,而是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推广善行、改善社会的入世精神,还有一套详细的安顿乡村秩序、培养各种人才的规划。用现在的话说,由五个分会组成的云起社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才培养基地。
也正由此,云起社在晚明思想史、社会史上显得很特别,很值得关注。通过对其活动形式及其指导观念的分析探讨,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启发我们对17世纪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道德与文化所发生的一些新趋向获得一定的了解:一是在已呈衰世的晚明社会,地方乡绅往往以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涣散、世风不古,为了重整世风、改善人心,有必要将讲学与劝善结合起来;二是在那些地方乡绅当中,并没有多少人受过严格的儒家知识的训练,他们往往并不介意于儒道佛之间强分疆界的做法,而在他们的观念形态中更多地蒙上了三教混合的特征;三是那些地方乡绅的讲学并不是空谈形上玄理,他们以为,通过组织讲会及推动行善以实现自我改善和重建社区是应当不断努力的一项个人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社会事业。
[1]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2][日]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J].清史研究,2005,(2).
[3][日]寺田隆信.明代乡绅の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
[4]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M].杜正贞、张林译,赵世瑜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袁了凡.了凡四训·立命之学[A].袁啸波.民间劝善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陆继萍
B248
A
1671-7511(2012)05-0041-14
2012-04-02
吴震,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